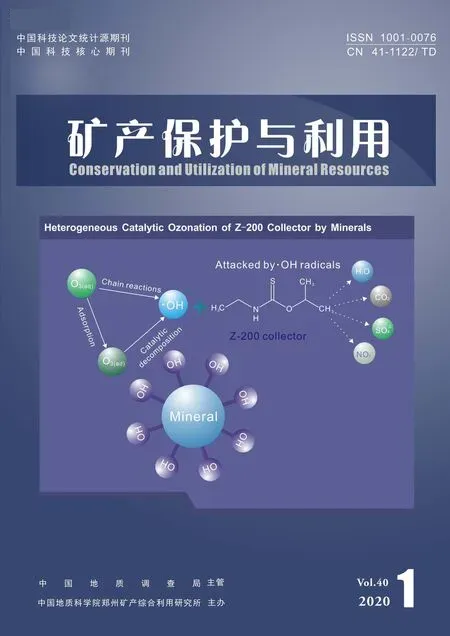硅藻土在選礦廢水處理中的應用研究
李昂,殷堯禹,盧瑞,李國棟,趙思凱,魏德洲,沈巖柏
東北大學 資源與土木工程學院,遼寧 沈陽 110819
引 言
選礦作業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資源,由此產生的廢水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循環利用,或經過凈化處理后排放。目前我國只有少數鉛鋅類國有礦山企業可以實現高效率選礦廢水的回用,而大多數選礦企業由于目前技術水平受限,回用廢水的效率較低,或因環保意識淡薄而選擇直接外排選礦廢水[1]。不同選礦廠的廢水成分和性質往往不同,在循環利用廢水時要綜合考慮廢水成分與目標作業所需水質的匹配關系。如鉛鋅浮選尾礦水直接返回浮選作業中將有利于硫金屬的浮選,但在其它礦物浮選過程中使用未經處理的選礦廢水則會明顯影響浮選指標。除此之外,選礦廢水中所含有毒有害物質會嚴重威脅礦區周圍生態環境和安全。近年來,我國逐漸加強重視礦山環境問題,國務院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而且自2018年起與《環境保護稅法》同步施行,開征環保稅,停止征收排污稅。因此,凈化選礦廢水是礦山企業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也是建設綠色礦山的必然要求。
目前許多廢水處理方法只能選擇性地去除廢水中的污染物,對于復雜程度更高的實際廢水降解效果不佳,甚至可能引起二次污染等問題,因此開發和利用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是未來處理實際選礦廢水的發展方向。非金屬礦物材料是指以非金屬礦物或巖石為基體或主要原料,通過深加工或精加工制備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現代新材料[2],一些非金屬礦物(如硅藻土、膨潤土、沸石、海泡石、凹凸棒石等)來源廣泛、經濟適用,可通過靜電吸附、離子交換等作用方式降解廢水中污染物[3]。在上述非金屬礦物中,硅藻土因具有孔道分布均勻有序的硅質多孔結構[4],而被廣泛用于對顆粒態和膠體態物質及多種重金屬離子的吸附處理[5]。此外硅藻土因物理化學特性優異也被用作光催化劑載體,更加有利于充分發揮光催化劑礦化有機污染物的作用,促進硅藻土基光催化材料用于降解選礦廢水中的應用前景。
1 選礦廢水的來源及特點
1.1 選礦廢水的來源
選礦廢水的主要來源包括洗礦廢水、破碎系統廢水、選別廢水和沖洗廢水[6]。其中,洗礦廢水中一般含有大量的泥沙、礦石顆粒、重金屬離子等;破碎系統廢水中主要含有礦石顆粒;重選與磁選中所涉及到的廢水污染物以固體懸浮物為主;浮選過程產生的廢水中除了含有懸浮微細物質之外,還包含浮選藥劑、重金屬離子以及氰化物等有毒有害物質;沖洗廢水中通常含有有機藥劑和礦石顆粒。值得注意的是,硫化礦物形成的酸性礦山排水與浮選作業產生的廢水具有類似的成分,處理辦法也趨近相同[6,7]。
1.2 選礦廢水的特點
(1)排放量大。選礦過程中產生的廢水約占整個礦山廢水量的34%~79%。據估計,我國礦山選礦廠每年的廢水排放量占全國工業廢水排放總量的十分之一[8]。每處理1 t礦石,磁選和浮選法需消耗4~7 m3的水,重選法需消耗20~26 m3的水,浮磁聯選和重浮聯選分別需耗水6~10 m3和20~30 m3[9]。
(2)成分復雜。除懸浮物及礦石本身帶來的重金屬離子外,各種選礦藥劑的添加也使得選礦廢水的成分十分復雜。全世界每年約有20億t的礦石采用浮選法處理,需消耗近400萬t的選礦藥劑。這些選礦藥劑品種極多,絕大多數沒有經過任何環境風險評價、甚至不明成分的僅以代號表示就投入使用,且浮選藥劑與重金屬離子之間還存在交互污染的情況,給廢水降解帶來了極大難度[10]。以黃藥為例,目前現有黃藥污染檢測和治理法規僅考察黃藥的殘留濃度,即降解后黃藥濃度達標即可排放。但這種含硫藥劑在分解產生CS2和COS的同時,一系列水溶性小分子的二次污染物如醇類、醛類、酮類、腈類等,可能也會與廢水中的重金屬離子發生螯合作用,使選礦藥劑二次污染鏈延伸、加長和復雜化[11]。
(3)危害性大。選礦廢水處理后進行循環使用是廢水資源化的重要手段,但目前對使用回水時礦物浮選行為及機理研究不夠透徹,且不同選礦廠的廢水成分復雜程度、處理方式各異,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選礦廢水回用的發展[12]。盲目地回用廢水不僅不會降低成本,反而會使分選結果變差[13]。含重金屬離子廢水對環境仍具有潛在的累積性影響,如西班牙伊比利亞黃鐵礦帶中的某礦區,在關閉后200年后仍然產出酸性含重金屬廢水[14]。20世紀在日本出現的“痛痛病”和“水俁病”案例也歸因于工廠超標排放含重金屬離子廢水,造成下游大量魚類死亡,Cd、Hg離子在生物體內積累,經過生物鏈傳遞,嚴重影響工業區人類身體健康[15]。
2 選礦廢水的主要處理方法
自然降解法是大多數選礦廠普遍采用的降低廢水污染物濃度的方法[16],主要是將廢水在尾礦池中貯存一段時間,在未經處理的情況下通過水體自凈化作用降低其中懸浮物的含量。一些易分解藥劑通過該法可以實現部分降解,而想要進一步去除其中的重金屬離子和有機藥劑,則另需其它手段輔助[15]。如利用自然曝曬法來降解有機浮選藥劑丁基黃藥等,但該法存在處理時間長,且降解后產物易產生二次污染的缺點,仍需進行后續處理[16]。到目前為止,針對礦山不同的廢水污染源,一些凈化選礦廢水的方法已經被采用,按照反應原理主要分為物理化學法、生物法及其他方法。
2.1 物理化學法
2.1.1 吸附法
吸附法是利用吸附劑與吸附質之間的分子間作用力或化學鍵力的作用而去除選礦廢水中多種污染物的一種方法,按照吸附原理可細分為物理吸附和化學吸附。常用的吸附劑有活性炭、黏土類吸附劑、高分子吸附劑、廢棄物制備的吸附劑、復合吸附劑和煤質吸附劑等[17]。其中活性炭是最常用的吸附劑材料,但其價格較高、對低分子極性強的有機物和大分子有機物的吸附效果不佳,且不能有效去除氯化致突變物質的前體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廣泛使用[5]。
2.1.2 膜分離法
膜分離法是利用膜對廢水中各組分污染物的選擇性滲透作用,以外界能量或化學位差為推動力對混合物進行分離的方法[18]。該法中的微濾和超濾膜技術可根據膜的孔徑不同,選擇性地截留污水中的超細顆粒,一般微濾膜孔徑為4~0.02 μm,超濾膜孔徑為0.2~0.02 μm。電滲析、反滲透、納濾等膜技術也常被用來處理含重金屬離子的廢水,具有分離效率高、操作簡便等優點,但存在膜污染、成本過高等問題[19]。
2.1.3 電化學法
電化學法是指在外加電場作用下,廢水中污染物在電極上發生直接電化學反應或間接電化學轉化,最終使懸浮顆粒、重金屬離子和有機污染物轉化為沉淀或氣體,并從廢水中分離的方法[20]。電化學法主要包含電絮凝法[21]、電氣浮法和電化學氧化法等,該方法不涉及藥劑使用,綠色環保,但能耗大、成本高等因素限制了其大規模應用[22]。
2.1.4 沉淀法
沉淀法一般分為混凝沉淀法、氫氧化物沉淀法及硫化物沉淀法。混凝沉淀法利用不斷向選礦廢水中加入明礬、氯化鋁等絮凝劑,使廢水中膠體通過壓縮雙電層、吸附電中和、吸附架橋、卷掃等過程實現被處理物質脫穩并凝聚成團,最終在重力的作用下沉淀下來。氫氧化物沉淀法則是利用向廢水中添加NaOH、Na2CO3、KOH、Ca(OH)2或CaO等沉淀劑與重金屬離子直接作用生成沉淀的方法。硫化物沉淀法也常被用來去除廢水中重金屬離子,常用的沉淀劑有Na2S、NaHS、H2S、CaS、FeS[23]。沉淀法雖然操作簡便、成本較低,但大量沉淀劑的使用仍會帶來二次污染問題。
2.1.5 中和法
中和法是處理選礦廢水常用的方法,依照實際廢水的酸堿性,適量添加中和劑(如針對酸性廢水的堿性中和劑:石灰、白云石、苛性鈉、碳酸鈉等,針對堿性廢水的酸性中和劑:H2SO4等),利用酸堿中和原理將廢水pH值調整至合適范圍,使廢水中所含的金屬離子以氫氧化物沉淀或碳酸鹽的形式得以去除。采用該法需大力提倡“以廢治廢”的原則,即優先利用礦廠周圍的酸性或堿性廢水作為中和劑。中和法操作簡單、成本較低,但由此產生的污泥量大、易引起二次污染等問題使其應用受到一定限制[24-26]。
2.1.6 化學氧化法
化學氧化法是一種深度礦化廢水的方法,常用的氧化劑有次氯酸鈉、臭氧、過氧化氫、Fenton試劑等。董棟[27]針對廣西某鉛鋅礦尾礦庫廢水,以次氯酸鈉和雙氧水為氧化劑,考察了兩種藥劑用量和不同pH值條件下對廢水CODCr去除效果的影響,結果表明與其他方法相比化學氧化法可以更加有效地去除廢水中殘留的浮選藥劑。值得注意的是,在進行模擬廢水降解時,氧化劑存在選擇性作用的現象,該試驗中次氯酸鈉和雙氧水對黃藥和乙硫氮的去除率達90%以上,但對腐殖酸鈉僅有15%的去除率。然而,由于氧化劑成本較高,該方法并不適合大規模工業應用。
2.2 生物法
利用微生物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氧化還原作用實現降解廢水是一種綠色環保、極具潛能的方法。目前許多科學家已經著手利用馴化菌株來降解選礦廢水中殘留的有機藥劑。張東晨等[28]總結了黃藥、黑藥、羥肟酸類、松油醇等選礦藥劑生物降解技術的研究進展,指出目前用于降解選礦廢水殘留有機物的菌種種類有限,且僅限于試驗室研究水平,較實際應用仍有較大差距。
利用微生物自身的積累作用、溶解作用以及氧化還原作用來降低廢水或土壤中重金屬污染同樣備受關注,因微生物細胞壁具有特殊的結構及化學基團,可通過表面物理吸附、分子間絡合作用、離子交換和形成微沉淀等方式,達到去除重金屬離子的目的。王建龍等[29]總結了針對不同重金屬離子的細菌生物吸附劑,強調活細胞生物吸附的重要前景以及結合其他方法充分發揮生物吸附的發展方向。
2.3 多方法聯合使用
多方法聯合水處理技術是較為常見的廢水處理方式,目的是通過結合多種方法的優點,以實現提高降解廢水的整體效果。
低溫等離子水處理技術是集電、化學氧化、光于一體的水處理高級氧化技術[30]。高壓脈沖電源在水中放電的過程中可以產生大量的活性粒子,如H+、OH-、O、O3、O2、H2O2和光子、電子等,與同時形成的紫外光和沖擊波協同作用,可以顯著降解水中有機污染物。董冰巖等[31]采用高壓脈沖放電技術處理選礦廢水中的殘余乙基黃藥和丁基黃藥,通過控制初始質量濃度、針-板間距、曝氣量、峰值電壓、脈沖頻率等參數,有效降解了兩種黃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過聯合高壓脈沖放電與BiVO4協同降解和單脈沖放電降解的對比發現,前者對兩種黃藥降解效果均有所提升,尤其對丁基黃藥的降解率和礦化速率提高更為明顯。但該方法由于處理廢水量小、設備耗能大、處理成本高等缺點限制了其在工業應用的推廣。
趙志強等[32]針對南京棲霞山銀鉛鋅礦廢水回用問題,開發出分段濃縮—分質回用—末端凈化處理技術。該技術將70%的選礦廢水直接返回相應作業段,利用混凝沉淀—活性炭吸附法處理其余廢水,隨后將其回用于選鉛和磨礦作業。結果顯示,使用處理后的廢水與使用新鮮水的選鉛效果基本相同,節約了95%以上的選礦新鮮水用量。
Fenton氧化—電滲析聯用技術作為膜處理的前處理過程,有效緩解了反滲透裝置的膜污染問題。馬昕等[33]針對廢水中含鹽量及COD高,且存在多種難降解有機污染物的復雜情況,采用Fenton氧化—電滲析—超濾—反滲透膜聯合水處理技術,使水質達到循環水使用標準。
人工濕地法是一種通過構建基質-微生物-植物復合生態系統,利用物理、化學和生物協同作用以實現去除廢水中污染物的方法[34]。但人工濕地法不具有普適性,即針對不同選礦廢水的特性要相應地調整基質和優化結構設計,不利于廣泛推廣[35]。
3 硅藻土的特性及應用現狀
3.1 硅藻土概況
硅藻屬硅藻門,其細胞壁主要由SiO2構成[36]。硅藻的大量死亡導致其細胞壁中的礦物質在海水或湖水中沉積,經過成巖作用后形成硅藻土礦床。由于其特定的成礦條件,硅藻土被定義為不可再生資源。硅藻土質輕,無毒,主要成分是50%~90%的水合無定形二氧化硅(SiO2·H2O),同時存在少量Al2O3、Fe2O3、MgO及微量Na2O、SO3、V2O5、TiO2、MnO2等雜質。硅藻土種類較多,主要有支鏈型、圓篩型、冠盤型、羽紋型等[37],常見顏色有白色、黃灰色、淺灰色,也偶有因存在有機雜質而呈現深灰色和棕灰色[38]。硅藻土是一種多孔且孔隙分布十分規則的天然硅質礦物材料,其比表面積大,一般為19~65 cm2/g,孔隙率約占80%以上,孔半徑范圍為50~800 nm,孔體積為0.45~0.98 cm3/g,吸水吸油性強,熔點為1 650~1 750 ℃,耐酸(除HF酸),不耐強堿,是熱、電的不良導體[39,40]。
全球硅藻土資源豐富,已探明儲量18.42億t~20億t[41]。我國是世界上硅藻土儲量第二大國,截至至2018年,我國硅藻土已探明儲量達5.11億t[42],僅次于美國。相比于其他國家由于礦床位置和地形限制而大多采用地下開采,美國的硅藻土則主要是通過低成本露天開采的。僅2018年,美國生產約79萬t硅藻土(圖1)[43]。與美國相比,我國優質硅藻土整體占比較小,只有吉林長白山、云南騰沖縣的部分地區存在可不經選礦直接加工的一級硅藻土,且探明儲量僅占當地硅藻土儲量的15%~30%。而其他地區如內蒙古化德等的硅藻土品位低,且伴有填充在硅藻土孔道中難以分離的雜質(如黏土礦物、碎屑礦物和自生礦物等),提純難度明顯加大[44]。

圖1 全球主要國家硅藻土產量分布(USGS,2018年)Fig.1 Distribution of diatomite production in major countries of the world(USGS,2018)
3.2 硅藻土應用現狀
3.2.1 硅藻土的傳統應用
作為一種重要的礦產資源和功能礦物材料,硅藻土最開始被廣泛應用于一戰后,美軍用其去除受污染水中的微細粒物質[35]。我國過去對硅藻土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助濾劑、功能性填料、保溫材料、水泥混合材料、釩催化劑載體等領域。而資源質量和國內需求決定了不同國家的硅藻土應用結構,美國優良的lompoc硅藻土礦有2/3應用在助濾劑領域,丹麥豐富的Moler型硅藻土被廣泛應用于保溫材料領域,法國和德國主要在助濾劑和填料領域大規模利用硅藻土,而日本在填料和助濾劑領域消耗了2/3的硅藻土,其余主要用在建筑材料和保溫材料[45]。
(1)助濾劑
助濾劑是硅藻土應用的第一大領域,因其具有極強的吸附能力而被廣泛使用于酒類、烹飪油和飲料生產中。硅藻土可以被用來濾除0.1~1.0 μm的微粒,降低1.4%左右的酒損,且經過硅藻土過濾的酒品、飲品可長時間保持清新[39]。任華峰等[46]利用硅藻土CD08為助濾劑組裝了試驗室級硅藻土預涂膜過濾裝置,有效降低了某浴場海水濁度。
(2)填料
硅藻土的添加使得一些產品的特定性能得到改善或提高,還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產成本。如硅藻土作為橡膠填料可提高其耐熱性能[47],作為塑料填料可減少膜間粘結[48],作為涂料填料可賦予涂料調濕和耐磨耐熱性能[49]、作為造紙填料可顯著改善紙張的抗張指數、撕裂指數、耐折度和耐磨度等[50]。
3.2.2 硅藻土的新應用
制備高附加值硅藻土產品是目前科技領域亟需努力的方向。被用作混凝土骨料的硅藻土只有10美元/t的效益,但用于藝術品、化妝品、DNA提取等專業市場的硅藻土每噸逾1 000美元。美國每年有大約1%的硅藻土應用于藥物和醫學用途[43,51]。
基于硅藻土無毒、多孔性、表面積大、良好滲透性、化學惰性好等天然優勢,科學家對硅藻土的研究興趣逐年增加,特別是對其天然大孔/介孔型孔結構方面的應用研究。Abo-Shady等在埃及不同地區選取了59個硅藻土樣品,用以研究硅藻土的孔徑尺度、結構和孔分布特點。結果表明,硅藻土樣品孔徑在5~500 nm之間,天然大孔/介孔結構使其在納米過濾、藥物載體、光、電學等領域均有可開發的應用潛能[52]。近年來,其他一些領域,如環境領域(污水處理)、新能源領域(電池、儲能)[53]等也逐漸拓寬了硅藻土資源高附加值利用的道路。
4 硅藻土對選礦廢水中重金屬離子的去除
天然硅藻土的比表面積大,表面呈負電性,被廣泛應用于處理含重金屬離子的廢水,但同時硅藻土中的雜質也會對吸附效果產生消極影響[36,54],通過改性處理技術可以顯著提高硅藻土的吸附性能[17]。常見的硅藻土改性方法有擦洗法、焙燒法、微波法、酸改性法、使用無機大分子改性劑的無機改性法和通過在硅藻土表面接枝功能性大分子的有機改性法[55]。另外,由于原礦及相應選礦工藝制度的不同,浮選過程中所添加的浮選藥劑種類和用量往往不同,因而廢水中相應的重金屬離子種類和含量也會有所變化。如何確保選擇性地吸附一種或幾種目標重金屬離子而保留某些必要的金屬陽離子,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技術問題。
張秀麗等[56]考察了碳酸鈣改性硅藻土用量、吸附時間、溶液pH值對模擬廢水中Cu2+離子(10 mg/L)吸附性能的影響,結果表明改性硅藻土對Cu2+的吸附效果明顯優于未經改性處理的硅藻土。在模擬廢水的pH值為4、硅藻土用量為0.4 g、吸附50 min時優化試驗條件下,碳酸鈣改性硅藻土對Cu2+的吸附率可達88.15%。
郭紹英等[57]利用焙燒、新生碳酸鈣及十二烷基磺酸鈉(SDS)對硅藻土改性處理,以模擬廢水中的Cu2+為吸附目標,對比了三種改性硅藻土對Cu2+的吸附效果。結果顯示,在最佳改性條件下,三種改性方法均可以明顯提升硅藻土對模擬廢水中Cu2+的去除效果。新生碳酸鈣改性可以促使新生碳酸鈣與硅藻土之間形成微孔結構,同時新生碳酸鈣會與Cu2+發生反應,使其對Cu2+的去除效果提升最為明顯,去除率可達99.9%。經SDS改性的硅藻土,其圓盤上嫁接了大量基團,硅藻土的表面性質及孔隙結構得以改變,可實現對Cu2+的去除率達90.0%。相比之下,硅藻土焙燒改性后,其孔容擴大、雜質含量降低,利于對Cu2+的吸附,但吸附率提升有限,僅可去除37.6%的Cu2+。凌靜[58]在水漿中使用陰離子表面活性劑十二烷基磺酸鈉對硅藻土進行改性,與天然硅藻土相比,改性硅藻土對模擬廢水中Cd2+和Pd2+的吸附性能有所增強。
朱健等[59]通過動邊界模型討論了Cu2+、Zn2+、Mn2+在硅藻土表面的吸附過程,即液膜擴散、顆粒孔道擴散、離子與孔道內表面活性基團的吸附,整體吸附過程的決速步為離子在孔道內發生的吸附反應。史明明等[60]肯定了硅藻土的孔徑、孔容對重金屬離子吸附的重要作用,即孔容決定硅藻土對重金屬離子的吸附量,孔徑決定重金屬離子在孔道內的擴散速率,且在一定范圍內孔徑越大重金屬離子的擴散速率越快。通過對硅藻土吸附前后的SEM圖片對比發現,吸附重金屬離子后的硅藻土孔道因被吸附物占據而變小且模糊不清。
易煒林等[61]比較了硅藻土經熱活化、錳氧化物、Mg(OH)2、聚丙烯酰胺、氨丙基三乙氧基硅烷、微乳液和Cu2+等7種改性方法后,并考察改性硅藻土對模擬液中Cd2+、Pb2+、Cu2+吸附效果的影響。結果表明,利用錳氧化物和Mg(OH)2改性的硅藻土,對三種目標重金屬離子的吸附效果要優于使用其余改性劑改性的硅藻土的吸附效果,比表面積顯著提高、硅羥基的出現是其吸附能力提升的重要原因。
研究發現,針對不同廢水中的污染物,對硅藻土的改性方法也不盡相同,改性后的硅藻土降低了雜質含量、孔道結構得到優化,顯著地提高了其對一些特定重金屬離子的吸附能力。總體上,改性硅藻土對單一或有限組分的重金屬離子的吸附效果較好,但在多組分系統中改性硅藻土的吸附行為尚不明確。
5 硅藻土基光催化材料對選礦廢水中有機物的去除
單一硅藻土吸附有機污染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吸附易飽和、降解不徹底等。朱勇等[62]提出可以利用硅藻土的吸附性能來處理過濾膜中殘留的成分復雜的膜濃縮液,結果表明硅藻土可以有效去除膜濃縮液中的易降解有機物,而面對難降解有機物如腐殖酸等,僅僅依靠硅藻土本身的吸附作用則很不理想。而光催化技術是一種綠色環保并可以完全礦化廢水中所含有毒害有機污染物的方法,該法主要是利用適宜波長的光照射半導體材料,價帶電子(e-)受到激發躍遷到導帶,價帶留下空穴(h+)在電場作用下分離并遷移到半導體表面,光生空穴的強氧化能力將其表面吸附的OH-和H2O分子氧化為·OH自由基,由此產生的·OH自由基可以無選擇地將有機物氧化為CO2和H2O[63]。目前已有多種類型的光催化材料被用于降解有機污染物,但光催化劑的應用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TiO2雖然光催化活性很高,但面對選礦廢水中殘留的低濃度有機藥劑時,由于其材料本身對有機物的吸附能力欠佳,影響二者之間有效碰撞,從而降低了光催化效率[64]。微納米級光催化劑的比表面積高,但粒度過小易引起團聚,降低了進行光催化的有效表面積。此外廢水中存在的高價陽離子也會造成催化劑團聚[65],使得光催化劑難以充分利用光而導致光催化效率降低,且不利于光催化劑的回收再利用。因此,將光催化材料與礦物材料進行復合,利用硅藻土作為載體來提高光催化劑的分散性,對提高光催化效率具有重要意義。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異相光催化反應發生在催化劑表面,將硅藻土與光催化材料復合后,硅藻土本身的吸附能力也有助于有機物的降解,協同作用使得硅藻土基復合材料優于單一光催化材料對有機污染物的降解[66]。
5.1 硅藻土的吸附作用對光催化降解的影響
孫志明[44]探究了基于硅藻土載體的復合光催化材料對羅丹明B的吸附影響,同時采用相同的處理工藝對比兩地硅藻載體、P25、未負載TiO2和硅藻載體復合TiO2材料對羅丹明B的吸附情況。研究結果表明,由于硅藻土載體的存在,復合材料對羅丹明B的吸附效果較P25和未經負載的TiO2有明顯提升。值得注意的是,隨著TiO2在硅藻土上的負載量增加,復合材料較單一載體的吸附能力有所下降,這可能是因為TiO2占據了一些硅藻土原有的孔道結構。光催化降解羅丹明B的試驗證明,與原土相比,提純后的硅藻土對羅丹明B的吸附能力有所下降,但用其作為載體光催化降解效果更佳,這表明硅藻土載體本身對有機污染物的吸附能力與TiO2/硅藻土復合材料的光催化性能之間沒有必然聯系。此外,作者還強調了硅藻土形貌完整性、提純降雜質對TiO2在載體上分散性的影響。
5.2 硅藻土的負載作用對光催化降解的影響
硅藻土作為載體的影響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1)為光催化劑提供合適的孔結構,發揮硅藻土的分散功能,增加光催化劑與有機物的接觸率,加強光催化劑活性位點的暴露,實現靶向富集,有利于提高降解效率;(2)硅藻土會影響光催化劑的晶體生長特性;(3)硅藻土儲量大、價格低廉、無毒,可避免水體的二次污染;(4)硅藻土的化學惰性使其在實際應用中作為載體更具有優勢。
5.2.1 改善催化劑的分散性
為解決光催化劑的團聚問題,王利劍等[67]以TiCl4為原料利用水解沉淀法在提純圓筒型硅藻土上包覆了平均粒徑為12 nm的TiO2,負載成功后的硅藻土的微孔依然存在,但孔徑有所減小,且微孔內部及周圍為TiO2提供分散性良好的負載位置,經過20 min的降解,羅丹明B的脫色率可達到90%以上。
宋海燕等[68]在利用TiO2/硅藻土復合材料探索光催化降解氯仿反應的最佳pH值時發現,理論上TiO2的等電點約為6.0時,TiO2將易于團聚不利于光降解;但當模擬廢水pH值在6.0附近時,光催化降解效果非常好,且在pH值約為7.0時效果最佳,作者認為是硅藻土的負載作用使TiO2的分散性能基本不受pH值的約束。吸附試驗結果表明,pH值為7.0時硅藻土對氯仿的吸附量最大,此時氯仿與TiO2的接觸頻率最高,達到最理想的降解效果。
5.2.2 影響催化劑的晶體生長特性
目前,一些學者們認為TiO2的晶型和粒徑大小對光催化效果會產生影響。一般認為TiO2晶型對光催化降解效率的影響存在下列規律:銳鈦礦/金紅石兩相>銳鈦礦相>金紅石相,銳鈦礦和金紅石兩相之間的混晶效應,會有效降低電子-空穴的復合,從而有利于光降解效果[69],商用P25就是混晶TiO2的典型代表,其中銳鈦礦相約占80%。一些學者[70]認為,納米光催化劑的粒徑大小對光催化效果有影響,粒徑越小,比表面積越大,光催化活性越高,但過小的粒度容易引起二次團聚給降解過程帶來不利影響。王利劍等[71]對比了相同條件下制備的TiO2和圓篩型硅藻土/TiO2復合材料,發現在熱處理過程中復合材料中的TiO2的晶型轉變有滯后現象,即復合材料中TiO2的晶型轉變所需熱處理溫度有所提高,而且復合材料中TiO2晶粒生長速度慢于非負載TiO2的晶粒生長速度。
5.3 硅藻土改性對光催化降解的影響
經過改性處理改變硅藻土的表面特征,可使負載的TiO2形成分級多孔結構,有助于提高電荷傳質效率,從而提高光催化效率。Xia等[72]在對比了兩種預處理硅藻土(煅燒和磷酸活化)作為載體負載TiO2的光催化效果,通過XPS、氮氣吸附-脫附、XRD、SEM等檢測手段及光催化效果評價,發現經磷酸活化后的硅藻土,除對TiO2晶型轉變有遲滯影響外,還可有效增強復合材料對甲基橙的光催化效果。XPS結果顯示,隨著磷酸的濃度增加,Si-O-Si鍵的強度逐漸增強。且當磷酸濃度達到15%時,461 eV的結合能處出現了額外的肩峰,認為Si和Ti之間形成了Si-O-Ti鍵。通過Si-O-Ti結合的TiO2與硅藻土界面會改變Ti在邊界區域的電荷分布,提高了電荷轉移效率,增強了光催化能力。與煅燒活化相比,采用磷酸改性硅藻土制備的復合材料對甲基橙具有更好的降解效果,分析認為磷酸改性過程中引入P元素會限制TiO2的生長,有助于顆粒間形成微孔-中孔-大孔的分級多孔結構,提高光催化效果。
硅藻土作為光催化劑的載體,解決了光催化劑易團聚、難回收等問題,同時會影響光催化劑的反應活性。在降解廢水中有機污染物時,硅藻土吸附和光催化劑強氧化的協同作用使硅藻土基復合材料光催化降解有機污染物的效率得以提高。
6 結論
選礦過程帶來的水資源污染問題是我國礦業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因此衍生出的多種處理選礦廢水的方法已被研究或應用,但這些方法存在處理效率低、易造成二次污染、能耗大等問題。硅藻土作為一種重要的非金屬礦產資源,具有優異的物理化學特性,可以作為吸附劑或光催化劑載體材料降解選礦廢水中污染物。
今后硅藻土在選礦廢水處理應用方面存在以下問題:(1)硅藻土的孔結構和表面活性有限,改性處理是提高硅藻土吸附作用的重要手段。我國對硅藻土改性技術的研究仍處于試驗室階段,很少直接用于降解選礦廢水。因此優化改性方法對降低硅藻土吸附劑成本、增強吸附性能十分必要。(2)目前硅藻土對于不同污染物的吸附機理研究不夠透徹,特別是在面對含多組分污染物系統時,硅藻土的吸附機理不明確,限制了其實際應用。如何處理吸附后的硅藻土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3)在降解實際選礦廢水過程中,硅藻土基吸附材料適用于高濃度廢水前處理,而硅藻土基光催化材料適用于深度廢水處理,因此綜合把握硅藻土基復合材料吸附與光催化降解之間的平衡是提高其降解效率、降低成本的關鍵。針對具體水質設計廢水降解方案,才能充分發揮硅藻土材料的凈化作用,拓展其在環境領域的應用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