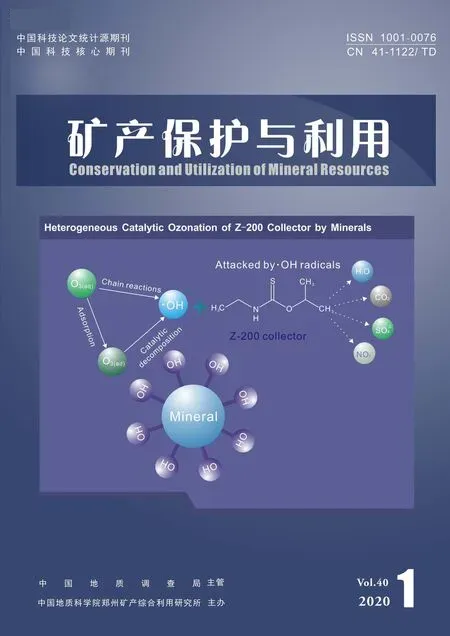西藏礦山環境恢復治理現狀遙感研究
陳玲
中國自然資源航空物探遙感中心,北京 100083
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環境工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習總書記“十九大”報告中,更明確地要求“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礦山環境恢復治理逐漸成為衡量地方礦政管理部門工作業績的重要指標之一。而遙感具有宏觀、客觀、快速等技術優勢,近些年逐漸被應用于礦山環境恢復治理情況的調查與監測[1-2]。
雖然很早就有學者探討過礦山環境的問題[3-5],但迄今關于使用遙感技術開展礦山環境恢復治理情況調查與監測的報道尚不多。楊金中等[1-2]在《中國礦山地質環境遙感監測》專著中報道了全國礦山環境恢復治理情況遙感調查成果概況;楊顯華等[6]報道了利用高分辨率遙感數據研究冕寧牦牛坪稀土礦的礦山環境綜合治理情況;陳琪等[7]報道了利用遙感和GIS技術開展云南省元陽某金礦礦集區的礦山環境恢復與治理規劃情況;王海慶等曾報道過山東濟寧[8]和西藏日喀則[9]礦山環境恢復治理情況遙感監測的工作成果。
但利用遙感技術開展礦山開發占損土地的報道卻已屢見不鮮,尤其是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地質調查局部署的礦產資源開發多目標遙感調查與監測、礦產資源開發多目標遙感監測、全國礦產衛片遙感解譯、礦山遙感調查與監測、全國礦產資源開發環境遙感監測、全國2017年新增的恢復治理狀況監測、全國礦山開發狀況遙感地質調查與監測、全國礦山環境恢復治理狀況遙感地質調查與監測等一系列礦山遙感監測項目在全國的實施,對礦山開發占損土地面積的遙感調查方法日趨成熟。比如,魚磊等[10]、王昊等[11]、楊涵水等[12]、汪潔等[13]、楊顯華等[14]、馬國胤等[15]、于博文等[16]、王曉紅等[17]、鄧瑩[18]、蔣勁等[19]、楊金中等[20]、強建華和于浩[21]、路云閣等[22]、周英杰等[23]、高永志等[24]、強建華[25]、方雪娟等[26]、郝利娜等[27]從不同角度介紹了礦山遙感監測的技術方法或調查成果;王海慶等利用遙感技術開展了多項礦山開發損毀土地方面的調查研究[28-32]。
上述報道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借鑒。本文綜合利用以上報道的技術方法,結合承擔項目的實際情況,對西藏自治區礦山環境恢復治理現狀進行遙感調查研究,分析不同恢復治理措施的治理效果,進而提出相應的推廣建議及適用地區。
1 研究區概況
西藏地處青藏高原,是典型的生態環境脆弱區。據百度網絡資料,西藏的地貌大致可分為喜馬拉雅高山區、藏南谷地、藏北高原和藏東高山峽谷區。藏南和藏北氣候差異很大。藏南谷地受印度洋暖濕氣流的影響,溫和多雨,年平均氣溫8 ℃,最低月均氣溫-16℃,最高月均氣溫16 ℃以上。藏北高原為典型的大陸性氣候,年平均氣溫0 ℃以下,冰凍期長達半年,最高的7月不超過10 ℃,6~8月較溫暖,雨季多夜雨,冬春多大風。總體來說,西藏海拔高,空氣稀薄,植被生長極其緩慢,礦山環境恢復治理難度大。
西藏自治區已開發利用的礦產有30余種。礦產資源開采主要集中在岡底斯成礦帶[32],尤其是拉薩市墨竹工卡縣—日喀則市謝通門縣一帶,拉薩市的礦山相對密集,其余地區礦山比較分散。遙感調查發現,西藏自治區總體礦山開采強度不高,正在利用的涉礦用地面積為86.54 km2[31],廢棄的涉礦用地面積小于正在利用的涉礦用地面積[1-2]。礦業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地表景觀破壞、固體廢棄物裸露、地表揚塵以及礦山地質災害等。

表1 常見恢復治理前后情況對比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common situations before and after rehabilitation
2 調查方法
2.1 遙感數據源與預處理
為了實現本文的研究目的,獲取了西藏自治區2016和2017年度同一時間節點、并經過專業隊伍預處理的衛星遙感數據。2016年度的遙感影像的類型涉及GF1、GF2、ZY3、YG8、CB04、PLB、RE、SPOT6、SPOT7、BJ2等,包括單波段的灰度圖像和真彩色合成圖像;空間分辨率以5 m為主,其次是2 m,人口密集區域為1 m或0.5 m。2017年度的遙感影像的類型涉及GF1、GF2、ZY3、YG8、02C、PLB、RE、SPOT6、BJ2、WV2等,也包括單波段的灰度圖像和真彩色合成圖像;空間分辨率以5 m為主,人口密集區域、主要礦區為2 m或1 m。兩個年度的衛星圖像中,云雪覆蓋較少,且主要集中在喜馬拉雅等高山區;大部分地區都有植被覆蓋,但受采礦作業影響,礦區內植被稀少;成像質量較佳;結合GoogleEarth等網絡遙感影像資源,可以較好地用于識別礦山地物和調查礦山環境恢復治理面積等。獲取的遙感數據較好地覆蓋了西藏自治區全境,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遙感數據基礎。
鑒于兩個年度的衛星圖像涉及多種衛星傳感器和不同的空間分辨率,在使用之前,首先進行數據預處理,包括高精度幾何糾正和空間配準、地圖投影校正等,以確保礦山地物在地理位置、空間形態與面積、不同來源圖像匹配等方面的準確。
2.2 遙感識別方法
恢復治理前的礦山開發占損土地遙感識別方法成熟,前人、尤其是礦山遙感監測技術人員,對礦產資源開發占損土地的遙感識別方法有過大量報道,其技術方法比較成熟,本文不再贅述。
遙感解譯和調查結果表明,西藏自治區主要的恢復治理措施有:自然恢復、回填平整、綠化、改造再利用等。恢復治理后土地類型主要是農業用地、林地、草地、建設用地、水域、以及平整后的空閑地、裸露地、內陸灘涂等,通過多期遙感數據對比,易于識別。常見的恢復治理前后情況對比影像見表1。

表2 不同恢復治理措施涉及圖斑數量和面積一覽表Table 2 List of the number and area of patches involved in different rehabilitation methods
2.3 野外驗證情況
野外驗證是開展礦山遙感監測必不可少的工作環節,也是提高遙感調查成果質量的必要措施。野外驗證的主要工作內容是驗證室內遙感解譯成果的正確性,比如遙感判別的恢復治理措施是否正確、遙感判定的恢復治理效果是否合適、遙感圈定的圖斑邊界是否恰當等,并根據驗證結果修改完善室內遙感解譯成果。
在野外驗證時側重于遙感解譯有疑問圖斑的驗證,側重于遙感判別不確定圖斑的驗證,側重于遙感判定有爭議圖斑的驗證,側重于邊界不明確圖斑的驗證。共驗證恢復治理圖斑78個。其中,野外觀察結果與室內遙感判定結果一致的圖斑有67個,占86%;野外觀察結果與室內遙感判定結果不一致的圖斑有11個,占14%。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部分地區遙感數據分辨率不高、數據質量不是很好,造成了一定的誤判。
3 調查結果
根據獲取的遙感數據,開展遙感調查,在西藏自治區共圈定礦山環境恢復治理圖斑213個(不含連帶治理),涉及面積85.08 km2。涉及的開采礦種主要有:砂金、建筑用砂、鐵礦、金礦、石灰巖、花崗巖等。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和藏南谷地,藏東高山峽谷區和喜馬拉雅高山區相對較少。回填平整是最主要的恢復治理措施,無論圖斑數量還是圖斑面積都排在首位;其次是自然恢復;然后是改造再利用,以及綠化(表2)。
4 恢復治理措施推廣建議
4.1 恢復治理效果簡析
經遙感室內解譯與野外調查驗證,發現西藏自治區的礦山環境恢復治理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改變了原先礦山開采遺留的不良地貌景觀,不同程度地改善了當地生態環境。但如前文所述,西藏自治區植被生長極其緩慢,不同恢復治理措施需要的維護成本不一,恢復治理效果也有差異(表3)。
總體上,改造再利用需要的投入較多,效果也較好;洪水恢復能夠將礦業用地變成自然地貌形態,效果也不錯;而綠化后需要較多的后期維護(圖1),其效果因當地氣候條件和后期維護程度而異;自然復綠并不能改變礦業用地的地貌形態,在西藏特殊的氣候制約下,自然復綠需要較長的時間;涉及圖斑數量和面積最多的回填平整,能夠改變礦業用地的地貌形態,但在回填平整過程中可能破壞更多土地[9],且在西藏特殊的氣候制約下,短時間內難以恢復成自然地貌形態(圖2)。

表3 不同措施恢復治理效果Table 3 Governance effect of different rehabilitation methods

圖1 缺少后期維護而枯死的樹苗Fig.1 Dead seedlings due tolack of late maintenance

圖2 某礦坑回填平整三年后現場照片Fig.2 On-site photographs of a mine after backfilling and leveling for three years
4.2 恢復治理措施推廣建議
根據西藏自治區恢復治理現狀遙感調查成果,結合其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建議在城區及人口相對集中的鄉村附近,可采用改造再利用的方式開展礦山環境恢復治理;在水量豐富的喜馬拉雅山地區、三江并流地區、河流谷地等地區,可采用綠化的方式開展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但需要加強后期維護;在河流谷地,可等待洪水恢復;其余地區可使用回填平整與自然恢復相結合的方式開展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但回填平整過程中應盡量減少破壞附近的土地(表4)。

表4 恢復治理措施推廣建議Table 4 Suggestion on promotion of rehabilitation measures
5 結 論
(1)本文分析了西藏自治區礦山環境恢復治理現狀,發現回填平整是最主要的恢復治理措施,無論圖斑數量還是圖斑面積都排在首位;其次是自然恢復;然后是改造再利用,以及綠化。
(2)西藏自治區的礦山環境恢復治理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改變了原先礦山開采遺留的不良地貌景觀,不同程度地改善了當地生態環境。
(3)綜合恢復治理所需投入和效果,建議在西藏自治區采用自然恢復為主、回填平整為輔、多種恢復治理措施相結合的策略,因地制宜地開展礦山環境恢復治理工作。
(4)本文探討的恢復治理效果相對簡單,未能深入探討生態環境質量等內容,望有志學者繼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