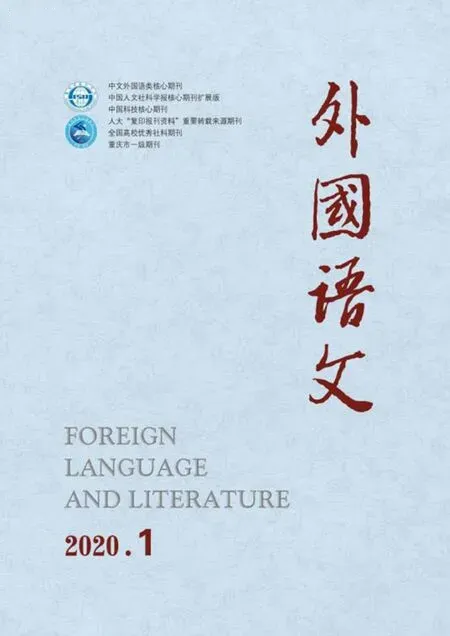雅各布森《夏洛克是我的名字》中的當代猶太人形象
2020-05-22 08:51:08田俊武侯麗娜
外國語文
2020年1期
關鍵詞:猶太人
田俊武 侯麗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外國語學院,北京.00191)
0 引言
2015年,英國霍加斯出版社發起“霍加斯·莎士比亞系列”大型出版項目,邀請當代世界名家改寫莎翁經典劇作,賦予經典新意,重燃公眾對莎翁經典作品的熱情,以此向莎翁致敬。霍華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于2016年推出的對《威尼斯商人》的改寫之作《夏洛克是我的名字》(ShylockisMyName),便是這一項目的主要成果之一。《英國衛報》《每日郵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各大媒體對此紛紛盛贊,例如《英國獨立報》書評人魯卡斯特·米勒稱此書“超高水準的重寫,透徹而戳動人心……夏洛克在這里是一個能夠喚起你我同情心的人物”(Miller,2016)。批評家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也給予本書高度評價:“在我看來,雅各布森對《威尼斯商人》的重寫以及他對這部作品的洞見似乎表明兩者有著命中注定的緣分。”(Hoare,2018)然而,盡管媒體對霍華德的這部改寫之作好評如潮,卻鮮有學者深入地對這兩部作品做過比較性研究。借助互文性理論,本文試圖揭示霍華德的《夏洛克是我的名字》在主題和敘事情節方面對莎翁的《威尼斯商人》的繼承、變異和超越。
1 《夏洛克是我的名字》與《威尼斯商人》的互文性呈現
朱莉亞·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Kristeva,1986: 37)身為一代文豪,莎士比亞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都不是他的原創,而是吸納并改寫了前輩文本中的情節或創意,《威尼斯商人》也不例外。如今,輪到他的戲劇被后人進行改寫了。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作文與考試·高中版(2018年30期)2018-11-26 09:51:30
作文與考試·高中版(2018年29期)2018-11-19 07:25:00
作文與考試·初中版(2018年29期)2018-11-19 07:20:44
作文與考試·高中版(2018年33期)2018-10-25 11:46:12
作文與考試·高中版(2018年32期)2018-10-25 11:46:04
作文與考試·初中版(2018年32期)2018-10-25 11:44:48
讀者(2018年12期)2018-05-30 05:16:40
戲劇藝術(上海戲劇學院學報)(2016年2期)2016-12-23 09:18:06
經濟社會史評論(2015年4期)2015-02-28 01:50:09
探索財富(2009年3期)2009-06-18 03: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