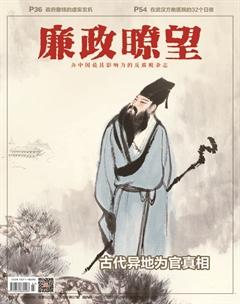古代異地為官制度缺了點啥
鄧苗苗
清 朝末年,美國傳教士明恩溥來華生活近五十年,對中國鄉土社會有足夠的了解。在他的著作《中國鄉村生活》中,一個悲劇故事道盡了異地為官制度之下的官場丑態。
明恩溥所居地附近有一戶顯赫人家,家中權勢最高的人官至閣老或大學士。當地縣令不太會曲意逢迎,又在一些事上惹到了這位閣老的兒子,被他一封家書告到了京城父親那里。不久后,縣令接到一紙調令,前往四川某縣任職。異地任職、不定期調動,對于清朝官員來說是常事,可這次調動幾乎要跨越整個中國,沿途花費巨大,麻煩甚多。他剛任新職不久,又接到升遷云南的任命。這又是一次耗時費神的艱苦行程。誰知剛到云南,又被通知升任關外某地的道臺……直到此時,這位縣令才明白自己遭受了多么惡毒的報復。他無法忍受行程中所染疾病的折磨與難以承受的路途開銷,無奈之下只好吞金自殺,永遠避開了進一步的“升遷”和無休無止的磨難。
像故事中縣令這樣為了避免權貴打擊報復,主動結束“仕宦生涯”的大概不多。但“為功名走遍天涯路”卻是古代官員仕宦生涯的真實寫照,從他們步入仕途起,基本就注定了要離開故土,在不同地方之間輾轉奔波,宦游之間難免生出飄零感。蘇軾也曾感嘆“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
仕宦的奔波,主要因為一項異地為官的制度。作為回避制度的核心,異地為官從不成文到草創,再到嚴格執行,綿亙千年,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回避的范圍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東漢“三互法”成型時,屬地任職還稱得上是主流。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已經開始要求原籍與就任地點五百里之內的“均行回避”。可見歷代統治者十分認同這項制度,并不斷進行修修補補,日趨嚴格。
這其實很好理解。古代官員異地任職的目的,是通過某種限制減少公權力行使中的利益沖突,并讓地方官員跳離人情網而全心全意地效忠朝廷、貫徹朝廷的政策。另外,與西方甚少采用“地域回避”不同,中國傳統社會向來有著鄉土情結。在統治者看來,這樣的情結除了會影響吏治,甚至還可能因“州郡相黨,人情比周”,影響到中央與地方的博弈。考慮到統治者加強對地方控制、集中權力的私心,異地為官制度能長久地實行下去也就不奇怪了。
無論是異地為官制度的制定者還是擁護者,主觀出發點都是為了減少地緣人情羈絆、遏制貪污腐敗、避免地方勢力坐大。但回顧整個古代官場,異地為官的優點并未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顯現,不僅無法擺脫貪污腐敗、結黨營私等痼疾,反而還滋生了更多統治者不想看到的現象,諸如行政效率低下、官員無心勤政等。
鑒于此,異地為官制度從誕生那天開始就伴隨著爭議。隨著清末地方自治理念開始興起,譚嗣同曾提出,這樣的制度使得地方官視“民如驛卒”,而當地百姓又視“官如路人”,誰也不把誰放在眼里,又怎能利于地方治理呢?而本地人任職卻好處多多,關于這一點,曾任曾國藩幕僚的楊象濟認為,“既為本地之人,則必休戚相關,不敢為暴虐奸邪之事”。
但為官的復雜性,又豈是籍貫這一點能囊括?古代異地為官的邏輯并非牢不可破,本地為官并非絕對良策。沒有其他相應制度的匹配與保障,一切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