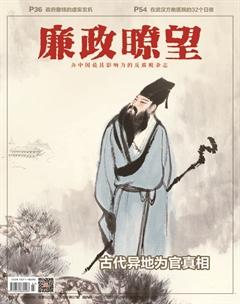古代異地為官制,最終不敵人情網(wǎng)
龍?jiān)谟?/p>
廣東海康(今屬雷州市)人陳瑸,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中進(jìn)士,后來被安排到福建古田縣做縣令。他疏議廢加耗、懲貪官、崇節(jié)儉、興書院、飭武備,很快得以升官,后任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等。他在外面做“裸官”20多年,從未攜帶家屬。兒子想去探望,苦于路途遙遠(yuǎn)缺少路費(fèi),最后也沒去成。
陳瑸沒有請(qǐng)師爺,只有一兩個(gè)仆從,以瓜果蔬菜為食,史稱“官?gòu)N惟進(jìn)瓜蔬”。他與海瑞、丘浚齊名,號(hào)稱“嶺南三大清官”之一,他清廉卓絕,康熙稱贊他為“苦行老僧”。“苦行”二字,實(shí)在是對(duì)陳瑸人生最精妙的概括,古代為官者,大部分都如陳瑸一樣。至于“苦行”的根源,還要從異地為官的用人機(jī)制說起。
“千年都行漢政法”,制度雷同“異”有別?
上世紀(jì)90年代,一個(gè)盜墓團(tuán)伙來到江蘇省連云港市東海縣溫泉鎮(zhèn)尹灣村西南約2000米的高嶺上,他們用鋼釬探明了一個(gè)直徑3米多、深5米的土坑,打開了一個(gè)棺蓋。很快,溫泉鎮(zhèn)的工作人員趕到現(xiàn)場(chǎng),制止了盜掘行動(dòng),并將此事上報(bào)給了相關(guān)單位。
此后不久,專業(yè)考古團(tuán)隊(duì)來到這里,進(jìn)而有了震驚學(xué)界的發(fā)現(xiàn)——尹灣漢墓群。尹灣漢墓墓主是西漢東海郡功曹吏師饒。漢墓簡(jiǎn)牘中,注明了東海郡124名官員官職和籍貫。令人驚訝的是,其中的123人不是東漢郡本郡人,唯一的一個(gè)例外,也是本郡其他縣調(diào)遷而來。這說明,早在西漢時(shí)期,官員的籍貫回避制度已經(jīng)建立起來。
尹灣漢墓的發(fā)現(xiàn)更推翻了史學(xué)界一直以來的觀點(diǎn)——官員異地任職制度起源于東漢桓帝時(shí)期。這一論點(diǎn)的主要支撐在于,中國(guó)第一個(gè)關(guān)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規(guī)“三互法”在東漢末期出臺(tái)。
漸漸地,史學(xué)界有了新的看法,官員異地任職制度草創(chuàng)于西漢,那時(shí)雖未明文記載,卻成為官場(chǎng)內(nèi)一種不成文的規(guī)矩。有一句詩叫做“百代都行秦政法”,不過在官員異地任職這一點(diǎn)上,卻是“千年都行漢政法”。自漢朝以來,每一個(gè)封建王朝都延續(xù)了官員異地任職制度,并不斷加以完善。
異地為官這一制度延續(xù)千年,但這個(gè)“異”字,在不同朝代卻有不同的含義與規(guī)定。在隋唐兩代,“地方官用外地人,回避本郡”,也就是說,本郡人士不得擔(dān)任該郡的官職。宋代規(guī)定進(jìn)一步細(xì)化,地方官員不僅須回避本籍, 而且非本籍而有地產(chǎn)之地亦須回避。有的官員,都因?yàn)檫@項(xiàng)規(guī)定,令自身仕途為之一變,朱熹便是其中之一。
朱熹祖籍徽州(今安徽),出生于南劍州(今屬福建)。《朱文公集》說,因?yàn)榛乇苤贫龋麩o法在出生成長(zhǎng)的南劍州任職,甚至因?yàn)榧易逵刑锂a(chǎn)在徽州婺源,他也無法去徽州任職。
眾所周知,朱熹對(duì)于祖籍地徽州懷有一份濃濃的鄉(xiāng)愁,無數(shù)次在詩文中表達(dá)對(duì)這片土地的向往。但就因?yàn)檫@條“在法也合回避”,他的仕途只能繞道而行,最終只是以學(xué)者的身份踏足故土,開壇講課。歷史上,只要官員不掌權(quán)了,回老家做教職人員,政府是不會(huì)管的。
到了明代,除了延續(xù)本省人不得在本省做官的慣例,更進(jìn)一步細(xì)化為,“南北更調(diào),已定為常例”。 也就是說,讓南方人到北方去做官, 北方人到南方去做官。到清代,異地任職有了改變,不再以行政區(qū)劃為標(biāo)準(zhǔn),而改以五百里為限, 即官員原籍、寄籍五百里以內(nèi)( 包括鄰省) 的地區(qū), 都得回避。

朱子文化園中的朱熹塑像。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浙江紹興府通判一職出缺,按人事任命制度,先由吏部文選司在初審基礎(chǔ)上選出符合條件的若干人選,再以抽簽方式?jīng)Q定取舍,結(jié)果,順天籍張廷泰中選。據(jù)說乾隆帝接見張廷泰時(shí),聽出了他的紹興口音,便問明緣由,得知其幼年曾隨父在紹興居住數(shù)年,于是乾隆取消原擬任命,讓張廷泰到福建任職去了。
配套政策沒跟上,就會(huì)有人鉆空子
南宋抗金將領(lǐng)、詩人張守,是江蘇人,在被朝廷任命為紹興知府時(shí),他主動(dòng)申請(qǐng)辭免,理由是張家在紹興府會(huì)稽縣置有三百畝田產(chǎn)。張守以此為理由,申請(qǐng)回避。官員的自覺固然符合封建社會(huì)對(duì)于官員的“德治”要求,但作為權(quán)力中央,深諳制度比道德更靠譜。
異地任職制度在執(zhí)行中,催生出其他配套制度。在宋代,對(duì)于官員的檔案管理非常嚴(yán)密,甚至建立起某種財(cái)產(chǎn)登記制度。宋代《吏部條法總類》規(guī)定,凡“應(yīng)參選注闕官”,俱須于差注前驗(yàn)實(shí)“本官委的有無祖產(chǎn)并妻家田產(chǎn)在所射處”。所以,朱熹、張守在徽州、會(huì)稽等地有田產(chǎn)的事,朝廷能夠知曉。清代的官員檔案管理或許較為粗糙,張廷泰幼年的生活經(jīng)歷,朝廷并不知曉,只知道他是順天籍。若不是乾隆聽出了張廷泰的紹興口音,他便“衣錦還鄉(xiāng)”了。
有時(shí)候,配套政策沒跟上,就會(huì)有人鉆空子,進(jìn)而影響吏治。《清代四川南部縣衙門檔案》記錄了從順治十三年到宣統(tǒng)三年的,256年時(shí)間里,南部縣144名知縣的詳細(xì)狀況。在官員異地任職十分嚴(yán)格的清代,這些縣令的籍貫全都在500里外的地方。不過再仔細(xì)查閱這些縣令的生平則發(fā)現(xiàn),盡管他們來自外省,但大多在四川多年。
一名叫章儀慶的縣令,是浙江紹興人,光緒二十七(1901年)年入川,經(jīng)過“多崗位鍛煉”,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擔(dān)任南部縣令。結(jié)束在南部任職經(jīng)歷后,他又輾轉(zhuǎn)四川多地,成為四川官場(chǎng)的“老熟人。”還有一名叫侯昌鎮(zhèn)的知縣,原籍湖南,出任南部知縣之前,已在四川奉節(jié)、開縣等地做過兩任知縣。
像章儀慶、侯昌鎮(zhèn)這樣的外地官,在某省官場(chǎng)一待就是幾十年,在古代官場(chǎng)屢見不鮮。一名歷史學(xué)者介紹,古代交通不便,官員遠(yuǎn)離家鄉(xiāng)為官已是千里跋涉,若再頻繁遠(yuǎn)距離調(diào)動(dòng),那更是麻煩。因此,許多外地官員到任后,大多在一個(gè)省調(diào)動(dòng)。如此一來,這些官員在一個(gè)地方任職幾十年,雖是外地人,卻難免卷入當(dāng)?shù)乇P根錯(cuò)節(jié)的關(guān)系中。這與異地為官制度的初衷或許背道而馳。
科舉考試中屢禁不止的“冒籍”,就與異地為官制度有關(guān)。江南歷來富庶,教育水平也很高。這就意味著,籍貫江浙的人士,不僅在科場(chǎng)上面臨更大壓力,一旦通過考試步入官場(chǎng),還得去西南、西北等偏遠(yuǎn)地區(qū)為官。于是,許多江南的生員想盡辦法修改籍貫,不僅成為“高考移民”,還能在未來分配中占便宜。
清末著名的實(shí)業(yè)家張謇是江蘇海門人,不幸投胎到三代都沒有讀書應(yīng)試的家庭,按當(dāng)時(shí)的規(guī)定,沒資格去考試。張謇的老師宋琳支招,把他帶到二百里外的如皋,更改戶籍,給當(dāng)?shù)厝藦堮x做了“孫子”,但張謇家萬萬沒想到,裝孫子變成了遭人訛詐的“真孫子”。
后來他中秀才,付給張駒與老師宋琳大約300兩銀子。卻不料張駒愛抽大煙,以舉報(bào)冒籍威脅張謇家,敲詐索要350兩銀子。一次得逞,張駒再三敲詐。最后張謇家不堪其擾,拒絕再掏錢。張駒惱羞成怒,報(bào)了官府。好在當(dāng)?shù)卣異巯瞬牛瑸閺堝澜獬寺闊5珡堝兰覟榇烁冻隽?000兩銀子的代價(jià),負(fù)債累累。
大多數(shù)朝代,朝廷并沒限制官員帶家屬赴任,能帶上家人,就少了些孤單寂寞冷。然而,礙于路途遙遠(yuǎn),調(diào)動(dòng)頻繁,不少官員上任都少有帶家屬的。有時(shí)候官員家屬卻成了危害百姓的一種勢(shì)力,就會(huì)引起朝廷的注意。
唐代律令對(duì)于可能蘊(yùn)含于家庭“親情”中的腐敗風(fēng)險(xiǎn),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范。《大唐六典》明確規(guī)定:諸外任官人,不得將親屬賓客往任所……與百姓爭(zhēng)利。
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御史劉子章條奏外官禁止多帶家口。這是清代首次對(duì)官員攜帶家丁作出限制。各級(jí)官員都規(guī)定有相應(yīng)名額。例如“藩臬帶家人四十名,道府帶三十名,同知、通判、州縣帶二十名……”
人治社會(huì)的制度,是用來被打破的?
唐太宗時(shí)期,有廉能之名的賈敦實(shí)擔(dān)任饒陽縣令后,他的哥哥賈敦復(fù)又被派往瀛洲任刺史,成了弟弟賈敦實(shí)的上司。兄弟倆都是異地為官,不過卻違背了當(dāng)時(shí)的回避制度。按照唐朝制度,同一祖父名下的本家成員,都不能在一個(gè)部門任職。但唐太宗卻打破慣例,“以其兄弟廉謹(jǐn),許令同州”。這也說明,“回避”制度雖然嚴(yán)格,但皇帝金口一開,就沒有破不了的規(guī)矩。
籍貫回避制度到了中央集權(quán)式微時(shí)期,基本就形同虛設(shè)了。
明朝末年,天下大亂。大臣楊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wǎng)”之策鎮(zhèn)壓農(nóng)民軍,深得崇禎皇帝賞識(shí)。崇禎帝派楊嗣昌為督師,前往湖廣作戰(zhàn)。督師在明朝是一個(gè)官職,地位比總督更高。不過楊嗣昌是湖廣人,他督師湖廣,顯然違背了異地為官的原則。但滿朝上下誰也沒說什么,一來是楊嗣昌深得皇上喜愛,二來國(guó)事艱危,誰肯打誰就上,回不回避倒無所謂了。
有一個(gè)有趣的現(xiàn)象,在一個(gè)封建王朝的初期,官員異地任職制度往往執(zhí)行較為嚴(yán)格,到了王朝末年卻是另一番景象。明代的楊嗣昌督師湖廣即是一例,安徽人李鴻章也接替了恩師曾國(guó)藩兩江總督的位子,管轄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王朝末年綱紀(jì)松弛,到了危急時(shí)刻,滿朝上下都認(rèn)為異地任職過于刻板,誰有本事誰就上,這也暴露出人治社會(huì)的任何制度,都不太牢靠。

《東海郡屬吏考績(jī)簿》漢,木牘,長(zhǎng)22.3 厘米、寬6 厘米,兩面書寫。正面為《東海郡下轄長(zhǎng)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背面為《東海郡屬吏設(shè)置簿》,連云港市博物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