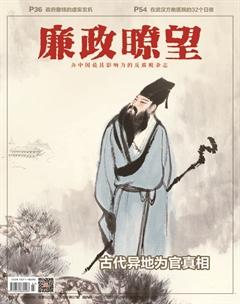守望相助:國際救援中的東亞特色
鄧苗苗

泰國清萊,當地的藝術家們創作了一幅主題壁畫,致敬營救“野豬”足球隊的救援人員。
國家之間的官方救災援助,自古有之。就拿位于東亞文明中心的中國來說,救助各國海難“漂流民”是歷朝政府的一項工作,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形成固定制度。乾隆皇帝曾下令,對外國漂流民的救助,應“動用存公銀兩,賞給衣糧,修理舟楫,并將貨物查還,遣歸本國”。如今,隨著國際交流日漸頻繁,各種災害的影響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國際救災援助的作用也愈發重要。
國際救援背后的政治
2008年5月2日,一場被命名為“納爾吉斯”的颶風并未按照人們預測的路線移動,而是突襲緬甸南部地勢低平、人口稠密的伊洛瓦底三角洲,并于次日凌晨直逼緬甸最大的城市仰光。迅猛的颶風造成14萬人死亡,80萬人流離失所。而根據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辦的長期評估,240萬人受到這次風暴直接侵害。
相關人士認為,這場災害造成的后果可能就連那些國力富強、應急得當的國家都難以承受,更何況緬甸。在這種情況下,接受國際援助不失為一種好的選擇。
但令人意外的是,在這個問題上,緬甸軍政府一直猶豫不決,直到5月9日,才正式宣布接受國際援助,但不允許外國專業救援人員進入,只限于食品、藥品等物資及資金援助。
這樣的操作被國際社會認為是違背人道主義。迫于愈演愈烈的輿論壓力,10天后,緬甸終于同意接受來自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的救援,并逐漸開始接受更廣泛的國際援助。
災難面前,接受國外專業救援是應對其影響、盡可能搶救生命的有效做法。但這與古代中國官方對漂流民的救助不同,一旦涉及外國相關人員入境,受災國就有可能對此持保守態度。因為,盡管國際援助秉承人道主義精神,有中立等原則,實際上卻不可避免地會涉及政治,甚至帶有地緣政治的色彩。
二戰后,日本就是靠著經濟援助改善與亞洲諸國的關系,于20世紀80年代前后開始關注國際救援,在他國自然災害發生后,積極主動地伸出援手,提供人力、物力幫助。
而2013年菲律賓因臺風“海燕”遭受巨大生命、財產損失后,美國更是派出陣容強大的救援團隊,一度有13艘軍艦、近8000名軍人參加,聲勢浩大。美國一些媒體直言不諱地表示,“美國借救災增強在亞洲的軟實力”“美國援助菲律賓暗含外交目的”。
根據主權和不干涉原則,國際救災援助首先需要受災國同意,但面對生命可能即將消逝,決策的天平向人道主義傾斜成為了大的趨勢。
2018年6月23日,泰國一個名為“野豬”足球隊的12名少年隊員和1名教練進入泰國北部清萊府一處洞穴后集體失蹤。泰國當地搜救團隊聯系國家防災減災廳、警方、軍隊等部門緊急開展聯合救援行動。由于搜救進展緩慢,泰國方面當機立斷做出了向國際求援的決定。次日,英國、中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搜救團隊就抵達現場,迅速組建成一支由國際頂尖專家組成的聯合救援隊伍,一場牽動全世界的救援行動就此展開。
困住13人的洞穴長達10公里,內部結構十分復雜,加上暴雨引發的洪水把洞穴的入口堵住,救援難度相當大。經過多國救援人員長達半月的努力,7月10日,被困13人全部獲救,走出了暗無天日的洞穴,這場被贊為“奇跡”“史無前例”的救援成功落下帷幕。
國際救援怎么“救”
國際救援的成功,離不開多方配合,建立有效的協作機制是各國一直在探索的方向。比如,在經歷中國“5·12”汶川地震和日本“3·11”大地震后,中、日、韓決定建立三國間的“災害管理和救災合作渠道”,探討在一國發生災難后,其他兩國如何快速有效地提供救援工作。
而泰國洞穴奇跡般的救援,也得益于各國救援人員經歷了語言不通、存在爭議誤解等困難后,以充分信任的姿態不斷磨合、組織協調,最終制定出了行之有效的救援方案——潛水救人。
一般來說,受災國在請求或同意接受國際救援后,須在行政上明確安排衛生部門與政府、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包括與他們的聯絡、協調及與他們的監督關系。而境外救援隊入境后,則須按照國際慣例行事,先去災區指揮部或協調中心報到,聽從統一指派救援任務。
在國際救援組織協調方面,發達國家似乎走在了前面。早在1985年,丹麥和德國就簽署了《丹麥和德國關于災害或嚴重事故時互助協定》,對雙方在應急響應階段給予對方緊急救援人員的入境豁免等方面進行了規定。
為了共同應對重特大突發事件,1992年,歐盟的前身歐共體還成立了歐共體人道主義援助辦公室,2010年2月更名為人道主義援助與民防總局,專門負責歐盟的重特大突發事件的預警監測、應急響應協調、信息共享、人員培訓等,并向重特大突發事件的受災國統一提供應急救援支持。不過在此次歐洲疫情期間,讓一系列協定成為了紙上童話。
值得一提的是,國際救援還有一些約定俗成的原則,比如救援隊伍首先要保證自己的安全與補給充足,不能給受災國增加麻煩。還要保證救援的時效,反應慢的救援隊伍甚至可能在路上就被受災國要求終止救援任務。2005年10月巴基斯坦地震后,有隊伍因為在機場滯留時間較長,還在奔赴災區的途中就接到巴基斯坦政府的要求,打道回府了。
除了派遣專業救援人員,物資支援也是極為關鍵的一面。日本為了能及時提供救援物資,不僅在東京成田機場建立了國內倉庫,還在新加坡、墨西哥、美國華盛頓、英國倫敦等地建立了海外倉庫以便調度。
可以說,國際救災援助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不僅各國對此的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積極轉變,相應的機制也在實踐中不斷完善。盡管其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義、利的博弈,但面對災難,國與國之間真誠的守望相助又何嘗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