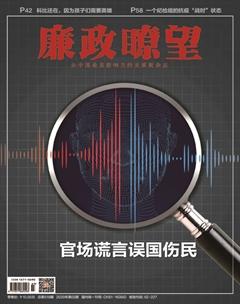一場冤獄的煉成
張鳴
刑訊逼供,自古以來很容易煉成冤獄。但是,明清兩朝,地方官兼任司法官,多半不熟悉刑獄之事,審案沒有經驗,一靠師爺,二靠刑訊。師爺如果不給力,那就只能靠刑逼供了。明朝中葉的戴用,是做過御史和道臺的人,但是,他未及第之前,差點因為一場冤獄,斷送了性命。
戴用是江西高安人,家境富有。在尚未進學之前,他父親為他請了一個塾師。請來之后,才發現這位塾師特別喜歡打官司,在那個時代,算是一個訟師。然而,訟師在民間的口碑里,就是訟棍,名聲很不好。所以,他的父親就把這個塾師給辭退了。
當地的風俗,只要被人辭退的塾師,以后就沒人請了。所以,這個塾師懷恨在心,恨大了,就設計了一個計謀,自己找了個隱蔽的所在,藏了起來,然后讓家人去告狀,說是塾師有本特別值錢的經義,被戴用看上,索取不遂,就把塾師弄死了。于是,戴用就吃了官司,而且是人命官司。
按理說,這樣的人命官司,理當慎重,而且說是人死了,活不見人,死不見尸,說殺人取經,全是原告的一面之詞。退一萬步說,一本經義能值多少錢呢?至于讓人甘冒殺人的風險嗎?然而,地方官居然認定戴用殺了人,嚴刑逼供。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一個文弱書生,又不是江洋大盜,哪里熬得住刑,只好屈打成招。被押在死牢里,等著挨刀。
幸好,戴用的家人憑蛛絲馬跡,知道這個塾師還活著,于是,出大價錢懸賞有知道此人下落的人。在官司眼看無望的時候,突然有人舉報這個人還活著,而且說出了這個人躲在什么地方。在這個人被揪出了之后,官府只好把戴用放了。
如果是保護無辜的人,那么,就無論如何不能刑訊逼供。如果是為了所謂打擊罪犯,那么刑訊逼供,就根本免不了。骨子里,就是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有罪推定。
后來戴用一路考上來,也做了大官,但是已經沒有機會去會會當年草菅人命的地方官。此案給他的教訓就是,所有刑獄之事,一定要慎重,切不可草率從事。戴用家里還算是有點錢的,能高價懸賞知情者,最終還自己清白。而那些沒有錢的百姓,在這樣葫蘆僧亂斷葫蘆案的情況下,不知有多少冤魂,屈死于朝廷的刀下。
官員偏聽偏信,是一個問題,因為那個塾師,也是個訟棍,知道怎么編故事,能騙到天真的官員,由此,在完全沒證據的情況下,審案的地方官就一邊倒地相信原告的說辭。但是,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刑訊逼供。在一個刑訊逼供基本上合法的司法條件下,只要審案的人勇于而且敢于用刑,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自己想要的結論。
只要允許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就一定會大量地存在。你可以比較順利地破一些案子,也能因此而懲治一些罪犯。但是,同樣大的概率,是冤枉了一些根本沒有犯罪的好人。這里,關鍵是,你審案的出發點是什么,如果是保護無辜的人,那么,就無論如何不能刑訊逼供。如果是為了所謂打擊罪犯,那么刑訊逼供,就根本免不了。骨子里,就是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有罪推定。
歷史的教訓,就一件件擺在哪兒了。能不能吸取教訓,就看今天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