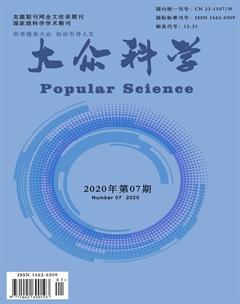細胞外基質與齲病
王家旺
摘 要:生物膜是嵌入在細胞外基質中的微生物群落,具有高度組織結構。齲病是多種因素參與的,生物膜中微生物長時間在菌斑深層產酸,牙體硬組織發生慢性、進行性破壞而形成的。基質的結構和生化特性,增強了生物膜的表面粘附性、空間和化學非均質性、協同/競爭性相互作用以及對抗菌藥物的耐受性。本文我們討論生物膜基質在齲病發病機制中的作用的新進展。
關鍵詞: 生物膜;齲病;細胞外基質
齲病是以細菌微生物為病原體,多種因素參與的,發生在牙體硬組織的慢性、進行性破壞的疾病。通常情況下,致齲性膳食糖緊緊貼附于牙面,使得唾液蛋白形成獲得性膜并牢固地附著于牙面 ;在適宜溫度下,生物膜中微生物長時間在菌斑深層產酸,侵襲牙齒,使之脫礦,并進而破壞有機質,導致牙齒組織的缺損,乃至整個牙齒缺失。WHO對 186個國家的人群口腔健康進行長達 20 年的縱向調查結果顯示,齲病仍影響著 60%-90% 的學齡兒童和大部分成年人,給社會和個人帶來較大的經濟負擔。
目前關于齲病病因學的說法主要有三種[1],一是認為齲病是由口腔中的某些特異性致齲細菌所引起; 二是認為齲病是由口腔中的一些常駐菌群所導致; 第三種也是目前比較公認的說法,認為齲病是由于口腔微生態環境失衡所致。已經知道,在微生物和宿主之間的共棲和共存中,口腔微生物群保持穩態。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寄生關系發生變化,齲齒微生物的上升導致齲齒。隨著先進的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發現了新的致齲微生物種類,人類口腔微生物群也逐漸被了解。然而,我們通常采取的齲病預防措施不能完全適用于每個人。個體發生蛀牙的機會取決于免疫系統和口腔微生物群等因素。本文中,我們回顧了相關文獻,并討論了微生物生物膜在齲病中的作用。
1口腔生物膜
生物膜被定義為基質包裹的互相粘附,或粘附于牙面、牙間,軟而未礦化的微生物群落,其由口腔微生物、宿主和宿主飲食之間動態相互作用,導致口腔表面的微生物定植及牙菌斑的形成[2-3]。隨著DNA和RNA測序技術的發展,不同口腔部位生物膜菌群的組成、基因組和行為的多樣性逐漸被認識。同時,對于細胞外基質如何控制細胞與細胞間相互作用、創造微環境和改變生物膜毒力方面的認識也逐步深入[4]。
影響口腔表面微生物群組成的因素有很多,尤其是當牙齒萌出時,此時共生和機會性病原體的定植有了新的、非表皮的表面,這些影響因素包括年齡、飲食、口腔衛生、全身情況和免疫狀況以及某些藥物作用等[5-6]。研究者們已在病人或實驗動物身上證明了飲食在微生物定植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當宿主過度暴露于食物中的糖分時,牙齒上形成的生物膜的結構和組成將發生顯著的變化,定植的微生物群落變得非常適合代謝碳水化合物并產酸,導致齲齒[7]。
2 EPS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膜的微生物組成上,近期的研究發現,生物膜內的微生物嵌入在含有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EPS)的基質中。基質在微生物集體行為和毒力,以及對抗菌藥物的耐受性方面的作用,正日益得到認識,并被認為是生物膜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EPS直接介導微生物對表面的粘附和細胞間的粘附,同時形成聚合物基質,增強生物膜的機械穩定性。此外,EPS基質有擴散修正特性,導致化學/營養梯度的形成。pH、氧化還原和營養利用率的不同,會影響生物膜內微環境及其微生物行為[8]。因此,在基質中,細胞組織成多細胞生態系統,彼此發生協同和拮抗作用,有助于創造具有不同致病潛能的局部微生態。
隨著微生物組學和基質生物學的發展,逐漸認識到多微生物相互作用和局部生物膜微環境的變化,對齲病的發生發展起重要作用。相反,數十年的研究清楚地表明,病原體已經發展出一系列機制來增強生物膜[9]。口腔內環境的變化,例如糖的消耗增加或免疫反應的改變,均可以觸發病原體重塑局部微環境和微生物群落。然而,關于病原體如何改變微生物群落和群落行為,重塑局部微環境的,卻鮮為人知。此外,共生菌和病原體是如何共存的,并且在生物膜基質中相互競爭以影響疾病過程仍然不清楚。
基質的結構和生化特性提供了生物膜的新特性,包括表面粘附性、空間和化學非均質性、協同/競爭性相互作用以及對抗菌藥物的耐受性增強。EPS基質的形成取決于基質有效性、胞外物質的合成和分泌、剪切等應力。與齲齒相關的口腔生物膜的主要基質成分是多糖,特別是變形鏈球菌衍生葡聚糖。此外,其他物種(如放線菌、唾液鏈球菌和紅鏈球菌)和雜交種也可產生可溶性葡聚糖和果聚糖淀粉葡聚糖。與其他基質一樣,致齲生物膜也含有eDNA[10],具有淀粉樣特性的細菌衍生蛋白質,以及宿主蛋白質和糖蛋白,它們與葡聚糖結合形成基質支架。然而,這些外聚物在基質中的功能和結構仍不清楚,它們在生物膜的微生物組成和致齲潛力中的作用需要進一步研究來闡明。葡聚糖是由鏈球菌葡萄糖基轉移酶(glucosyltransferases,Gtfs)協同作用產生的[11]。細胞外釋放的Gtf酶可以活性形式結合于牙齒表面,就地產生葡聚糖,提供新的細菌結合位點。此外,分泌的Gtf還與其他口腔微生物(共生鏈球菌,放線菌、乳酸桿菌,甚至白色念珠菌)結合,使其產生葡聚糖。研究者在Gtfs合成葡聚糖的過程中,使用熒光探針直接摻入時發現,EPS基質時空順序及其與生物膜中細菌的空間排列被顯現出來。這些細胞外聚合物在細胞膜上的不同位置聚集,各種聚合物相互補充,形成新生的EPS基質,并協調生物膜的發育,包括表面粘附、細胞-細胞粘附和形成類似于其他生物膜系統中發現的微菌落的細胞團。隨著生物膜的成熟,EPS的持續原位生成,使基質三維擴展,包圍細胞團,并在3D基質支架內形成一個高度分隔但有凝聚力的結構。EPS合成形成的這種空間組織,及其合成的不均勻性,恰恰可以解釋在人類口腔生物膜中發現的不同大小和組成的微生物群落[12]。
EPS也會影響生物膜的力學性能,例如增加對表面的粘合強度和粘結性。隨著生物膜的成熟,基質硬度會增加。在后期,成熟的生物膜可以釋放出小的聚集體,甚至單個細胞,通過基質降解,在其他部位重新啟動生物膜的生命周期[13]。生物膜基質的物理化學性質還可以通過減少藥物的獲取和觸發抗菌藥物的耐受性來保護嵌入的細菌。例如,EPS可以結合陽離子抗菌藥物,如氯己定,防止滲透到生物膜的深層,從而降低滅菌效能。
大多數生物膜內化學和營養“梯度”的形成,依賴于基質物理屏障作用和局部微生物代謝之間的平衡。在此過程中創造出許多不同濃度的pH、O2、無機離子、信號分子、代謝物和其他溶質的生物位點。因此,微生物的定位和它們的應激反應機制可能與它們對低pH或低氧環境的敏感性和特定配體、營養素或生物分子的存在有關。這種異質環境可以局部調節基因表達,影響不同物種之間或分布在生物膜結構內的不同細胞群之間的代謝和細胞間信號傳導,協調它們共同的“社會行為”、空間組織和/或生理異質性。最近的研究表明,細菌聚集體可以誘導生物膜內細胞亞群的轉錄組變化。
牙齒表面的唾液能夠緩沖中和口腔中的酸,而EPS基質限制了帶電離子在緩沖液中的擴散,而不帶電的溶質,如蔗糖,可以擴散到生物膜中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被嵌入的細菌代謝成酸。此外,胞外葡聚糖似乎可以直接捕獲質子,幫助在生物膜中保留和積累酸。生物膜基質還可以通過固定外源酶,使它們能夠在接近細胞的同時代謝底物,參與基質重塑。pH在口腔生物膜結構中的不均勻空間分布一直備受重視。直接固定在生物膜基質中的熒光pH探針顯示,盡管暴露在中性條件下,完整生物膜內的仍顯示出三維pH分布,并且在這些特定區域積聚和限制的酸不易中和。因此,EPS可以通過幫助生物膜粘附、空間定位代謝物,調節牙齒界面的持續酸化,并可能限制唾液的緩沖,有助于創建齲齒微環境。
總之,EPS增強了細菌間的粘附-結合和種間的結合,同時通過基質的形成,將細胞嵌入到不同的微生物群組中。EPS基質作為一個擴散控制屏障,通過調節溶質進入生物膜內部并將產生的酸捕獲在生物膜內,除了產生氧梯度外,還是內源酸的產出場所。內嵌的微生物必須處理各種應力(酸性、低氧)和不斷波動的營養成分,以維持口腔生物膜,這是齲病發病的先決條件。產生EPS的病原體可以被認為是“生物膜環境調節器”,有助于在復雜的微生物群落中建立病理微生態。
目前對于齲病發生發展過程中,細胞外基質分子和功能變化,及其與多微生物相互作用的時空變化仍有待進一步研究。此外,目前對于EPS基質如何提供結構支架,如何控制微生物的聚集、定位和活動的,并不十分清楚。基質介導的變化可以改變細胞間的相互作用,特別是不同微生物物種之間的相互作用。深入分析生物膜基質、局部微生物組分和宿主之間的結構和功能相互作用,將促進我們對口腔和其他多微生物疾病致病機制的了解,以提供精準的靶向治療及預防措施。
參考文獻:
[1]李瑩,儀虹.高齲和無齲人群口腔唾液微生物群落結構分析[J].中國醫刊,2015,50(3):68-71.
[2]Marsh, P.D. and Zaura, E. (2017) Dental biofilm: ecological interactions in health and disease. J. Clin. Periodontol. 44 (Suppl. 18),S12–S22
[3]Hobley, L. et al. (2015) Giving structure to the biofilm matrix: an overview of individual strategies and emerging common themes.FEMS Microbiol. Rev. 39, 649–669
[4]Koo, H. and Yamada, K.M. (2016) Dynamic cell-matrix interactions modulate microbial biofilm and tissue 3D microenvironments. Curr. Opin. Cell. Biol. 42, 102–112
[5]David, L.A. et al. (2014) Diet rapidly and reproducibly alters the human gut microbiome. Nature 505, 559–563
[6]Maslowski, K.M. and Mackay, C.R. (2011) Diet, gut microbiota and immune responses. Nat. Immunol. 12, 5–9
[7]Pitts, N.B. et al. (2017) Dental caries. Nat. Rev. Dis. Primers 3,17030
[8]Mira, A. et al. (2017) Role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eriodontal diseases and caries. J. Clin. Periodontol.44 (Suppl. 18), S23–S38
[9]Lamont, R.J. and Hajishengallis, G. (2015) Polymicrobial synergy and dysbiosis in inflammatory disease. Trends Mol. Med. 21,172–183
[10]Rostami, N. et al. (2017) A critical role for extracellular DNA in dental plaque formation. J. Dent. Res. 96, 208–216
[11]Besingi, R.N. et al. (2017) Functional amyloids in Streptococcus mutans, their use as targets of biofilm inhibition and initial characterization of SMU_63c. Microbiology 163, 488–501
[12]Mark Welch, J.L. et al. (2016) Biogeography of a human oral microbiome at the micron scale.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113, E791–E800
[13]Liu, Y. et al. (2016) Topical delivery of low-cost protein drug candidates made in chloroplasts for biofilm disruption and uptake by oral epithelial cells. Biomaterials 105, 15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