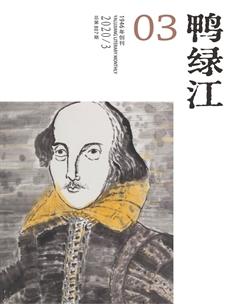免疫力
劉家朋
一
李光元跟王智仁一家人交往日漸頻繁。
當(dāng)智仁心里犯悶的時(shí)侯,光元便熱心地說些風(fēng)趣的話語給他解悶;當(dāng)智仁高興時(shí),光元便也和他同樣笑逐顏開,隨著他的興致說話;當(dāng)智仁遇到了什么難辦的事的時(shí)侯,光元便會(huì)熱心地幫他出主意。只這些倒也不算,因李光元是個(gè)木匠,家中日子過得比較富裕,當(dāng)智仁需要用錢,恰恰又手頭逢艱難時(shí),只要被李光元知道,李光元便慷慨解囊立即借錢給他。并且,李光元還常常無償?shù)貛椭侨始腋梢恍┝闼榈哪竟せ睢?/p>
智仁夫妻見李光元對他們是那樣的熱心相交,感動(dòng)之余,對李光元也同樣不錯(cuò)。
正月十八日這天,吃罷早飯,智仁急著到建筑隊(duì)干活去了,兒子小強(qiáng)也上學(xué)了。為了提前為今年種花生準(zhǔn)備好種子,媳婦銀花便一個(gè)人在家忙著掰花生。正掰著,只聽得院里的大門搖栓“吧噠”一聲響,門搖栓被人搖開,隨即“哐當(dāng)”一聲,門被推開。她定神一看,原來是李光元來了。
李光元比王智仁大兩歲,今年四十二歲,高大魁梧,眉毛濃而黑,眼睛大又亮,留著時(shí)興的大分頭,實(shí)是相貌堂堂。再加上對銀花一家總是那樣的關(guān)心,見他來了,一種崇敬之情油然涌上銀花的心頭。
“喲,弟妹在家忙著掰花生種啊!”
“嗯,是呀!大哥快進(jìn)屋坐坐。”銀花笑容滿面,熱情地應(yīng)答著李光元。
銀花生的圓圓的蘋果臉,柳葉眉毛下有兩顆如星星般雪亮的大眼睛。她性格開朗,歷來愛說愛笑,本來人就長得美,要是說話時(shí)再露出靚麗的笑容,那別提多討喜了!
說話間,李光元很快便來到了屋里。銀花一側(cè)身,將身旁的一個(gè)馬扎遞給了李光元,李興元接過馬扎便坐在了銀花身邊。
銀花隨便問一句:“忙活活的,大哥怎么還有空耍呀?”
李光元說:“別人忙,我可不太忙,我那點(diǎn)地早就雇別人用拖拉機(jī)耕完了。”說著,兩眼看著銀花,不知不覺便顯現(xiàn)出貪婪的神色。
“那,花生種也掰完了?”
“嗨,掰花生這活,天生就是娘們的活,就讓你嫂子慢慢在家掰吧,我可沒有耐心干這個(gè)。”李光元一邊說,一邊在銀花那漂亮的臉蛋上左右掃視。
“那,你最近的木匠活不忙?”銀花問著,羞澀地避開了他的目光。
李光元說聲“不忙。”目光一直離不開銀花的臉,“嗨,妹子,我這個(gè)活呀,說忙,到時(shí)侯還真忙;說不忙,只要向客戶說一聲,把打造用具的完工時(shí)間往后延長一些就行了,好辦。”
“呵呵,大哥日子過得真自在。”
接下去,二人便你一句我一句地繼續(xù)拉些家常話。李光元一邊說著話,一邊仍時(shí)不時(shí)地飄向銀花的臉,目光中,那貪婪的神情愈加顯露。
銀花本來是早已覺查到李光元的神情有些不對頭,可是,自己的虛榮心偏偏又跟戒備心作對,見李光元這樣放肆地瞅她,不但沒引起反感,卻暗暗為自己的魅力得意自豪起來。
看就看唄,男人嘛,見了對眼的女人難免就愿多看幾眼,這也是很正常的事。自要自己把心擺正了,任憑他再怎么看,無非也就是過過眼癮罷了。
銀花這樣想著,便裝做什么也不知,低著頭只管掰她的花生。
李光元砸了砸嘴,似無計(jì)可施的樣子,隨即便往屋子四下里端量了一番,最后目光盯在東間的東墻壁上。那墻壁上貼著一個(gè)一尺半見方的由木框鑲邊的針織刺繡大福字,甚是美觀,他的眼光突然比起初亮起來,“喂,弟妹,你們東墻上那個(gè)大福字是你繡的?”
“啊,是呀!你看這個(gè)福字好看嗎?”銀花笑著說。然后抬起頭看了他一眼,眼神中自然不自然地便帶出了親昵的神情。
“哦,妹子的手可真巧哇!我敢說,咱們村除了你以外,能繡出這樣福字的女人再?zèng)]有了。”李光元借著這個(gè)話題便說起夸獎(jiǎng)話來。
銀花謙虛地說:“快別夸啦,大哥!我都覺得自己手拙得像鴨子巴掌不分路。”
李光元一時(shí)間沒了言語,腦門兒微皺。
銀花心里明白,他這是見自己的話語在她身上沒起多大的作用,覺得無招可施了,不由得笑出聲來,“嘿嘿,大哥,剛才你還承認(rèn)自己日子過得自在,怎么這一陣又皺起腦門來了?”說著,臉上便不覺飛起一片紅潤。
“什么,我皺腦門了嗎?妹子真是察人入微啊!”李光元急忙掩飾。可是,掩飾歸掩飾,臉上那得意的神色,簡直像打上了興奮劑一般,根本抑制不住。
“奧,大哥可能是又在想嫂子了吧!”銀花戲謔著,因?yàn)樾Φ姆却螅嫒籼一ā?/p>
忽然,李光元瞅了瞅銀花坐著的那用紅色尼龍繩襻的馬扎,又低頭看看自己坐的馬扎,見馬扎襻的很是美觀,像是突然發(fā)現(xiàn)了什么奇跡:“嘿,弟妹,你們的馬扎襻得太好了,又美觀又結(jié)實(shí),是你自己襻的?”
銀花說:“還真讓大哥給說中了,我家里共四個(gè)馬扎,都是我自己襻的。”她說著,臉上便堆滿了自豪的笑容。
“呀!我說的么,除了你,誰能干出這樣的巧活?我當(dāng)了多年的木匠,要說讓我襻馬扎,肯定還是襻不出這個(gè)美觀的樣子。”接著,他的兩眼緊盯著銀花的臉,“妹子長相也出眾,凡是容貌漂亮的女人,手都巧。”
銀花高興極了,嘴里說著:“呵呵,大哥夸我了。”心里卻興奮得像喝了美酒,便關(guān)切地問他最近生意怎么樣,又問他出外干木匠話是否能和一些不講理的人鬧起來,又問他天天出外當(dāng)木匠,大嫂一人在家,是否能忙過地里的活來等等。李光元呢?則把自己出外見過的新鮮事兒說給銀花聽,說一會(huì)兒新鮮事兒,還參插講一些動(dòng)聽的小故事。在講他見過的新鮮事兒和小故事的時(shí)侯,時(shí)而捎帶著夸耀銀花與他所說的事件中人物類似的長處。銀花是越聽越愛聽,越聽越想聽,漸漸聽得有些入迷了……
二
原來,這個(gè)李光元是個(gè)十足的偽君子!他之所以對王智仁一家人熱情相待,是因?yàn)樵缇涂瓷狭算y花的美色!以前,他覺得火侯不到,不敢太放肆,現(xiàn)在他覺得時(shí)機(jī)已到,便開始用言語行動(dòng)企圖勾引銀花……
傍晌天的時(shí)侯,智仁突然從石材廠回來了。當(dāng)李光元看見王智仁搖開門栓,走進(jìn)院里時(shí),由于心虛,神情不由得一陣慌亂,話語嘎然而止。
“哦,大哥在這呀!”王智仁本不覺得李光元在自己家有什么不妥,畢竟以前經(jīng)常來,但李光元臉上慌張神色讓他不免有些疑惑。
李光元甕聲地說:“嗯,在家閑著沒事干,隨便到你們這里坐坐。”
銀花急忙用話語轉(zhuǎn)移智仁的注意力,“咦,你中午一般不回家,怎么今天突然回來了?”智仁告訴她,聽天氣預(yù)報(bào)說,氣溫要下降,回來多穿件衣服。一邊說一邊再次觀查李光元的神色。此時(shí),李光元見王智仁先和氣地跟他搭腔,心里像卸下了一副千斤重?fù)?dān)那樣輕松起來。但是,盡管這樣,在智仁的兩眼瞅向他的時(shí)侯,他的目光還是不由得便左右躲閃。智仁見他這樣,心中愈加疑惑,不禁又想起了李光元五年前因拈花惹草所鬧出的一場沸沸揚(yáng)揚(yáng)的風(fēng)波。
五年前的一個(gè)初夏時(shí)節(jié),李光元應(yīng)邀去南面二十里外的大瞿家村,給一家戶主叫瞿大江的人家打一口大衣柜。把活兒接到手后,按照瞿大江夫妻對衣柜的制作要求,李光元預(yù)算了一下,最少也得六個(gè)工作日才能完工。瞿大江夫妻見他騎自行車往返奔跑,實(shí)在是勞累,又恐他為此耽誤干活,便留他食宿,直至完工。瞿大江熱情地跟李光元交待:只要活兒干得對他們心意,不算吃飯住宿的成本,起初講得多少工錢,仍給多少工錢,決不苛扣他一分一厘。不想,李光元只是嘴里表達(dá)謝意,因見瞿大江媳婦吳玉蓮長的漂亮,心里便生邪念。瞿大江天天忙著去鄰村一家石材廠上班,廠子老板為了讓工人們抓緊生產(chǎn),設(shè)有食堂,瞿大江中午不回家,到傍晚往往也是回來的很晚。吳玉蓮本來就寂寞,又因著李光元長得英俊魁梧,又不停地給她送煙、斟茶水的獻(xiàn)殷勤,又陪著他說話時(shí)間,便一時(shí)間鬼迷心竅,很快兩人便做出了丑事。
常言說:雞蛋無縫孵小雞。李光元與吳玉蓮的桃花事件不慎被鄰居發(fā)覺,鄰居便把這事傳到了瞿大江耳朵。瞿大江憤怒之下,又要跟老婆離婚,又要跟李光元拼命。后來,在親朋好友們的說合下,由李光元拿出三千塊錢,賠償了瞿大江精神損失費(fèi),這事才算了結(jié)。
一想到這,王智仁的疑心更重了。
“既然回來了,就在家吃了飯?jiān)倩厝グ伞U美畲蟾缭谶@里,我炒幾個(gè)菜,柜里有上好的‘竹葉青,你們哥倆一起喝上幾盅。”銀花見智仁那不高興的樣子,急忙想用這種方法調(diào)節(jié)他的心情。
智仁暗想:人的表情不自然,原因多去了,要是李光元心里沒有什么事,很快也就心平氣和了,如果心里有事,肯定會(huì)更不自然。于是便連連點(diǎn)頭道:“好好,多少日子沒和大哥一起喝酒了,今天湊巧大哥來了,那就一起高興高興。”
不想,李光元因懷疑自己的行為已被智仁看出破碇,急忙推辭:“不,不不!”瞅一眼銀花,然后又看著智仁,“兄弟,今天中午我家里有客人,我還得回家陪客人喝幾盅呢!”一邊說,一邊站起身來,邁步便向門外走去。
銀花喊話留他。智仁便跟出門外攔住他,“大哥,別走別走,你不是愛吃豆瓣醬燉黒魚嘛!我這就燉給你吃。”
“不不,兄弟,我家里今天真有客人。”急忙推辭。
智仁見他執(zhí)意要走,便不再勉強(qiáng)。冷不丁賂南面方向看了看天空,但見,青天白日下,南河邊他們家那棵高大的白楊樹上的喜鵲窩周圍,有兩只鳩鷹為了爭巢,與六只喜鵲左右盤旋,啄斗不休。智仁聯(lián)想起李光元從前拈花惹草的事,再想想剛才他的一舉一動(dòng),心中甚是不悅。
“怪了,李大哥今天好像不如以前那么實(shí)在了。”李光元走后,智仁對銀花說。
“你沒聽人家說家中今天有客人嘛!人家怎么不實(shí)在了?”銀花急忙解釋。
智仁暫時(shí)沒有回答銀花的話,良久便說:“看他那表情,好像有些不自然,也不知為什么。”
銀花說:“神經(jīng)病!你就能瞎尋思。”
不想,智仁卻是一個(gè)說話不善于講究策略的人,開口便說:“不對,人的眼神和說話語氣都是心靈的門戶,只要眼神和說話語氣有些不自然,心里肯定有鬼。”
“什么!”銀花一聽智仁說出這話,不覺氣得眉毛倒豎,“你今天這是怎么了?難道你懷疑自己老婆偷漢養(yǎng)漢不成?!”
“哦,哦,不是不是。”智仁急忙解釋:“對你,我是一萬個(gè)放心,我是擔(dān)心李大哥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惹你生氣。”
“瞎尋思!”銀花見智仁話語的矛頭并不是指向她,口氣稍緩和了一點(diǎn),“人家李大哥雖然以前為作風(fēng)問題鬧過亂子,可是,近些年不是變好了么嘛!再說啦,有關(guān)他那回事,不過就是傳說罷了,說不定人家根本就沒有那么回事。”
原來,自從經(jīng)過五年前那場風(fēng)波后,李光元吃夠了苦頭,出外辦事便開始小心謹(jǐn)慎起來,每逢與女人們見面都表現(xiàn)得彬彬有禮。幾年的時(shí)間過去,他與吳玉蓮做出的那件丑事,漸漸很少有人議論了,即便有人偶爾提起這件事,眾街坊們都認(rèn)為這是謠傳。似這樣,他本來可以重新做人了。可是,只因一年前銀花求他到家制了一個(gè)碗柜,銀花每天對他熱情招待。他見銀花不僅長的漂亮,而且還是一個(gè)很容易動(dòng)情的人,便“舊病復(fù)發(fā)”。
智仁說:“什么事都難說啊!天上無云不下雨,地下無風(fēng)不起塵,既然當(dāng)時(shí)人們對他議論的那么兇,最起碼他在這方面是值得人懷疑。看表面是變好了,誰知他是真變好了,還是假變好了。”他本來不會(huì)咬文嚼字表達(dá)一些文縐縐的話語,也不知從那本戲文里學(xué)來的詞句,此時(shí)竟然用上了。
“你放屁!你。”銀花聽智仁打得比如對她有刺激意味,頓時(shí)又來火了,“叫我說你這人凡事就是肯犯疑心病,在你沒進(jìn)家的時(shí)侯,李大哥跟我談些在外見到的熱鬧事,說得正有興致,你便突然回來了。人家肯定就是怕你犯疑,這才說著說著忽然停下的。因他話語停得急了些,表情本來就會(huì)不自然一些,你可倒好,胡亂懷疑人家這事,懷疑人家那事。人家這也幫咱,那也幫咱,似你這樣懷疑法,要是讓人家看出來,不就把人家得罪了?!”
智仁見銀花氣得臉色鐵青,急忙便說:”好了好了,就算我得了疑心病便是。你壓壓火,慢慢說不行?”
銀花大聲呵斥:“不行!你這說法并不是在懷疑別人什么,純粹是不相信自己老婆,你今天不把話說明白,我跟你沒完!”
“你……”智仁剛要再跟她解釋,只聽得外面大門聲響。夫妻倆不約而同地往外看去,原來是他們夫妻倆初戀時(shí)的介紹人王大嬸來了。
王大嬸一生酷愛讀書,能言善變。進(jìn)家后,先見到銀花一臉怒容,又見智仁也是一臉生氣的表情,便問他們發(fā)生了何事。兩口子覺得王大嬸是知心人,并不隱瞞,把事情發(fā)生的原委毫不保留地跟她細(xì)說一番,然后讓王大嬸給他們夫妻評理。
王大嬸說:“依我看,你們倆光這么大動(dòng)肝火抬死杠根本沒用,還是沉下心找到事情的關(guān)健才能把事情處理好。”接著,她便面向智仁微笑著說:“先說你,作為一個(gè)男子漢,本來什么事沒發(fā)生,你用一些側(cè)面話語暗示一下媳婦,使她自己能引起注意就是了。人都說,打人不打臉,你可倒好,內(nèi)心本來想把事情處理好,卻捕風(fēng)捉影地給人亂下結(jié)論,又話語那么生硬,不管誰聽了,誰都受不了。”
智仁連連點(diǎn)著承認(rèn)自己的不是。
接著,王大嬸又對銀花說:“銀花,我看這事智仁雖然說話方式讓人難以接受,不過,他說的也不是沒有半點(diǎn)道理。你和李光元是清白的,智仁僅憑主觀猜測便亂下結(jié)論,這是他的不對。但你這個(gè)做媳婦的應(yīng)理解丈夫的心才對。”
“不,大嬸。”銀花臉色頓時(shí)又陰起來,“我已經(jīng)夠理解他了,他這純粹就是無事找事!”
王大嬸沉著地說:“不對,叫我說,人沒有一個(gè)愿無事找事的。”
“照大嬸這說法,那么,他胡亂懷疑人就是對的了。”
“這個(gè)我不是已經(jīng)批評他了嘛!”
“那,我還能有什么錯(cuò)?”銀花腦門緊皺起來。
王大嬸稍一思考,忽然問道:“銀花,你知道人在起初得病時(shí),那病毒是怎么進(jìn)入人體內(nèi)的嗎?”
“怎么進(jìn)入身體的?”銀花疑惑不解。
王大嬸說:“人啊!在得病初期,病毒大都是乘人的身體虛弱的時(shí)侯進(jìn)入人體的。而身體強(qiáng)壯的人呢,體內(nèi)的免疫力就像強(qiáng)壯的士兵那樣,給整個(gè)身體把關(guān),因此,病毒就不敢侵入。作為你來說,依我看,在思維方式與處理問題的能力方面,還須增加免疫力。”
“大嬸是提醒我真的需要對李大哥防備點(diǎn)?”銀花覺得王大嬸的話語不但含有瞧不起李光元的意味,同時(shí)也是對她人格的一種貶低。
“你別不愿聽啊,銀花。”王大嬸先溫和地提醒她一句,然后直言不諱地說:“做為李光元,以前曾因拈花惹草惹過禍,就等于精神免疫力低下的人得過病一樣,一旦周圍遇到肯犯病的環(huán)境,就很可能病情復(fù)發(fā),并且也很容易把這種病傳染給別人,咱們不得不防。”
銀花不言語,心里只是覺得王大嬸的話刺耳。
王大嬸微微一笑,“病毒的‘味道和毒性大小各不一樣,有苦的、有辣的、有咸的、有酸的、有無色無味的;有的呢?卻帶點(diǎn)甜頭。那些無色無味的和帶有甜頭的病毒自然而然便開成了偽裝的特性,它們長期圍繞在人們的身邊,讓人防不勝防。”
接著,王大嬸又說:“有些病毒潛伏期可大啦!不到把你身體摧垮,你是覺查不出來的。”
銀花心里明白王大嬸是在拐著彎兒勸她,忽然便說:“可是,人交人畢竟要講究誠心啊,人家李大哥對咱不錯(cuò),并且這幾年也再?zèng)]犯過那錯(cuò),咱不可明里接受人家的幫助,暗里卻對人家這么一個(gè)不放心,那么一個(gè)不放心,要是那樣的話,咱自己不就連做人的人格都丟了嘛!”
王大嬸說:“你做人講究誠信,這沒有錯(cuò),但你要明白:人并非個(gè)個(gè)都是圣人,畢竟還是普通道德水準(zhǔn)的人占多數(shù)。人人都可被人懷疑,人人也都可懷疑一人。他敬你們一分,你們以后可以敬他二分,這就算對他很講誠信了,不可事事對他連半點(diǎn)提防心都沒有。”
“怎么防!”銀花心里一急,“人家就是來耍耍,要是照大嬸這么說法,那就干脆跟李光元絕交算了,省得王智仁一天價(jià)瞎尋思!”
“斷絕交往倒是用不著,人家對你們不錯(cuò),你們不可就因?yàn)槿思覐那胺高^錯(cuò)便跟人家絕交。不過,你在日常跟他見面時(shí),還是提防著他點(diǎn)為好。比方說,你發(fā)現(xiàn)他跟你說話特別激動(dòng)時(shí),而這種激動(dòng)恰恰又有些不自然,你滿可以說些別的話語把話題岔開,或找個(gè)恰當(dāng)借口起身干點(diǎn)別事,以此轉(zhuǎn)移一下對方的思路,不然的話,他一時(shí)激動(dòng),扯扯拉拉的,場面就不好修拾了。真到了那一步,對誰都沒有好處。”
“這……大嬸言重了。”銀花覺得王大嬸說話除了比智仁藝術(shù)性巧妙以外,同樣是對她不放心。越聽越心犯,因覺得王大嬸是好意勸她,怕說話生硬傷了感情,忽然改變說話口氣,“那,照大嬸的說法,容易做錯(cuò)事的人又該如何增加免疫力呢?”
王大嬸說:“兩個(gè)途徑,一是平日多向一些德才兼?zhèn)涞娜藢W(xué)習(xí),二就是需要多看書,通過吸取書中人物的間接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來提高自己處世為人的能力。”
王大嬸歷來對李光元看法不好。接著,她便又細(xì)心跟銀花講解具體如何防范李光元的一些細(xì)節(jié)做法,銀花表面點(diǎn)頭贊成,而內(nèi)心里卻一直是毫不服氣。
三
李光元不愧是一只狡猾的狐貍。
對于他想得到銀花這種心底,就好比黃鼠狼想吃到雞一樣的盼望,而對于他這個(gè)機(jī)警程度,恰似這條黃鼠狼偷雞時(shí)躲避人的那種心態(tài),一時(shí)一刻都不想讓人覺查到;自從那天對銀花想入非非被智仁看出破碇后,他便放慢了陰謀得到銀花的腳步。他打定了主意:必須琢磨透這只雞的抵抗能力及主人家的一切防范情況,瞅準(zhǔn)時(shí)機(jī)方可下手。
時(shí)光易過。隨著陣陣的雁鳴,節(jié)氣很快到了驚蟄以后,溫暖的陽光天天普照大地。眾鄉(xiāng)親們有的用牲口或拖拉機(jī)忙著耕地;有的抗著锨镢到自己地里挖堰下渠;有的忙著用各式各樣的車輛往地里拉土糞,還有的在自己承包的果園里給果樹剪枝整樹型;菜園里,已有人忙著種大蒜,育白菜種和羅卜種,還有人在用竹鈀清理菜畦子等等。眾多景象綜合在一起,繪制成一幅幅繁榮昌盛的畫面。然而,李光元的心里卻并不繁榮昌盛,他一直都不出遠(yuǎn)門,天天只是待在家中干那些已接原料在手的零星木匠活,耐心等待再次與銀花談話的機(jī)會(huì)。他老婆張立菊見他一天價(jià)神情不自然,又突然間不再出遠(yuǎn)門,對他疑心重重。
常言說,無巧不成書。這天,智仁逢休班日。中午,有人喊他到街上打撲克,他便興奮地出來跟大家湊湊。因李光元門口寬敞,大家恰恰聚集在那里。撲克打到興頭上,智仁興奮地不由得身體左右晃動(dòng),不想,因坐下的馬扎上面襻著的塑料繩已變質(zhì),不慎一屁股跌落在硬地面上,疼得他“哇呀”叫了兩聲。眾人哄然一陣大笑,隨后有牌友便說,“咦,咦咦,正好這兒有木匠,讓光元回家再拿個(gè)小凳或馬扎給你坐著,把這個(gè)破的讓他取回家給你修修便是。”
而此時(shí)的智仁,自從王大嬸勸說他看問題不可亂下結(jié)論那天起,他改正了遇事捕風(fēng)捉影的缺點(diǎn)。然而,他又適得其反,對李光元言行舉止竟然又粗心大意起來,因見李光元多日再?zèng)]有去他們家單獨(dú)找銀花聊天,心中那份防范心早已消散在九霄云外。
就在智仁以求助的眼神看著李光元的同時(shí),李光元也含笑地看著他,智仁便毫不猶豫地說:“好,好好,大哥,你就給我把這破馬扎修修吧。”
李光元見智仁對他失去了防范心,心里不覺一動(dòng),“嗬,這倒是一個(gè)最能促使我與銀花再相會(huì)的機(jī)會(huì)!”急忙上前扶起智仁,然后提著破馬扎便回家去。一會(huì)兒,便從家中取出一個(gè)新馬扎讓智仁坐著繼續(xù)打撲克。他便又轉(zhuǎn)回家修整那個(gè)破馬扎去了。
智仁因李光元給他修好了馬扎,心里不過意,到晚上,便請李光元到家喝幾盅。李光元故意裝作反復(fù)推辭,最后見智仁執(zhí)意相請,便就去了。從這天開始,李光元有時(shí)侯借口到智仁家借東西用,有時(shí)侯便裝做有事要與智仁倆口子商量,隔不上三五天便會(huì)到智仁家去一次。有時(shí)侯去時(shí)還隨手帶瓶好酒或好吃的禮物。智仁夫妻熱情相待。
晴明節(jié)將至。
在膠東半島這個(gè)地方,每逢晴明節(jié)前后十幾天內(nèi),半大孩子們都有個(gè)打秋千的風(fēng)俗習(xí)慣。頭著晴明節(jié)五天,小強(qiáng)便哼鬧著非讓智仁給他吊個(gè)秋千架子不可。不想,智仁平日干一些出大力的活還頂用,要是讓他干一些需要巧門的活,卻是個(gè)外行。小強(qiáng)反復(fù)哼鬧,智仁只是不理不睬。吃罷早飯,垮上自行車便上班去了。小強(qiáng)看了看銀花,哼鬧著說:“媽,要不,你給我吊嘛!你給我吊嘛!”此時(shí),銀花早已把王大嬸囑咐她的話忘的一干二凈,立即便說:“我不會(huì)吊,你快去村北頭把你光元大爺找來,他肯定能給你吊起個(gè)好秋千。”
一會(huì)兒,小強(qiáng)去把李光元找來,便上學(xué)去了。
秋千很快便吊好,銀花取臉盆盛了半盆水讓李光元洗罷手,李光元便要告辭回家。銀花忽然覺得麻煩他一頓,讓他空手走了實(shí)在是不好意思,想想他是個(gè)木匠,平日里給人干活有時(shí)侯是按日工論工錢的,于是便說:“大哥別急著走,你給我干活,我不能白用你,就按你平日給別人干木匠活的工日給你錢便是。”說著,便迅速走向衣柜邊,要到衣柜里取錢。李光元急忙上前攔住,“別別,別,這是誰跟誰呀!我就給你們干這么點(diǎn)話,你還要給我錢,這不是見外了嘛!”銀花硬是要取錢,他用手拽住銀花的胳膊就是不讓她取。銀花無奈,只得做罷,忽然想起李光元喜歡喝酒,便說:“大哥實(shí)在不收錢,我也沒法,今日天氣有些冷,要不我倒點(diǎn)酒,你喝點(diǎn)酒暖和暖和再走吧。”李光元點(diǎn)了一下頭,“嗯 ,喝盅酒還可以。”
銀花把飯桌放倒,取馬扎讓李光元坐在飯桌前歇著。然后取炒瓢到煤氣罐上炒了兩個(gè)菜,又從碗柜上取下一瓶煙臺(tái)古釀,斟滿了一盅酒,恭敬地端到李光元面前。這時(shí),李光元喝了一口酒,又吃了一口菜,然后貪婪地看一眼銀花的臉,嘻皮笑臉地說:“嘻嘻!妹子不但炒的菜可口,干起活來也麻利,炒兩個(gè)菜半點(diǎn)都不費(fèi)事的樣子。”
銀花便說:“大哥又夸我了,炒菜這樣話,誰都會(huì)干,這算不了什么。”
李光元急忙說:“不,不不,妹子不管干什么活倒就是比一般家庭婦女干得又好又快。”
銀花耳朵里聽著,心里一陣喜悅。便取個(gè)小凳坐在李光元對面,準(zhǔn)備隨時(shí)給他斟酒,李光元又奉承道:“妹子想事真周到啊!還能想到天冷讓大哥喝幾盅酒再走。”
銀花不好意思地說:“這樣小事大哥別掛在嘴上,您不是給我們干過活嘛!這都是我應(yīng)該做的。”
“那,你既然覺得關(guān)心大哥是應(yīng)該的,我給妹子干點(diǎn)活,自然也是應(yīng)該的嘍!”李光元聽罷銀花的話,愈加裝做通情達(dá)理的樣子,
銀花不由得心中躍過一個(gè)念頭:這個(gè)李大哥,倒是一個(gè)與人處事很寬容的人,給我們干了半天活,就給他喝幾盅酒,他便是那樣的滿足。”
李光元的兩眼在銀花身上上下打量,忽然看到銀花的腳上穿著一雙白色的力士鞋,那鞋的前頭已打上了補(bǔ)丁。李光元便問道:“妹子,你現(xiàn)在腳上穿的鞋就是用來平日干活和在家時(shí)穿的吧?”
銀花聽李光元這么問,不由得看了看他的腳,他腳上穿著一雙晶光油亮的純牛皮鞋,不覺一種自卑感瞬間襲上心頭。
“不是,我每到春秋季節(jié)里里外外就穿這一雙鞋。”
“我可不敢跟大哥相比,穿黒油亮的牛皮鞋。”
“妹子喜歡皮鞋?喜歡不要緊,可以買雙嘛 !”李光元試探地說。
“咱可穿不起。皮鞋都是像您這樣有錢人穿的。”銀花說著,差點(diǎn)沒流下淚來。
李光元急忙便說:“這有何難!你要是想買,我借錢給你。”
“真的?”
“真的。”
“快算了吧,以前欠你情已經(jīng)不少了,即使你給我借錢買上皮鞋,我不知猴年馬月才能還你,也是不好辦。”銀花臉上顯現(xiàn)出難為情的樣子。
李光元毫不猶豫地說:“嗨,妹子,還不起錢不要緊,什么時(shí)侯有了錢,什么時(shí)侯便還。一輩子沒有,就一輩子不用還。”說著,他想了想,兜里正好裝有四百塊錢,急忙把錢掏出來,“吶,妹子,這四百塊錢你拿去買皮鞋用。”“啪!”地一下把錢放在了飯桌邊。
銀花兩眼看著錢,心里想取,但卻又不好意思取,囁嚅地說:“俺不要。”
李光元急忙取錢在手,站起身轉(zhuǎn)過飯桌,硬給銀花塞進(jìn)衣兜里,“拿著,拿著,別見外嘛!”說著,便又夸銀花能奔操過日子,她與智仁至今未發(fā)家,只不過屬于時(shí)運(yùn)不佳而已。被他這一夸,銀花便陷入了沉思,竟然怨起自己命苦來了。她想起智仁一天價(jià)只能憑出大力掙有數(shù)的幾個(gè)錢,而李光元平均干一天的木匠活,至少也掙智仁三倍的錢;并且,相比之下,智仁干點(diǎn)別的話也遠(yuǎn)不如李光元手巧;論說話,又比不上李大哥會(huì)說。就在這暗暗埋怨自己命苦的節(jié)骨眼上,不知不覺,她心里竟然真的對李光元盟動(dòng)了愛睦之心……
她不覺全身的熱血沸騰起來,忽然又想起自己家還欠李光元兩千塊錢,可是,人家李光元不但不急著討債,還不斷地零碎幫自己一家人的忙,似這樣的善良人實(shí)在是世上少有!不覺暗暗自語:看來,那些愿傳話的人就是嘴癢,這個(gè)說人家拈花惹草,那個(gè)說人家拈花惹草,似這樣的好心人肯定是那些作風(fēng)不好的女人先對他動(dòng)了心,事情敗露后,因丟不起那個(gè)面子,又惹不起自己男人,最后翻過臉來陷害他便是……
她怕再多想會(huì)失態(tài),急忙操起酒瓶給李光元斟酒。而就在她伸出右手到桌子邊操酒瓶的時(shí)侯,肩部一陣酸痛,她急忙伸左手把酒瓶操過來,然后給李光元斟酒。這時(shí),李光元便問:“妹子,你的右胳膊怎么了?怎么看你取酒瓶時(shí)很像是疼痛樣子?”
銀花說:“不是胳膊的事,我是最近有點(diǎn)肩周炎。”
李光元說:“嗨!妹子,你怎么不早說呢,一會(huì)兒我給你揉搓揉搓。”
銀花聽他這么說,不由得心里一緊張,可是,剎那間又覺得有些好奇,“那,大哥在外面還學(xué)會(huì)了醫(yī)學(xué)按摩?”
李光元說:“當(dāng)然,我從前年就學(xué)會(huì)了這門手藝,只是在自己村沒給人按摩過罷了。”銀花想了想,沒應(yīng)他的聲。
李光元把酒喝足了,銀花便拾掇碗筷和酒瓶。就在她把那剰下的半瓶酒往碗柜上放的時(shí)侯,因碗柜高了點(diǎn),她剛用右手往上放,一抬胳膊,又覺得疼,急忙換左手放了上去。李光元這時(shí)便說:“哎呀!妹子,你就別不好意思了,一會(huì)兒還是用我給你理一理吧。緩解一下,說不定慢慢就好了。”
“昂,那就試試吧。”銀花羞澀地答應(yīng)下來。說著,便向院里大門那邊瞟了一眼。李光元急忙奔到院里把大門關(guān)嚴(yán),然后把大門的插拴“哐”的一聲插上了。
李光元也的確在外面跟別人學(xué)過按摩術(shù)。銀花躺在床上,任他先慢慢揉搓頸椎和肩部,銀花頓時(shí)感到被揉搓的部位輕松得很,一會(huì)兒,李光元便把雙手慢慢往下移動(dòng),本來是一只魔掌,而此時(shí)的銀花,反覺得這只手不管觸摸到她身體的任何部位,對她都是那樣的溫存。魔掌漸漸地觸摸到銀花的胸部,她本能地用兩手一推,“大哥,你……”
李光元瞇著色眼看著她,忽然張開雙臂,一下子撲到她的身上,嘻皮笑臉,“嘿嘿,嘿嘿,你們欠的我那兩千塊錢,我不要了。你們欠我的那兩千塊錢我不要了……”
銀花嘴里念叨著:“大哥別這樣,大哥別這樣……”全身卻飄飄然,連半點(diǎn)反抗能力都沒有了。那張美麗的蘋果臉蛋不由不忍地向李光元的胸前依偎過去……
四
屋子里的氣氛有些肅然起來。天花板木著臉,墻壁顯現(xiàn)出疑惑的神色,四下里的一切器俱似乎也都顯露出質(zhì)疑的目光……
李光元走后,銀花想想智仁為這個(gè)家庭日夜奔波,并且對她也一直不錯(cuò),再想想以往自己曾對智仁立過的那些海誓山盟,心里不覺為自己的失貞有些悔意。良心這個(gè)無形的評判員在遣責(zé)她。可是,與此同時(shí),心中那份欲望天性無時(shí)無刻又在誘惑著她,她沉思默想一會(huì)兒,她把心一橫,便自我安慰起來:沒什么的,只要把這件事絕密,平日再對智仁加倍關(guān)心一點(diǎn),自然也就問心無愧,身體是自己的,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呢!
日子一天天的過去,李光元每隔六七天便到銀花家揉躪銀花一次。銀花呢?也便糊涂地接受他。她還教李光元,以后凡是她在他身邊的時(shí)侯,言語表情都要裝得自然一些,李光元點(diǎn)頭稱是。于是,在沒有外人知曉的情況下,二人都覺得這種做法是一種幸福。然而,他們之間畢竟沒有純潔的思想意識方面的溝通,性欲就像小孩子們盼望吃順口的食物一樣,吃了后,便就不再如饑似渴地追求了。漸漸地,在李光元眼里,銀花并非和從前那樣美了,銀花的言行,也不如從前那樣高妙了,他不禁暗暗自嘆:唉!在沒得到她時(shí),時(shí)時(shí)都覺得她是那樣的美,原來,她也是很普通的嘛!此時(shí)此刻,他想起自己從前對銀花一家人有求必應(yīng),不免有些后悔起來:咳,自己真是傻呀!就玩?zhèn)€女人,根本不值得破費(fèi)那么大!他想起銀花家還欠他兩千塊錢的事,忽然一個(gè)鬼主意繞過心頭:“嘿,乘她現(xiàn)在跟我熱乎,她欠我兩千,我便找借口向她也借兩千,如此,我一直不還她,不就兩來無事了嘛!”
時(shí)正值1999年的時(shí)侯,在農(nóng)村,鄉(xiāng)親們除了大面積的農(nóng)活利用機(jī)械化操作外,有些小小的零碎活,還是需要牲口。大約是谷雨前后,忽然一天,李光元家的牛得病死了,到中午,便匆匆來到銀花家中,裝作很為難地說:
“壞了,銀花,我家的牛死了,打算再買一頭。你看看能不能暫時(shí)給我搗借兩千塊錢用?待我手頭寬綽了,白給你多少都可以。”
銀花笑著說:“嘿,和大哥這樣富戶,銀行里存款有的是,你到銀行里取出幾千便是,這樣小事何須求我呢?”
李光元說:“銀行里有錢不假,可是,我都存的死期存單,要是取出來,要是不到期便取,把利息都瞎了。”
銀花一聽是這情況,替他著急起來。立即應(yīng)聲說要到銀行取錢還他。其實(shí),她家里和銀行里都沒有錢,打發(fā)李光元走后,去二十里外的大姐家借得兩千塊錢,還給了他。
太陽公公躲進(jìn)云層里了,涼風(fēng)習(xí)習(xí)。
這天上午,天氣突變,已是陰歷四月初的時(shí)節(jié)了,氣溫驟然下降到零度左右。李光元隔了十幾天沒和銀花相會(huì),便又去銀花家找銀花了。
銀花見李光元走進(jìn)院里,心里一熱,什么話沒說,身子一轉(zhuǎn),把他引進(jìn)了里間。
“大哥最近好吧?”
“我很好,你也好吧……”
二人說著話便相互親吻,然后,脫衣解帶便抱在了一起。
就在這個(gè)時(shí)侯,忽然有人大喊:“干什么!干什么!”二人慌得魂飛魄散,抬頭定神一看,竟是張立菊站到了面前。
原來,李光元和銀花都大意了,銀花忘了囑咐李光元,李光元也粗心了,進(jìn)屋時(shí)竟然忘了插上院門。
李光元提上褲子便溜出門外走了。還沒等銀花靜下神來,張立菊大聲罵道:“你個(gè)不要臉的騷貨,你該死了你!”上前抓住銀花的頭發(fā),連撕帶打。銀花不服地說:“你打誰!你打誰!這事是你們李光元來找我的,可不是我找他的,你要管先管好自己男人!”說著便還手也撕打張立菊,兩個(gè)女人相互撕打在一起。
撕打了一會(huì)兒,兩個(gè)人都累了,不知不覺都松了手。張立菊氣喘吁吁往外走,一邊走,一邊倒回頭來說:“你等著,你個(gè)死X!今天來教訓(xùn)你這是輕的,等我回去向李光元問明白情況后再說,看看這事要是屬于你先勾搭他的,我還得揍你!”
銀花大聲罵道:“你放屁!你放屁!”忽然覺得張立菊來得這么突然,很似他們夫妻設(shè)計(jì)害她,明明知道 這種可能性不大,也隨口混淆起來:“你們兩口子設(shè)計(jì)陷害我,我還要去法院告你們呢!”
張立菊走后,銀花坐在床邊流下淚來,越想越覺得自己挨這這頓打窩囊,抽咽了一會(huì)兒,忽然心想:“不行,決不能讓這個(gè)瘋老婆這么猖狂,我必須給李光元點(diǎn)壓力,到時(shí)侯,李光元向瘋婆子下跪,你個(gè)瘋婆子看在自己男人面上,還得向我求饒呢!”想罷,她立即到床頭操起電話機(jī)筒便給李光元打電話。那邊李光元接通了電話。
“喂,銀花,真對不起,誰也沒想到事情會(huì)鬧到這一步。”
“你不用多說,李光元,說不定就是你和老婆做了這么個(gè)扣子害我呢,我不能讓你!”
“別別別,銀花,咱們有話慢慢說。”聽李光元說話的口氣是想繼續(xù)和她保持那種關(guān)系。
只聽得話筒里“噗!”“噗!”連續(xù)兩聲響,隨即便聽到張立菊大罵:“你該死了,你!事到這般地步你還和她柔聲和氣的。”不用分析,那噗噗的兩聲響顯然就是張立菊踢了李光元兩腳,銀花心里猜測著,那邊的的電話機(jī)“嘩啦”一聲,電話便掛斷了。
過了大約一個(gè)鐘頭,銀花又給李光元掛電話,逢巧,她這次掛電話,張立菊不知干什么去了,還是李光元接電話。銀花怒氣沖沖地說:“李光元,既然你老婆對我這么兇,你得趕緊還我那兩千塊錢,昂!不然我跟你沒完。”不想,李光元在老婆的嚴(yán)歷管制下,終于變了良心,把口一改,“銀花,你忘了嗎?你們以前還欠我兩千塊呢,如此咱們就誰也不欠誰的了。”
“啊!你不是說那兩千塊錢是給我們了么!你……”還沒等銀花把話說完,李光元“嘩”地一聲又把電話掛斷了。
“騙子!”銀花怒罵一聲,不覺頭暈?zāi)垦#鹤约褐愿迷诹艘黄穑窍氲玫剿恼嫘南鄲郏y道就為了圖他用小恩小惠欺騙然后任意糟蹋靈魂么!她一下子斜倒在電話機(jī)邊,放聲大哭。一邊哭,一邊暗暗發(fā)誓:“你等著,李光元,我會(huì)雇人把你們倆口子修拾個(gè)半死!”然而,發(fā)誓歸發(fā)誓,她心里卻明白,架并不是那么好打的。且不提雙方打起來誰勝誰負(fù)的問題,不管誰受了重傷,都會(huì)惹起官司。官司一起,自己受到法律制裁就更不合算了。一會(huì)兒,她停止了哭聲,開始沉思默想,一計(jì)不成,又生一計(jì),便決定違著良心把事件的真實(shí)情況胡亂一編,告李光元一個(gè)強(qiáng)暴婦女罪,可是,想想當(dāng)時(shí)都是自己同意的,真論起法律來,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想用這個(gè)辦法報(bào)復(fù)他們倆口子,那也是很愚蠢的呀!左思右想,她沒了主意,只有在那里生悶氣。失身丟面子倒也罷了,問題是自己覺得小腦瓜并不笨,卻讓別人當(dāng)傻子耍了,只這些還不算,還得受張立菊那瘋婆娘的氣。似這樣的人活著還有什么意思呢?忽見北墻上掛著一卷備用的如小指那么粗細(xì)的尼龍繩子,她下地摸起那根繩子,想想未曾裝修的西里間露著梁,操著繩子便進(jìn)去上吊。她把繩子的一端打到了梁上系緊,然后取了個(gè)板凳,雙腳踏上去,把繩子剩余的一端系了個(gè)圓扣子,正要往里伸脖子,忽聽的有人大喊:“混賬!”喊聲未絕,一腳給她把凳子踢翻。她一下子癱坐在地上。定神看了看,是王大嬸救了她。
原來,王大嬸是聞?dòng)嵑筇匾廒s來救她的。王大嬸把她攙扶出里間,讓她在床上坐好,便開始勸說她:
“你看看你,我以前勸你對李光元這樣人要多加小心,你當(dāng)時(shí)答應(yīng)得好好的,可是內(nèi)心里就是不聽,事到于今果然把事鬧大了。”
“既然事情已到了這般地步,你不為自己著想,也得為智仁和小強(qiáng)想想啊,你一死了之倒也輕松,撇下他們倆個(gè),這以后的日子怎么有法過!還有你和智仁雙方的父母,你這一死,不能為他們養(yǎng)老,可是大不孝哇!”
銀花聽罷,一頭倒在王大嬸懷里“嗚嗚”的便哭出聲來。
接著,王大嬸便勸說她:人生在世,畢竟是各人有各人的長處。但不管是誰,長處再多,要是心緒不正,這種長處往往就會(huì)釀成惹禍的根苗,要是心底善良,即便長處不多,也同樣值得人們尊敬。別的不足,通過夫妻間相互包容,取長補(bǔ)短,終久會(huì)得到解決的。所謂真正的生活要靠自己去創(chuàng)造,正是這個(gè)道理。又給她講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過日子經(jīng)驗(yàn),等等, 等等。在王大嬸 反復(fù)勸說下,銀花終于想開了,立誓以后改正自己的錯(cuò)誤,重做新人。
王大嬸見銀花已想開了,心中這才松了一口氣。然而,她心里終還是有些不快,雖然銀花的人命已得救,但畢竟還是因未能深通人情事理而犯下了大錯(cuò),再想想李光元的無德,張立菊的庸俗無智。再想想智仁的粗心大意,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來說去就是一句話,這些人還是缺乏思想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