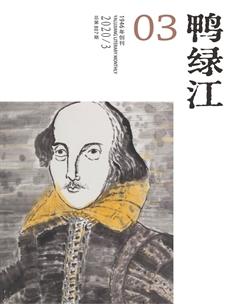母親是我心中一盞明燈
我的母親是一位軍醫,外祖父給她起個男孩的名字,叫陳傳鏗。
我出生在北國冰封的哈爾濱,在軍營里度過快樂的童年。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母親隨父親轉業回廣東,他們毅然放棄安排廣州優越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主動選擇到雷州半島支邊。經過40小時的長途奔波后,我們到達徐聞縣錦和公社衛生院,前來迎接我們全家的,是一輛牛車和漫天的紅土……
母親在福州長大,福州話和雷州話同是閩南語系的方言,母親完全融進了雷州半島的群眾中。她頭戴著竹笠,身背著“紅十字”藥箱走遍錦和的每條村莊,一切就像當年電影《春苗》中的女赤腳醫生一樣,表現出一名醫生真情奉獻,一名共產黨員的執著和堅持。
在錦和衛生院從醫5年,母親腦里總是想著病人,心里總是惦記著病人。家務都由我這個屁大毛孩撐著,有時她連自己的生日也給忘了,而母親對子女的關愛和教育都處理得有條有理。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公社有了農村合作醫療,醫務人員在缺醫少藥的情況下,24小時值班候命,一旦發生病情背著藥箱就跑。有一次,紅星大隊合作醫療站王醫生請母親出診,她們一路小跑10多里趕到病人家里。母親在條件差的情況下,給病人做了人工呼吸,為病人口對口用力吸痰十分鐘,然后對癥用藥,由于搶救及時,這位呼吸衰竭病人脫離了生命危險。當時,病人的女兒抱頭伏在我母親的肩膀上,流著眼淚說:“陳醫生,你是我媽媽的救命恩人!”
母親曾在前山衛生院工作了五年,全家居住20多平方米舊瓦房,屋頂舊瓦,一下雨就漏,老鼠、蟑螂橫行霸道,大蜈蚣爬進家里很嚇人。在那個艱辛歲月里,母親把青春奉獻鄉村衛生事業。前山南安村許大叔家人一有急病都找母親治療,有時他沒有錢買藥,母親就自先墊著,等他家里有錢再補交。
曾家村有位姓楊的胃病患者,到處尋醫問藥,花了一萬多元,因病致貧,病情越來越重,每次發病痛得死去活來。當母親知道他的病情和家庭窘況后,就經常上門為他看病,送醫送藥,免費針灸治療。有一年大年三十晚,我們全家正在吃團圓飯,楊的兒子找上門說他父親胃病發作,病情特別嚴重。母親二話不說,冒著嚴寒到了楊家,為病人打針開藥。
母親的醫術醫德在錦和、前山一帶出了名,一提到“陳傳鏗”這個名字,群眾都異口同聲稱贊。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母親離開前山時,鄉親們捎來甘蔗、雞、鴨、花生油送她,母親硬是不要,鄉親們執拗要表達對她的真情和敬意。
母親從前山衛生院調到和安衛生院工作。那年的大年除夕,母親上班,8歲的弟弟沒人照管,弟弟在衛生院后的山溝玩耍時,被山溝的陡坡土丘掩埋。失去小兒子之后,母親加倍疼惜群眾因病無錢醫治的小孩,在基層衛生院工作20多年來,她自己掏錢救治了10多個病孩,從死亡線上救活了近10個小孩。有一次,和安村一位群眾抱著一個奄奄一息的小孩來到衛生院,經醫院全力搶救后確認無指望了,這位群眾丟下小孩傷心地回家。母親依然不甘心,她大膽地采用自己學過的知識和經驗,給小孩加壓和輸氧,全身按摩,終于,把這個小孩從死神的手里奪回來。她將救活的小孩帶回家中調養和護理,直至小孩完全康復。當那位父親見到自己死而復生的孩子時,感激的熱淚奪眶而出。
1984年,母親調到縣防疫站,由于母親醫術精湛,每天慕名而來找她看病的病人很多,她每天接診城鄉病人達幾十例甚至上百例,她的門診給縣防疫站帶來很大比例的收入,但她從不計較報酬,也從不隨便向組織伸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母親退休時,一些朋友想借母親的名氣與醫術開私人診所,但她卻答應領導懇求返聘,繼續留縣防疫站工作。
1996年的一天,母親積勞成疾,突然病倒在門診的工作臺上,醫院診斷她患上了胃賁門癌(晚期),她被施行了胃全切除手術。手術后第二天她醒來,他拉著我的手說:“孩子啊,我怕是不行了,你回去幫媽媽交完這個月的黨費吧!”
聽完她的話后,在場的人都哭了……
母親從醫幾十年,從部隊到地方,穿過的白大褂不知有多少件,舊了、黃了,但在人們心中,白大褂永遠只有一件,清白、溫暖、貼心。
母親雖然離開了我們,但她永遠是我心中的一盞明燈。
作者簡介:
李青,廣東徐聞作協副主席,湛江市作協會員,湛江市政協文史專員,嶺南師范學院雷陽文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西部散文學會會員。
籍貫廣東梅州,出生于黑龍江哈爾濱,原執業醫師,國家公務員,業余創作。作品散見于《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南方日報》《海南日報》《西部散文選刊》《湛江日報》等報刊,多篇散文入選國家級出版社散文作品集,在全國征文大賽中獲獎十余次,出版文學作品集《從北國到大陸之南》《踏著月亮回家》。現為《作家文苑》首席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