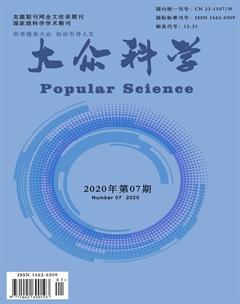中國的伊斯蘭教建筑演變概況
莊逸清
摘 要:中國作為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歷史的國度,以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對多元化的世界。歐洲建筑、伊斯蘭建筑、中國建筑體系并稱世界三大建筑體系,中國也吸收其他建筑風格的精華,與自身建筑特點相結合,形成具有獨特美感的建筑形態。本文將從清真寺的產生,伊斯蘭建筑在中國的發源寫起,以演變、結合為主體,總結伊斯蘭風格建筑在中國的變遷。
關鍵詞:伊斯蘭建筑;結合中式風格;變遷
一、清真寺建筑的出現及演變
清真寺建筑的基本形態和布局原則,是根據伊斯蘭教不斷發展,逐步確定下來的。
伊斯蘭教傳說中最古老的清真寺,是麥加的“天房”。位于麥加城中心,原名克爾白或卡巴(kabah),系一立方體的石砌房屋,是阿拉伯古代遺傳下來的一處宗教信仰圣地。
穆罕默德傳教初期,并未修筑清真寺,禮拜時只要選擇一塊干凈的地方,能夠俯首叩拜即可。這種地方成為“買斯志德”。當穆罕默德由麥加遷到麥地那后,就非常需要一個進行宗教活動的中心,建筑清真寺就顯現出重要地位。公元622年在麥地那他的住處,修建了第一所清真寺,這就是著名的先知寺。這座清真寺十分簡樸,是四周邊長約50米的一個院落,圍墻高約3.5米,用土坯砌筑。東部有穆罕默德及其親屬的住房,北部建有用樹干排列的柱廊(因穆罕默德創教初期,將朝拜的地方定在耶路撒冷),上覆以簡單的頂棚,為禮拜時不被日曬。寬闊的中庭和做禮拜的柱廊作為最基本的條件,在清真寺的布局形制中,被首先確立下來。與公元624年,穆罕默德又將朝拜方向改為麥加克爾白,從此世界所有穆斯林,叩拜對準麥加方向成為一條重要法則。因此,將柱廊位置改建到南側。
公元707年,重建先知寺,為進一步明確朝拜方向,在吉布拉壁面上設置了一座神龕(mihrab),自此,神龕成為指明方向的重要標志。[1]
在清真寺建筑中,都有一座或數座高高的塔,稱宣禮塔(minaret),又有叫拜樓、喚醒樓、邦克樓等名稱。本是為了召喚教民來禮拜用的。因晚間還有點燈做標志的功能,所以又稱其值更樓。
上述說明了伊斯蘭教清真寺建造的布局和發展。即一座清真寺,無論大小,都是在建筑基地上環以圍墻,沿吉布拉的壁面排列數行柱廊,上覆以屋頂,在壁面設神龕,并在其近旁安放宣諭臺,再以宣禮塔組合而成。中庭的其余三個方向,一般也建柱廊,或布置成其他輔助房間。
二、伊斯蘭教傳入中國
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首次遣使來長安,作為伊斯蘭教正式傳入我國的開端。
唐朝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與阿拉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文化最發達的兩個國家。國力強盛,社會、人民的包容成為了兩國建交的基礎。貿易往來由“兩路”為主導。“絲綢之路”,將絲綢、茶葉、瓷器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物品送往阿拉伯及各大洲;根據“香料之路”收獲許多未曾見過的香料等各種具有各國特色的物件。當然,中國的四大發明也通過這兩條道路游歷世界各地。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海上貿易的進行,不少阿拉伯商人居住在中國的沿海口岸廣州、泉州等地,為了其信仰及傳教的需要,建立起了中國最早的清真寺。而廣州懷圣寺則是最早建立的清真寺之一。這座始建于唐朝的清真寺由阿拉伯人主持修建,雖有當時中國人民的資助,但風格遵循傳統阿拉伯式建筑。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光塔(宣禮塔)則是證明。高36.3米磚結構分上下兩段,上段高約為下段的三分之一,有明顯收分。塔下有前后二門,內有雙螺旋形梯級,可拾級而上,塔身表面抹灰,無任何裝飾。塔頂原置有金雞,可隨風旋轉,以測風向,后為颶風所墜,遂該為今狀的葫蘆形寶頂,塔身的基本形制沒有變。[2]這與中國傳統的木構架體系是完全不同的,且其平面布局不強調對稱。
這一時期,雖有部分民眾信仰伊斯蘭教,但人數并不多,故尚未形成一個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
三、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
宋朝是伊斯蘭教在中國過渡發展的時期。從當朝者擴大中阿貿易往來為開端,允許漢人與阿拉伯人通婚為過渡,以阿拉伯商人資助修筑泉州城為高潮。
兩宋時期,由于當時中國西北部常有戰亂,故阿拉伯、波斯商人經海路來華,從而使我國南方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由于來華商人眾多,且多聚集在廣州、泉州、杭州等地,故于唐、宋兩朝,在沿岸商業城市,專為阿拉伯、波斯商人撥地,為其提供集居之處,稱“蕃坊”;并于其中設立“都蕃長”(宋時稱“蕃長”),且由他們自己推舉有聲望者擔任,并由中國政府允許。蕃坊內設居住區、清真寺、店鋪、市場、蕃學等基礎設施,便利其生活。
此時的清真寺建筑以泉州圣友寺為代表,雖曾修葺過,但主要結構和形態還是完全的阿拉伯風格,以石砌筑,并沒有中國傳統建筑的色彩。
唐宋兩朝的清真寺建筑雖沒有與中國建筑藝術相結合,但其頗具特色的阿拉伯風格吸引著中國建筑設計師。中式伊斯蘭建筑的種子便由此時播下。
四、中國的伊斯蘭教建筑開篇
在唐、宋兩朝的鋪墊、整合下,元朝初步形成中國的伊斯蘭教建筑雛形已是蓄勢待發。再加上元朝軍事力量的強悍,先后征服多個地區,并有大批中亞、西亞的各族人民被遷徙到東方來,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波斯人民的到來,更是為形成中國的伊斯蘭教建筑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
來到東方的中、西亞人民,多以聚居形式從事農業生產,久而久之,他們適應了環境,安心定居,并接受了“回回”這個稱號,且原來在回回之間的不同民族的界限也逐步消失,形成“元時回回大盛”的局面。
元朝統治者給予歸附者較好的政治待遇,使其擔任一定官職。在中西交通暢通無阻的條件下,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回回商人來華經商的規模比唐宋更盛。足跡遍布全國、子孫繁衍,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族、漢族人數日漸增加,成為中國形成回族的一個重要因素。前期定居與后期進入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商人多以大分散小集中的聚居形式在水路便利之處居住,共同的心里狀態、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將他們聯系起來,推動中國回族的形成。
伴隨中國信仰伊斯蘭教人數的增加,元朝時回族雛形形成。這一時期的伊斯蘭教建筑,其規模和數量也隨之增加。建筑形態以杭州鳳凰寺(真教寺)為例:后窯殿多用磚砌圓拱頂做法,即是仿照阿拉伯清真寺圓拱頂技藝。由三間磚砌圓拱連成一橫長方形,為磚結構無梁殿頂。四壁上端轉角作菱角牙子疊澀收縮,上覆三個半球形穹窿頂,外觀作三個攢尖頂,中間一個八角檐,左右均為六角單檐,屋頂作法是明顯的中國傳統建筑和西亞伊斯蘭教建筑相互融合的特色。[3]
五、中國的伊斯蘭教建筑發展
明朝統治者,對各種宗教信仰給予一定重視,特別對回族,給予其與漢族相同的政治待遇,這是由于初建明朝時,回族人民參加了反元大起義,對明朝建立有功勞。且那時回族中出現了許多杰出人才,為人廣泛所知的便是鄭和:曾七次率領團隊下西洋,擴大了明朝對外的影響,對中外科技、文化等方面交流皆有推動作用。而且就是在明朝,回族完全成為一個獨立的民族。
這一時期,新疆地區的各族人民(維吾爾、塔吉克、哈薩克等)皆改信伊斯蘭教,其他宗教逐漸消失,因而伊斯蘭教建筑也得到巨大發展。
從明朝修建或重建的許多清真寺實例看,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且中國特有的兩大伊斯蘭教建筑體系--中國內地伊斯蘭教建筑、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建筑。
中國內地伊斯蘭教建筑完全以木構架為主體,其總體布局多為以禮拜殿為中心的縱軸形制,并以庭院為單元向縱深及橫向延展,組成龐大的院落族群。其單體建筑也突破中國古代建筑的局限,創造許多組合復雜、規模宏大、氣勢雄偉的禮拜大殿,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建筑的平面組織和外觀的處理手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甘肅蘭州解放路清真寺。
由二門進入內院,迎面聳立精美的邦克樓。這是立大殿與大門之間的一個裝飾性雕刻建筑。樓凡四層,下層平面為方形,兼作大門用;上層為六邊形,主要用六根木柱通達上下,但其中四根為垂柱(吊柱),最上層不用立柱,只用厚木枋壘起并中間開一壺門,枋上安的半拱出三跳,為當地特殊做法。樓四壁周圍有欄桿,在第三層樓的欄桿前后均有一小段如飛橋跳出層面之上。每層樓板正中央,均開一六角形洞口,用欄桿圍起,使每層樓上下都可內部互相看見。[4]
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建筑的實際情況,大體上分成兩大類。其一是以維族寺院為代表的維族式清真寺;其二是以回族寺院為代表的回族式清真寺。這兩種建筑形式都是普遍存在的,其中回族式清真寺同內地清真寺的特點比較類似,維族式的清真寺建筑則多結合當地的傳統,其建筑更多的保留了阿拉伯形式,并結合當地的氣候、材料及建造技術,形成了新疆地區伊斯蘭教建筑不同于內地伊斯蘭教建筑的特有風貌。
新疆地區由于地處偏遠,其禮拜寺的總體布局,受中國傳統建筑的影響較少,基本上仿照阿拉伯及中亞地區的伊斯蘭教建筑形制,不強調院落重重,也不強調軸線對稱等原則。有的布置隨意,有的開門見山,進入大門便可看見禮拜大殿,其余的附屬建筑很少。
禮拜殿多使用木柱上架井字格的木梁,梁上鋪密肋,之后覆草、席加鋪黃土頂。這種屋面的形成同新疆地區常年雨水稀少有關。除了這種木柱密肋梁平頂外還有一種半圓形拱頂的屋面形式,這可能傳自阿拉伯、波斯的做法,多在內殿圣龕處設全寺最大的一個拱,這種半圓拱內部一般用黃土制成。外面用琉璃磚鑲嵌,形成了獨特的民族建筑風貌。[5]
六、中國的伊斯蘭教建筑發展高潮
清朝是我國伊斯蘭教及伊斯蘭教建筑發展的高潮時期。這時,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已達十個,即回、東鄉、保安、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塔塔爾、柯爾克孜、撒拉,分布全國各地。回族村莊數量也在中國西北等地分布較密集,清真寺則成為普遍的宗教建筑,普遍存在。
結語
當擁有先進文化的唐朝和阿拉伯帝國相遇,會產生怎樣的化學反應?歷史的畫筆將經過一幕幕記錄。四大發明經阿拉伯人民傳向世界,瓷器、茶葉經絲綢之路旅行各地。擁有五十六個民族的中國以其包容共贏的心態接納新鮮事物,一路走來,陪伴我們的是世界各族人民。
雙手繪制的建筑設計圖以豐富的形態向國人及世界展示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各民族的獨特建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長,見證社會生活的點滴。清真寺建筑獨特的藝術風格和中國傳統技藝的交流使中阿人民驚喜,傳承并發展至今日的陸、海“絲路”也向世界傳達著中國共同繁榮發展的決心。
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發展更是將世界以數字化的方式連接在一起,縮短了相見時間,拓展了交流廣度。世界文化是否會聯合起來向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沒有人可以預料,但歷史終會用畫筆記錄下每一幕故事。
參考文獻
[1]邱玉蘭,于振生:《中國伊斯蘭教建筑》,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頁。
[2]邱玉蘭,于振生:《中國伊斯蘭教建筑》,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頁。
[3]邱玉蘭,于振生:《中國伊斯蘭教建筑》,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4頁。
[4]《 分析中國傳統建筑風格---清真寺》,載論文網
[5]莫自元:《中國新疆伊斯蘭教建筑考察與研究》,同濟大學碩士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