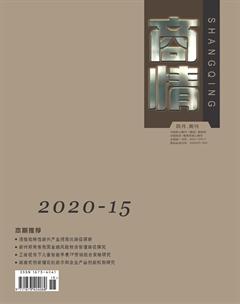關(guān)于日本茶道歷史發(fā)展的研究
葉佳鑫
【摘要】文化是相對(duì)于經(jīng)濟(jì)、政治而言的人類(lèi)全部精神活動(dòng)及其產(chǎn)品,是地區(qū)人類(lèi)生活要素習(xí)慣的統(tǒng)稱。本文通過(guò)學(xué)習(xí)日本茶道的初始到繁榮經(jīng)歷的一系列變遷來(lái)理解茶道文化和日本民族精神,促進(jìn)兩國(guó)異文化之間的理解和交流。
【關(guān)鍵詞】日本茶道 ?民族精神 ?思想觀念 ?歷史人物
茶道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日本文化之魂。早在南宋時(shí)期,日本成為了最早接受中國(guó)茶文化的國(guó)家之一,在中國(guó)茶文化傳到日本一千多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從最初的模仿到不斷地革新并逐步趨于平民化,最終形成了代表和體現(xiàn)日本民族性的文化,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日本茶道的“美的宗教”。日本茶道是融宗教、哲學(xué)、禮儀、倫理為一體的綜合性文化活動(dòng)。它的目的,并非在于鑒別茶質(zhì)的優(yōu)劣、品嘗味道的濃淡,而在于通過(guò)復(fù)雜的程序和儀式達(dá)到追求幽靜、加強(qiáng)和諧、陶冶情操的目的。
茶道即“茶湯之道”,早在鐮倉(cāng)初期傳入日本,到了室町中期由一位叫做村田珠光的僧侶進(jìn)一步改革發(fā)展成了“茶道”。十六世紀(jì)末,由千利休繼承、汲取了歷代的茶道精神,創(chuàng)立了正宗的日本茶道。從此日本茶道逐漸走向成熟與繁榮。故人們常將村田珠光看作是茶道鼻祖,將武野紹鷗定位為中興名人,將千利休作為集茶道文化之大成者。
一、茶道早期的發(fā)展和確立
在東山時(shí)期,茶道初期茶室似乎都為中國(guó)式樣,被稱為“飲茶亭”。南北朝時(shí)期又引進(jìn)了書(shū)院建筑,能阿彌將此建筑的客廳作為茶室,后又編制了書(shū)院建筑以及臺(tái)子裝飾的規(guī)則。因?qū)④姴粷M足于簡(jiǎn)單的點(diǎn)茶法,能阿彌想出了“臺(tái)子點(diǎn)茶”,此時(shí)的臺(tái)子點(diǎn)茶種類(lèi)繁多,形式復(fù)雜。除此之外,能阿彌還將足利將軍家傳承的唐物名器分三等,并將其中的上等品和中等品中的上品命名為“東山御物”,無(wú)一不展現(xiàn)著這個(gè)時(shí)期的茶道所流行的奢靡之風(fēng),自然是平民百姓所觸手不及的文化。能阿彌還規(guī)定了茶會(huì)上主客雙方出席茶會(huì)的服裝,根據(jù)身份地位的高低對(duì)應(yīng)不同的服飾,如身份低下的庶民應(yīng)穿禮服“裃”;貴人則穿“素袍”;將軍則是著“神官服”。不僅僅是服裝,古代茶室的入口、洗手池等等細(xì)節(jié)上都可以充分地體現(xiàn)此時(shí)茶道的階級(jí)性。
傳聞早期的村田珠光因怠慢寺役而被逐出了寺廟,后跟隨能阿彌學(xué)習(xí)過(guò)立花和唐物鑒別,又跟隨一休和尚參禪并獲得了“印可”之正。大徹大悟后作出了“佛法亦存在于茶湯”的論點(diǎn),隨后不斷創(chuàng)新并確立了新的茶湯之法,把場(chǎng)所從富麗堂皇的書(shū)院建筑變成了名為“數(shù)繼屋”的草庵茶室,整體的裝飾也向簡(jiǎn)單樸素轉(zhuǎn)變,并在茶湯中注入了精神層面的“道”,逐步給中國(guó)式的茶室注入了日本的風(fēng)俗文化,使其開(kāi)始走向日本化。珠光主張人要擺脫物質(zhì)的牽絆和人人平等的思想。為了消除了茶湯中存在的明顯的階級(jí)差別。他讓大家統(tǒng)一使用本該是下人使用的東西,貫徹茶道的“侘”。“侘”原意引申為“寒酸貧窮”“失意落魄”,后因受到禪宗及茶道的影響,開(kāi)始趨于積極化,引申為“真誠(chéng)、謹(jǐn)慎、謙遜、平和”。在珠光理念中最為重要的一條便是“賓主舉止”,他認(rèn)為主人應(yīng)該去尊敬客人,客人則應(yīng)該持有著“一期一會(huì)”的態(tài)度去敬畏主人。由此以品茶為名將彼此的心連結(jié)在一起。
在室町時(shí)代末期的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的堺城出了兩位有名的茶藝大師,那便是武野紹鷗和千利休。武野紹鷗原是大名武田氏的后裔,他在茶道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無(wú)疑是一位承上啟下的人物,被稱為是“茶道之中興”。他在珠光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自身的特點(diǎn),在茶室及其裝飾上發(fā)明了新穎的紹鷗派風(fēng)格。紹鷗還是一位歌人,他不像前人那樣否定戀歌,還將和歌掛在壁龕中。和歌是日本較為古老的一種文學(xué)形式。《八重葎之歌》就是第一首掛在壁龕中的和歌。紹鷗將和歌的美學(xué)與茶室的裝飾相結(jié)合,使佗茶變得更為素凈典雅,無(wú)形之中使茶道更加富有靈活性。其次,紹鷗杰出的鑒賞能力“目明”也令他發(fā)現(xiàn)了以竹、木、粗陶瓷為材料的簡(jiǎn)陋器具所具備的美,并將其用作茶具登上茶會(huì),逐漸成為主角,這一舉措更是在無(wú)形中降低了茶道的門(mén)檻,使許多愛(ài)好茶道平民得以享受茶道的樂(lè)趣。武野紹鷗傳道時(shí)還提出了關(guān)于茶事的十二條告誡,這都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紹鷗對(duì)茶道的“潛心鉆研”,以及對(duì)器物的珍惜和對(duì)人的尊敬。其實(shí)在武野紹鷗之前,堺城這個(gè)文化之都也存在著不少的杰出茶人,有一位法名為“空海”的茶人,屬于能阿彌流派,其弟子北向道城就是千利休的老師,而珠光的再傳弟子武野紹鷗也是千利休的老師,因此千利休是在繼承了能阿彌和珠光的理論基礎(chǔ)上,親手對(duì)茶道進(jìn)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使其成為深入人心的國(guó)民文化。所以說(shuō)千利休是茶道的集大成者確實(shí)是當(dāng)真無(wú)愧。
千利休,1522年出生在一個(gè)平民階層的富裕家庭中,自幼便愛(ài)好茶道,拜過(guò)許多師,1540年改名為宗易,號(hào)拋筌齋。“利休”這個(gè)稱號(hào)是為了輔佐豐程秀吉開(kāi)辦茶會(huì)的相關(guān)事宜,由大德寺的古溪和尚挑選,天皇御賜的名號(hào)。利休在茶道方面的貢獻(xiàn)是有目共睹的,他把茶室和室內(nèi)裝飾簡(jiǎn)化縮小到了最小限度,隨手便將生活用品用作茶具;還很大程度上簡(jiǎn)化茶道的規(guī)定動(dòng)作和形式并形成了“四規(guī)七則”的茶道禮法。“四規(guī)”是指千休利在珠光所提出的茶道精神的基礎(chǔ)上改動(dòng)了一個(gè)字,提出將“和、敬、清、寂”作為茶道的宗旨,“七則”則是指要提前備好茶,提前放好碳,茶室應(yīng)冬暖夏涼,室內(nèi)插花保持自然美,遵守時(shí)間,備好雨具,時(shí)刻把客人放在心上。千利休的行為使茶道掙脫了物質(zhì)的束縛,打擊了拜物主義風(fēng)氣。茶會(huì)本該是營(yíng)造人與人相互尊重,促進(jìn)心與心交流的活動(dòng),如若過(guò)分注重身外之物,則辜負(fù)了茶道的本義。
二、茶道的弘揚(yáng)及變革
千利休因過(guò)于接近權(quán)勢(shì)者,在木像事件和茶器出售事件的雙重罪名下,被勒令切腹自盡。但千利休的弟子們繼承了利休的茶道并為之發(fā)揚(yáng)光大。“利休七哲”之一古田織部是日本茶道歷史上第五位名人,織部并沒(méi)有像絕大部分弟子那樣原封不動(dòng)地沿襲師傅的做法,反而對(duì)茶道進(jìn)行了不斷的創(chuàng)新。織部有著華麗的審美,他為茶室設(shè)計(jì)了“織部窗”,使壁龕顯得略微明亮,便于欣賞壁龕里的字畫(huà),這恰到好處的昏暗正是織部茶室的特點(diǎn)。他還會(huì)在數(shù)寄屋“露地”上種植蒲公英,吸引鳥(niǎo)雀啼鳴,這樣的茶會(huì)和之前的侘茶相比,實(shí)屬風(fēng)雅。這也正是桃山時(shí)代所盛行的華麗美學(xué)。同期的還有一位名叫小堀遠(yuǎn)州的茶師,他給茶室增加了書(shū)院茶室的元素,同時(shí)恢復(fù)了茶室的明亮感,還用小路連結(jié)了露地,增加了樹(shù)木池塘等元素,構(gòu)建成一個(gè)具有王朝風(fēng)格的庭院。遠(yuǎn)州還經(jīng)常使用色彩鮮艷華麗的茶器,彰顯著“古雅之美”,女性喜歡上茶道大抵是從這兒開(kāi)始的吧。遠(yuǎn)州還是首個(gè)提出要為茶器添加和歌銘文的人,如音羽山的茶葉罐,它的名字源于《古今集》中的戀歌“朝過(guò)音羽山,遙聞山間有杜鵑,啼鳴高樹(shù)巔”,如此一來(lái),茶具好似凝聚了更加高雅的趣味。兩位名人雖都在利休的茶道基礎(chǔ)上融入了自身的看法和喜好,但是他們對(duì)茶道的感悟和對(duì)其精神的貫徹卻是相同的。利休的子孫在延續(xù)和推廣茶道的道路上也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其中千利休的孫子--千宗旦的貢獻(xiàn)更是不可小覷。他的貢獻(xiàn)概括來(lái)講可分為三點(diǎn):一是為民間普及了利休流傳下來(lái)的茶道;二是奠定了“千家十職”的基礎(chǔ);三是成立了茶道三千家,分別為武者小路千家、表千家和里千家。為了不步利休的后塵,宗旦并沒(méi)有投靠在當(dāng)時(shí)權(quán)勢(shì)者的名下,而是作為一介民間茶師,向百姓普及千家茶道。其實(shí)發(fā)揚(yáng)茶道的還有一位茶師,名為片桐石州,他是德川將軍府的茶師,在茶道的弘揚(yáng)上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xiàn),區(qū)別是他是向?qū)④姶竺A層的人普及茶道。確立了新的結(jié)構(gòu) “家元制度”和新的茶道游藝“七事儀式”,即品茶、花月、回碳、回花、一二三、且座和數(shù)茶。打破原有的規(guī)則具有兩面性,不可否認(rèn)這一變革給茶道其他流派提供了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為茶道注入了新鮮血液,也使茶道多一分自由豁達(dá)的韻味。
三、總結(jié)
如今的日本茶道一定還存在著些許問(wèn)題,但不可否認(rèn)它其中所蘊(yùn)含的知識(shí)及其精神都是著的我們?nèi)W(xué)習(xí)和鉆研的。茶道的發(fā)展首先離不開(kāi)“創(chuàng)新”二字,歷屆著名的茶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不斷創(chuàng)新,融入新的風(fēng)格。不僅限于茶道,任何事物都離不開(kāi)這兩個(gè)字,我們每個(gè)人都存在著可能性,要學(xué)會(huì)在落實(shí)中創(chuàng)新,勇于實(shí)踐。其次是茶道的精神,雖然茶道在不斷變革,但追溯其根源,千利休所指定的規(guī)范并未過(guò)時(shí),現(xiàn)代的有些茶會(huì)變得趨于形式化和利益化,過(guò)分拘泥于茶具和搭配,而忽略了主客之間的心靈交流,過(guò)于追求物質(zhì),而忽視了精神上的體驗(yàn)。這樣的茶道已經(jīng)失去了原有的初心,根本觸及不到侘的境界。應(yīng)該抱有著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去探尋適合的茶具,留心于身邊的每一處風(fēng)景,而不是人為擺放華麗的裝飾,過(guò)于追求形式只會(huì)止步不前,茶道應(yīng)該是純粹、和諧、但又充滿樂(lè)趣的。在現(xiàn)在這個(gè)錯(cuò)綜復(fù)雜的社會(huì)中,也希望能保持著這份初心,敢于發(fā)現(xiàn)和嘗試,學(xué)會(huì)打破常規(guī),砥礪前行。
參考文獻(xiàn):
[1]桑田中親.《茶道六百年》[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2.
[2]桑田中親.《茶道六百年》[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27-29.
[3]藤原定家.《小倉(cāng)人一百首》[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12.
[4]桑田中親.《茶道六百年》[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89-90.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2019年度遼寧對(duì)外經(jīng)貿(mào)學(xué)院校級(jí)大學(xué)生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項(xiàng)目《中日茶文化的對(duì)照研究(編號(hào)2018XJDCA09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