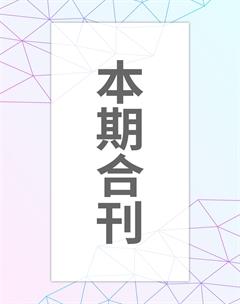羅馬教皇在黑暗中為病患祈禱
韓碩 馮璐

2020年3月27日,方濟各在圣彼得廣場舉行一個人的祈禱儀式,為全球各地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擾的人送上祝福。
不勝負荷的醫院充滿消毒水味,軍車排長隊轉運遺體,鋪天蓋地的訃告……在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至暗時刻,一位83歲的白衣老人在圣彼得大教堂為遭受痛楚的病人祈禱,雨中的孤獨背影令全世界動容。
圣彼得大教堂位于羅馬西北角的梵蒂岡,而這位老人是羅馬天主教第266任教皇方濟各。疫情蔓延期間,他多次通過網絡直播見教徒,還呼吁神職人員“鼓起勇氣,主動探望病人”,給意大利和全球帶去信仰的慰藉和希望。
雨中祈禱的教皇
當地時間3月27日傍晚,暮色四合,夜燈初上,方濟各獨自走上圣彼得大教堂的石階,做了一場“致全城與全球”的特別演講。這種形式的活動,一般只在復活節、圣誕節進行,彼時的梵蒂岡信眾云集、熱鬧非凡。
而這次演講,偌大的圣彼得廣場空無一人,天空下起紛霏細雨。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時刻,方濟各特意安排這場“獨角戲”,通過網絡將自己的祈愿傳遞給全世界。
儀式開始前幾分鐘,意大利公布當地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達86498例,官方稱疫情高峰仍未到來,采取的封鎖措施將延長。當時的意大利,已經是全世界新冠肺炎病亡人數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梵蒂岡3月6日確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此后染病人數增加到7人。
“夜幕降臨,黑暗越來越濃密。”方濟各在寂靜中獨白,“突如其來的暴雨讓我們猝不及防,所有人都一樣脆弱、迷茫。同時,所有人都一樣重要而必不可少,病毒使所有人同舟共濟、互相安慰。”隨后,他稱贊了醫生、護士、超市員工、清潔工、護理人員、運輸工人、警察和志愿者,“他們在書寫我們時代的決定性事件”。
方濟各的出鏡經驗很豐富。他常和信眾一起玩自拍,找角度、擺姿勢都駕輕就熟,還曾在紀錄片《教皇方濟各:我的藝術觀》和電影《教皇方濟各:言出必行的人》中本色出演。疫情期間,他的祈禱直播也顯得自然、親切。
為了這場祈禱,羅馬教廷展出兩件圣物。一件是羅馬圣母大殿的拜占庭圣母像,另一件是羅馬圣瑪策祿堂的基督受難雕像。這一雕像在500年前、1519年教堂的大火中奇跡般幸存;三年后的羅馬大瘟疫中,雕像被舉著在城內巡游,16天后疫情奇跡消失。

2020年4月5日,方濟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主持閉門的主日彌撒。
圣彼得廣場外的協和大道上,一些信眾來到大道旁的庇護十二世廣場,與教皇同時祈禱。城市被凝重與悲怮的氛圍籠罩,但星星點點的街燈,依然溫情地閃耀著。
方濟各呼吁世界各國將新冠肺炎危機視為對團結的考驗。“每個人應當被這次疫情喚醒并彼此團結,這種團結能夠為眼下全人類的困境提供力量、支持和希望。”
在疫情中凝聚人心,方濟各的擔子并不輕松。但他非常清楚,自己必須保持充滿希望的形象。站在教廷頂端的老人絕不能眼神焦愁、一臉倦容。
致完祈禱詞后,方濟各來到圣母像前面祈禱,親吻了十字架上基督的腳。方濟各向他信仰的上帝求助說:“不要將我們留在暴風雨中。”教堂里奏起格里高利圣詠曲,空靈的吟唱響徹天際。雨越下越大,似乎也在為人間的災難哀痛。在遠程直播的視頻中,方濟各年邁的身影顯得謙卑而無助,令看到這一幕的上千萬人幾欲落淚。
儀式結束后,圣彼得大教堂響起莊嚴鐘聲。濃厚的黑暗籠罩了廣場和街道。有救護車從大道駛過,令人不安的鳴笛聲,與祈禱儀式一道,傳遞給全世界。
多名神父“逆行”染病去世
在整個意大利被動員起來抗擊疫情時,方濟各一直沒閑著。早在此前的3月8日,方濟各就打破教廷百年傳統,首次通過廣場大屏幕直播的方式進行周日禱告儀式。他在羅馬教皇圖書館主持儀式,隨后來到窗前,與圣彼得廣場上的人們短暫問好。他還在沒有公眾參與的情況下舉行棕枝主日彌撒,并向全球基督徒發起誦念禱文以及通過直播方式參與朝拜圣體祈禱等活動。
以身作則之外,他還向神父們發出“逆行”指令:勇敢走出去,去看望那些生病的人。在意大利疫情特殊時期,醫護人員自然要“沖鋒陷陣”,神職人員則是另一個“舍生忘死”的群體。盡管所有的公共彌撒在封鎖期間被禁止,但神父們響應方濟各的號召,依舊出入人群聚集地,給大眾送去信仰上的支持。他們甚至走進重癥監護室,給瀕危者帶去臨終慰藉。
伴隨著運送尸體的卡車發動機的轟鳴,教堂鐘聲響起,周邊居民紛紛聚集到陽臺或窗邊,做出劃十字的手勢。戴著口罩和白色手套的警察朝著卡車離開的方向立正、敬禮。這樣的場景在意大利循環上演著。
按天主教的習俗,人死去要神父祝福才能安息,而90%的意大利人是天主教徒。堅持臨終關懷和直面死亡的意大利神父成了感染新冠病毒的高危人群。
據報道,至少50名天主教神父因新冠肺炎病亡,超過了意大利犧牲醫生的數量。犧牲的神父中,從45歲到104歲都有,大多是五六十歲。他們是在探訪病人、安慰臨終病人等活動中被感染的。此外,意大利還有大量神職人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有的人已是重癥。
危險從未如此刻般迫近。方濟各年過八旬,患有坐骨神經痛,還曾因肺結核切除了一部分肺。3月初,他身體抱恙,取消了部分工作安排,同時因屢次在公開場合咳嗽引發大眾對其身體狀況的擔心。他自稱正在從支氣管炎中康復,不過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
盡管多人“因公殉職”令方濟各的鼓勵遭受非議,但總體來說,勇敢的神父還是向社會傳遞出正能量,他們的“逆行”讓感染者獲得精神安慰,有助于康復治療;嚴重的病人也得以有尊嚴地告別這個世界。
在意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北部貝加莫市,奧廖內中心創始人濟利祿神父離世前在病榻上做出勝利手勢的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鼓舞了許多病患和醫護人員。意大利72歲的貝拉德利神父,因為主動把民眾為自己購置的呼吸機讓給陌生的年輕人,不幸去世。他的棺材被抬去埋葬時,小鎮居民紛紛從窗戶和陽臺上探身,一邊鼓掌一邊目送,以此來表達內心的敬意。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對此,有人引用《圣經》的原話感嘆說。
傳教和醫療事業密不可分
歷史上,救死扶傷一直是基督教會的職責之一。公開資料顯示,公元1世紀,基督教剛問世,基督徒發現病人便悉心照料。教會要求他們效仿耶穌基督醫治病人的行為, 并對修士、修女培訓醫學知識,這是基督教大力發展醫療事業的最直接原因。
公元325年,基督教會第一次主教特別會議規定,主教要在每一座有教堂的城市建造醫院或收容所,主要功能是看護、治療病人。這些醫院被稱為“救濟院”,是根據“基督要關心身體有疾病之人”的命令創建起來的。公元369年,第一座基督教醫院在卡帕多西亞建立。到了公元6世紀中期,基督教大量修建醫院,醫院成為修道院的常規組成部分。

左圖:病床上的濟利祿神父。 右圖:生前的貝拉德利神父。
在疾病大流行、自然災害中,基督教神職人員更是積極參與救援工作。從2014年至2016年,西非暴發的埃博拉疫情奪去了上萬人的生命。教會利用一切機會支持防控工作,提高公眾對埃博拉的認識,確保他們了解疾病,并采取應對措施。據歷史記載,“黑死病”14世紀在歐洲肆虐橫行。1347年至1353年,瘟疫共奪走了2500萬人(約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的性命。在中世紀,只有基督教會具有強大的財力和人才力量去發展醫療。于是,陷入恐懼的人們到神職人員處祈求保護和安慰。許多神職人員冒死堅守崗位,用掌握的醫學知識救治、照顧病患,同時為大量病亡者舉行宗教儀式。
然而,收容病人的修道院不可避免地出現大范圍感染悲劇:比利時主教成為瘟疫受害者;德國1/3神職人員死亡;法國蒙彼利埃一個修道院中的140名修士中,只有一人幸免于難。在災難面前,神職人員和普通人一樣驚慌失措,基督教在歐洲的權威性開始動搖。
不過,在基督教向東方傳播時,傳教與慈善并重的路線由來已久。辦學校和醫院被形容為“打開傳教的楔子”。在為成千上萬病人解除痛苦或挽救生命的過程中,不少贏得聲望的西方醫生打開了傳教的“方便之門”。
國際紅十字會的出現,使得宗教和醫療事業更加密不可分。1863年,信仰基督教的瑞士人亨利·杜南倡議成立該協會,并選擇了基督教的十字架——基督受難、救贖的象征,作為這個組織的標志。如今,染成紅色的十字架已被公認為是人道主義的象征。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方濟各對大眾進行心靈撫慰之余,還向意大利重災區貝加莫當地“若望二十三世教皇”醫院捐款6萬歐元(約合46萬元人民幣)。他也擁有自己的醫療機構,如坐落在梵蒂岡的耶穌圣嬰兒科醫院,如今已是歐洲最大的兒科醫院和研究中心。該院每年住院量超過2.7萬人次,急診量達到8萬人次,門診量超過了170萬人次。
此外,在方濟各的鼓勵下,許多修女報名到各地醫院輪替值班,照顧病患,為醫護人員分擔壓力。也有神職人員保持電話暢通,隨時隨地向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援。
年邁的方濟各一直在梵蒂岡的住所里祈禱,并鼓勵那些宅在家里的人,找到有創造性的生活方式。“你們要為即將到來的未來,好好照顧自己。”他叮囑說。
方濟各1936年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本名豪爾赫·馬里奧·貝爾格里奧。梵蒂岡時間2013年3月13日,方濟各被選為羅馬天主教第266任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