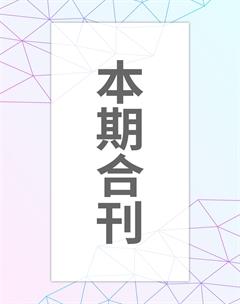杜鵑花,適當(dāng)?shù)拿利?/h1>
2020-05-27 09:36:09崔瑩
環(huán)球人物 2020年8期
崔瑩
傳說(shuō)杜鵑晝夜悲鳴,啼至出血,鮮紅的血滴落在漫山遍野,化成一朵朵美麗的杜鵑花。每年四五月是杜鵑花盛開(kāi)的時(shí)節(jié),我常常在愛(ài)丁堡的皇家植物園見(jiàn)到來(lái)自中國(guó)的各種杜鵑花。
“杜鵑花之王”的七次探險(xiǎn)
紅的、粉的、黃的、紫的、白的……一簇簇,一叢叢,盛開(kāi)的杜鵑花爭(zhēng)先恐后掛滿(mǎn)了枝頭。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愛(ài)丁堡皇家植物園,便被這些繁盛的杜鵑花吸引。和今天身為園林熱寵、家養(yǎng)花卉常客的待遇迥然不同,杜鵑花原本生長(zhǎng)于云南的懸崖或是深谷里,隱逸于世,獨(dú)自美麗。
但美麗的它,終于遇到了知音。
全世界有1000多種杜鵑花,愛(ài)丁堡皇家植物園擁有600多種,其中的400多種是蘇格蘭人喬治·福雷斯特在中國(guó)發(fā)現(xiàn)、搜集,帶到英國(guó)的。“福雷斯特”這個(gè)姓很有趣,像極了英文單詞“森林”,我想,這也許是他和植物產(chǎn)生不解之緣的原因吧。
1873年,福雷斯特出生于離愛(ài)丁堡不遠(yuǎn)的蘇格蘭小鎮(zhèn)福爾柯克。他18歲結(jié)束學(xué)業(yè),開(kāi)始在藥店工作。正是這段工作經(jīng)歷讓他認(rèn)識(shí)了大量藥草。他原本可以按部就班地工作到退休,但一筆意外之財(cái)改變了他的人生。1898年,福雷斯特從叔叔那里繼承了一筆遺產(chǎn),他決定前往澳大利亞淘金,結(jié)果無(wú)功而返。于是,他寫(xiě)信給愛(ài)丁堡皇家植物園的伊薩克·包爾佛教授,得到了在植物園的工作機(jī)會(huì)。
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很多歐洲人到中國(guó)西南部搜集植物花卉,尤其是亨利·威爾遜的收獲讓英國(guó)人確信中國(guó)西南是植物花卉的寶藏。棉花商布雷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機(jī),他迫切希望能從中牟利——找到新的、有商業(yè)價(jià)值的花卉新品種。1904年5月,福雷斯特和布雷簽訂了一份年薪100英鎊、為期3年的合同,開(kāi)始了第一次中國(guó)之行。福雷斯特沒(méi)有搜集植物的經(jīng)驗(yàn),但他很努力,他自學(xué)中文,還給自己起了個(gè)雅致的中國(guó)名字——傅禮士。他熱衷慈善,為當(dāng)?shù)厝藥チ祟A(yù)防天花的疫苗,還捐款幫當(dāng)?shù)厝硕冗^(guò)自然災(zāi)害,這讓他在中國(guó)西南交到了不少朋友。
從此28年的歲月里,福雷斯特總共7次遠(yuǎn)涉中國(guó),在昆明和滇西搜集植物。每一次,他都在當(dāng)?shù)毓腿耍M建團(tuán)隊(duì)幫他搜集。第一次就是1904年到1907年,他以云南騰沖為基地。第二次是1910年,他主要在麗江以北考察,最大的收獲是發(fā)現(xiàn)了新品種的杜鵑花。1912年,福雷斯特第三次赴中國(guó),正值辛亥革命風(fēng)起云涌,清王朝剛被推翻,地方局勢(shì)動(dòng)蕩不安之際,他克服種種困難繼續(xù)搜集植物。1917年到1919年,福雷斯特第四次到云南,找到了罕見(jiàn)的杜鵑品種——樹(shù)高24米、樹(shù)干周長(zhǎng)2米多、樹(shù)冠寬12米的大樹(shù)杜鵑。大樹(shù)杜鵑號(hào)稱(chēng)“花之王”,是杜鵑花中的活化石,對(duì)研究生物進(jìn)化具有重要意義。這一發(fā)現(xiàn),舉世矚目。
杜鵑花多生長(zhǎng)在懸崖深谷,尋找的過(guò)程困難重重,但福雷斯特樂(lè)此不疲。他在寫(xiě)給《地理雜志》的文章中描述:“我們抓住垂下的樹(shù)枝,把身體掛在巖石上,或以巖石槽口為支撐,緊緊地貼著山崖面攀行,我想猴子更擅長(zhǎng)這種攀登。”1921年到1922年,福雷斯特第五次去云南,他在滇西北靠近西藏東南處,搜集到了大量杜鵑花。1924年到1925年,他第六次來(lái)到云南。1930年11月,是福雷斯特的第七次云南之行,也是最后一次。福雷斯特自述,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拾遺補(bǔ)缺,他寫(xiě)道:“若一切順利,那我過(guò)去這些年的辛勤勞作和努力將畫(huà)上一個(gè)完美的句號(hào)。”
然而造化弄人。當(dāng)搜集工作接近尾聲時(shí),意外發(fā)生。1932年1月5日,在野外打獵的福雷斯特突發(fā)心臟病而亡。59歲的福雷斯特被葬在騰沖郊外的來(lái)鳳山上,墓地緊挨著他的朋友、英國(guó)駐騰沖領(lǐng)事列敦的墓。
福雷斯特永遠(yuǎn)留在了中國(guó),留在了他喜歡的云南,但他帶給英國(guó)大量無(wú)法用金錢(qián)衡量的財(cái)富。他先后采集了10余萬(wàn)份動(dòng)植物標(biāo)本運(yùn)回英國(guó),其中包括400多種杜鵑花,他也被因此譽(yù)為“杜鵑花之王”。
愛(ài)默生寫(xiě)下《紫杜鵑》
今年,因?yàn)樾鹿诜窝滓咔椋瑦?ài)丁堡皇家植物園暫時(shí)關(guān)閉,成片的杜鵑花只能獨(dú)自開(kāi)放,獨(dú)自美麗。沒(méi)有游客的杜鵑花海,會(huì)不會(huì)寂寞?86年前,美國(guó)詩(shī)人、哲學(xué)家拉爾夫·沃爾多·愛(ài)默生在思考同樣的問(wèn)題。
愛(ài)默生在參觀(guān)美國(guó)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奧本山公墓時(shí),發(fā)現(xiàn)那里的杜鵑花姹紫嫣紅,但當(dāng)?shù)亓葻o(wú)人煙,他寫(xiě)下了能和英國(guó)詩(shī)人華茲華斯的名詩(shī)《水仙花》媲美的《紫杜鵑》。
愛(ài)默生在詩(shī)中感慨:“杜鵑啊!如果智者問(wèn)你,這樣的景致為何要留給不會(huì)欣賞的天空與大地,告訴他們,若神是為了看而造雙目,那么美就是自己存在的緣故:你為什么在這里,玫瑰般迷人的花?我從未想過(guò)問(wèn)你,也不知曉答案; 可是,無(wú)知的我有一個(gè)單純的想法:是引我前來(lái)的那種力量引你來(lái)到世間。”
愛(ài)默生認(rèn)為杜鵑花和玫瑰一樣美麗,但它們低調(diào)謙卑,藏在深林里,被茂密的叢林遮掩,人們很少看到它們的美麗。愛(ài)默生繼而給出自己的解釋?zhuān)好赖拇嬖诓恍枰魏卫碛伞D敲矗瑸槭裁丛?shī)人能欣賞到杜鵑花的美麗?愛(ài)默生指出:是一種神奇的力量讓他來(lái)到杜鵑花的身旁,這種力量同樣促使杜鵑花來(lái)到世間。
這首詩(shī)表明愛(ài)默生開(kāi)始思考人性和大自然的關(guān)系。后來(lái),他的這些觀(guān)點(diǎn)體現(xiàn)在著作《論自然》中。《紫杜鵑》和《論自然》存在多處呼應(yīng)。比如,愛(ài)默生在《論自然》中認(rèn)為物欲泛濫,導(dǎo)致人類(lèi)忘記存在的意義,建議人們最好遠(yuǎn)離喧囂社會(huì),去凝望群星,去面對(duì)自然,去敞開(kāi)心扉……這如同在人跡罕至的荒野里盛開(kāi)的紫杜鵑,不在乎周?chē)沫h(huán)境,不在乎是否有觀(guān)眾,只保持自己內(nèi)心的傲嬌和美好。
“陽(yáng)光照進(jìn)大人的眼睛里,但卻照進(jìn)孩子們的心里。”愛(ài)默生在《論自然》中寫(xiě)道,與兒童不同,大多數(shù)成年人已經(jīng)失去了欣賞自然的能力,而只有最可能看清楚大自然的人才會(huì)成為詩(shī)人。這正如《紫杜鵑》中愛(ài)默生援引的一種世俗觀(guān)點(diǎn)——美因受眾而存在,沒(méi)有受眾,美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價(jià)值。他認(rèn)為,只有純真無(wú)邪的兒童,才會(huì)發(fā)現(xiàn)美、感受美。
愛(ài)默生在《紫杜鵑》一詩(shī)中感慨:“杜鵑啊!如果智者問(wèn)你,這樣的景致為何要留給不會(huì)欣賞的天空與大地,告訴他們,若神是為了看而造雙目,那么美就是自己存在的緣故:你為什么在這里,玫瑰般迷人的花?”
“花是地球的微笑”“花是自豪的斷言,一束美麗的花勝過(guò)世界上所有的設(shè)施”,愛(ài)默生的文字,洋溢著他對(duì)花、對(duì)大自然的熱愛(ài)。今年復(fù)活節(jié)的前一天,我在愛(ài)丁堡郊區(qū)的野山里散步,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大片杜鵑花,不禁想到大洋彼岸愛(ài)默生發(fā)現(xiàn)杜鵑花時(shí)的驚喜。
“入侵”橡木林
隨著東西方的更多交流,杜鵑花也落戶(hù)到了其他國(guó)家。如今,它在各個(gè)國(guó)家的待遇大相徑庭。在保加利亞,杜鵑花被列為稀有瀕危植物,人們對(duì)它關(guān)愛(ài)備至。在西班牙南部,杜鵑花也面臨滅絕的危險(xiǎn)。但在土耳其的東北部,杜鵑花的數(shù)量眾多,并被視為破壞性植物。
而在愛(ài)爾蘭,人們對(duì)它的評(píng)價(jià)是“侵入性物種,嚴(yán)重破壞生態(tài)”。因?yàn)槎霹N花不僅遮擋了本地其他植物的幼苗,而且還分泌化感酸,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長(zhǎng)。同時(shí),杜鵑花的繁殖能力超強(qiáng),一株杜鵑花每年可產(chǎn)生上百萬(wàn)顆輕如塵土的種子,借風(fēng)而行,輕而易舉侵占更多領(lǐng)地。
因?yàn)橥寥馈夂蜻m宜,杜鵑花在愛(ài)爾蘭的生長(zhǎng)肆無(wú)忌憚。人們不得不和杜鵑花展開(kāi)搏戰(zhàn),甚至不得不請(qǐng)求調(diào)遣士兵擺平它們。否則,原本具有生態(tài)多樣性的園區(qū)很有可能淪落成杜鵑花園。最傷腦筋的要屬愛(ài)爾蘭的基拉尼國(guó)家公園,該園的橡木林正一點(diǎn)點(diǎn)被杜鵑花吞噬。
誰(shuí)也不曾想到,美麗的杜鵑花竟然會(huì)成為侵略者,遭人討厭。看來(lái),即使再美的東西,數(shù)量過(guò)多也未必是好的。過(guò)猶不及,適當(dāng)最重要。我不禁想到,在日本吉卜力工作室制作的動(dòng)畫(huà)片《我的鄰居山田君》中,老師寫(xiě)在黑板上、送給學(xué)生們的新年目標(biāo),正是“適當(dāng)”兩個(gè)字。
杜鵑花的一生,原是處處適當(dāng)?shù)摹K谏窖轮屑澎o盛放,直到深谷遇知音,一個(gè)蘇格蘭人帶著它走向英國(guó)、走向世界,世人始知它的美麗;它開(kāi)始被熱鬧包圍,但美國(guó)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愛(ài)默生卻在寂寥中遇到它,為它寫(xiě)下雋永的詩(shī)歌。如今,也有人為杜鵑花的“不適當(dāng)”入侵擔(dān)憂(yōu)。可這一切,何嘗不是人類(lèi)自尋的煩惱呢?100多年來(lái),人們對(duì)杜鵑花、對(duì)新物種的態(tài)度在不停改變,從冷淡到熱寵,不變的其實(shí)是植物、大自然本身。無(wú)論在哪里,無(wú)論是否有知音,只要有土壤、有光亮、有水,杜鵑花都會(huì)歡喜地生長(zhǎng)。
猜你喜歡
植物的防身術(shù)少兒科學(xué)周刊·兒童版(2017年5期)2017-06-29 22:24:28 把植物做成藥少兒科學(xué)周刊·兒童版(2017年5期)2017-06-29 16:46:33 哦,不怕,不怕紅領(lǐng)巾·萌芽(2017年5期)2017-06-23 10:35:59 美麗的夜晚學(xué)苑創(chuàng)造·A版(2017年6期)2017-06-23 10:10:38 我們創(chuàng)造美麗幼兒教育·父母孩子版(2017年4期)2017-06-13 05:41:24 平凡又美麗學(xué)苑創(chuàng)造·A版(2017年3期)2017-04-27 22:30:42 將植物穿身上爆笑show(2016年7期)2017-02-09 09:36:13 誰(shuí)是最美麗的蟲(chóng)(三)小溪流(畫(huà)刊)(2016年11期)2017-01-05 12:30:06 美麗的花娃娃樂(lè)園·3-7歲綜合智能(2016年4期)2016-10-24 09:35:39 不可錯(cuò)過(guò)的美麗配飾們Coco薇(2015年12期)2015-12-10 02:38:16
崔瑩
傳說(shuō)杜鵑晝夜悲鳴,啼至出血,鮮紅的血滴落在漫山遍野,化成一朵朵美麗的杜鵑花。每年四五月是杜鵑花盛開(kāi)的時(shí)節(jié),我常常在愛(ài)丁堡的皇家植物園見(jiàn)到來(lái)自中國(guó)的各種杜鵑花。
“杜鵑花之王”的七次探險(xiǎn)
紅的、粉的、黃的、紫的、白的……一簇簇,一叢叢,盛開(kāi)的杜鵑花爭(zhēng)先恐后掛滿(mǎn)了枝頭。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愛(ài)丁堡皇家植物園,便被這些繁盛的杜鵑花吸引。和今天身為園林熱寵、家養(yǎng)花卉常客的待遇迥然不同,杜鵑花原本生長(zhǎng)于云南的懸崖或是深谷里,隱逸于世,獨(dú)自美麗。
但美麗的它,終于遇到了知音。
全世界有1000多種杜鵑花,愛(ài)丁堡皇家植物園擁有600多種,其中的400多種是蘇格蘭人喬治·福雷斯特在中國(guó)發(fā)現(xiàn)、搜集,帶到英國(guó)的。“福雷斯特”這個(gè)姓很有趣,像極了英文單詞“森林”,我想,這也許是他和植物產(chǎn)生不解之緣的原因吧。
1873年,福雷斯特出生于離愛(ài)丁堡不遠(yuǎn)的蘇格蘭小鎮(zhèn)福爾柯克。他18歲結(jié)束學(xué)業(yè),開(kāi)始在藥店工作。正是這段工作經(jīng)歷讓他認(rèn)識(shí)了大量藥草。他原本可以按部就班地工作到退休,但一筆意外之財(cái)改變了他的人生。1898年,福雷斯特從叔叔那里繼承了一筆遺產(chǎn),他決定前往澳大利亞淘金,結(jié)果無(wú)功而返。于是,他寫(xiě)信給愛(ài)丁堡皇家植物園的伊薩克·包爾佛教授,得到了在植物園的工作機(jī)會(huì)。
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很多歐洲人到中國(guó)西南部搜集植物花卉,尤其是亨利·威爾遜的收獲讓英國(guó)人確信中國(guó)西南是植物花卉的寶藏。棉花商布雷也看到了其中的商機(jī),他迫切希望能從中牟利——找到新的、有商業(yè)價(jià)值的花卉新品種。1904年5月,福雷斯特和布雷簽訂了一份年薪100英鎊、為期3年的合同,開(kāi)始了第一次中國(guó)之行。福雷斯特沒(méi)有搜集植物的經(jīng)驗(yàn),但他很努力,他自學(xué)中文,還給自己起了個(gè)雅致的中國(guó)名字——傅禮士。他熱衷慈善,為當(dāng)?shù)厝藥チ祟A(yù)防天花的疫苗,還捐款幫當(dāng)?shù)厝硕冗^(guò)自然災(zāi)害,這讓他在中國(guó)西南交到了不少朋友。
從此28年的歲月里,福雷斯特總共7次遠(yuǎn)涉中國(guó),在昆明和滇西搜集植物。每一次,他都在當(dāng)?shù)毓腿耍M建團(tuán)隊(duì)幫他搜集。第一次就是1904年到1907年,他以云南騰沖為基地。第二次是1910年,他主要在麗江以北考察,最大的收獲是發(fā)現(xiàn)了新品種的杜鵑花。1912年,福雷斯特第三次赴中國(guó),正值辛亥革命風(fēng)起云涌,清王朝剛被推翻,地方局勢(shì)動(dòng)蕩不安之際,他克服種種困難繼續(xù)搜集植物。1917年到1919年,福雷斯特第四次到云南,找到了罕見(jiàn)的杜鵑品種——樹(shù)高24米、樹(shù)干周長(zhǎng)2米多、樹(shù)冠寬12米的大樹(shù)杜鵑。大樹(shù)杜鵑號(hào)稱(chēng)“花之王”,是杜鵑花中的活化石,對(duì)研究生物進(jìn)化具有重要意義。這一發(fā)現(xiàn),舉世矚目。
杜鵑花多生長(zhǎng)在懸崖深谷,尋找的過(guò)程困難重重,但福雷斯特樂(lè)此不疲。他在寫(xiě)給《地理雜志》的文章中描述:“我們抓住垂下的樹(shù)枝,把身體掛在巖石上,或以巖石槽口為支撐,緊緊地貼著山崖面攀行,我想猴子更擅長(zhǎng)這種攀登。”1921年到1922年,福雷斯特第五次去云南,他在滇西北靠近西藏東南處,搜集到了大量杜鵑花。1924年到1925年,他第六次來(lái)到云南。1930年11月,是福雷斯特的第七次云南之行,也是最后一次。福雷斯特自述,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拾遺補(bǔ)缺,他寫(xiě)道:“若一切順利,那我過(guò)去這些年的辛勤勞作和努力將畫(huà)上一個(gè)完美的句號(hào)。”
然而造化弄人。當(dāng)搜集工作接近尾聲時(shí),意外發(fā)生。1932年1月5日,在野外打獵的福雷斯特突發(fā)心臟病而亡。59歲的福雷斯特被葬在騰沖郊外的來(lái)鳳山上,墓地緊挨著他的朋友、英國(guó)駐騰沖領(lǐng)事列敦的墓。
福雷斯特永遠(yuǎn)留在了中國(guó),留在了他喜歡的云南,但他帶給英國(guó)大量無(wú)法用金錢(qián)衡量的財(cái)富。他先后采集了10余萬(wàn)份動(dòng)植物標(biāo)本運(yùn)回英國(guó),其中包括400多種杜鵑花,他也被因此譽(yù)為“杜鵑花之王”。
愛(ài)默生寫(xiě)下《紫杜鵑》
今年,因?yàn)樾鹿诜窝滓咔椋瑦?ài)丁堡皇家植物園暫時(shí)關(guān)閉,成片的杜鵑花只能獨(dú)自開(kāi)放,獨(dú)自美麗。沒(méi)有游客的杜鵑花海,會(huì)不會(huì)寂寞?86年前,美國(guó)詩(shī)人、哲學(xué)家拉爾夫·沃爾多·愛(ài)默生在思考同樣的問(wèn)題。
愛(ài)默生在參觀(guān)美國(guó)馬薩諸塞州的劍橋奧本山公墓時(shí),發(fā)現(xiàn)那里的杜鵑花姹紫嫣紅,但當(dāng)?shù)亓葻o(wú)人煙,他寫(xiě)下了能和英國(guó)詩(shī)人華茲華斯的名詩(shī)《水仙花》媲美的《紫杜鵑》。
愛(ài)默生在詩(shī)中感慨:“杜鵑啊!如果智者問(wèn)你,這樣的景致為何要留給不會(huì)欣賞的天空與大地,告訴他們,若神是為了看而造雙目,那么美就是自己存在的緣故:你為什么在這里,玫瑰般迷人的花?我從未想過(guò)問(wèn)你,也不知曉答案; 可是,無(wú)知的我有一個(gè)單純的想法:是引我前來(lái)的那種力量引你來(lái)到世間。”
愛(ài)默生認(rèn)為杜鵑花和玫瑰一樣美麗,但它們低調(diào)謙卑,藏在深林里,被茂密的叢林遮掩,人們很少看到它們的美麗。愛(ài)默生繼而給出自己的解釋?zhuān)好赖拇嬖诓恍枰魏卫碛伞D敲矗瑸槭裁丛?shī)人能欣賞到杜鵑花的美麗?愛(ài)默生指出:是一種神奇的力量讓他來(lái)到杜鵑花的身旁,這種力量同樣促使杜鵑花來(lái)到世間。
這首詩(shī)表明愛(ài)默生開(kāi)始思考人性和大自然的關(guān)系。后來(lái),他的這些觀(guān)點(diǎn)體現(xiàn)在著作《論自然》中。《紫杜鵑》和《論自然》存在多處呼應(yīng)。比如,愛(ài)默生在《論自然》中認(rèn)為物欲泛濫,導(dǎo)致人類(lèi)忘記存在的意義,建議人們最好遠(yuǎn)離喧囂社會(huì),去凝望群星,去面對(duì)自然,去敞開(kāi)心扉……這如同在人跡罕至的荒野里盛開(kāi)的紫杜鵑,不在乎周?chē)沫h(huán)境,不在乎是否有觀(guān)眾,只保持自己內(nèi)心的傲嬌和美好。
“陽(yáng)光照進(jìn)大人的眼睛里,但卻照進(jìn)孩子們的心里。”愛(ài)默生在《論自然》中寫(xiě)道,與兒童不同,大多數(shù)成年人已經(jīng)失去了欣賞自然的能力,而只有最可能看清楚大自然的人才會(huì)成為詩(shī)人。這正如《紫杜鵑》中愛(ài)默生援引的一種世俗觀(guān)點(diǎn)——美因受眾而存在,沒(méi)有受眾,美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價(jià)值。他認(rèn)為,只有純真無(wú)邪的兒童,才會(huì)發(fā)現(xiàn)美、感受美。
愛(ài)默生在《紫杜鵑》一詩(shī)中感慨:“杜鵑啊!如果智者問(wèn)你,這樣的景致為何要留給不會(huì)欣賞的天空與大地,告訴他們,若神是為了看而造雙目,那么美就是自己存在的緣故:你為什么在這里,玫瑰般迷人的花?”
“花是地球的微笑”“花是自豪的斷言,一束美麗的花勝過(guò)世界上所有的設(shè)施”,愛(ài)默生的文字,洋溢著他對(duì)花、對(duì)大自然的熱愛(ài)。今年復(fù)活節(jié)的前一天,我在愛(ài)丁堡郊區(qū)的野山里散步,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大片杜鵑花,不禁想到大洋彼岸愛(ài)默生發(fā)現(xiàn)杜鵑花時(shí)的驚喜。
“入侵”橡木林
隨著東西方的更多交流,杜鵑花也落戶(hù)到了其他國(guó)家。如今,它在各個(gè)國(guó)家的待遇大相徑庭。在保加利亞,杜鵑花被列為稀有瀕危植物,人們對(duì)它關(guān)愛(ài)備至。在西班牙南部,杜鵑花也面臨滅絕的危險(xiǎn)。但在土耳其的東北部,杜鵑花的數(shù)量眾多,并被視為破壞性植物。
而在愛(ài)爾蘭,人們對(duì)它的評(píng)價(jià)是“侵入性物種,嚴(yán)重破壞生態(tài)”。因?yàn)槎霹N花不僅遮擋了本地其他植物的幼苗,而且還分泌化感酸,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長(zhǎng)。同時(shí),杜鵑花的繁殖能力超強(qiáng),一株杜鵑花每年可產(chǎn)生上百萬(wàn)顆輕如塵土的種子,借風(fēng)而行,輕而易舉侵占更多領(lǐng)地。
因?yàn)橥寥馈夂蜻m宜,杜鵑花在愛(ài)爾蘭的生長(zhǎng)肆無(wú)忌憚。人們不得不和杜鵑花展開(kāi)搏戰(zhàn),甚至不得不請(qǐng)求調(diào)遣士兵擺平它們。否則,原本具有生態(tài)多樣性的園區(qū)很有可能淪落成杜鵑花園。最傷腦筋的要屬愛(ài)爾蘭的基拉尼國(guó)家公園,該園的橡木林正一點(diǎn)點(diǎn)被杜鵑花吞噬。
誰(shuí)也不曾想到,美麗的杜鵑花竟然會(huì)成為侵略者,遭人討厭。看來(lái),即使再美的東西,數(shù)量過(guò)多也未必是好的。過(guò)猶不及,適當(dāng)最重要。我不禁想到,在日本吉卜力工作室制作的動(dòng)畫(huà)片《我的鄰居山田君》中,老師寫(xiě)在黑板上、送給學(xué)生們的新年目標(biāo),正是“適當(dāng)”兩個(gè)字。
杜鵑花的一生,原是處處適當(dāng)?shù)摹K谏窖轮屑澎o盛放,直到深谷遇知音,一個(gè)蘇格蘭人帶著它走向英國(guó)、走向世界,世人始知它的美麗;它開(kāi)始被熱鬧包圍,但美國(guó)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愛(ài)默生卻在寂寥中遇到它,為它寫(xiě)下雋永的詩(shī)歌。如今,也有人為杜鵑花的“不適當(dāng)”入侵擔(dān)憂(yōu)。可這一切,何嘗不是人類(lèi)自尋的煩惱呢?100多年來(lái),人們對(duì)杜鵑花、對(duì)新物種的態(tài)度在不停改變,從冷淡到熱寵,不變的其實(shí)是植物、大自然本身。無(wú)論在哪里,無(wú)論是否有知音,只要有土壤、有光亮、有水,杜鵑花都會(huì)歡喜地生長(zh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