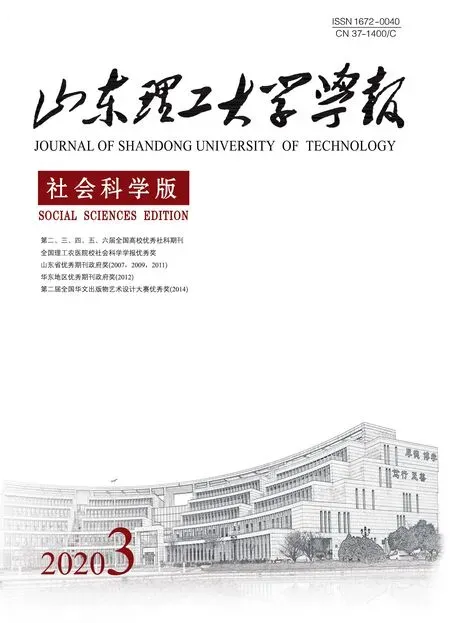基于利他主義理論的我國城市居民慈善捐款利他傾向研究
——以山東省部分城市為例
張進美,厲紅磊,牛喜霞
慈善作為人類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它有助于調節貧富差別,也有助于增加人類福利。2018年11月5日發布的《第五屆中國城市公益慈善指數報告》指出:2017年,221個樣本城市的社會捐贈合計達到了660.14億元,同比漲幅為4.86%,占當年全國捐贈總量的44.01%。隨著近幾年我國城市慈善事業平穩有序地發展,城市居民的慈善捐贈意識和志愿服務量也在穩定增長,很多人都表現出了慷慨的一面,但其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一些問題急需探討與解決,這引起了學術界和慈善領域相關者的持續關注。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思路
(一)問題提出
每一次慈善捐贈,都是一次典型的助人利他行為。但在捐贈中,為何有人愿意多捐而有人一點也不愿意捐?為何有人愿意捐贈給這一批求助者而有人則愿意捐贈給另外一批求助者?為何有人只捐贈給親戚朋友而有人則捐贈給其他陌生人?這些問題的答案都離不開一個問題本質,就是居民慈善捐贈時持有哪種利他傾向。要探清楚這個問題,離不開慈善領域經典理論之一的利他主義理論。
長期以來,利他主義備受倫理學界推崇。19世紀,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第一次提出利他主義(altruism)。利他主義強調他人利益,提倡為他人做出犧牲。在該理論的支撐下,學者對慈善問題的探討不斷有新發現。
早在20世紀80年代,國外一些學者就曾利用利他主義理論研究捐贈問題。如James Andreoni主要構建了“非純粹利他”的捐贈模型,并假定人們可以從捐贈中得到一種“溫暖效應”[1]。與先前的文獻研究結果不同,該模型研究所得到的靜態比較結果表明:慈善的“擠出效應”是不完全的。同時,David C. Ribar和Mark O. Wilhelm通過理論和實證研究得出結論,認為利他動機和基于快樂的動機是個體參加慈善捐贈活動的兩大動機[2]。
在國內,利他主義在慈善捐贈問題上的應用雖不多,但少有的幾項研究也表明了該理論的適用性。朱憲辰和宋妍在其研究中提到:捐贈時,因捐贈者并未直接從捐贈中獲得可排他的收益,即人類行為并非都因自利而發生,所以,將利他偏好或者行為傾向整合到捐贈者的效用函數中,就是捐贈者捐贈的緣由——增加他人效用[3]。
由于借助利他主義研究捐贈問題的文章并不是很多,所以,研究者通過探尋同樣具有利他性的志愿服務問題來汲取借鑒。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一些學者用該理論分析志愿者的志愿行為動機。Smith用志愿服務動機的兩因素模型區分利他動機和利己動機[4];Fitch提出志愿服務的三個動機:利他、利己和社會責任[5];Morrow等則認為志愿服務除了利他動機外,還有社會交往和獲得物質利益兩方面的動機[6]。國內學者關于志愿服務動機的研究起步較晚,最近幾年的研究主要是結合汶川地震、奧運會、世博會、世園會等大型事件來研究志愿者參與志愿服務的動機,如張俊指出,利他主義是志愿服務的理論根源,城市志愿者參與動機主要分為理想奉獻型、互惠利他型、回報傾向型、盲目跟風型等四種類型[7];董海軍和倪赤丹則借用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分析出志愿者參與活動的動機從低到高依次為:親和動機、利他動機、結群動機、榮耀動機和成就動機[8]。
綜上所述,利他主義被關注以來,已有不少學者從不同學科視角用它來探究慈善相關問題。分析城市居民慈善捐款時所持有的利他類型,驗證捐款利他傾向對捐款行為的影響程度,從根本上采取相應措施來推動更多人將捐款傾向轉為實際捐款行為,便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標。我們以設計利他傾向變量并細化為不同利他傾向類型為研究開端。
(二)研究思路
慈善捐款利他傾向是一種捐款動機,也是一種捐款狀態,這決定了該問題的研究難度,所以,研究者嘗試借助利他主義理論作為基礎,通過設計具體測量題目進行問卷調研,借助統計分析軟件對定量數據進行分析來探究慈善捐款利他傾向相關問題。對此,本研究計劃調查500個受訪者,基于第三屆中國城市公益慈善指數排名情況(臨沂為七星級慈善城市,青島為五星級慈善城市),按照人口規模成比例抽樣原理,結合2015年青島市、臨沂市和淄博市三個城市的市區人口規模,各個城市應抽取樣本量=各城市人口數/三個城市人口總數(1023.22萬人)× 擬抽取總樣本量(500人)。最終,這三個城市分別應抽取的樣本量個數為224人、130人、146人,合計500人。
經過嚴謹而相對科學的問卷調查后,獲取了492份問卷,但由于部分問卷缺失值過多或個別選項人為理解錯誤等原因,剔除了12份無效問卷,最終收獲有效樣本480份,問卷有效率為96%。接下來,研究者借助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定量分析和研究。
二、居民慈善捐款所持利他傾向的基本類型
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為:“利他有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分別是自然形態的‘親緣性利他’,普通狀態的‘互惠性利他’和信仰狀態的‘純粹性利他’。”[9]在本研究中,我們按照這種劃分方式將利他傾向劃分為三種:第一,親緣性利他是人性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它是隨著人類繁衍發展而形成的,是人類道德生活的起點。親緣利他性的最典型表現就是人們會自然而然地關愛與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對他們奉獻出自己所擁有的物質和精神。第二,互惠性利他是指人們彼此幫助,但又期待能得到一定回報。這種互惠合作不以經濟利益為前提,而是基于對方處境的同情。第三,純粹性利他是指一個人純粹為了他人利益而從事活動。這種純粹性利他不求任何回報,從事活動僅僅是為讓其他個體獲得益處。
為了測量中國城市居民做慈善捐贈時究竟持有哪種類型的利他傾向,我們設計相應題目分別測量受訪者的親緣利他、互惠利他和純粹利他傾向程度(1)我們設計“在未來一年里,我會在幫助親人之后再量力而行地去救助那些處于困境中的陌生人”一題來測量居民慈善捐贈時的親緣利他傾向程度;通過“在未來一年里,你可能會為了‘能減免部分個人所得稅’或‘日后能得到他人的幫助’而去捐款”一題來測量居民的互惠利他傾向程度;通過“在未來一年里,你向身處困境中的陌生人捐款并不是為了得到回報,只是想讓自己的精神得到滿足”一題來測量居民的純粹利他傾向程度。。每個測量題目都有7個選項,從“1分”到“7分”分別代表“非常不贊同”到“非常贊同”的各個利克特等級。對利他主義傾向各題項進行描述性分析,見表1。
由表1可知,在“幫親人”一題中,受訪者對該題的贊同程度以“4分”為轉折點,且此題項均值為4.61分,總計有54.0%的受訪者作答不低于“5分”。可見,受訪者的親緣性利他傾向還是比較高的,他們認為幫助親人很重要。這一研究結果與我們另一項研究結果相類似(該項研究的調查規模更大,范圍更廣,且研究結果也證實居民的親緣利他程度在慈善捐贈時表現最強)[10]。
表1 居民對利他主義傾向各題項的描述性分析(樣本量=480)

利他傾向1分2分3分4分5分6分7分%%%%%%%均值方差標準差偏度峰度幫親人6.35.813.520.421.514.418.14.612.9911.729-0.327-0.672得到幫助19.811.515.416.716.511.39.03.683.7211.9290.091-1.128精神滿足6.06.79.418.822.317.319.64.753.0281.74-0.489-0.571
在“得到幫助”一題中,46.7%受訪者的作答分數不高于“3分”,且該題項的均值僅為3.68分,相比較其他兩個題項而言是比較低的。可見,大部分人捐款并非為了以后得到他人幫助或者減免稅收。也就是說,他們捐贈時的互惠利他傾向程度并不高。
在“精神滿足”一題中,總計有59.2%的受訪者選擇了不低于“5分”的分數,甚至作答“7分”的受訪者比例高達19.6%,而且受訪者的作答均值是4.75分,即使與“幫親人”“得到幫助”兩題的均值作比較,此題的均值也是最高的。可見,受訪者捐款時所持有的純利他傾向是較強的。與現有的另外兩種利他傾向類型相比,捐款者的純利他傾向要強一些。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利他行為可以用純度和廣度兩個維度來衡量,而廣度又與一個人認同感的范圍和對象相關:認同范圍和對象不同,每個人的認同感強弱也會不同。不同人認同感有強變弱的差異性表現為:對親屬、朋友的認同感最強,然后依次是鄉鄰、階層、階級、民族、國家、種族。在本研究中,廣大居民捐贈時所持的利他傾向類型也與慈善認同有一定相關:在三種利他傾向中,表現最強的是純粹利他傾向,排在第二位的是親緣性利他,最弱的是互惠利他。
既然每個人的利他傾向類型并不同,而且每種類型的強弱程度也不同,那么,這種利他傾向會影響其慈善捐款行為嗎?我們以利他傾向為自變量,以總慈善捐款行為(2)這里對“總捐款行為”這個因變量的測量是指居民個人向陌生人、慈善組織和乞丐等三個大類別捐贈對象所做的總捐款數。為因變量,構建回歸模型:CG=α0+α1AT+ε。其中,CG(Charitable Giving)代表捐款行為,AT代表利他傾向,α0為常數項,α1為解釋變量的系數,ε為隨機誤差。運用SPSS17.0對模型所作的擬合度檢驗結果為:模型R2為0.019,調整R2為0.017,模型的各個參數估計結果見表2。
表2 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模型非標準化系數B標準誤差標準系數tSig.常量-248.555259.395-0.9580.338利他傾向總分 (AT)68.47822.5280.1383.0400.002
由表2可知,該回歸方程結果為:CG=-248.555+68.478AT,從統計學意義上看,利他傾向對捐款行為影響顯著,也就是說,通過居民利他傾向狀況預測其捐款行為是有意義的。
三、利他主義視角下推動居民慈善捐款的建議
本研究以利他主義理論為基礎,不但分析了當前廣大居民的利他傾向類型,而且用回歸分析驗證了利他傾向變量對居民捐款行為存在顯著影響。這從理論層面說明了利他理論應用于分析捐款行為時的適用性和可行性,也為我們利用該研究探尋居民慈善捐款行為提出了依據。
(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基礎,加強現代慈善理念宣傳
當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標語已遍布大街小巷,而且已經建立了大量的宣傳平臺和宣傳途徑,因此,進行慈善理念宣傳時,完全可以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平等、友善”理念與“平等、互助、友愛”的現代捐贈觀念相融合,充分借助社會各界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所應用的各個途徑和各大平臺,加大現代慈善理念的宣傳力度。除此之外,可以借助慈善領域專門宣傳渠道展開,如,各種慈善活動募捐平臺、基金會官網、專業慈善網站等途徑,還可以借助公益歌曲展播等方式。現代慈善意識提倡“博愛、平等、互助、共享”,尤其以“博愛”和“平等”為慈善發展基礎。因為一個人只有“博愛”,才愿意把自己的財富拿出來贈與他人,一定程度上實現與他人“共享”;只有實現捐贈者與受贈者人格上“平等”,才能吸引更多人走上捐助之路,甚至長遠的“互助”之路。
(二)抓住中國式慈善捐贈傾向特點,突破有些居民捐款時僅限于親緣利他的范疇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親緣利他測量題項的作答均值為4.61分,且總計有54.0%的受訪者作答不低于“5分”,即他們贊同要在幫助親人之后再量力而行地去救助那些處于困境中的陌生人。也就是說,不少居民進行慈善捐贈時持有較濃的親緣利他傾向。因此,要促進更多居民參與慈善捐款,就必須抓住這種慈善利他傾向特點。一方面,雖然持有親緣利他傾向者優先選擇親人作為捐贈對象,但是他們確實發生了利他行為,這種利他意識就有助于我們通過充分地慈善宣傳將其動員為捐贈者,從而增加了潛在捐贈者數量。另一方面,汲取中國式慈善捐贈傾向的優點,以親緣圈子中的某個人為出發點來有針對性地推行以熟人圈子為中心的慈善募捐活動。在這樣的親緣圈子中,每當他們看到圈子內有親人發布別人的求助信息時,由于他們互相信任,就更容易被帶動參加捐贈活動或者轉發求助信息,這既提高了他們對圈子內人員的捐贈熱情,也提高了他們對陌生人捐贈的可能性。同時,這種拿錢幫助親人的行為,也是一種互助行為,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地發展。
(三)汲取互惠利他的優點,完善以稅收優惠為主的慈善捐款激勵機制
雖然本研究發現居民的互惠利他傾向是三種利他傾向中最弱的,但它仍然存在,而且《國務院關于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61號)公益性捐贈所得稅稅前扣除作了相關規定:“個人公益性捐贈額未超過納稅義務人申報的應納稅所得額30%的部分,可以從其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11]《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第九章第七十七條也規定: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捐贈財產用于慈善活動的,依法享受稅收優惠。所以,可以依據此政策規定對符合條件的捐贈者進行扣稅。但是,有的人并不了解該政策,有的人“嫌辦理免稅手續太麻煩”,還有的人將善款捐給了不具備扣稅資格的慈善組織,上述種種情況都沒有發揮出稅收優惠政策的激勵作用。因此,應加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等法律法規方面的政策宣傳力度,完善免稅程序,方便于捐贈者扣稅。
(四)借助純利他傾向的強刺激作用,重視精神獎勵對慈善捐款的激勵
由前文回歸分析結果可知,利他傾向會影響居民的捐款行為,且他們捐款時所持的純粹利他傾向最強。而秉持“純粹性利他”者多表現為不追求物質回報,注重精神滿足,這意味著對這些捐贈者進行精神性激勵是可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第一章第八條指出:“對公益事業捐贈有突出貢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由人民政府或者有關部門予以表彰。”[12]《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也指出:國家建立慈善表彰制度,對在慈善事業發展中做出突出貢獻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有關部門予以表彰。因此,慈善組織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充分利用褒獎來促進個人捐贈:對于日常性小額捐贈,可通過網站、廣播、告示欄等不定期發布捐贈告示表揚捐贈者的善舉;對于日常性大額捐贈或特殊情況下的捐贈項目,可以聘請捐贈人擔任慈善組織的名譽性職務,也可以署名立傳,還可以授予“榮譽市民、慈善大使”等榮譽稱號。當然,對志愿服務的表彰也不可忽視。當前,我國每年一度的“中華慈善獎”的評選表彰,就是對突出貢獻的個人和組織在慈善捐贈和志愿服務方面的表彰。我們應繼續完善和實施,并予以廣泛宣傳,號召全社會向其學習。因為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我們可以借助榜樣的力量來帶動更多的愛心匯聚,推動慈善事業發展。
(五)持續長久地宣傳慈善的意義,激發居民更大慈善熱情
對于捐贈人和求助人而言,慈善捐款對于他們雙方都有特定的意義。對于求助人來說,慈善捐款有可能會幫助他們走出當前困境;對于捐款人而言,慈善捐款既是他們在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又可以實現他們自己的捐贈目標。因此,應該通過各種方式持續動員更多人參加慈善捐款,或者借助各種宣傳途徑將慈善意義傳播開來,以吸引更多人成為慈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