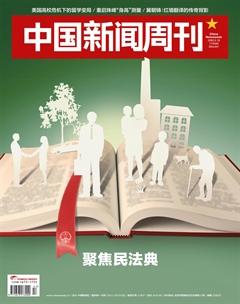打通大涼山脫貧攻堅“最后一公里”:精準施策破貧窮“困局”
岳依桐 湯雁

2020年伊始,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布拖縣烏依鄉(xiāng)阿布洛哈村變得熱鬧起來。過去,受交通條件制約,這個三面環(huán)山、一面臨崖的村莊十分閉塞。村民們外出,需要沿陡峭山路步行約3小時才能到達對外通道公路。
2019年12月31日,阿布洛哈村通村硬化路主體工程基本建成,加上橫跨峽谷的索道,這座中國最后一個不通公路的建制村終于打通了對外通道。最后一公里通村公路也在修建中,預計今年6月前正式通車。
“村里彝家新寨的地基已經(jīng)快要修好,大家都在期待住進新房。不少人買了摩托車,還有村民計劃開小賣部。”阿布洛哈村村支部書記吉列子日說,如今村民外出工作、做生意十分方便,運輸物品再也不用肩挑背扛,步行翻山越嶺。
阿布洛哈村的變化只是涼山彝族自治州脫貧攻堅成效的縮影。幅員面積6.04萬平方公里的涼山是中國最大的彝族聚居區(qū)。新中國成立以后,這里“一步跨千年”,從奴隸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惡劣的自然條件、落后的思想觀念、復雜的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造成了涼山地區(qū)的深度貧困。2015年,中央吹響脫貧攻堅號角,彼時涼山州尚有11個深度貧困縣、2072個貧困村。5年來,通過艱苦卓絕的精準扶貧,涼山州目前已累計實現(xiàn)1772個貧困村退出、80.1萬貧困人口脫貧。
2020年,涼山州吹響脫貧攻堅總攻的號角,將打通擺脫貧困的“最后一公里”,全面完成最后7個貧困縣摘帽、300個貧困村退出、17.8萬名貧困群眾脫貧的任務(wù)。這片廣袤的土地正煥發(fā)出全新的生機。
交通建設(shè)助大涼山“天塹變通途”?
再過兩三個月,金陽縣的“明星作物”青花椒就將成熟。屆時,客商用于收購的卡車將順著公路把青花椒運到中國各地,并出口至韓國、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國家。十幾年前,司機們從涼山州州府西昌到金陽都常常耗費12個小時,有時還得在山中過夜,鮮有外地客商到金陽收購農(nóng)產(chǎn)品。
上世紀50年代初僅靠3條馬幫驛道與外界相連的金陽,是涼山州交通建設(shè)條件最困難的縣之一。受地理條件等因素制約,改善當?shù)亟煌顩r“難上加難”。“生活物資進不來,農(nóng)副產(chǎn)品出不去”曾是當?shù)氐恼鎸崒懻眨煌l件的改善為當?shù)卦杏鲋赂粰C遇,成為民眾脫貧的“金鑰匙”。
“以前路不好,農(nóng)作物只能靠人背出去賣,一次也背不了多少,大家基本就種些土豆、玉米自己吃。”紅聯(lián)鄉(xiāng)沙馬村村民李代秀告訴記者,很長一段時間里,自家一年僅有兩三千元收入。而如今李代秀家承包了30畝花椒地,每年能賺十余萬元,“路好了,東西不愁賣”。
金陽縣交通運輸局局長盧金貴介紹,經(jīng)歷過鑿石開道、炸山修路的艱辛,1961年金陽第一條公路昭金公路建成通車,目前金陽全縣公路里程達1564.674公里,道路通達連接各個村寨。正在修建的宜攀高速、西昭高速途經(jīng)該縣,估算總投資3.4億元的金陽河特大橋也正在建設(shè)當中。
通達道路助力金陽花椒產(chǎn)業(yè)蓬勃發(fā)展。為幫助不斷擴大種植規(guī)模的花椒尋找更多有效銷路,經(jīng)金陽縣紅聯(lián)鄉(xiāng)沙馬村駐村工作隊隊員、成都市公安局軌道公交分局刑警支隊民警何宇牽線,于2019年促成四川省火鍋協(xié)會與金陽縣簽訂收購花椒的意向協(xié)議。今年秋季,四川省火鍋協(xié)會將進行初次收購,金陽花椒將被端上更多食客的餐桌。
啃下交通“硬骨頭”的金陽,不僅將花椒賣到世界各地,也迎來了四方游客。熱柯覺鄉(xiāng)丙乙底村集中安置點是涼山州第一個“大涼山旅游特色小鎮(zhèn)”入選點,直通村口的公路讓當?shù)厥f畝索瑪花田、百草坡、熔巖漏斗天坑群等自然景觀不再“藏在深山無人識”。
熱柯覺鄉(xiāng)黨委書記楊克哈介紹,該村2019年4月正式對外開放,當年接待游客總數(shù)超3萬人次,最多的一天同時迎來200余輛自駕游車輛。“去年依靠旅游業(yè),全村共增收76萬元,隨著基礎(chǔ)設(shè)施和配套設(shè)施不斷完善,我們預計今年旅游業(yè)收入將翻倍”。
“要致富,先修路”。自脫貧攻堅以來,涼山打響“交通大會戰(zhàn)”。2019年初,四川省人民政府印發(fā)《涼山州2019—2020年公路水路交通建設(shè)推進方案的通知》指出,2019年至2020年,四川將投入420億元用于涼山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項目建設(shè),助大涼山“天塹變通途”。
目前,涼山農(nóng)村公路總里程達2.2萬公里,鄉(xiāng)鎮(zhèn)、建制村通暢率均為100%。州府西昌通往各縣的主干道全部改造完畢,縣鄉(xiāng)道得到提升。
教育為“橋”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讀書不要緊,會做活路更重要”的觀念曾一度在大涼山盛行,無數(shù)彝族娃被“困”于深山,還沒看過世界便重復著上一代的生活。貧困的代際傳遞讓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們難以“破局”。
扶貧先扶智,教育扶貧“喚醒”了大山深處的教育需求。金陽縣教育體育和科學技術(shù)局局長爾古子合見證了當?shù)氐淖兓Kf,如今教育在涼山是“熱門話題”,大家討論的都是如何提高娃娃成績,讓孩子讀大學、考研究生,甚至出國留學,從而找到好工作,過上好日子。
作為走出大涼山的大學生,今年28歲的阿史殷菊從成都師范學院畢業(yè)后選擇回鄉(xiāng)教書,成為金陽縣紅聯(lián)鄉(xiāng)中心校的一名老師。看著窗明幾凈的教室、寬敞整潔的操場,這位彝族姑娘不由得感慨,“學校里各種設(shè)施一應(yīng)俱全,我讀書時條件沒這么好,一個班也就二三十個學生,現(xiàn)在我教的班有60多個學生,把教室坐得滿滿當當”。
由于歷史、地理、經(jīng)濟等多方面的原因,四川民族地區(qū)的教育發(fā)展一度嚴重滯后。2000年起,四川先后出臺多項政策,通過大小涼山彝區(qū)教育扶貧提升工程、“9+3”免費職業(yè)教育計劃等舉措,在民族地區(qū)普及九年義務(wù)教育、豐富教育體系,以教育為“橋”,打破貧困“壁壘”,助民族地區(qū)學生“飛更高”。
不斷夯實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為涼山教育發(fā)展打好了“地基”。2012年以來,涼山州累計投入辦學條件改善資金86.3億元。截至2018年底,涼山州共有各類學校1572所。目前,涼山州在校學生達到117.83萬人。
彝族民眾大多普通話(漢語)水平低下,聽不懂老師說什么、跟不上學習進度曾是彝族學生進入九年義務(wù)教育階段后面臨的一道“難關(guān)”。為此,涼山州級財政投入20億元實施“一村一幼”“一鄉(xiāng)一園”工程,修建348所鄉(xiāng)鎮(zhèn)幼兒園,大力開展“學前學會普通話”。目前涼山有“一村一幼”村級幼教點3117個。
這一舉措成效顯著,如今大涼山的學生基本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金陽縣紅聯(lián)鄉(xiāng)中心校一年級學生趙文雯的母親趙元興告訴記者,自己小時候沒有堅持讀書,是人生的一大遺憾。現(xiàn)在趙元興全力支持娃娃讀書,“女兒能讀多久我就供多久,最好考個博士”。

不少彝族民眾通過種植煙葉脫貧致富。攝影/冷文浩

鹽源縣40萬畝花椒成為二半山區(qū)貧困群眾增收致富的支柱產(chǎn)業(yè)。圖為2018年8月13日,鹽源縣衛(wèi)城鎮(zhèn)大寫村群眾的花椒喜獲豐收。攝影/曾成緒
從“要讀書”到“讀好書”,涼山還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教育”,不斷推動優(yōu)質(zhì)教育資源下沉。目前涼山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學校1215所,建成“班班通”教室17000余間,普通高中采用成都七中優(yōu)質(zhì)資源、初中采用成都石室中學優(yōu)質(zhì)資源開展遠程錄播教學,小學則以“本土化”的優(yōu)質(zhì)教學資源為重點開展遠程植入式教學。
特色產(chǎn)業(yè)為民眾脫貧致富“造血”
涼山州晝夜溫差大、日照充足、自然資源豐富,擁有得天獨厚的農(nóng)牧業(yè)、旅游業(yè)等產(chǎn)業(yè)發(fā)展條件。以前受交通條件等限制,當?shù)禺a(chǎn)業(yè)發(fā)展十分困難。隨著脫貧攻堅的持續(xù)深入,涼山州產(chǎn)業(yè)發(fā)展條件愈發(fā)完善。近年來,涼山持續(xù)發(fā)力,破解產(chǎn)業(yè)發(fā)展之困,結(jié)合當?shù)貙嶋H,探索出為脫貧致富不斷“造血”的“涼山密碼”,助民眾持續(xù)增收。
涼山州已脫貧人口中,一半以上都是通過農(nóng)牧業(yè)實現(xiàn)脫貧。在涼山州脫貧攻堅綜合幫扶工作隊的幫扶下,當?shù)靥厣r(nóng)產(chǎn)品如“雷波臍橙”等還遠銷黑龍江、上海、北京等地,甚至走出“國門”。
建設(shè)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園區(qū)是涼山州產(chǎn)業(yè)扶貧的重要抓手之一。近年來,涼山州新建了5個省級培育園區(qū),95個州縣級園區(qū),通過土地租金、園區(qū)務(wù)工、入股園區(qū)建設(shè)分股金等方式,輻射帶動了7.64萬人實現(xiàn)了脫貧,幫助10.3萬人實現(xiàn)增收。
計劃總投資3.25億元的昭覺縣涪昭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產(chǎn)業(yè)園第一期于2019年4月投產(chǎn),截至目前共銷售各類蔬果6000余噸,實現(xiàn)銷售收入1800余萬元。產(chǎn)業(yè)園全面建成后,預計將實現(xiàn)年產(chǎn)值1.2億元,銷售利潤5000萬元,帶動1500戶貧困戶增收。
該產(chǎn)業(yè)園負責人趙繼飛說,利用科技手段,土地畝產(chǎn)值從過去約2000元增至3萬余元。“種植效率提高帶動經(jīng)濟收入增長,同時還能改變民眾觀念,讓他們逐步參與到現(xiàn)代設(shè)施農(nóng)業(yè)的發(fā)展中來,實現(xiàn)長期增收。”
在該產(chǎn)業(yè)園務(wù)工的吉勒阿呷從前僅靠種地勉強維持一家溫飽,如今她不僅每月領(lǐng)著“大棚種植員”2500余元的工資,還有4畝土地在園區(qū)流轉(zhuǎn)。談及變化,這位彝族婦女喜上眉梢,“過去我家年收入不過萬余元,現(xiàn)在日子越來越有‘奔頭,一年下來差不多掙4萬元”。
涼山州地廣人稀,豐富的植被資源也為畜牧業(yè)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2019年,涼山出欄生豬、牛、羊、小家禽分別達444.53萬頭、38.54萬頭、435.38萬頭、2018.48萬只。除了政策支持以外,數(shù)據(jù)背后還是當?shù)孛癖妼γ撠氈赂坏钠谂魏蛯Ξa(chǎn)業(yè)發(fā)展的信心。

涼山州級財政投入20億元實施“一村一幼”“一鄉(xiāng)一園”工程,修建348所鄉(xiāng)鎮(zhèn)幼兒園,大力開展“學前學會普通話”。目前涼山有“一村一幼”村級幼教點3117個。供圖/涼山州委宣傳部

吉好也求一家在新居外合影。攝影/劉忠俊
金陽縣依達鄉(xiāng)瓦伍村探索“高山生態(tài)種草養(yǎng)畜項目”,采取“放牧+補飼”方式科學化開展牛羊養(yǎng)殖,目前村里共有1650頭羊和756頭牛。村莊另一側(cè),5000余畝人工草場正茁壯生長,每畝出草量達4500至6000斤,同天然草場一道,保障牛羊的“口糧”。
依達鄉(xiāng)黨委書記達久烏薩介紹,過去村民大多種植土豆、玉米等作物,每畝土地產(chǎn)值僅1000余元,通過該項目,畝產(chǎn)值增長近5倍。2019年瓦伍村總產(chǎn)值近200萬元,人均純收入達6110元。“大家積極性很高,今年我們將進一步加大投入,擴大養(yǎng)殖規(guī)模,預計今年人均收入將超過1萬元。”
文明新風吹走“看不見的貧困”
“娃娃親”、高彩禮、愛攀比等陳規(guī)陋習曾讓彝族民眾面臨“看不見的貧困”。婚喪嫁娶時,殺幾十頭牛“充場面”的情況比比皆是,哪怕到處借錢也要“充面子”,辦一場婚事可能會掏空家底,甚至因此負債累累,使得脫貧致富“開倒車”。
昭覺縣三岔河鄉(xiāng)三河村村民吉好也求在大女兒吉好有作小時候便為她定下了一門“娃娃親”,十幾年前,這種定親的行為在當?shù)厥謱こ!5ツ辏靡睬笾鲃勇?lián)系對方,為吉好有作解除了“娃娃親”,讓女兒安心學習。
“以前的想法太不成熟了,現(xiàn)在觀念都進步了。”吉好也求不好意思地笑道,“女兒有權(quán)利選擇自己的另一半。我的孩子們只需要好好讀書,做他們喜歡做的事情。”
吉好也求一家的變化并非個例,在物質(zhì)脫貧的過程中,文明新風吹遍大涼山。
昭覺縣解放鄉(xiāng)火普村于2016年創(chuàng)新設(shè)立“道德積分”。村干部定期到村民家檢查,從環(huán)境衛(wèi)生、愛老敬老、鄰里互助等方面進行打分,1分等于1元錢,村民可從村中的“道德銀行”將錢取出,也可用積分到商品齊全的“雄鷹基金超市”換取等值的生活用品。
火普村第一書記馬天告訴記者,從前火普村人畜同寢,地上到處都是牲畜的糞便和各種垃圾。“道德積分”剛推出時,村民們不相信愛干凈、做好事就能賺錢。“現(xiàn)在大家早就養(yǎng)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和道德習慣,見面還會討論彼此又賺了多少分,得分高的人特別有面子”。
除了巧用“道德積分”等舉措外,涼山3745所農(nóng)民夜校還采取集中教學、分片分組教學、上門送學、火塘夜話、現(xiàn)場培訓等多種方式,累計開展脫貧奔康技能、移風易俗、道德法制、掃黑除惡、環(huán)保生態(tài)等培訓8.2萬場次,培訓民眾123.6萬人次。
隨著精神脫貧的不斷深入,走出大山的年輕一代思想變得更加“時尚開放”。今年30歲的布拖縣居民吉斯小鷹告訴記者,未來自己不會以彩禮數(shù)額的多少為兒女選擇另一半,“這種觀念早就過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