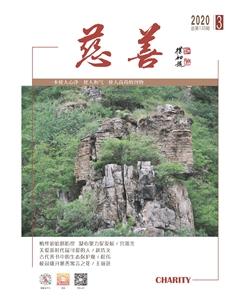古代善書中的生態保護觀
程偉
善書即勸人向善之書,自宋以來在民間逐漸流行,其內容包括儒家的忠孝友悌、佛教的慈悲果報、道教的積德無爭等理念。善書語言淺白,圖文并茂,通俗易懂,流通廣泛,至清代曾“遍于州縣,充于街衢”。善書多以生活事例為題材勸化世人,內容包羅萬象,不僅倡導人與人之間的互助救濟,更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將破壞生態列為惡行
善書通常將人的日常生活細節分列為善行或惡行,以此規勸世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約成書于北宋末的《太上感應篇》是我國最早的勸善書,其列舉的善行有二十多條,惡行約一百六十多條。該書提出“慈心于物”,慈心謂慈愛之心,倡導“不獨遠近親疏之人,待若同胞,即飛潛動植之物,亦視為吾與”,告誡世人“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太上感應篇》所列舉的惡行明確提到“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用藥殺樹”“春月燎獵”“無故殺龜打蛇”等,將肆意傷害動植物歸入惡行之列。約成書于宋明時期的《文昌帝君陰騭文》教人要“救蟻”“濟涸轍之魚”“救密羅之雀”“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等。清初的《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也教人要“戒殺放生”“利物救民”,反對“宰殺牛犬”。古代善書汗牛充棟,而尤以《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和《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三部善書最受尊崇,因三部善書傳播之廣、影響之大和注釋之多,自清代始就已被稱為善書三圣經,后世新出現的善書或對其進行圖說、注釋,或常將此三書刊于篇首,奉為圭臬。
功過格是善書的重要一類,主要將人的善(功)與惡(過),采用量化的形式進行計算統計,以此規勸世人,積功累德。功過格最初為道士自記個人善惡功過的簿冊,明朝末年,功過格在民間開始流行,指導普通民眾進行道德實踐。在各種勸善功過格中,愛惜物命、保護生態常被劃入“功”的行列,無辜濫殺、破壞自然屬于“過”的范疇,功與過的大小視不同的情形有所區別。如《太微仙君純陽呂祖師功過格》規定:“救一無力報人畜命,一功”“救一有力報人畜命,十功”“殺細微十命,一過”“填覆一巢穴,二十過”。《匯纂功過格》中規定:“勸阻一殺龜打蛇,三功”“勸化一屠牛者改業,不惜出財助其資本,準五十功外,更論錢多寡,或不必還,或不取利,另照例記功”。
通過報應故事警戒破壞生態者
人的福禍與善惡行為緊密相連是勸善書的一個基本觀點。《太上感應篇》開篇即道:“福禍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南宋大儒真德秀生平喜好刊刻善書,其在為《太上感應篇》作序時指出:“顧此篇指陳善惡之報明白痛切,可以扶助正道,啟發良心”。善書在民間廣泛傳播,不僅在于其內容直白生動,更在于其宣揚的善惡報應學說貼近百姓心理需求,具有強烈的啟迪意義。事實上,善惡報應理念在我國早期典籍中已有記載,如《周易》中“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書》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等,這些理念與后來道教的賞善罰惡和佛教的因緣業報思想結合,在善書中得以繼承和發揚,對民間百姓止惡向善形成強大的驅動力。
善書常舉破壞生態、殘殺生靈遭受惡報的事例來告誡世人,應對自然界鳥獸草木懷敬畏和悲憫之心。清初的《太上感應篇圖說》中曾詳述一事: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名姓,專好攫取飛禽,或賣銀錢,或恣口腹。善用鳥銃,殺傷甚多。年四十無子,忽產一兒,頭角端正,心甚愛之。此人因得子之后,改悔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就塾,偶因膳師之饌,復持鳥銃打取飛禽,以供飲食,日復一日。又有年余,一日其子忽患痘疹,滿身紫泡,延醫視之,不解何癥。皮肉焦爛,每一毫孔內有鐵珠一粒,如是者不計其數,哀號痛哭而死。
類似這樣因殘殺生靈而遭惡報的故事在善書不勝枚舉。此外,正如這一故事中所述,個人的善惡行為不僅關乎個人福禍,更會延及子孫。所謂“近報在身,遠報子孫”,在重視血緣和子嗣延續的傳統社會,“報及子孫”無疑對個人具有強大的警醒和震懾作用。
借助民間信仰勸人敬畏天地
古代善書常假托神仙降筆,以民眾所信奉的神仙名義勸化世人,如《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中的關圣帝君原型為三國時期的關羽,其死后經通俗文學的塑造和帝王的封賜,逐漸成為神通廣大的仙人,廣為民眾供奉和祭祀。明清時期,民眾對關帝的信奉從遍布各地的關帝廟中可見一斑。清代文人趙翼在《陔余叢考》中說,“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關帝)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古代善書正是借助于民間信仰的神圣性,強化其說教內容的權威性,《關圣帝君覺世真經》中勸誡世人要“敬天地,禮神明”、不可“宰殺牛犬,穢溺字紙”,并提出:“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若負吾教,請試吾刀”。此外,《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太微仙君功過格》《呂祖功過格》等諸多善書均假借神仙口吻勸人常懷敬畏天地之心,以增強傳播效果,達到勸善止惡的目標。
以通俗詩歌、俚言宣揚保護生態
為便于傳播,讓文化程度不高的鄉民也能知曉善書中的理念,通俗詩歌、俚言常被運用于善書中,成為勸善止惡的重要體裁。乾隆年間善書《慈心寶鑒》專門收錄真德秀、蘇軾、云棲大師等歷史人物關于勸誡殺生的詩文,其在序言中寫道:“萬物在天壤間,莫不貪生而畏死。人奈何但知己之生而全不念物之死”,里面收錄白居易的《戒殺詩》寫道:“世間水陸與虛空,總屬皇天懷抱中。試令設身游釜甑,方知弱骨受驚沖”,這些都表達了萬物一體,痛鰥切身的理念。善書中所述萬物,不局限于動物,也包括植物,所謂“草木盡屬生靈,蛾蟻都關佛性”“毀垣而發蟄,覆巢以毀卵”等行為都應避忌。
除了詩文,歌謠、俚言更易于口耳相傳,成為護佑生命,保護生態的勸善手段。清代善書《化愚俗歌》收錄了十八個主題的勸善歌謠,“重牛犬”“寶五谷”成為其中兩個重要門類。云棲大師的《戒殺俚言》寫道:“飛禽鷹雀等鳥,走獸虎狼一切,世間只有人狠,射箭捕網打獵,水類田雞螺絲,黃鱔鳥魚鰍鱉,分明不害于人,何苦將他命絕”,語言通俗直白,在民間流傳較廣。
綜觀古代善書中的生態保護觀,其中雖不乏一些神異的描述,但仍有不少合理成分至今具有啟迪意義,如倡導尊重生命,遵循自然規律,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的理念。善書倡導保護生命,但并非杜絕人類一切正常需求,而是主張遵循自然規律,適度利用自然資源。《太上感應篇》中提出“是道則進,非道則退”,衡量是否符合“道”的重要關鍵是天理和人心,所謂“順天理合人心,坦平正直即是道也。逆天理,拂人心,荊棘險嶇,即非道也”。譬如前述的“春月燎獵”,因燎獵濫殺蟲豸無遺,且春月正是草木復蘇,鳥獸繁殖之時,“天方生之,我輒戕之”,有違天道。
日本學者酒井忠夫指出,善書“表現了宋以后中國民眾的主體性規范意識”。善書在中國歷史上存在近千年,其曾對民眾的日常行為和觀念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至今仍或隱或顯的存在,深入研究善書中的慈善文化,全面挖掘其內涵,汲取其中的積極成分,對構建當代慈善文化,促進當代慈善事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