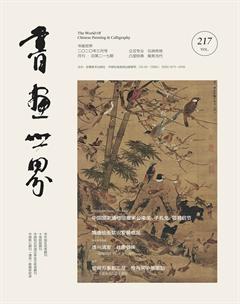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宋公欒戈、子孔戈、鄂君啟節
馮峰



編者按:2018年伊始,安徽美術出版社與中國國家博物館聯袂推出《中華寶典——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法帖書系(第一輯)》,本刊從2018年第一期開始,陸續刊登了法帖部分內容,受到讀者的歡迎。現第一輯已介紹完畢,從2018年第十一期開始,本刊繼續刊登本書系第二輯和第三輯的內容,包含宋拓顏真卿《東方朔畫贊碑》《劉熊碑》、民國拓《元顯雋墓志》等精良拓本,以及董其昌行書《贈張旭、題盧道士房詩卷》、文天祥草書《謝昌元座右辭卷》等珍貴墨跡本,希望廣大讀者能喜歡并提出寶貴意見。
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4件東周時期的器物宋公欒戈、子孔戈和2件鄂君啟節,銘文皆以錯金工藝制成,極具特色。
宋公欒戈長22.4厘米,傳1 936年安徽壽縣出土。援上揚,中起脊;闌側有三穿;內上有一穿,末端上角圓而下角內凹,內的兩面飾錯金變形獸紋。胡部有錯金銘文6字,一面4字,一面2字。宋公欒即宋景公(前516-前469在位),因此戈的時代為春秋晚期。
宋公欒戈的錯金銘文是所謂“烏篆”體, “宋”“公”二字上附加烏首等紋飾,全銘字形修長,筆畫宛曲,多加肥筆。“烏篆”體流行于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的楚、蔡、宋、吳、越等國,是—種獨具風格的美術字體。
子孔戈長22.7厘米,1957年于河南陜縣后川2040號墓出土。形制接近宋公欒戈。內兩面均飾錯金的雙線云紋,胡部有錯金銘文10字。做器者子孔可能就是后川2040號墓的墓主,他應是前453年三家分晉后魏國的—位高級貴族。
子孔戈銘文字體端正秀麗,風格不同于“烏篆”體,別有韻味。
鄂君啟節是戰國時期楚王下令鑄造并頒發給封君鄂君啟的銅節,以作為后者進行商業活動的免稅憑證。鑄造時間據銘文可知為“大司馬昭陽敗晉師于襄陵之歲”,這一年相當于公元前323年,距今已有2340余年。
銅節現存5枚,均出土于安徽壽縣丘家花園(1 957年出土4枚,1960年出土1枚),可分“車節”和“舟節”兩組: “車節”3枚,長約29.6厘米,銘文148字(合合文三、重文一);“舟節”2枚,長約30.9厘米,銘文164字(合合文一、重文一)。原有5枚,可合為竹筒形。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車節”和“舟節”各1枚。
兩組銅節的銘文在記錄相同的鑄造背景后,分別詳細地規定了在車行(陸路)和舟行(水路)兩種交通方式下鄂君啟運輸貨物可免稅通過的地點(交通路線),以及免稅的限制,對研究戰國時期楚國的符節制度、交通地理和商業政策等方面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需要指出的是,鄂君啟節銘文中的許多問題,學術界曾長期有爭議。有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如關于鄂君啟之封邑鄂(水、陸交通路線的起點)的地望,一向有東鄂(在今湖北鄂州)和西鄂(在今河南南陽)兩說,有學者將“舟節”銘文中的“ ”成功隸定為“油”并讀作“淯”后,西鄂說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2012年南陽夏響鋪春秋時期鄂侯墓地的發現,又為此說提供了關鍵性的證據。再如兩組銘文中均有的關鍵字“ ”,曾被釋為“庚”等,在有學者根據西周金文和戰國楚簡的材料將其隸定為“就”、訓為“至”后,西鄂說也逐漸得到了公認。但有的問題尚未解決。如“舟節”銘文中的免稅限額單位“究竟是何字、有何含義顯然至關重要,但至今沒有確切的解釋。再如兩組銘文中均有的“”、“車節”銘文中的地名“ 禾”之“ ”等字,也不清楚該如何隸定。這些疑問都有待學術界的進一步研究,特別期待有助于解決問題的地下新材料的發現。
鄂君啟節是楚懷王親自下令鑄造的楚國高等級青銅制品,其銘文在已知的東周楚國青銅器銘文中是篇幅最長者,用語習慣和文字的特征都具有顯著的楚國色彩。青銅器上的錯金工藝始于春秋晚期,盛行于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另外錯金銘文的總體數量不多,字數一般較少。鄂君啟節“車節”和“舟節”的銘文分別為148字和164字,是目前已知字數最多者(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的欒書缶銘文字數僅次于鄂君啟節,48字),顯示出高超的工藝水平。銘文排列齊整,字體優美,是精美的書法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中華寶典——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法帖書系(第三輯)-宋公欒戈、子孔戈、鄂君啟節》收錄銅器銘文的釋文力求進行最合理的隸定,但力有未逮。在體例方面需要說明的是,有些字后面有帶括號的字,代表這些字通常的(或在傳世文獻中的)寫法;若括號內的字加“?”,則代表只是可能的通常寫法,并不完全肯定。有的字后面的括號內只有“?”,代表該字的隸定本身就是存疑的。有些字還不確定如何隸定,因此在釋文中照錄它們在銘文中的原狀。2枚鄂君啟節的銘文摹本采自《殷周金文集成》。
本欄目圖文選自安徽美術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的《中華寶典——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法帖書系(第三輯).宋公欒戈、子孔戈、鄂君啟節》,《中華寶典》叢書項目為“十三五”國家重點出版物出版規劃項目。
約稿、責編: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