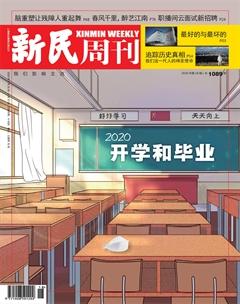小時(shí)候吃膩

胡展奮
小時(shí)候被我們吃膩的當(dāng)然不會(huì)是翅參鮑肚。那時(shí)過(guò)節(jié)才吃肉。那時(shí)只要聽(tīng)見(jiàn)樓下的“阿三”哭——那種哭是炸雷型的,現(xiàn)在賭場(chǎng)有種叫“炸金花”的,不知是不是——我就知道他們家的餐桌上紅薯了。這東西上海人喜感地叫“山芋”,有“栗子山芋”,聞起來(lái)香香的,吃口就是寡淡的淀粉,吃快了,胸悶;吃多了,泛酸。有“糖心山芋”,山芋中的貴族,外皮紅紅的,內(nèi)里黃心或紅心,吃口噴香而且蜜甜,但是事后泛酸更厲害,胃里像醋缽打翻,而且越好吃,越泛酸,反酸的結(jié)果必然是痛苦的“燒心”,弄堂里無(wú)數(shù)人因此落下了胃病。
所以那些日子往往樓下阿三哭了,我們也跟著哭,家長(zhǎng)們憤怒地責(zé)罵我們,說(shuō)我們“嚎喪”。哪里知道,那時(shí)候還有大量吃山芋藤的,甚至連山芋藤都吃不上的。
世事難料,小時(shí)候吃膩的東西不知何故,現(xiàn)在統(tǒng)統(tǒng)變臉了。
當(dāng)然,那幾乎是六十年前的事了,每個(gè)月規(guī)定25日是買(mǎi)大米的日子,大家備好“購(gòu)糧證”去排隊(duì),問(wèn)題是家家的大米都挨不到“25日”那一天的,常常20日左右就沒(méi)米了,于是雜糧登場(chǎng),遠(yuǎn)遠(yuǎn)地,我們看了就哭,誰(shuí)叫我們還是不懂事的孩子呢?
小時(shí)候吃膩的還有“面疙瘩”。計(jì)劃大米是不夠吃的,除了山芋,我們常常吃面疙瘩,母親先放點(diǎn)鹽,把面粉拌得像厚漿糊一樣,燒沸了水,一勺子地刮成手表大小,甚至更大些,丟進(jìn)沸水,熟了撈出,就是“面疙瘩”,油花,幾乎是看不見(jiàn)的,偶爾滴一點(diǎn)麻油或豬油,那可要仔細(xì)聞,耐性聞,才能聞到。弄堂里,面疙瘩大普及,使很多玩伴的綽號(hào)就叫“面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