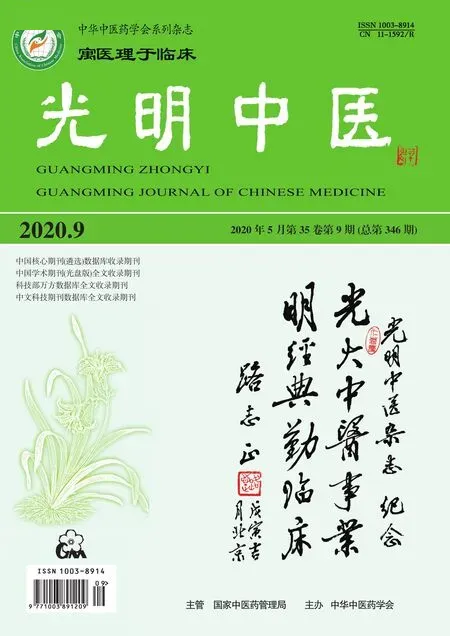穴位電刺激對腦缺血后大鼠臂叢神經細胞凋亡的影響*
林菊珊 蔡 楠 楊代和△ 張世欣 吳雅婷 謝步霓 潘曉鳴 廖遠生
肢體疼痛是腦缺血后常見并發癥,發生率高達30%以上[1],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肢體疼痛的產生與神經損傷密切相關[2]。前期研究證明,穴位電刺激可抑制大鼠脊髓背角及脊神經后根細胞凋亡,緩解疼痛癥狀[3]。臂叢神經是上肢疼痛傳導通路,目前穴位電刺激是否影響臂叢神經細胞凋亡尚未知,本研究通過腦缺血再灌注大鼠(MACO)模型,觀察穴位電刺激曲池、足三里對大鼠臂叢組織中Caspase-3、Bax和Bcl-2表達及神經細胞凋亡的影響。
1 材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120只雄性SD大鼠(400~450 g)隨機分為3組,每組40只,假手術組(S組)、缺血再灌注組(I/R組)和電刺激組(EA組)。3組都用10%水合氯醛0.5 ml腹腔注射麻醉,消毒大鼠頸部皮膚,從頸部正中線作縱行切口(約2 cm),鈍性剝離,暴露左側頸總動脈、頸外動脈和頸內動脈。S組,逐層縫合皮下筋膜及皮膚,未進行其他處理; I/R和EA組造腦缺血再灌注模型,在頸總動脈近分叉位置剪開“V”形小口,將3-0單股尼龍線從小口插入(提前在尼龍線上做好刻度標記,頭端磨鈍,并用10%L-賴氨酸浸泡),經頸總動脈分叉處插入頸內動脈,以頸動脈分叉為起始,插入深度為(1.5±0.5) cm,縫合切口,栓塞1 h后取出尼龍線,蘇醒后提尾,以右前肢屈曲或爬行向右側劃圈為腦缺血再灌注造模成功標志,I/R組未進行其他處理,EA組給予“曲池”“足三里”穴位電刺激治療。分別于實驗前(T0)及實驗第1天(T1)、3天(T2)、7天(T3)、14天(T4),通過電子測痛儀觀察并記錄大鼠疼痛閾值。于T1、T2、T3和T4各取10只大鼠處死,取出右側臂叢神經,采用Western blot檢測大鼠臂叢神經中Caspase-3、Bax和Bcl-2蛋白的表達。
1.2 方法
1.2.1 穴位電刺激方法 自然光照,室溫控制(22±3) ℃。每天9:00—9:30和15:00—15:30將3組大鼠放置于自制固定裝置,暴露四肢及尾部。馬冉冉等[4]研究認為通過電針刺激患側”曲池”“足三里”,可抑制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后炎癥級聯反應,本研究中EA組選取上述穴位,將華佗牌28號1寸毫針(蘇州醫療用品有限公司)插入患側“曲池”“足三里”,入皮5 mm,毫針接LH-800型韓式穴位神經刺激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制造),用疏密波(頻率2~15 Hz,強度1 mA)進行穴位電刺激。從造模成功后第1天開始,每天上午、下午各1次,每次30 min。S組及I/R組則不進行穴位電刺激。
1.2.2 觀察指標 ①疼痛閾值檢測。用Von Frey電子測痛儀(IITC Life Science公司,美國)檢測各組大鼠造模前、造模后T1、T2、T3和T4時患側足底機械縮足反射閾值(mechanical withdrawal threshold, MWT)[5]的變化,記錄各組大鼠疼痛閾值。②Western blot檢測Caspase-3、Bax和Bcl-2蛋白表達。取標本放入組織裂解液中勻漿,離心后取上清,即為組織塊用冷TBS洗滌3次,去除血污,剪成小塊置于勻漿器上。加入10倍組織體積本試劑(使用前數分鐘配制,cocktail+磷酸化蛋白酶抑制劑),徹底勻漿;將勻漿液轉移至1.5 ml離心管中振蕩,冰浴30 min;以12000轉離心5 min,收集上清為總蛋白溶液;灌膠,上樣加足夠電泳液后電泳,待電泳至溴酚藍剛出時終止電泳,進行轉膜;在脫色搖床上將轉好的膜用5%的脫脂牛奶(0.5%TBST配)封閉1 h。稀釋一抗(TBST溶解的5%脫脂牛奶),4 ℃過夜。在TBST脫色搖床上洗3次,每次5 min。用TBST稀釋二抗3000倍,室溫下孵育30 min,在室溫下在TBST脫色搖床上洗3次,每次5 min。將膜蛋白面朝上與混合液充分接觸,1~2 min后,去盡殘液,包好后放入X光片夾中曝光。將膠片掃描,用Alpha軟件分析目標帶的光密度值,用相對灰度值代表蛋白表達情況(相對灰度值=待測蛋白灰度值/β-actin灰度值)。
1.2.3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用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組內比較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組間比較采用成組樣本t檢驗。
2 結果
2.1 一般行為學觀察 3組大鼠一般情況良好,體質量穩定上升,3組比較無顯著差異性表現。I/R組和EA組大鼠均出現提尾右前肢屈曲或爬行向右側劃圈,但EA組大鼠患側前肢屈曲及爬行向右劃圈等癥狀得到一定改善。I/R組大鼠死亡2只,EA組大鼠死亡1只,實驗過程中對應補齊數據。
2.2 疼痛閾值結果 3組大鼠實驗前MWT無明顯差異性(P>0.05);S組MWT實驗前后無明顯差異(P>0.05);與組內T0比較,T1、T2、T3和T4時I/R組和EA組MWT更低(P<0.01);與S組比較,T1、T2、T3和T4時I/R組和EA組MWT更低(P<0.01);與I/R組比較,T3和T4時EA組MWT更高(P<0.05或0.01)。見圖1。

圖1 各組大鼠MWT比較
2.3 Western blot檢測臂叢神經細胞Caspase-3、Bax和Bcl-2蛋白表達結果
2.3.1 臂叢神經細胞Caspase-3蛋白表達結果 S組大鼠臂叢神經細胞Caspase-3蛋白表達實驗前后無差異(P>0.05);與組內T1比較,T2、T3和T4時I/R組和EA組Caspase-3蛋白表達增強(P<0.01);與S組比較,T1、T2、T3和T4時I/R組和EA組Caspase-3蛋白表達更高(P<0.01);與I/R組比較,T3和T4時EA組Caspase-3蛋白表達更低(P<0.01)。見圖2。
2.3.2 臂叢神經細胞Bax蛋白表達結果 S組大鼠臂叢神經細胞Bax蛋白表達實驗前后無差異(P>0.05);與組內T1比較,T2、T3和T4時I/R組和EA組Bax蛋白表達增強(P<0.05或0.01);與S組比較,T1、T2、T3和T4時I/R組和EA組Bax蛋白表達更高(P<0.01);與I/R組比較,T3和T4時EA組Bax蛋白表達更低(P<0.01)。見圖3。

圖2 各組大鼠Caspase-3比較

圖3 各組大鼠Bax比較
2.3.3 臂叢神經細胞Bcl-2蛋白表達結果 S組大鼠臂叢神經細胞Bcl-2蛋白表達實驗前后無差異(P>0.05);與組內T1比較,T2、T3和T4時I/R組和EA組Bcl-2蛋白表達降低(P<0.05或0.01);與S組比較,T1、T2、T3和T4時I/R組和EA組Bcl-2蛋白表達降低(P<0.01);與I/R組比較,T3和T4時EA組Bcl-2蛋白表達更高(P<0.01)。見圖4。

圖4 各組大鼠Bcl-2比較
3 討論
大鼠臂叢神經由C5~8和T1前支組成,包括傳入和傳出神經纖維,支配前肢的感覺和運動功能。腦缺血后引起對側肢體癱瘓和功能障礙,本研究采用左側頸內動脈插入尼龍線,制作腦缺血/再灌注大鼠模型,表現右前肢偏癱,在運動中偏癱肢體自我保護能力差,并且容易受傷,導致偏癱側肢體臂叢神經損傷。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導致交感神經和傳入神經偶聯會產生惡性循環,增強患側肢體交感神經的興奮性,造成局部組織發生營養障礙,引發患側肢體疼痛[6]。袁群芳等[7]研究認為,臂叢神經損傷,可以導致脊髓前角運動神經元細胞的損傷及死亡,并對前后角的功能起到了損傷作用,發生神經性疼痛。本研究發現,穴位電刺激組比腦缺血/灌注組疼痛閾值高,與前期研究相符,穴位電刺激能降低腦缺血/灌注損傷大鼠的脊髓背角神經細胞凋亡,穩定脊髓背角神經細胞功能的作用,調節疼痛信息的傳遞,減緩神經病理性疼痛發作[3];也可能與穴位電刺激可以下調中腦導水管周圍灰質、中縫背核、中縫大核中孤啡肽受體mRNA的表達,提高體內腦啡肽和內啡肽效力,起到鎮痛效果有關[8]。
中醫學認為,疼痛的病機在于各種原因造成的氣血運行障礙,“不通則痛”;氣血虛少,“不榮則痛”。針刺是中醫的特色療法,電刺激穴位能有效緩解急慢性疼痛,療效得到國內外認可。“曲池”“足三里”穴是治療肢體疼痛的常用穴位,電刺激穴位鄰近神經以及周圍血管,改善局部血液循環,減少炎癥和滲出,緩解疼痛癥狀[9]。
Bax和Bcl-2基因在細胞凋亡調控過程中是一對重要的調控基因,它們功能相互對立,Bax促進細胞凋亡,而Bcl-2則可通過多種途徑抑制細胞凋亡,而Caspase-3在細胞凋亡過程中則是關鍵的凋亡執行蛋白酶。有文獻報道,電針對腦缺血后內源性神經干細胞的增值、分化和修復方面有一定的調節作用,針刺治療可下調Bax的表達,上調Bcl-2水平,提高Bcl-2/Bax的比值,抑制Caspase-3的活性,抑制神經細胞凋亡[10,11]。Wang Y等[12]研究認為神經損傷可促使小膠質細胞活化和促炎細胞因子IL-1β釋放,誘發神經源性疼痛超敏反應,產生持續性神經病理性疼痛,2 Hz穴位電刺激能增加脊髓神經傳導通路上α-7煙堿乙酰膽堿釋放,抑制脊髓小膠質細胞活化和促炎細胞因子IL-1β釋放,從而改善大鼠腦缺血再灌注損傷,促進神經細胞修復,起到鎮痛效果。本研究2-15 Hz穴位電刺激組比腦缺血/再灌注組臂叢神經細胞中Caspase-3和Bax表達更少,Bcl-2表達更多,凋亡細胞更少,表明穴位電刺激可以減少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大鼠臂叢神經細胞凋亡,并且可能通過臂叢神經α-7煙堿乙酰膽堿釋放,抑制臂叢神經小膠質細胞活化和促炎細胞因子IL-1β釋放,從而促進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大鼠臂叢神經修復,以及癱瘓肢體康復。
總之,對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大鼠“曲池”和“足三里”穴位進行電刺激,可以提高疼痛閾值,緩解疼痛,減少臂叢神經凋亡,促進臂叢神經修復,可能與調節凋亡相關蛋白Casepase-3、Bax和Bcl-2的表達有關,但其中詳細的細胞分子機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