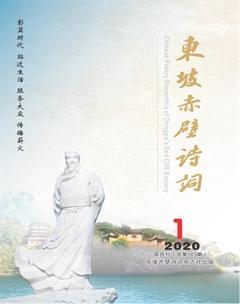抗疫情
劉立玉
“每臨大事有靜氣”,于詩人似乎不宜。不要說真正的詩人,就是一般的愛好者,往往是激動型的,甚或是沖動型的,凡大喜大憂大憤慨,他們便策詩馬,登詩山,駕詩舟,穿詩海,一往無前,一發而不可收拾。何也?情之所系,性之所致。
君不見,正值庚子攜春至,卻被一個從天而降的怪物——新型冠狀肺炎撞了個趔趄。其傳播之烈,擴散之廣,全社會面臨的挑戰壓力之大,觸目驚心,駭人聽聞,世所罕見,甚或絕無僅有。而抗擊之猛,動員之眾,施策之精,耗費之巨,魄力之大,信心之足,打了一場九州昂首、友邦瞠目、鬼魅飲恨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戰爭,令無數人夜不能寐、涕泗橫流、感慨萬千,亦令詩者詩泉噴涌,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 是也。我也忝列其中。“國之不幸我心寒,一摞詩箋折紙船。雷火凌空燒個透,送它瘟疫上西天。”作為年近耄耋的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唯將詩稿寄前沿”,只能敲敲邊鼓,喊喊加油。“抗疫甚于鋼對鐵,爭分奪秒何曾歇。白衣天使是鋼刀,削鐵非泥贏慘烈。” 這首詩, 便是我對這場戰爭最初的預判和粗略的紀錄。
君不見,在“九省通衢爆肺炎,開門待客暫無緣”,患者爆滿、一床難求的初戰之期,正是一些人悲觀之時,我寫道,“抗疫夜來常失眠,淚泉酸澀染毫端。行間字里聲聲喊,不信江城夢不甜!”并特意說:“號令一聲傾廣宇,信心就是小湯山!”
君不見,每一次苦難就是一所學校,每一次大災就是一次大考。這一次也不例外,各行各業,各路人馬,強迫入校,天價應試,成績如何?我寫道:“誰施高壓甚高考?生死攸關疫命題。一紙遺言鈐手印,渾身解數解狐疑。降妖出入盤絲洞,采藥攀爬蝎子區。陽春閱卷曬金榜,撣盡煙塵是白衣。”金榜題名者誰?非白衣天使莫屬。是他們,仁心仁術,大愛無疆,用超乎人力的神力在支撐著,用超乎人性的神性在奮斗著,真乃實至名歸。
君不見,在這場人民戰爭中,無論國內外、省內外、軍內外,英雄輩出,前赴后繼,不拘一格,可歌可泣。“男兒有淚不輕彈,淚眼婆娑淚不干。多少英雄多少事,忽然一座小湯山。”作為抗疫生力軍、主力軍的醫護人員,更值得大書特書。就群體而言,他們“戎裝素裹戰猶酣,扼斷冠魔器宇軒”。他們“舍命擒瘟疫,銜枚解倒懸”。
就個體而言,則星光璀燦,數不勝數,而我毫不猶豫首選了他。誰呀?請看這首散文詩(節錄),《一個響亮的名字——鐘南山》:正值談冠色變時,來了鐘南山,快人快語建諍言:病毒傳人人傳人,守土封城防擴散。用他耄耋的偉岸,將新型肺炎阻攔,用他無字的論文,寫滿患者的笑臉。令那名利客羞愧,教那昏庸者汗顏。他把人奉為天,人把他尊為仙,真可謂“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他,就是一座山,一座小湯山,敢教冠魔化輕煙。院士之愿啊,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綠如藍。啊,鐘南山,鐘情人民,不老南山!
有人評價,他有院士的專業,戰士的勇猛,更有國士的擔當。這是恰如其分的。在一方刻有鐘南山精美雞血石印章上,我留下一行詩:“江漢夜空光燦燦,該留名者永留名。”
當然, 還有“金銀潭里一神龍,以身許國是初衷”的院長張定宇,和不計其數的無名英雄。
有這樣一家抗疫人:“從醫獨子近荒唐,借故蔽屏奔武昌。父母曾經紅小鬼,潸然一笑共裝佯。”
有這樣一位捐款人:“曾經擠出早餐錢,非典時期正讀研。千萬莫留名與姓,疫情似火烙心尖。”解囊千萬而隱其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君不見,一位重癥病患老農民,硬是被白衣天使從死神手里搶了回來。其再生之情喜于言表,其感激之情難以言表,遂請醫護人員摘下面罩,以便日后相認拜謝。此情此景,我用拙筆記錄于次:“一介農夫搶救中,奈何橋斷夕陽紅。出艙識得東風面,濁淚橫流三鞠躬。”
還有這位倔老漢:“小子宅家裝醉態,一聲臭罵鎖茅臺。是誰喋血陰陽界?老漢踉蹌祭掃來。”表達的是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凄凄悲凉,是對抗疫英靈的依依不舍和崇高敬意。
對那些不守規矩自我解禁者,我用委婉的口吻勸導:“隔窗弱柳欲勾魂,豈許花心撬后門。抖落嚴冬殘夜夢,甩開大步沐陽春。”聽者是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屈原)?尚不得而知。
大疫當前,許多詩人句句血,字字淚,顯初心,有擔當。而有個別的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顧左右而言他,令人費解,難免腹誹:“逆天肇事關家國,淡墨輕描抗肺炎。得句春游微信上,情商停在幼兒園。”
在這度日如年的非常時期,不知不覺竟得詩三十余首,花居多,也有刺,不得已而為之。請看,這里,有私分抗疫捐贈款物且自鳴得意案;有販賣抗疫急需物資牟暴利被罰幾十幾百萬元案,我都分別給予了關切:“冠狀與貪官,黑心猶爛肝。任憑他沆瀣,看我一鍋端。”“甚于非典萬重霾,生死存亡物價抬。國家不幸誰家幸?竊喜趙公元帥來。”
還有比上述更為惡劣的誤導延誤疫情案。我毫不客氣地還以顏色:“曾拜杏林神圣地,者番抗疫墜煙云。細看柳葉刀尖血,人不傳人種禍根。”(注:《柳葉刀》乃世界權威醫學刊物)
更有甚者,是少數昏庸無能而又剛愎自用的決策者,他們擅長掩蓋真相,掐滅良知,讓卑鄙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成為高尚者的墓志銘。我痛心疾首,哽咽無語:“老漢宅家心火燒,忍看鬧市半枯焦。人無遠慮憂患近,教訓焉能打水漂?”教訓啊教訓,血的教訓,人財物的損失,無法估量,無法挽回。天災與人禍,? 一加一大于二。更有一雙雙陰森森狼眼盯著我們,“趁你病,要你命”。
“歷史給人們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來都不會汲取歷史的教訓。”(黑格爾)正所謂“事出反常必有妖”,若不弄清來龍去脈,若引不來集體的反思,教訓依然故我,等于零,甚至零下。因為,它還可以按下復制鍵、粘貼鍵。否極泰來,禍福倚伏,絕非自然而然。因此,必須“揮淚斬馬稷”,讓那些德薄而位尊、智弱而謀大、力小而任重的附骨之疽,到他應該去的地方去,以平民憤——不能白受這場罪!否則,“多難興邦”便是麻醉劑,自欺欺人。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我與疫情漩渦中的武漢市民感同身受,陪他們驚心濺淚。我以絕句為主,因為它短小精悍,易記易懂,符合戰時特點。我注意盡量不寫全景式的,因為境界不高,眼界不寬,駕馭文字能力不強。我力圖避免雷同,因為有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須放開眼光,用盡腦髄,另辟蹊徑。我把大量的贊美,主要傾注在不計報酬、不論生死的白衣天使身上。因為,他們的中國精神,中國力量,無不來自黨、國家和民族基因,是間接的直接,是不言而喻的,力避“俗熟”和“概念化”之嫌。這次,一個詞火爆——逆行,我在運用時格外注意:“不見硝煙未響槍,分明戰火蔓城鄉。逆行何只上甘嶺,最愛白衣黃繼光。”把它和英雄黃繼光連在一起,似乎貼切而富有新意。我提醒自己,要注意戰疫的重要節點及其亮點,比如習主席2月10日視察北京,圍繞他盛贊武漢及其人民的“英雄”二字,填《采桑子》一首:“當年抗戰今防控,金鳳翱翔,黃鶴翱翔,啄爛冠魔心肺腸。? ?神兵天降爭分秒,苦也昂揚,死也昂揚,忘我贏來春卉香。”
我還注意到,詩詞如文章,“非實不足以闡發義理,非虛不足以搖曳神情,故虛實常宜相濟也。”(清·唐彪)回頭審視,作品如何?姑且不論,《圣經》說,用淚水播種,必收割歡喜。是耶,非耶?
人們熟記了清朝趙翼的“國家不幸詩家幸”,并大加引用,以致被一些人垢病攻訐,認其為幸災樂禍,或成為偽詩人泛濫、泡沬詩橫流的推手。其實誤解了。他緊接著說,“賦到滄桑語始工”,似乎更重要:滄桑往往來自于不幸,就看你寫不寫得出滄桑來。國難不因詩家生,也不為詩家滅,但它確能催生精品,包括這次的抗疫詩,連同捐贈品上的詩詞引用,譬如郎平的“四海皆兄弟, 珍重待春風” 就恰到好處。
我寫抗疫,我要寫抗疫,我要寫好抗疫,寫出它的高度、深度、溫度、精準度和滄桑感,作為我對這段歷史的側記和剪影,對白衣天使尤其是抗疫英烈們的些許報答,也是對我心靈的拷量與慰藉。但愿不是一廂情愿。
有人愛說:“天佑中華”。“天”謂何物?何“佑”之有?君不見,幾十天來,黨政軍民學,鋼筋混凝土;東西南北中,峽江拉纖繩。“何方蘋果何方橘?滿口生津香撲鼻。串串淚珠嵌枕巾,入夢山呼好兄弟!”
全國一盤棋,血濃于水,絕非虛言,重疫區受捐贈者無不感激涕零。“此生無悔入華夏,來世再做中國人”,肺腑之言,共同心聲。
我們終于勝利了,盡管是慘勝。能抿一口喜悅,我問心無愧。因為,我也是參與者,是志愿者,是精神醫護員,而不是局外人士旁觀者。
有人愛說:每個冬天的句號,都是春暖花開。也不盡然,也許還有倒春寒。直到拈花一笑時,也不應忘了這句話:誰在凱旋時戰勝自己,誰就贏得兩次勝利。故在歡送援鄂醫療隊凱旋時,我寫道:“敢欺黃鶴太猖狂,惹惱白衣拼命郎。一針扎破毒王膽,轉戰家鄉再逞強。”拈一個“再”字,強調“戰斗正未有窮期”。但愿只是杞人憂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