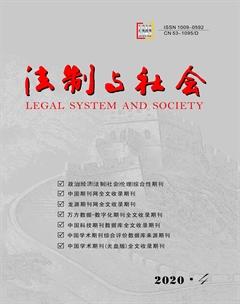協議選擇管轄制度中的“實際聯系原則”研究
關鍵詞 國際民商事訴訟 協議選擇管轄制度 “實際聯系原則”
作者簡介:章璐,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
中圖分類號:D9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014
國際民商事交往,特別是商事交往中,當事人為預判其交易風險,保證糾紛的順利解決,往往為雙方可能發生的爭議案件達成選擇管轄法院之協議。當事人選擇的法院是不是必須要與當事人或爭議存在實際的聯系是該制度中爭議最多且司法實踐中處理差異較大的問題。大陸法系國家普遍持聯系說,即要求被選擇法院與爭議存在實際聯系,而英美法系國家則大多持“非聯系原則”。我國2017年6月27日修訂的《民事訴訟法》沿用了2012年《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對“實際聯系原則”持肯定態度,列舉了包括原、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簽訂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
一、“實際聯系原則”的理論依據
現實中,當事人的地位往往不完全平等,“實際聯系原則”的目的在于保護弱勢一方當事人的利益,以及防止當事人的選擇對國家司法管轄權造成侵害。一方面,如果當事人協議選擇了與案件無任何關聯的法院管轄,訴訟過程中會存在諸多不便,如取證困難、審理效率低等,甚至判決結果最終無法得到實際執行,結果反而損害了當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當事人通過選擇管轄規避本國管轄,造成對本國司法管轄權的侵害,或者給被選擇國家帶來不當的司法負擔。
二、“實際聯系原則”缺乏統一適用標準
對于《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列舉的五種情況之外的地點是否屬于有實際聯系的地點,即該條款中“等”字如何解釋,最高人民法院并沒有給出明確意見。因缺乏統一的適用標準,故而在審判實踐中,各地法院適用該原則時存在諸多困難。實踐中往往更依賴于法官個人的主觀判斷,從而導致選擇管轄協議的適用存在不確定的法律風險。
比如,當事人同時選擇該國法律為準據法是否使得該國獲得“實際聯系”,司法實踐中就存在不同的認識。在中國江蘇某公司與阿聯酋某公司買賣合同管轄權異議案中,最高院認為,當事人以瑞士法律作為準據法,瑞士與爭議在法律上就產生了實際聯系,故協議管轄條款有效。而在我國山東某公司與新加坡某公司買賣合同管轄權糾紛再審案中[1],雖然當事人在選擇英國倫敦法院為管轄法院的同時選擇英國法為準據法,但最高院認為,當事人未能證明英國與本案爭議存在實際聯系,故協議管轄條款無效。
三、“實際聯系原則”之反思
意思自治原則是協議管轄制度的理論基礎,然而,具體到某一實際的國際民商事交易往來,其關聯國度往往數目有限,因此,“實際聯系”的要求實際上將當事人可以選擇的法院限定在一個很小的范圍,這樣還何談意思自治呢?
(一)“實際聯系原則”可能構成對當事人權益的侵害
如前文所述,“實際聯系”原則的出發點是為當事人而考量,即防止當事人濫用選擇權,在沒有考察的情況下隨意地選擇法院,導致訴訟出現許多不便。選擇與爭議有關的法院,可便于當事人進行諸如調查取證等訴訟活動,降低訴訟成本,節約訴訟時間,方便應訴及執行等;而選擇與爭議毫無關聯的法院管轄,則該法院拒絕受理案件的可能性大增,當事人的選擇很可能落空。
然而,訴訟是否便利應該是協議管轄制度的首要考量嗎?事實上,相比方便與否,當事人所重視更多的是司法是否公正公平。國際民商事交易往來中,當事人必然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或地區,而與交易有實際聯系的地點往往僅涉及雙方當事人各自所屬國。在商定管轄條款時,強勢一方當事人極有可能提出選擇其本國法院管轄的條件。而對任何一方當事人來說,到對方當事人所在國訴訟,意味著可能面對地方保護主義帶來的困擾,且對方當事人對其本國司法體系、法律制度的認知水平一般是大大優于己方的,到對方國進行訴訟,己方必然會處于天然的劣勢,因此,在選擇己方所在國無望的情況下,相較于強勢方所在國,弱勢一方當事人當然更希望選擇中立第三國法院管轄。在我國山東某公司與韓國某公司網絡游戲代理及許可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案”中[2],雙方當事人通過多次協商最終選定由新加坡法院管轄,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地方保護主義導致的不公。而“實際聯系”的規定會讓當事人不能選擇絲毫沒有聯系的中立的第三國法院管轄,當事人的內心懷著對這類不公平的懼怕,必然影響商業談判,對商事來往的開展非常不利。又或者,弱勢一方為了達成國際貿易,不得不服從于強勢一方的要求,選擇對強勢一方有利的法院,這種選擇反而損害了弱勢一方當事人的權益。可見,“實際聯系原則”雖以維護當事人權益而提出,卻實際導致了當事人無法真正根據自身需求自由選擇的結果。
協議管轄制度是意思自治原則在管轄權領域的具體表現,而要求所選法院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無疑是對意思自治的強烈限縮。所以,“實際聯系原則”與協議選擇管轄制度在本質上是背道而馳的。只有讓當事人進行合理、自由的選擇,才能實現國際貿易的締約,才能促進訴訟的正常進行,并最終有效地解決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爭議。“一國法院應當摒棄‘家父心態,相信合同當事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將選擇法院的利益衡量和合理性判斷留給當事人”。[3]當事人是其本身利益最大化的決策者,自會綜合考慮訴訟是否便利、管轄法院是否具有類似案件的審判經驗、訴訟效率如何、裁決是否可以執行等。當事人最終作出的選擇必然是其全面衡量之后作出的最佳方案,立法如何保證自己的預設比當事人的考慮更合理,在個案中更有利于當事人呢?更何況,隨著互聯網技術、增強現實技術等科技的發展,各國在線上視頻庭審、電子證據調取審查等遠程審理程序方面都作出了不少探索和創新,所謂的不便程度越來越低,法院是否便利也不再是當事人選擇法院時的首要考慮。當事人的選擇或是條約兩方達成彼此讓步的成果,或是信賴被選擇法院的公平或其審判經驗。立法應當給予當事人充分的處分權,立法給與當事人越大的選擇空間,則當事人作出的選擇就可能越能平衡交易雙方的需求。
總而言之,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取消“實際聯系”要求會讓當事人擁有更加自由廣闊的選擇空間和范圍,可以實現當事人對被選擇法院公正性、中立性、專業性、便利性的綜合需求。
(二)以“實際聯系原則”維護國家司法權益并無實際必要
“實際聯系原則”要求當事人無論是選擇外國法院管轄,還是選擇本國法院管轄,都必須要符合實際聯系要求。從國家的角度來剖析,堅持“實際聯系”或為維護本國司法主權,或為減輕本國司法負擔。本文認為,上述二者,其實均無必要。
一國要求協議選擇的外國法院符合實際聯系要求,是為了避免本國的管轄權被管轄選擇協議任意排除。但是,管轄選擇協議本就是契約自由在管轄權領域的延伸,因此,在保護當事人意志自由和維護管轄權之間,立法必須要權衡輕重,并適當取舍。通常情況下,在個案中,當事人選擇他國法院管轄,為的是其私人利益的最大化,當事人處分的只是其私人權利,不構成對本國管轄權的侵蝕。更何況,各國國內法為了保護本國權益,大多限定選擇管轄協議不得違背專屬管轄及公共秩序保留,因而,再作出“實際聯系”之限定其實沒有必要。
一國要求選擇本國法院的協議符合實際聯系要求,則一般是出于對法院負擔的考量。但是,對各個法院的負擔作出預先判斷并非法律的任務。有學者認為,經濟機制在法院的負擔均衡方面將大大抵消協議選擇法院管轄任意性的負面影響。[4]是否需要花費更多的金錢和時間,忍受更多的不便去選擇與爭議毫無關聯的第三國法院管轄,這樣的問題交給當事人在個案中考慮即可。顯然,并非所有當事人都愿意承擔更多的費用、付出更多的時間、花費更多的精力去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處理糾紛。因此,從持非聯系說各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允許當事人自由選擇也并未給其司法帶來太重的負擔。
一般來說,當事人在衡量“性價比”后仍然選擇與爭議無關聯的法院,一般是因為信服該國的司法體系或豐富的審判經驗。即使會給該國司法造成負擔,卻能提高該國司法權威性,擴大國際影響力。英國法院在實踐中更傾向于接受當事人的選擇,雖然表面上英國為此付出了有限司法資源的代價,但是卻吸引更多外國當事人來英國解決爭議,并且通過對各類國際商事案件經驗教訓的吸取,確立了自己在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的領先地位,也維護了自己在國際商事領域的優良名譽。為服務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大局,提升我國司法制度形象,我國不妨接納與我國無關聯的爭議案件,推進我國法制發展,樹立專業高效的司法形象,使我國司法競爭力和影響力得以提升和擴大。
四、結語
2005年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通過的《選擇法院協議公約》已于2015年10月生效。我國于2017年9月簽署該公約,成為該公約第33個締約國。雖然尚未獲得國內批準,但我國參與了該公約的起草、談判過程,批準該公約并不會損害我國利益,且對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有正向促進作用,故公約的批準應為大概率事件。該公約起草過程中,就“實際聯系原則”的取舍也曾有過重大分歧,最終該原則未被寫入公約。通過本文討論,我們可以看到,“實際聯系原則”侵犯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間,也不利于國際民商事交往爭端的解決。當事人選擇的管轄法院與爭議無關聯時該選擇是否有效,只要賦予法院自由裁量權即可,無需由立法預先強制劃定選擇范圍。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書(2011)民提字第312號.
[2]山東聚豐網絡有限公司與韓國MGAME公司、天津風云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網絡游戲代理及許可合同糾紛管轄權異議案[J].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10(3).
[3]焦燕.法院選擇協議的性質之辯與制度展開[J].法學家,2011(6):169.
[4]孫邦清.民事訴訟管轄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