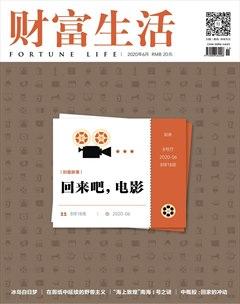荔枝小傳
游星
荔枝的風靡史


荔枝原產于我國南方亞熱帶地區,根據歷史地理學家的考察,最早的野生荔枝群落大致分布在今天的嶺南一帶。野生荔枝果實極為酸澀,經過馴化之后誕生了可以人工栽種的良種,果實甜度提高,并因其數量稀少而味道獨特,最終成為了嶺南地區向朝廷進貢的珍品。
荔枝最早被稱為“離支”,“支”同“枝”,見于西漢司馬相如的《上林賦》中:“于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奈厚樸,梬棗楊梅,櫻桃葡萄,隱夫薁棣,答沓離支,羅乎后宮,列乎北園。”當時的荔枝作為漢武帝破南越的戰利品而被帶到上林苑中栽培,《三輔黃圖》中記載了此事:“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后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十人。遂不復蒔矣。其實則歲貢焉。”由于水土不服,荔枝在長安未能栽培成功,漢武帝只能每年通過南越之地的歲貢才能嘗到荔枝的滋味。因為荔枝極易腐敗,一旦離枝,數日之后便不能食用,就漢代的交通條件而言,這種進貢可謂是勞民傷財,范曄在《后漢書》中如此形容進貢荔枝的艱難:“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為此東漢有一段時間為了民眾休養生息而停止過荔枝的歲貢。東漢的王逸曾經做過一篇《荔枝賦》專門贊美荔枝,晉人郭義恭在《廣志》對荔枝有更為細致的介紹:“荔枝,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蓬蓬然,冬夏郁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味。夏至日將已時,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百斛。”荔枝之珍奇和美味俘獲了當時上流社會的心,但由于運輸和保存的困難,普通百姓并無多少機會品嘗到這種珍貴的水果。
此后荔枝的栽培擴展到四川地區,巴蜀之地由于和長安的地緣更為親近取代了原產地嶺南成為唐朝時期荔枝的最大產地,荔枝也逐漸為普通民眾所知,張九齡等初唐詩人創作了不少荔枝相關的詩作,為荔枝打開了知名度。得到楊貴妃的青睞可以說是荔枝的高光時刻,也令它和這位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美人一樣,從此蒙上了一層悲情和傳奇的色彩。為了能使楊貴妃吃上最新鮮的荔枝,朝廷專門開辟了一條自涪州(今涪陵)到長安的驛道,被稱作“荔枝道”,確保當地的荔枝能在三日之內到達長安以供貴妃享用。安史之亂后,唐朝國力大為衰退,從巴蜀向京城進貢荔枝的做法也漸漸湮滅不聞。
及至宋代,全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江南和閩地成為朝廷歲貢的重點地區,福建地區取代巴蜀之地成為貢品荔枝的主要產地。福州、泉州、漳州三地的荔枝都被選為貢荔,同時海路運輸的發展和荔枝保鮮技術的革新讓荔枝貢品的種類有所增加,不僅進貢荔枝干、荔枝煎和圓荔枝等荔枝制品,還可以進貢生荔枝,將快要成熟的荔枝移植到木桶之中送往京城,等到達朝廷,荔枝正好成熟。到了南宋,王朝南渡使得福建的荔枝更受達官貴人的青睞,當時有“(荔枝)閩中第一,蜀川次之,嶺南為下”的說法。

清代廣東地區經濟地位的提升使嶺南的荔枝產業重新煥發了生機。陳鼎和徐渤燦都曾寫過《荔枝譜》,記錄的廣東荔枝大約有100多種,其中公認品質最好的是東莞出產的莞荔,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里如此描述當時廣東荔枝貿易的盛況:“南海、東莞多水枝,增城多山枝。每歲估人鬻者,水枝七之,山枝三四之。載以栲箱,束以黃白藤,與諸瑰貨向臺關而北、臘嶺而西北者,舟船弗絕也。”其中的“水枝”指的是近水種植、夏至前成熟的品種,“山枝”指的是靠山種植、夏至后成熟的品種。每年的端午節前后都是廣東荔枝固定的交易季節,臺灣出產的荔枝也在交易之列。
傳奇背后:一位美人與一群文人
如今荔枝已經是人們司空見慣的水果,但在相當漫長的時間里,荔枝都無愧于“珍果”和“仙果”之稱。古人很早就發現了荔枝一旦采摘離枝便會迅速腐敗的特點,白居易曾在《荔枝圖序》中說:“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新唐書·后妃傳》中記載:“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為了能讓楊貴妃吃上新鮮的荔枝,唐王朝不惜大興土木建造了專門的驛道。貴妃的青睞讓唐代的貢荔之舉愈演愈烈,等到安史之亂平定,原本只是作為珍果被歌詠的荔枝被視為唐王朝勞民傷財的象征而成為了諸多詠史和諷刺詩的主角,并永遠和一位美麗、任性又悲情的女人聯系在了一起,“妃子笑”也成為了最著名的荔枝品種之一。
后世的文人們往往在詩中提及楊貴妃嗜好荔枝招致禍亂的故事以諷時世,這對沒有實權的后宮妃子未免過于苛責,也令荔枝成為了古代文學中一項特殊的意象。杜甫就曾多次以荔枝入詩來勸諫朝廷改變勞民傷財的歲貢政策,他在《解悶十二首》中用四首詩的篇幅來寫荔枝,開啟了后來文人墨客們借荔枝來詠懷的先河,其中最著名的自然當屬杜牧那首《過華清宮》。在這些沉重的話題之外,杜甫在對荔枝的審美上也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他在《宴戎州楊使君東樓》中寫道:“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此后“輕紅”往往被引用來指代荔枝。唐代的荔枝相比于現在味道更偏酸一些,因此有“紅顆酸甜只自知”(杜甫《解悶·其三》)一說。一貫熱愛美食的白居易自然也留下了許多和荔枝有關的詩篇,他對荔枝不吝贊美之詞,將其比作“嚼疑天上味,嗅異世間香。潤勝蓮生水,鮮逾橘得霜。”(《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他還經常設宴用荔枝來款待親友賓客。
宋代書法家蔡襄堪稱福建荔枝的推廣大使,時任福州太守的他曾編撰了詳細的《荔枝譜》,記錄了三十多種荔枝品種,認定“今莆陽荔枝遂為天下第一”,莆陽即今天的莆田一帶。沈括《夢溪筆談》如此描述閩地荔枝: “閩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令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牙。”由此可見當時福建地區已經有相當高的荔枝栽種和培育水平。蘇軾那首膾炙人口的《惠州一絕》所記的乃是宋朝時并不出名的惠州荔枝,被貶的詩人雖然吃不到公認品質最好的閩荔,嶺南的荔枝同樣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宋代皇室也同樣癡迷荔枝,據《三山志》記載,宣和年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植宣和殿”,宋徽宗賜詩云:“蜜移造化出閩山,禁御新裁荔子丹。瓊液乍凝仙掌露,降苞初綻水精丸。酒酣國宴非珠粉,風泛天香轉蕙蘭。何必紅塵飛一騎,芬芬數本座中看。”可惜在開封培育荔枝的愿望很快隨著北宋的覆滅而煙消云散了。

吳俊卿荔枝圖扇頁圖 / 故宮博物院網站
清代的貢品荔枝大多出自福建和廣東,選擇長勢較好、即將成熟的荔枝栽培在木桶中,沿途用清水澆灌保持新鮮,裝船從海上溯流而上直達京師,到達之時荔枝正好成熟,能讓皇室品嘗到最新鮮的荔枝,不過這種方法往往因為路途顛簸,能保存下來的成熟果實寥寥。乾隆朝的一次歲貢中,乾隆皇帝本人也只吃到了4顆荔枝,還為此寫下了《荔枝至頒賜朝臣而有感》一詩:“閩中佳實秋前到,相對年年有所思。酬節只供原廟薦,承愚非復寢門時。飛來嶺外炎風送,斜倚欄邊揭露垂。料的擎歸舊鴛侶,幾多歡喜幾多愁。”可見一直到清朝中期,荔枝仍是非常昂貴和稀有的貢品。
荔枝百味,生活如蜜
荔枝之所以能在古代躋身于珍果之列,除了本身保存不易、運輸艱難之外,還在于其滋味甘美,外形鮮潔,吃起來有種特殊的風味。為了襯托身價的高貴,荔枝就連名字都透著格外的雅致。徐渤燦曾指出:“惠州荔枝味酸,樹亦甚少,至東莞漸多漸佳。”他在所著的《荔枝譜》中記載了當時東莞最著名的兩種荔枝:一名“公孫” ,“產東莞,每蒂一大一小,土人呼為公領孫,皮薄、核小、肉厚。”;一名“萬里碧”,“產東莞戴家園,皮色碧如中秋雨后天,與葉色不同。味甘香,肉潤滑,成熟皮色不變。”這兩個品種的命名雅致生動,頗有意趣。

道光年間《廣東通志》記載:“廣州荔以掛綠為第一品;十八娘并驅玉露霜產于新會厓門,明月珠產南海番禺山中,在掛綠之次;妃子笑產佛山;萬里碧產東莞戴家園;驪頂珠產順德龍巖山;珊瑚產清遠山中。粵中荔枝掛綠為最,福州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云,廣南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隨著荔枝栽種規模的擴大,各地都有了自己的代表品種,并認定本地荔枝的品質最佳。
《本草綱目》中認為荔枝“甘,平,無毒…… 止渴,益人顏色”,荔枝肉、荔枝殼和荔枝核都能入藥,可以用來治療痘瘡或者咳嗽,但因其性熱不宜多吃。現代醫學表明,荔枝含有豐富的果糖、維生素C 和植物蛋白,能夠緩解疲勞、消腫解毒,促進微細血管的血液循環,光滑皮膚,減少雀斑,因此荔枝自古以來便深受女性喜愛。
荔枝的吃法眾多,除了生吃之外,還可以白曬做成荔枝干,或者腌制成蜜餞和果脯食用。荔枝也是糖水甜品中的常用配料,荔枝雞蛋糖水是嶺南地區最常見的糖水甜品之一。這種用水果入饌的傳統可以上溯到宋朝,《山家清供》中就已經有了“糖荔枝”和“荔枝膏”等做法,還有一道“百花釀荔枝”直接拿荔枝入菜,做法也不復雜:將荔枝去殼去核桃,撒上生粉,釀入調味好的蝦餃,用蛋白和蟹黃依次封口,上鍋蒸大約四分鐘取出,勾芡即可。如今的創意餐廳中有不少主打荔枝菜肴的,包括蟹肉芝士荔枝球、荔枝黑豚扒、包心荔枝肉、荔枝紅茶鵝肝等等。無論時代如何變遷,荔枝仍舊在書寫著屬于它的美味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