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力與大國崛起
賈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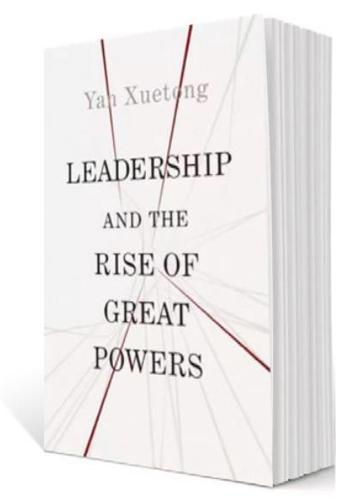
《領導力與大國崛起》
閻學通著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2019年4月
古希臘詩人阿爾基羅克斯曾留有詩句,“狐貍知道許多事,而刺猬只知一大事。”這個寓言曾激起20世紀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的無限想象,他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與狐貍》中對此詳加闡釋,認為歷史上大凡留有名氣的思想家莫不可分為兩大陣營:狐貍善于觀察,可以同時追逐多個目標,它們的思維跳躍而靈活;刺猬則固守一隅,頑強且執(zhí)著于某個目標,他們的思路穩(wěn)健而保守。這就是思想史研究中著名的伯林兩分法。
冷戰(zhàn)史名家加迪斯在其近著《大戰(zhàn)略》中同樣對伯林兩分法抱有濃厚興趣。和所有標榜客觀立場的歷史學家相似,加迪斯對非此即彼的思考路徑不以為然,在他看來“狐貍與刺猬的性格根源在于,缺乏對彼此間的關懷與理解”。
那么這兩種思維模式能否共存?答案自然是存在的,那就是把刺猬般的方向感和狐貍獨有的敏銳性有機結合起來,能夠同時培養(yǎng)這兩種素養(yǎng)的土壤,叫做常識。
這種常識簡單來說,就是告訴自己和他人,你要走什么路,同時也知曉路上會遇到什么障礙;但沒有關系,你的狐貍式快思維與刺猬范的慢思考將使你能保持前行,直至抵達目標彼岸。加迪斯認為,這也是真正大戰(zhàn)略思維的精髓。
以上提及的人物與圖景,皆為閱讀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的英文新著 《領導力與大國崛起》(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過程中所浮現的。這部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UP)出版的英文專著,亦是普林斯頓-中國研究叢書最新推出的研究力作。概而言之,本書將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傳統(tǒng)的外交實踐相結合,將考察視野擴及人、國家、體系三個層面,并指出崛起國家的政治領導力將決定該國在這三個層面上能否走向成功。
更為形象地說,這是一位深耕國際關系理論本土化的刺猬型學者的多年思索與理念建構。這種解讀自然是簡略和單向度的,是建立在忽略學者生命歷程后做出的事實判斷。
或許更可如此表達,每一只能夠思考大問題的刺猬背后,都會閃現一只試圖解決急迫問題的狐貍身影,它們都會被遠方無盡的地平線所深深吸引。
刺猬依然還是刺猬
1952年出生于天津的閻學通身上有著鮮明的人民共和國烙印。他的青春歲月與新生國家的動蕩起伏息息相關,弱冠之年被時代洪流所裹挾,投身于北大荒無邊無盡的黑色土地之中,崇高的革命理想與冷峻的現實生活歷練出這代中國學人獨有的刺猬品質:他們的人生困惑與思想追求交融為一體,即使生命機遇發(fā)生重大轉軌,過往的痕跡依然清晰可見,并在日后的學術歷程中愈發(fā)凸顯其厚重與執(zhí)著。
上世紀90年代在加州伯克利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時,已近不惑之年的閻學通就在思考中國未來崛起的戰(zhàn)略方向與理論可能,這在彼時的學術界堪稱星辰大海般的議題。柏林墻崩塌與華盛頓共識興起,使得多數人都樂于接受美國治下的國際秩序,并認為這將是一個長期與不可逆的過程。閻學通對此持相反意見,他在目睹美國秩序如日中天的時候就開始為中國在新世紀崛起做純學術探討,并由此撰寫一系列研究著作,而本書便是其所倡導的“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的集大成之作。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大國崛起在中國主流話語體系中是隱匿和缺位的,甚至被刻意回避。即便閻學通早在1998年就公開提出這一概念,該詞匯也要到十年以后,在北京奧運與次貸金融危機共同震撼世界的時刻,才讓全世界多數人意識到這種戰(zhàn)略前瞻的特殊意義。
閻學通堅持認為,中國的國際關系與戰(zhàn)略研究界缺乏規(guī)范理論和科學實證的強力支撐;建立在西方話語之上的國關學術流派可以部分解釋中國崛起的戰(zhàn)略選項與行為偏好,但存在顯著的水土不服。
2005年閻學通加盟清華大學后,能夠有更多充裕時間進行閱讀和思索,并開始對中國歷史上的先秦時代及其思想產生濃厚興趣。從西周開始到春秋戰(zhàn)國時代直至秦一統(tǒng)六國,這段歷史對于絕大多數國人而言再熟悉不過,但對其中的戰(zhàn)略、思想理路習而不察。對閻學通而言,這些豐富的思想資源卻好比第二次思想解放。
先秦時代中國士人的天下觀、戰(zhàn)爭觀、治理觀與以近代500年為標尺的西方國際關系思想圖譜在腦海中匯聚成川,傳統(tǒng)中國的道義思想與現代國際治理規(guī)范得以穿過時空而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治理新資源,并由此產生宏闊的道義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思想輪廓。
經過上述思想解放之后,閻學通先生從其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精深造詣出發(fā),將中國外交實踐,尤其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外交思想,納入到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視閾,跳脫出西方中心主義及中國本位主義的束縛,在相當程度上推進了中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融匯與溝通。
伴隨著中國外交和對外政策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的蓄勢待發(fā)與巨大轉變,道義現實主義愈發(fā)顯現出其強大的闡釋力量,并引發(fā)廣泛共鳴。
領導力的四種類型
在《領導力與大國崛起》中,閻學通再次系統(tǒng)而有力地闡釋何謂道義現實主義。
在當今世界通行的國際關系理論三大流派中(現實主義、理想主義、建構主義),現實主義具有最為悠久的歷史,它更為強調在一個以無政府主義為顯著特征的國際政治舞臺中,國家間交往的首要原則就是維護國家利益,人類歷史上的諸次慘烈戰(zhàn)爭與締結和平都是國家間利益博弈后的產物。
現實主義的理論優(yōu)勢在于它比其他兩派理論能更好解釋國家間的行為邏輯與利益取舍,但它無法解釋國家間為何存在主導大國與崛起大國的秩序轉變。閻學通的辦法是引入政治領導力(political leadership)這個新變量維度。所謂政治領導力,也就是一國的政治領導團隊駕馭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判斷、執(zhí)行與評估能力。閻學通再三強調,這種政治領導力并非建立于對單個政治人物的性格把握,而是客觀評判其領導團隊的決策過程、依據的政策理念,以及政策執(zhí)行的效果評估。
按照這種分類,崛起大國的領導力類型可以分為無為型、保守型、奮發(fā)有為型與咄咄逼人型四種。在中國歷史上,這四種類型皆有可資參照的對象,譬如無為型可以比照西漢初期文景兩帝的“休養(yǎng)生息,睦鄰通婚”;保守型則對應改革開放前30年以經濟發(fā)展為核心,在國際舞臺低調示人的當代中國;咄咄逼人型則可以參照統(tǒng)一六國的秦帝國;奮發(fā)有為型則以漢武帝時期,以及盛唐為代表。以上四類皆為崛起中的大國應對復雜世界的選項可能。
而作為政治領導力在國際舞臺上的投射,閻學通又根據現實情況區(qū)分了四種類型,即所謂的王道(human authority)、霸權(hegemony)、昏庸(anmeocracy)、強權(tyranny)。王道是將國內政治道德原則與國際規(guī)范相結合的典范,也是理想型的國家行為模式。霸權則是奉行雙重標準的國際行為準則,面對盟友與非盟友,主導國的優(yōu)先選項亦會區(qū)分。強權則是典型現實政治的主導者,遵循絕對的零和博弈規(guī)則。昏庸則是對國際行為準則的隨意取舍和混亂采用。
從歷史上看,冷戰(zhàn)時期的美蘇兩大超級大國各自奉行了霸權模式,形成了相對穩(wěn)定而持續(xù)的國際秩序。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在國力可支撐下依然奉行了霸權模式,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的霸權體系不斷被削弱,其原本的雙重標準出現了內生性矛盾,其國內的民粹思潮和反全球化思想腐蝕并沖擊美國政治領導力的國際信譽。2017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tǒng)加劇美國霸權的內在衰退,導致美國政治淪落為昏庸治理的模式。在特朗普主義的旗幟下,當今美國無畏地選擇退出現有國際體系的制度安排、重新調整與盟友的合作與義務承擔,進一步打壓來自崛起大國的挑戰(zhàn),使得美國的國際戰(zhàn)略信譽度不斷被侵蝕。
對于崛起大國而言,王道模式自然是中國發(fā)揮政治領導力,尋求國際秩序轉型、公正與合理的最優(yōu)選項。但閻學通并不認為當下的中國已經具備實現王道秩序觀的內外基礎。
領導力不是無限承諾
阿伯特·赫希曼曾認為,從長遠角度審視,任何國家、社會、組織都會面臨衰退的可能,而能否維系其運行和成功與否,亦取決于組織內部成員采取何種措施進行應對,選擇呼吁改革(voice)還是偏好退出(exist),都取決于成員對這一組織或體系的忠誠維系(loyalty),這就是著名的赫希曼推論。
從赫希曼視角來看,當今的國際秩序所體現的大國行為,無疑就是“刻薄呼吁、優(yōu)待退出”。面對西方世界與守成大國對于國際秩序忠誠感的退潮和焦慮,來自東方世界的政治領導力,或許能補上這一課。
政治領導力不是對世界無限的承諾,而是對于自身能力和價值觀的再三衡量,這點閻學通教授說的異常清晰和明確,這不是一個比誰更好的時代,而是一個比誰更不壞的時代。面對時代的沉疴遍地,懷有道德理想感的國家與個體該如何關懷世界,如何去接受一個無法開倒車的兩強競爭時代,恐怕在當下這個時代的風陵渡口,執(zhí)著的刺猬更需要一個機警的狐貍伴其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