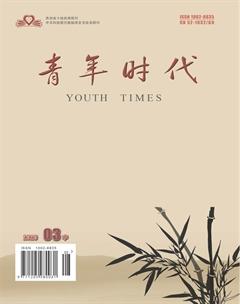“跨國史”與“國際史”異同芻議
陳郁晗
摘 要:“跨國史”與“國際史”是近年來史學界尤為關注的兩大史學范式,但兩者相近的關注主題,模糊了其真正的概念內涵,它們間的異同尚有待分明。就誕生背景而言,“跨國史”與“國際史”視角是對全球化熱潮的回應,但“國際史”的誕生是對傳統外交史范式的揚棄,而“跨國史”欲實現對“美國例外論”的超越和民族國家史學的補充。“國際史”仍以國家為單位,探究國家間的多向互動,以及國家框架下個人與群體的歷史活動;而“跨國史”側重于研究跨越國家邊界的現象與聯系。在空間維度之下,“國際史”將外交事務置于變化中的國際體系中看待的視角,與“跨國史”的內涵相一致,但“國際史”不具備“跨國史”中跨國網絡和跨國空間這兩大維度。
關鍵詞:跨國史;國際史;史學理論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以及區域共同體、非政府組織等超國家實體力量逐漸凸顯的現狀,美國史學界率先興起了一股包含“跨國史”“國際史”在內的“跨國轉向”潮流。這一潮流旨在突破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敘述重心和關注焦點的研究范式,力圖將以往被禁錮于國家疆域內的歷史現象,放置于更為廣闊的跨國背景下,探究其背后超國家范疇的歷史誘因、動力與影響。同時,其力圖探究移民族群流散、思想文化傳播等顯而易見的跨國流動現象,及跨國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等跨國非政治實體的作用。
進入新世紀后,國內學術界逐漸關注到在國外已注重探究商品技術流漸成規模的“跨國轉向”潮流,國內學者們或在引入國外的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提出新論,或借助“跨國史”“國際史”視角進行實證研究。然而,國內學術界中許多學者在使用“跨國史”和“國際史”概念時,常出現概念混同或表意不清的情況。本文在國內外學界已有的理論研究基礎之上,嘗試性地從誕生背景、詞源辨析和視角范疇等方面,探究“跨國史”與“國際史”的異同。
二、“跨國史”與“國際史”的異同
無論是“跨國史”還是“國際史”,都提倡以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寬廣視野看待歷史現象,這種超國家的視野無疑與近幾十年來逐漸勃興的全球化浪潮密切相關。新航路的開辟使世界逐漸從分散走向整體,然而在20世紀之前,已成規模的世界聯結仍是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主導下的不平等的聯結。進入20世紀后,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一度使全球化陷入停滯,而冷戰初期各國經濟文化聯系雖逐步加強,卻未能逃脫出美蘇冷戰的兩級格局之外。隨著美蘇冷戰局勢的緩和,屢次遭遇阻礙限制的全球化趨勢終于在20世紀70年代后真正從牢籠中掙脫。
全球化浪潮之下,跨國公司的影響力日益增大,并推動人員、商品和資本等以往受限于國家疆界內的事物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循環輪轉,思想、文化和技術等無形之物更以潤物細問聲之勢流向世界各地。在國際政治領域,聯合國、歐盟等超國家實體在國際事務中逐步掌握一定話語權,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其在參與全球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而被視作“第三種國際政治力量”和“20世紀后期國際關系中最引人矚目的事態之一”。在非國家行為體分擔全球治理責任,為國際秩序穩定貢獻力量的同時,全球化浪潮也為現有國際秩序帶來新的“挑戰者”。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借助全球化時代下緊密相連的人員、物資網絡而逐漸興起,并正在取代傳統的民族國家成為國際社會動蕩不安的誘因和現有國際秩序的攪動者。“新世界”在呼喚史學家突破民族國家史學的局限,以新的解釋框架、探究工具和研究方法來解釋歷史現象。同時,交錯縱橫的全球經濟、文化網絡又為史學家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靈感和方法,即超越民族國家疆界,將傳統國家事務放置于更廣闊的跨國背景中考察,關注跨國現象與非國家行為體力量。另外,信息時代下,互聯網的普及正在推動形成便捷的全球電子資源獲取渠道,相互交聯的人員流通網絡和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也使得跨國學術交流合作成為可能。
“跨國史”與“國際史”中超越民族國家的視角是對于當今全球化熱潮的回應,二者又同樣受益于全球化時代提供的新問題和跨國交流的機會。然而,“跨國史”與“國際史”的誕生又有其自身的學術背景,“國際史”的誕生是對傳統美國外交史或國際關系史研究范式的揚棄,而“跨國史”則欲以其豐富多樣的跨國主題,實現對“美國例外論”的超越和民族國家史學的補充。
傳統外交史學或國際關系史學,在誕生之初“是作為對國家治國方略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出現的,旨在記錄已發生的事實,揭示君主和政治家秘密戰略的模式”。在美蘇冷戰的國際局勢下,外交史學因其濃重的現實關懷和“最直接地支持和捍衛美國冷戰事業”的熱情而一躍成為美國顯學。然而自1980年代以來,外交史家逐漸意識到傳統外交史學“缺乏理論的嚴謹性和方法論的創新”,“問題意識狹隘、視野逼仄、不熟悉外國語言和資料”,史學界對“現實主義”與“進步主義”范式中狹隘的白人精英視角,過度關注國際局勢中的危機事件以及政治軍事問題,強調決策精英個人能力的發揮以及國內因素對外交決策的影響等問題的批判更是蔚然成風。
外交史學在進行自我革新的過程中,率先從新社會史和新文化史學中吸收其“自下而上”看問題的理念,關注決策精英以外的普通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和價值。而后“國際化”與“文化轉向”使得外交史學逐步重視多邊檔案和跨國合作的重要性,將外交史置于更廣闊的國際背景和文化經濟關系中考察,“外交史”從而發展為“國際史”。“國際史”從產生至發展都圍繞著批判革新外交史的主題,它將傳統外交史學中“蘭克史學”研究方法樹為標靶,從新社會史、文化史與“國際化”潮流中吸收精髓,從而實現對外交史學的揚棄和自身研究視角方法的確立。“國際史”的誕生背景使得它與“跨國史”共享著超越國家疆界,注重交流互動的跨國視角,但其所重視的“自下而上”的視角以及文化關系、意識形態,都并非“跨國史”強調的重點。
“國際史”的誕生發展是對傳統外交史學的“撥亂反正”,而“跨國史”的興起則是美國史學界對“美國例外論”的集體反思和超越。民族國家史學因其在構建“想象的共同體”和鞏固國家統一方面的特殊作用而長期在史學研究中占據主導地位。伴隨著20世紀上半葉美國國力和國際話語權的迅速增強,越來越多美國史學家們宣稱美國的發展進程規避了存在于歐洲大陸的階級沖突、革命劇變和獨裁政府,并為世界提供了“自由”的榜樣。然而全球化潮流下世界聯結的增強使得史學家逐漸意識到,強調國家差異,力證自身獨特性,忽視人類依存性的民族國家史學和“美國例外論”的局限性,由此史學家呼吁美國史學研究應突破民族國家史學框架,使“民族主義情景化,將美國歷史描繪為跨國主題的變體”。
當探究視角轉向兩者的詞源時,也可看出“國際史”與“跨國史”兩者內涵的明顯分野。“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中英文“inter”作為前綴一般表意為“在兩者或多者間”,而“international”則傳達出兩個以上國家間的交互聯系的含義。然而這個詞也表明“國際史”仍然以民族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之所以稱其超越民族國家框架,乃是源于它扭轉傳統的外交史學只從國家本身看問題的視角,將國家間交流放置于變化動態的國際背景下考察,但其內涵中“去國家化”的意義甚微。學者亞歷山大·迪肯認為外交史家、國際史學家以及國際關系研究者都認同一定的基本原則,即“將重點放在國家之間的關系上”。入江昭(Akira Iriye)作為“國際史”早期倡導者之一,他將“國際史取向”闡釋為“把一國的外交事務放在國際的框架,主要是政治學家們所說的國際體系下來考察”,這一國際體系既可以是傳統的權力體系,也可以是經濟體系與文化體系。因此雖然“國際史”日益重視普通人的歷史活動,但在這一視角中個人的活動仍帶著其從屬國家的標簽,“個人和團體依然是作為某一個國家的成員才成為有意義的研究主題”。
反觀“跨國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的詞義,入江昭曾解釋說“trans-”是超越、跨越以及穿越(cut across)的意思,即跨越國界、跨越邊界;“transnational”在表示越過國境的同時,也被用以形容“在國家之間建立聯系形成的全新的特性”。因此,從字面與詞源意義上對比“國際史”與“跨國史”可以發現,“國際史”仍然是以國家為單位,在此基礎上探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多向交流互動,以及國家框架下不同身份的個人與群體的歷史活動;而“跨國史”則側重于研究跨越國家邊界的現象與聯系。
以上僅是從語言本身分析“跨國史”的含義,然而事實上國外學界對于“跨國史”的內涵與研究范疇說法不一,“跨國史”本身仍是一個較為模糊的概念。伊恩·泰瑞爾(Ian Tyrrell)認為“跨國史”的目的在于“把國家發展置于背景之下,并從國際影響的角度來解釋國家”②;它關注“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以及塑成國家的國內因素和超國家因素,同時關注國家機構的形成”。而托馬斯·本德認為,不應以“大陸”和“朝里看”的視野看待美國殖民地時期的歷史上,而應將其視作形成全球聯結的海洋世界的一部分。泰瑞爾與本德作為較早回應入江昭“國際化歷史”倡議,并積極推動“跨國史”研究,兩人都強調“跨國史”研究關注國家之間關系,并努力把國家歷史放置于更廣闊的國際背景下考察,將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傳統國家事務視作國內外因素共同塑造下的產物。
《帕爾格雷夫跨國史詞典》編撰者之一皮埃爾·索尼耶對此持不同意見,他將“跨國史”界定為囊括“跨越國界的運動和力量”在內的種種敘述;在他看來,跨國史“是指商品,是指人員,是指觀念、話語、資本、威權和制度”。相較泰瑞爾和本德,索尼耶對“跨國史”概念的界定更加寬泛,他不僅將國際權力關系與國際背景下的國家建構容納在內,還將跨國運動與跨國行為體,不斷流動交換的跨國商品、人員、資本以及觀念都視作“跨國史”的研究課題。由于“跨國史”概念本身仍處于爭論之中且相關研究課題不斷推陳出新,因而學術界在介紹“跨國史”概念與研究范疇時的基本做法是采用入江昭與索尼耶在近年來所提倡的更為寬泛的定義①。
與“跨國史”模糊的定義不同,國際史學者對“國際史”的研究范疇的定義較為清晰。冷戰史是近年來從“國際史取向”中受益最多,成果最為豐碩的領域,冷戰國際史以其研究視角、主體、史料的多元性,與跨國機構、人員間頻繁交流而與傳統冷戰史研究相區別,其研究范疇與主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國際史”的研究特點。冷戰國際史著名學者梅爾文·萊弗勒在其論文中曾談到,“國際史學者已經把越來越多的因素編織到他們各自不同的敘事中”,他們既重視“觀念、價值、語言和文化”以及“種族和性別”,同時也探究強國與弱國間的關系,將經濟與地緣政治因素相結合,評估“意識形態對權力、威脅和機會的認知的影響”,考量“國內政治文化在塑造戰略、外交、戰爭和和平中的作用”以及“軍事能力和外交行動之間的相互關系”。可以看到,“國際史”研究范疇開始更多地考量社會、經濟與意識形態等因素對國家間關系與國際局勢的影響,其中對觀念、意識形態與種族性別的重視更體現了新社會史和新文化史對其產生的影響。然而,萊弗勒所談到的“國際史”研究敘事中顯然并不包含廣義“跨國史”所探究的跨國移民與族群流散,思想文化、商品技術跨國流動,勞工、環境與社會正義等跨國運動,疾病傳播、環境變化等跨國事務以及跨國行為體活動等課題。
借助“跨國史”與“國際史”研究者的論述,可以看到兩者在研究范疇和課題上存在區別,而空間層次分析能夠進一步幫助我們了解二者的異同。按照空間維度去看待“跨國史”,其研究課題本身可以被劃分為跨國框架、跨國網絡、跨國空間這三個維度。其中,跨國框架所強調的是將國家歷史放置于跨國背景下探究考察,一國事務之形成不再是簡單國內動因的疊加,而是國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每個國家從誕生伊始便是整個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無一不在參與塑成世界,而它們在影響著別的國家的同時也承受世界給它們帶來的不可逆轉的變化。跨國框架是用“上帝視角”審視國家如何被世界洪流所形塑又反作用于洪流本身,而跨國網絡則是指跨國移民與族群流散,思想文化、商品技術跨國流動所留下的足跡,在世界勾勒出縱橫交錯、星羅棋布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之中,無論是移民商品這類有形之物,還是思想文化等無形之物,它們的流動是不受國家疆界束縛的。除此之外,由于非國家認同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們所領導的勞工、環境與社會正義等跨國運動,以及這些群體所組成的非政府組織,都活躍于一個非民族國家單位的空間范圍之內,即跨國空間。
相較于“跨國史”多層次的空間維度,“國際史”的空間維度顯得更為單一。“國際史”的內涵是以多國且多元的檔案代替單一國家政府檔案,以國際化視角考察國家間關系與國際局勢,將外交事務置于變化動態的國際政治、經濟與文化體系之中,并將“‘高端政治以外的經濟與文化交流、人權、對外援助、疾病控制、環境治理等納入外交史研究”。其中,將外交事務置于變化中的國際體系中,考察國家間雙向互動交流對外交事務的影響的國際化視角與“跨國史”中在跨國框架內看待國家事務的內涵相一致。然而,“國際史”研究并不具備跨國網絡與跨國空間這兩個維度,“國際史”雖然提倡“自下而上”的研究視角,并努力挖掘價值觀念、意識形態、社會經濟因素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作用,但它僅僅是運用這些因素去分析外交事務與國家關系,而并非撕下“國家”標簽,考察思想文化、價值觀念本身的流動過程;它所關注的經貿交流、環境治理與疾病控制等議題,大多屬于國家主導下國際合作的范疇之內;它對聯合國、歐盟與北約的關注,更多地源于其遵循外交史學重視探究國際政治中占據一定話語權的行為體的固有傳統,而并非像“跨國史”那樣是出于對非國家認同意識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視,而去關注那些憑借超國家界限的利益關切進行自我建構的跨國非政府組織。
三、結語
“跨國史”與“國際史”都以超越民族國家的視角回應當今全球化熱潮,且又都受益于全球化時代提供的新問題和跨國交流的機會。然而從誕生背景上來看,“國際史”的誕生發展是對傳統外交史學中存在的固有弊端,如過度關注政治軍事事件,強調白人精英決策者,忽視中下層群眾等問題進行“撥亂反正”;而“跨國史”的興起則是美國史學界對民族國家史學狹隘的視野以及“美國例外論”的集體反思和超越。而若從詞源意義上辨析二者,“國際史”并未擺脫民族國家的單位限制,是在此基礎上探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多向交流互動,以及國家框架下不同身份的個人與群體的歷史活動;而“跨國史”則側重于研究跨越國家邊界的現象與聯系,其相較“國際史”而言擁有更為豐富的“超國家”內涵。最后,運用空間層次結構看待“跨國史”與“國際史”的內涵可以發現,“跨國史”中包含跨國框架、跨國網絡、跨國空間這三個維度;而“國際史”中將外交事務置于變化中的國際體系中看待的國際化視角與“跨國史”中在跨國框架內看待國家事務的內涵相一致,但“國際史”范疇的研究顯然并不具備跨國網絡和跨國空間的維度。
注釋:
①亞當·納爾森:《冷戰后美國史的轉向與全球知識經濟的興起》(陳希 整理),本文為納爾森于2017年6月7日,在北京大學所做題為《科學、教育和貿易:威廉·麥克盧爾和“礦物壟斷者”:1800-1820》的演講的整理稿,并于2017年7月6日刊發于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15698 (2018年2月9日)。
②Ian Tyrrell:《What is Transnational History?》,本文為作者于2007年1月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學院發表的一篇論文的摘錄,http://iantyrrell.wordpress.com/what-is-transnational history (2018年2月9日)。
參考文獻:
[1]王立新.新視野下的20世紀國際史——入江昭和他的《全球共同體》[J].世界知識,2009(6):65.
[2] Juliet Gardiner. What is History Today…?[M]. London: Macmillan, 1988.
[3]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8.
[4] Charles S Maier, “Mak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in Michael Kammen, ed.,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mell Univ. Press, 1980, p. 355.
[5] Dorothy Ros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84(4):909–928.
[6] 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1(4):1038.
[7] Alexander DeConde. Essay and Reflection: On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J]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988(2):286.
[8]入江昭.從民族國家歷史到跨國史:歷史研究的新取向[M].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第四輯).2007:4.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1 (Feb., 1989), pp. 4-5.
[9]王立新.試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國際化與文化轉向[J].美國研究,2008(1):26-46,34.
[10]入江昭.我們生活的時代[M].王勇萍,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1]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09(4):460.
[12]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13] Pierre-Yves Saunier, “Going Transnational? News from down under: Transnational History Symposium,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eptember 2004.”[J]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 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vol. 31, no. 2 ( 2006), pp. 118–131.
[14]王立新.在國家之外發現歷史:美國史研究的國際化與跨國史的興起[J].歷史研究,2014(1):153,144-160.
[15]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9(2):501–502.
[16]王立新,景德祥,夏繼果.走出傳統民族國家史學研究的窠臼[N].光明日報,2017-02-13.
[17]牛可.超越外交史:從外交史批判運動到新冷戰史的興起[J].冷戰國際史研究,2014(1):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