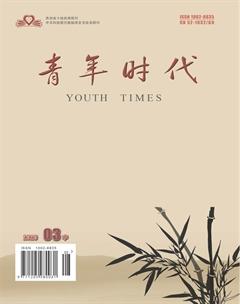試論“三月廟見”禮
李自鵬
摘 要:先秦婚禮中有“三月廟見”禮。這一禮儀從漢代起就受到經學家的關注。然而,關于這一禮儀的具體內容和作用,經學家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立足于文獻,結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認為“三月廟見”禮是春秋時期針對大夫以上階層的特殊禮儀,是當時的社會環境的產物,其目的在于防止新婦生下血統不純的子女。
關鍵詞:古禮;春秋時期;三月廟見
一、引言
家庭是構成人類社會的基本單位,而家庭開始于婚姻。因此,研究古代婚禮,對于認識古代社會意義重大。先秦婚禮中有“三月廟見”之禮,最明確的記載出于《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袝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1]
這段記載未必真出于孔子,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孔子時代的婚禮情況。春秋時期,貴族階層還保留著族墓制度,死者只有具備宗族成員的資格才能入葬于宗族墓地。廟見之前,如果女方不幸去世,則無法葬入男方宗族墓地,這意味著廟見之前,女方并不能算是男方家族成員。這一點著實令人感到奇怪,因此,也引起了后世關于“三月廟見”禮的種種爭論。本文希望對這些爭論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希望能解釋清楚“三月廟見”禮的性質和產生原因。
二、“不合人情”的古禮
“三月廟見”究竟是何性質的古禮?其具體內容是什么?從漢代起,學者們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鄭玄認為“三月廟見”禮僅僅適用于那些舅姑亡沒的新婚夫婦。《禮記·曾子問》鄭注云:“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1]鄭玄認為如果男方父母已經去世,新婦在祭祀過他們之后,才真正算“成婦”。這就像舅姑尤存時,新婦需侍奉舅姑盥洗及進膳食一樣。鄭玄有這樣的解釋,是有文本依據的。《曾子問》中“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講到了若男方父親已經去世,則需要在廟見禮后祭祀父親。這或許會引起某種歧義。孔穎達《正義》曰:“此謂舅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后,而于廟中以禮見于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于禰廟,以成就婦人盥饋之義。”[1]孔穎達認為若舅姑不存,新婦則需在嫁入男方家中三個月后,親自執饌,在祖廟中以禮祭奠舅姑。這是基于文本對鄭注做的維護。
但仔細讀《禮記·曾子問》,發現孔子并未明確說明“三月廟見”禮是針對“舅姑沒者”所設的特殊古禮。相反,緊接著曾子和孔子的問答表明廟見才是“成婦”的關鍵。所以,鄭注和孔疏的解釋顯得有些牽強。另外,根據《儀禮·士昏禮》記載,新婦成婚第二天就要舉行盥饋舅姑的儀式,如果“三月廟見”禮如鄭玄所說象征著“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的儀式,為什么“舅姑既沒”時不在成婚的第二天舉行象征性的祭禮,而非要等到三月之后舉行呢?
第二種看法以《白虎通》為主,認為“三月廟見”禮指新婦在新婚后第一次參與祭祖,適用于所有的新婚夫婦。《白虎通·嫁娶·授綏親迎醮子詞》曰:“婦入三月然后祭行。舅姑既歿,亦婦入三月奠菜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后可得事宗廟之禮。”陳立注云:“三月一時,婦道可成。然則舅姑存則厥明見,若舅歿姑存,則厥明見姑,三月后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如常禮也,即三月后亦宜告于祖廟。”[2]總之,無論是舅姑均沒、舅歿姑存、姑歿舅存、舅姑均存,最終都要告于祖廟。但是,新婦嫁入以后的第一次祭祖儀式,與婚禮的間隔時間未必一定是三個月。對此,胡培翚解釋說第一次祭祖與婚禮的間隔最多不會超過三個月,三個月只是一個概括性的說法,如果二者間隔不足三月,自然不用等三個月再祭祖,“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于時祭,則不必三月矣”。但是根據《禮記》本文來看,三月應該和前文“三夜”“三日”一樣是指一個固定的時間長度,而不是約數。因此,胡說不能成立。第二種看法也說不通。
第三種看法以服虔、賈逵、何休、劉毓崧、劉壽曾等人為代表,他們認為所謂“三月廟見”禮是針對大夫以上的階層制定的禮儀,指新婚夫婦必須等待三月,在廟見之后才能同房。當然,據《士昏禮》記載,新婚夫婦是當晚就同床的,不存在三月廟見而后成婦這一說法。因此,服虔等人認為“三月廟見”禮并不適用于士及以下階層,而大夫以上的階層,無論舅姑是否在世,都必須在新婦“三月廟見”后才能成婚: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后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3]。
春秋時期,如果貴族在婚姻中沒有遵行“三月廟見”禮,則會受到批評。《左傳》隱公八年載: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后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庶人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公子忽四月去陳國迎娶新婦媯氏,卻沒等到媯氏完成“三月廟見”禮,即沒有完成婚禮的儀式,就和她同房了。這是違背禮制的。因此,陳鍼子甚至咒罵他不得生育。可見當時貴族階層必須舉行完“三月廟見”之禮,才能真正成為夫妻。
以后人的眼光來看,三月廟見之后夫妻才能同房的規定非常不合人情。清人俞正燮曾羅列前人對鄭公子忽“先配后祖”的有關解釋,認為賈、服之說“非人情,不可用”。這其實是犯了以今度古的毛病。經學家皮錫瑞曾說:“古人制禮坊民,不以諧俗為務。故禮文之精意,自俗情視之,多不相近。又古今異制,年代愈邈,則隔閡愈甚……‘先配后祖當從賈、服,以祖為廟見,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始成昏,譏先配也。昏禮是士禮,當夕成昏,鄭謂大夫以上皆然,不如賈、服之合古禮。夫娶不告廟,又大夫以上三月廟見乃成昏,皆不近人情之甚者。”古禮是不斷變化的[4]。今人看來不近情理的禮俗,未必不是古代社會的真實寫照。因此,俞正燮以后世人情否定服虔對“先配后祖”的解釋的做法屬于臆測,并不可取。
那么,從文獻上看,春秋時期是否存在這一看似不近人情的禮儀呢?劉向的《古列女傳》中就有關于春秋時期貴族婚禮的記載: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于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于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于宋,致命于伯姬。還,複命。公享之,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勞于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后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5]
同卷“齊孝孟姬”: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孝公親迎孟姬于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授之綏,自御輪三,曲顧姬與輿。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后行夫婦之道[5]。
這兩則史料分別寫道“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三月廟見,而后行夫婦之道”,即“三月廟見”之后夫妻才可以同房。由此可見,在婚禮中,春秋時期的貴族確實要遵守“三月廟見”這一禮節。
三、“三月廟見”禮產生的歷史原因
古人制禮自有其理論根據,每一禮儀背后都有其“禮意”存在。“三月廟見”禮如此不合人情,那古人為什么還要制定這樣一個古禮呢?
孔穎達、萬斯大等學者認為廟見禮設在親迎三月之后是為了讓新婦參加按季度進行的較大規模的祭祀,即春祠、夏礿、秋嘗、冬烝中的一種。孔穎達說:“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6]。萬斯大對此有更詳細具體的發揮:“歲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必依于時祭。然婦入而遇時祭,或一月而遇,或二月三月而遇,遠不過三月,舉遠以包近。故曰‘三月,非必定于三月。”[7]從新婦嫁入夫家到第一次參加祭祀,時間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可能是兩個月、一個月,或者更少的時間。萬斯大認為這里通成為“三月”,是舉遠包近、舉多包少,是古代一種常用的修辭。可仔細閱讀文獻中的“三月而廟見”“婦人三月乃奠菜”“婦入三月然后祭行”等語句,可以發現“三月”是指一段固定的時間,而非“舉遠以包近”,將一月、二月都包含在內了。萬氏此解看似精妙,其實并無道理。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廟見前的三個月是夫家考察新婦品德的時期,此說以《白虎通》為代表。《白虎通》認為“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后可得事宗廟之禮。”“三月廟見”禮是為了讓夫家了解新婦的品行,這三個月是對新婦的考驗,若新婦能通過考驗,則可以上祭祖廟,正式成為男方家族的成員。這一說法似乎有理,實際卻經不起推敲[8][9][10]。首先,三個月的時間,未必能全面考察新婦是否在各方面都是一個合格的妻子,比如,新婦是否具備生育能力等。其次,新婦完全可以做好事前準備,將自己偽裝成溫柔孝敬的模樣來度過這三個月的考驗。再次,如果三月之后,舅姑不滿意,或者介于滿意與不滿意之間,難道能因此不顧夫妻之實,將新婦遣回娘家嗎?三月之后,新婦已經被男子家族的親屬所熟知,這個時候再“休妻”不但不合情理,而且會遇到極大的阻力。
何休則認為“三月廟見”禮的設立主要是為了考察新婦的貞潔。何休說:“古者婦人三月而后廟見稱婦,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后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絜,且為父母安榮之。”那這種說法是否合理呢?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時期對婦女貞潔的考察并不是婦女是否有婚前性行為,而是婦女是否在婚前已經懷孕。春秋時期,男女之間的婚前交往比較自由。當時,男子婚娶并不看重女子的貞操,女子改嫁并無不妥,如鄭穆公之女夏姬先嫁陳大夫御叔,再嫁楚大夫連尹襄老,后嫁楚大夫申公巫臣。這表明男女婚前交往比較自由,這樣就可能出現非婚生子的情況,如楚令尹子文、魯大夫孟鼓子均為私生子。西周宗法制度下,天子、諸侯、卿大夫既是各級政權中的君主,又是各級宗族組織中的族長,他們具有政治首領和宗族首領雙重身份。如果女方在結婚前已經懷孕,依靠當時并不發達的醫學知識,貴族們也無法判斷,那么新婦就有可能生下血統不正的長子。這血統不正的長子將會繼承父親的政治權力,乃至整個家族的財富。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某一貴族的后代特別是其嫡長子是否真正傳承了這位貴族的血統,就不單單受到該貴族本人的重視,同時也受到具有強烈宗族意識的全體宗族成員的重視,甚至要接受他們的監督[11]。
當時的醫學知識什么有限,缺乏有效手段來檢測新婦是否未婚懷孕。于是,三個月的驗貞期就成了檢驗的方法。古人認為第三個月是婦女懷孕后非常重要的一個時間點,古代醫學家有“三月始胎”的說法。這大概是因為婦女懷孕三個月后,身形會出現明顯的變化,三個月后,人們可以通過外形來判斷該女子是否懷孕。時間太短無法檢驗新婦是否未婚先孕,時間太長則務必要,“三月廟見”禮遂形成。等到宗法社會逐漸崩壞,醫學技術不斷進步,不需要觀察三個月也能確定女子是否有孕,“三月廟見”禮漸漸失去存在的意義,又因為此禮確實不近人情,終于逐漸消失了。
綜上所述,“三月廟見”禮是春秋時期存在于大夫及以上貴族婚姻中的禮儀。“三月廟見”禮是宗法制度下的產物,它要求貴族新婚夫婦必須等待三個月,在新婦完成宗廟祭祀的儀式后才能同房,其目的在于確保貴族子女的血統純正。這一古禮與當時男女交往的自由風氣和落后的醫學知識也有關系。
參考文獻:
[1][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黃侃經文句讀.禮記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王輝整理.儀禮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漢]劉向撰,[清]王圓照補注.古列女傳補注[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4][漢]班固撰,[清]陳立疏證,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M].北京:中華書局,2007.
[5][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清]萬斯大:《禮記偶箋》,溫顯貴校注.經學五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
[7][清]皮錫瑞著,吳仰湘點校.經學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8.
[8]陳戍國.中國禮制史·先秦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9]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10]胡新生.試論春秋時期貴族婚禮中的“三月廟見”儀式[J].東岳論叢,2000(4):98-103.
[11]王青.“三月廟見”說平議——兼談對古代禮制的理解方法[J].湖湘論壇,2016,167(2):126-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