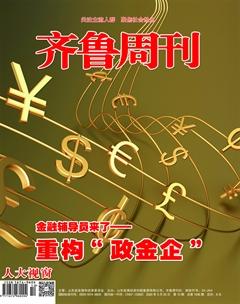黃河灘區(qū)遷建記:從水患村到幸福村
丁愛波

鄄城縣舊城鎮(zhèn)的一處在建村臺。
竹林村新貌
一棟黃色小樓坐落在長興集鄉(xiāng)竹林新村的文化廣場旁,這是竹林新村村委會辦公樓。樓內(nèi),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wù)站、農(nóng)家書屋等配套齊全,方圓幾百米之內(nèi),幼兒園、小學(xué)、文化戲臺等教育休閑設(shè)施一應(yīng)俱全。
俯瞰竹林新村,可以看到,統(tǒng)一樣式的兩層樓房錯(cuò)落有致,水泥硬化過的街道平坦整潔,家家戶戶都有一個(gè)門樓,門樓上鑲嵌的瓷磚在陽光下閃閃發(fā)亮。
所有這些建筑都坐落在一個(gè)占地800余畝、高約4米的大型村臺上。這個(gè)村臺夠大、夠高,能夠抵御黃河每秒12370立方米流量的洪水。
在竹林新村西邊約7公里處,就是滾滾黃河。過去幾百年間,人們在這里世代耕作,繁衍生息;可如果到了汛期,生活在這里則像一場噩夢,洪水淹沒道路和莊稼,直沖進(jìn)房屋……
“老一輩人說,住在灘區(qū),就是被淹的命!”因?yàn)樵鉃?zāi)次數(shù)太多,村委會的劉湘泉對那些被淹的記憶已經(jīng)有些模糊。“好像有一年洪水灌進(jìn)了家里,屋里的鍋碗瓢盆,順著水流全都漂走了,莊稼幾乎絕收。”
“但是和住房比起來,莊稼絕收根本不算啥。”過去,竹林村村民建房都是各自為戰(zhàn),家家戶戶門前房臺高筑,每戶人家都是一座“孤島”。這種村臺經(jīng)不住洪水沖刷,洪水一淹,地基就要動;地基一動,墻裂梁歪,住不了幾年就得塌。在劉湘泉記憶中,從10歲開始,他就跟著父母一起拉土筑臺,在以后的20多年里,拉土從未間歇,工具從馬車換成了拖拉機(jī),但是遇到大雨天氣,全家人仍是提心吊膽。
劉志華在竹林新村衛(wèi)生室工作,如今的他生活安逸, 正房是一棟兩層小樓,上下共有6個(gè)房間,寬敞透亮的客廳里放著沙發(fā)、電視、冰箱等家電用品,沿街是兩間配房,一間放雜物,一間作廚房。經(jīng)歷了筑臺建房、雨沖房毀、打工重建的輪回,劉志華對眼前的生活格外珍惜。“現(xiàn)在有了衛(wèi)生間,有了自來水,真沒想到生活能這么好,城里人住的也不比我們吧。”在寬敞明亮的客廳內(nèi),劉志華抱著女兒笑著說。
竹林新村是菏澤黃河灘區(qū)遷建第一村。2004年,東明縣爭取亞行貸款和省財(cái)政資金,開展建設(shè)村臺試點(diǎn),嘗試通過整村搬遷,解決灘區(qū)群眾安居問題,包括竹林村在內(nèi)的5個(gè)自然村、5100多村民被納入試點(diǎn)。
2010年,整村搬遷之后,不僅便捷了生活,而且極大地便利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過去,耕作半徑過長一直困擾著竹林村的人。在竹林村老址,有居民家中距離地頭最遠(yuǎn)可達(dá)七公里,整村搬遷之后,最遠(yuǎn)距離縮短至4.5公里。此外,竹林新村搬遷之后,騰退出耕地1190畝。
竹林新村還有扶貧車間,貧困戶和留守婦女可以就近就業(yè)。從竹林村到竹林新村,目前5100多人早已全部搬遷,遠(yuǎn)離水患、安居樂業(yè)。
這個(gè)村的遷建過程,為之后全面開展的黃河灘區(qū)居民遷建提供了先行經(jīng)驗(yàn)。同時(shí),也成為灘區(qū)群眾遠(yuǎn)離水患,開展幸福新生活的一個(gè)生動縮影。
找營村舊景
從竹林新村驅(qū)車兩三公里,很快便可以抵達(dá)找營村。在這里,呈現(xiàn)出的是和竹林新村完全不一樣的光景。一座座參差不齊的或土坯或磚砌的房子建在高低不等的土崗上,一條條蜿蜒不平的土路將這些房臺連接起來,人行其間,兩側(cè)房子都在頭頂上,宛如穿行山谷。

鄄城縣三合村村臺上新建的住房。
72歲的劉進(jìn)濤,從小就生活在這里,在他的前半生中,水災(zāi)和建房子是他生活中的兩大主題。他一共蓋了5次房子,在他的小院旁邊,有三個(gè)明顯呈梯形的房臺,這是三次大洪水之后,三次墊高房臺、重建房屋留下的印痕,每一次墊高都需要一車一車地拉土,墊一層需要幾個(gè)月的時(shí)間。
每一個(gè)在灘區(qū)生活多年的老人都有一部心酸的建房史。“我今年72歲,蓋了12次房子。每蓋一次房子要忙活好幾年。”東明縣長興集鄉(xiāng)的李留芹老人顫巍巍地用手比劃著說。
“在黃河灘區(qū)蓋房子,很難很難。為了防止發(fā)大水淹了,蓋房子需要先壘臺子,再在臺上建房。所以當(dāng)?shù)赜芯渌自挘喝陻€錢,三年墊臺,三年建房,三年還賬。”菏澤市發(fā)改委工作人員介紹,“往往是好不容易建成了房子,一來大水,又給沖沒了。”
在老一輩人記憶中,以前建房子,推土墊臺子是“大工程”。上世紀(jì)50年代,用獨(dú)輪小推車推土;60年代,用膠輪車推土;80年代,用地排車推土。
“用土坯建房子,用麥秸泥一糊就住人,一來大水就沖了。1977年,我們家壘了5級高的房臺。剛蓋好3天就來大水了,早晨起來一看,房臺沒影了,成泥糊糊了。”李留芹說。
在長興集鄉(xiāng)找營村,記者看到,這里的房屋地基比街道約高4米。“平時(shí)是街道,一來大水就是河溝,家家戶戶都有船或輪胎,逃生用。”村民馬秋玲指著家里梁上的輪胎說,“我是1981年嫁過來的,蓋了4次房,墊土越墊越高。”在她的房間里,記者伸手就能碰著梁。
修建房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三間房的地基所運(yùn)土方,兩個(gè)勞動力要一年的時(shí)間才能完成。若雇人其費(fèi)用相當(dāng)于建三間房之所需。要將整個(gè)院落抬高,代價(jià)就更高了。所以,自己動手的、請灘外親友幫助的、出錢買土的,有什么招用什么招。整個(gè)灘區(qū)如一個(gè)巨大的工程,像一個(gè)大的戰(zhàn)役,在施工、在戰(zhàn)斗、在改變著自己的生存條件。

我省灘區(qū)內(nèi)廣大村莊,普遍建有高高的村臺。

灘區(qū)村莊的老房子。
可是,一家一戶的房臺,面積有限,更經(jīng)不起特大洪水的威脅。更重要的是長期下去對堤防不利。最根本最徹底的解決辦法那就是將這些灘區(qū)村莊搬遷出去。
2017年5月6日,劉進(jìn)濤的小院里迎來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那天,劉家義到東明縣調(diào)研黃河灘區(qū)脫貧遷建工作,走進(jìn)劉進(jìn)濤家中,實(shí)地察看灘區(qū)群眾住房狀況,在農(nóng)家院落中,他與村民拉起家常,詳細(xì)詢問家庭收入多少,翻蓋過幾次房屋,愿不愿意遷到新村,共同暢談未來遷建新家園夢想。
當(dāng)年8月,山東黃河灘區(qū)居民遷建總體規(guī)劃獲得國家批復(fù),這是一個(gè)改變山東60萬灘區(qū)群眾命運(yùn)的百年大計(jì),劉進(jìn)濤的生活即將迎來徹底的改變。
那年9月,劉進(jìn)濤接通了省委書記劉家義的電話,他用最樸素的語言表達(dá)了他對未來生活的期許:“劉書記,您好!你上次走了以后,8號新村就開始動工了,進(jìn)度很快,東明縣縣委領(lǐng)導(dǎo)非常關(guān)注,明年就能建新村,老百姓都很期待。感謝您對我們的關(guān)心……”
時(shí)光轉(zhuǎn)瞬即逝,三年后,找營村即將搬遷入住的長興集鄉(xiāng)10號村臺主體建設(shè)即將完工,一排排漂亮的農(nóng)村小別墅正等待著劉進(jìn)濤們?nèi)胱 ?/p>
劉進(jìn)濤非常關(guān)注工程進(jìn)展,隔三差五就要到10號村臺看一下工程進(jìn)度。劉進(jìn)濤的老伴任軍梅,年輕時(shí)經(jīng)歷一場大洪水后,曾到山西逃荒要飯。如今看著新村臺的任軍梅告訴記者,以前塌屋蓋屋受苦受累,等新房子蓋好了,再也不會提心吊膽地住那個(gè)爛屋子了。
“感謝黨和政府,為我們筑臺建起幸福村,這一切成為永遠(yuǎn)的過去。”劉進(jìn)濤笑著說。
付出與“值得”
每天清晨5時(shí)30分,鄄城縣舊城鎮(zhèn)三合村村臺建設(shè)指揮長周朝紅都會準(zhǔn)時(shí)來到工地;此時(shí),項(xiàng)目經(jīng)理謝保記也來到指揮部。6時(shí),他們每天的碰頭會正式開始……
村臺上,一排排坐落有致、整齊劃一的新房已經(jīng)完工,運(yùn)料車輛來回穿梭,工人們干勁十足,處處熱火朝天。如今,三合村村臺(六合社區(qū))公共設(shè)施配套工程主體工程建設(shè)完成,基礎(chǔ)設(shè)施配套正快速推進(jìn),安置房正在室內(nèi)外裝修。
“5月20日前,小院內(nèi)塔吊務(wù)必全部拆除,過期不拆除的罰款200元……”這是謝保記工作筆記上記載的要點(diǎn)事項(xiàng)。作為項(xiàng)目經(jīng)理,從去年9月17日進(jìn)駐工地以來,謝保記的工作筆記記了三大本。
謝保記的家在舊城鎮(zhèn)蘇莊村,距離村臺僅2公里,然而進(jìn)駐工地后,他3個(gè)月吃住在工地沒有回過家。
“村臺社區(qū)建得不好,村民一找就找到老謝家,可不得責(zé)任心強(qiáng)一點(diǎn)。”5月13日,在村臺社區(qū)建設(shè)現(xiàn)場,周朝紅笑稱,村臺社區(qū)建成后,謝保記的家也要搬到這里。
今年正月十六(2月9日),謝保記他們是第一批復(fù)工的人員。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形勢下,每天一早,1200余名復(fù)工工人經(jīng)體溫檢測消毒陸續(xù)入場,進(jìn)入自己的崗位。為了趕上疫情耽誤的工期,他們需要盡快保質(zhì)保量完成剩余的外墻粉刷、水電安裝等工作。
三合村村臺是舊城鎮(zhèn)四個(gè)村臺中最大的一個(gè)。村臺開建之初,群眾心里嘀咕:這么大的事能搞成嗎?
“前期,鎮(zhèn)里向群眾宣傳黃河灘區(qū)遷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政策宣傳到位,把群眾的思想引導(dǎo)到位,營造關(guān)心搬遷、支持搬遷、參與搬遷的良好社會輿論氛圍。”周朝紅說,“灘區(qū)遷建工程是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干部們在工作中受了多少委屈、受了多少累,只有這些參與的同事最清楚。”
孩子年幼,妻子上班,周朝紅卻常常不能回家。“每天都要查看工程質(zhì)量、了解進(jìn)度,及時(shí)解決遇到的困難。為了灘區(qū)的群眾能早日搬進(jìn)新房,這些付出值得。”周朝紅說。
白墻灰瓦,紅門帶院。4月底,村臺樣板房裝修完成,附近村民時(shí)不時(shí)過來參觀,一聲聲贊嘆讓周朝紅真正體會到用心付出之后的“值得”。
在黃河灘區(qū)如此大規(guī)模淤筑防洪村臺,可謂前無古人,為了確保工程順利推進(jìn),許多人都在努力付出。
東明縣焦園鄉(xiāng)扶貧辦主任閆金生和父母一起生活。一天下午,在縣城工作的哥哥來看望父母,一家人做了燒烤。閆金生因在村里忙著做群眾遷建的思想工作,到了晚上8點(diǎn)多還沒有回家。因擔(dān)心烤肉涼了,父母便將燒烤爐搬進(jìn)房間,沒有熄火。后來,兩位老人睡著了,不幸中毒去世。出殯時(shí),痛心的哥哥堅(jiān)決不讓他參加。
長興集鄉(xiāng)李爍堂村民調(diào)主任樊鐵創(chuàng),左手的中指上有一個(gè)傷疤,這是他自己咬的。因修建村臺需要先拆遷14戶村民的房子,每戶獎勵(lì)3000元。拆遷當(dāng)天,有幾位村民圍著樊鐵創(chuàng)要錢,樊鐵創(chuàng)耐心解釋:“錢需要走程序,過幾天就打到你們卡上。”有村民激動地說:“你必須給俺打欠條,摁手印!”
樊鐵創(chuàng)寫了欠條,當(dāng)時(shí)桌子上沒有印泥,情急之下,他咬破中指,摁下了8個(gè)血手印。情緒激動的村民安靜了。“我也不覺得委屈,咱既然干村干部,就應(yīng)該盡一份責(zé)任。那段時(shí)間,包村干部和村干部,吃不好睡不好,苦口婆心地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工作進(jìn)展得很順利。”樊鐵創(chuàng)說著,眼里泛起淚花。
基層干部感人的故事,也是灘區(qū)疾步擺脫洪水威脅、圓夢安居的一個(gè)縮影。

東明縣焦園鄉(xiāng)的一號村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