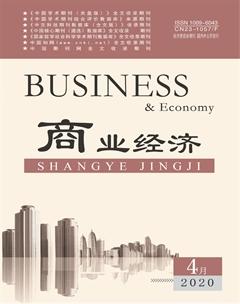我國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動態博弈研究
張汝根 張微



[摘 要] 基于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從博弈的視角在理論上分析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并結合我國歷史數據進行實證檢驗。通過選取金融創新度(FIL)、金融相關比率(FIR)及貨幣化率(MOR)來量化金融創新程度,進行實證分析,驗證了博弈結果的準確性,證明金融監管必須隨實際情況做出調整,不能一味的強監管,否則會抑制金融創新,以至阻礙金融業的發展。金融監管機構應轉變思路,既要根據時代要求不斷調整自己的監管規則、建立新的監管體系確保金融系統的穩定,又要為金融機構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來支持金融機構進行適度創新。
[關鍵詞] 金融創新;金融監管;動態博弈
[中圖分類號] F83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9-6043(2020)04-0163-03
金融創新主要指變更現有的金融體制、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獲取潛在利潤。金融創新是金融業發展的必要手段,但由于其具有高杠桿性和虛擬性等特點,往往會造成一定的風險。
一、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分析
當金融創新過度時,往往會導致市場失靈。當過度的金融創新造成市場失靈時,便需要監管機構加以管制,可見,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是有聯系的,若金融機構過度創新,便會突破既有的監管體制,打破原有的均衡,這可能會導致金融系統的無序,這時監管機構便會加大監管力度,維護金融系統的穩定。由此可見,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相互促進,相互推動,是一種動態博弈關系(其關系示意圖如圖1),正是這種“監管—創新—再監管—再創新”過程的不斷重復,推動著金融業不斷向前發展。
二、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博弈模型構建與分析
(一)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博弈要素
1.參與者:指博弈決策中的獨立決策個體(假設參與者均為“風險中性”),他們具有一定的統計分析能力和對不同策略效果的事后辨析能力。
2.效用函數:效用函數評價了參與者所做不同行為選擇時,其組合所產生的結果,它描述了參與者在博弈結束后所獲得的收益(博弈中假設參與者沒有效用函數以外的收益與損失,即效用函數可以完全反映參與者在相關博弈中的全部損益)。
3.決策變量:在某一時點,博弈參與者會根據自身需求選擇有利于自己的方案,決策變量便是參與者之間所選方案的組合。
4.信息:指參與者在做出決策時所需要的對策略選擇有用的情報知識,如其他參與者的特征等。由于我國市場信息存在著不對稱,因此本文在設定博弈模型時應采用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5.公共知識:指所有參與者均可獲取的知識,且任一參與者不會因掌握了公共知識而更具優勢。
6.均衡:當博弈達到均衡時,便意味著每位參與者所采取的策略都是對其他參與者所采取策略的最優反應。
(二)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博弈模型構建與求解
由上文分析可知,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的博弈是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由于不完全信息下的無限次博弈需要的計算量過于龐大,因此本文僅針對博弈的一個循環進行構建與分析。
1.基本假設
為方便研究,本文做出如下假設:
假設1:金融機構A和金融監管機構B對對方的博弈參與要素并沒有準確的知識,但由于該博弈具有先后順序,因此,后行動的參與者可以掌握先行動的參與者所采取的行動。
假設2:博弈參與雙方均為理性人,可根據其客觀條件,做出最優策略。
假設3:金融機構A的目標是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金融監管機構B的目標是通過執行有效的監管,維護金融業穩定。
假設4:若金融機構A不創新,其獲取的正常效益為U,若金融機構A創新,其獲取的超額效益為U,由于創新被監管繳納罰金所損失的效益為C1;若監管部門B監管,其效益為V,由于監管付出成本所損失的效益為C2。
假設5:金融機構A創新的概率為p,金融監管機構B監管的概率為q。
2.模型構建與求解
根據假設條件,構建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博弈模型如圖2,這是二者動態博弈的一個基本過程。
3.博弈分析
根據上文建立的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動態博弈模型所求得p、q值的表達式,可進行如下分析:
金融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創新實施監管,其自身產生一定的效應,這種效應在一定時期內不會有較大變動,即V相對穩定,且金融機構由于創新而被監管所交罰金在短時間內也是相對固定的,因此C1的變化也較小。隨著監管的不斷深入,金融機構創新技術不斷進步,所帶來的超額收益U不斷增加,但監管成本也不斷提高,直到監管技術成熟,其成本會慢慢降低,即C2先增加后減小。
因此,結合p、q的表達式可知,金融監管機構監管的概率將逐漸加大,金融機構創新的概率先增加后逐漸減小。這樣將會得到兩個均衡,即(創新,監管)、(不創新,監管),監管機構監管的意愿逐漸加強,金融機構起初為了獲得超額收益會選擇創新,但隨著監管的加強,其創新積極性便會被打消,最終可能會形成一種非良性循環,使得金融創新不足,抑制金融業發展。
三、基于我國經驗數據的實證檢驗
(一)我國金融監管實際情況分析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均由財政主導,對金融機構的管理亦是實行行政管制形式。1983年9月,國務院頒布《關于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決定》,規定:人民銀行應作為管理全國金融事業的領導機關;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發布,提出中國人民銀行可依法監督與管理銀行、證券、保險等所有金融行業和機構,這標志著中國金融監管的開端。1993年12月,國務院頒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銀行、保險、證券和信托應進行分業監管,之后隨著《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等的相繼頒布,進一步明確了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管職責,同時也在法律地位上確認了我國金融業分業監管模式的形成。為順應綜合經營趨勢、切實強化金融監管,2017年,我國又設立了金穩委(即金融穩定和發展委員會),并于2018年,將銀監會與保監會合并,構建了銀保監會(即銀行與保險監督委員會)。
我國的金融監管長期處于分業監管模式,這符合我國1990年代初期時的金融狀況,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我國金融的穩定,但其根本是以強制性管制為主,存在相當程度的政府干預,激勵不足。這便導致了我國金融市場中較高的業務門檻,也使得金融市場供給方競爭不足。另外,“穩定”是我國轉型時期經濟社會的獨特特點,然而如今的金融市場應以激勵為主,若監管過于嚴苛,便會不利于金融創新的發展。
綜合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我國金融監管體系總體過于苛刻死板,金融機構難以深度創新,間接阻礙了金融市場的深化與發展。
(二)我國金融創新實際情況分析
1.金融創新測量指標選取
本文選取了金融創新度(FIL)、金融相關比率(FIR)及貨幣化率(MOR)來量化金融創新程度,其中,FIL為金融創新的直接衡量指標,而FIR及MOR衡量了金融深化的程度。
金融創新度(FIL)=金融資產總量/交易性金融資產,該式中,交易性金融資產的數值可近似用狹義貨幣M1代替(因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可直接用于支付),因此,金融創新度FIL表達式便可簡化為(其中FA表示金融資產總量):
MOR是一個金融存量指標,若貨幣化率過低,則表明可滿足經濟發展的現有貨幣量不足,即貨幣供給不足,這將會導致金融體系的低效率;若貨幣化率過高,則表明投融資活動過度依賴于銀行存貸款,經濟發展過分依賴于貨幣性金融資產推動,導致非存款性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的功能沒有充分發揮,金融創新度不足。
2.指標數據選取
通過查詢中國金融年鑒及中國統計局官網,將所得數據整理,得出我國1981年-2018年相關指標數值如上表。
3.指標數據分析
根據上表的數據,1981-2018年金融創新度、金融相關比率及貨幣化率變化情況如圖4、圖5及圖6。
通過分析金融機構與金融監管機構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發現:金融監管機構監管的意愿較為強烈,而金融機構在初期也會為獲取超額收益而主張創新,但面對過于嚴苛的監管,其創新積極性遭到嚴重打擊。若金融監管不做出轉變,最終可能導致非良性循環,抑制金融業進步。
本文通過選取FIL、FIR及MOR指標進行實證分析,驗證了博弈結果的準確性,并從實際角度說明金融監管機構應轉變思路,既要與時俱進,根據時代要求不斷調整自己的監管規則、建立新的監管體系確保金融系統的穩定,又要為金融機構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環境來支持金融機構進行適度創新,從而推動國家金融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沈琪.博弈論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130-154.
[2]Kim T,Koo B,Park M. Role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in the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3,9(4):662-672.
[3]楊羽莎.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的問題與建議[J].時代金融,2014(33):70-71.
[4]潘穎.金融創新需以金融監管的范疇為限——以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之收益權的適法性為例[J].科技與金融,2019(8):81-85.
[5]駱婉琦,周春應.新型金融監管體系、監管問題及監管協調研究[J].經濟研究導刊,2018(31):88-90+101.
[責任編輯:史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