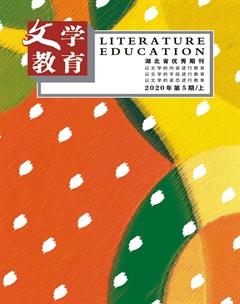每一棵樹都是精神的象征
學者程虹說道:“在這些自然文學作家的筆下,自然是神圣的代名詞。走向自然,實際上,也是走向神圣的風景,堪稱是心靈的朝圣。”當神圣這個崇高﹑尊貴,而不可褻瀆的前面加上莊嚴兩個字時,它的意義更是厚重,偉大起來了。學者程虹對于自然作家的評價,不是空談和煽情,這是最準確的評斷。
在這個時代,報章每天成批的產出文學作品,讀到一篇人與自然的好散文特別艱難。近期讀《中國環境報》,刊發李青松的《水杉王》。作家通過對水杉樹的描述,寫出大自然中的人與事。一個作家要找自己的敘述方式,進行新的創作。這不僅需要形式的新穎,而要對世界了解和觀察。
讀過李青松的一些作品,關注生態環境,這不是職業的關系,是作家的品質所決定。他的文字,好似沐著晨露,撲來清爽的草木氣息。大自然的寧靜,成為工業化城市的觀光旅游的地方,而在過里他們尋找的是娛樂,放松緊張的身體,不是心靈與心靈的相融。植物上的露珠,樹葉的紋絡,成為鏡頭下的小品,人與植物不是溝通。
人類的心靈是由大自然的萬物滋養,一片樹木的成長,有著它的歷史因素,和同于一般同類的個性。“當然,影響水杉葉片色彩的因素,主要還是取決于它的基因和生境,然而,它自身的潛能——那個藏在葉片里的美,只要有了對的空間和對的時間,它就會盡情地釋放出來,絢麗無比,令人迷醉。”一棵樹,在不同的季節,不同的時間,展示出不一樣的風景。每一道年輪,記上時間的痕跡。
當一個作家,面對一棵樹,不是突然間生出一股環保主義的激情,這種虛偽,空談的情感,如同過眼的云煙,一會兒散去。每一棵樹都是鮮活的生命,它的寧靜和自然,呈現活力和生機。“像是天宇下肅穆莊嚴的宮殿里的一尊神。具有恍如隔世的高古氣質,充滿巨大、神圣和永恒的能量。我凝神靜氣,不敢有一點造次。邁出的步子都是輕輕的。在它面前,我完全辨別不了方向,仿佛過去和未來都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它了。忽然,天空就滴下一些雨點,落在頭上,落在面上,落在手掌上。遠處的青山之間,霎時就升起了忽明忽暗的幽靈般的弧圈,在若有若無的云雨中閃閃發亮。”作家認為樹是一座神像,這不是在作文字游戲,故意玩弄情感。它是作家對樹木的敬畏,從它的身上體驗高潔的氣質。
李青松是一個行走的作家,不囿于書齋的寫作。他通過大自然的行走,尋找歷史的蹤跡,塑造自我的過程。每一次在林間,撫摸枝葉,人的情感波動,體溫與枝葉相觸,發生化學變化。這不僅是觀賞,是靈魂的升華。
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指出:“任何一種生命都具有它自己的重要意義。這種重要意義在于某種意義的脈絡之中——就這種脈絡意義而言,人們所能夠記住的任何一個時刻都具有某種內在固有的價值,而且,在記憶所具有的脈絡之中。它也與這個整體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是非常獨特的,因此,通過知識是不能透徹地了解這種重要意識的;然而,它就像萊布尼茨所說的某個單子那樣,以它自己的方式這個具有歷史性的宇宙。”哲學家認為生命的重要意義,不限于人類,卻是所有萬物的存在,都有它合理的重要意義。它們與人類是和諧相處,缺一不可。
在這個技術時代高速發展,人對世界的看法發生巨大變化。人與人的情感發生變化,作家所面臨的選擇。拒絕平庸、粗陋的寫作,不是口頭的空喊,需要作家精神上的堅守。李青松是行走派的作家,大量田野工作,使他對自然中的樹木認識,每一棵樹的自由生長,不受人工的束縛和修理。樹木的寧靜,撞擊著人的心靈。作家在大自然中,呼吸清新的空氣,聽到樹枝液的流動聲,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享受,和一種審美。作家用樹木的語言,去記敘大自然中的經歷,每一個文字散發野性,單純透明的情感,譜寫的錄事,不會空洞的夸張。
當城市的喧囂遠去,作家獨自對著樹林時,心情安靜,反而感受不到在人群中的孤獨。在這里每一棵樹傾吐情感,古樸自然,精神自由,身心享受的是健康,得到一種寧靜。
每一次走進大自然,嗅著樹木散發的清香,注視樸素的枝葉,這是走向內心,豐富精神生活的方式。心隨風中的枝葉而動,如同踏著古老的韻律,跳出一支完美協調的舞蹈。此時,人與樹木交融,成為自然中的一部分。
一個作家對大自然的熱愛,對樹木的親近,不是用華麗的詞語贊美,排列一串大詞。它是言行一致的,從心中發出的摯情,不摻雜功利的欲望。這件事情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非常難的事情。
在大自然中,和每一棵樹木相對,,聽風聲,看著天空中的飛鳥,人心清除思欲的雜念民。一個熱愛大自然樹木,一生獻身大自然,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選擇大自然的樹木,并不是人生受到打擊逃避,而是為了尋找真實,重新塑造自己。
李青松的文字看似平淡,透露詩意的樸素,卻又不失精神的深邃性。這是他與眾不同的地方,也是創作的向度。
高維生,著名散文家,出版散文集、詩集三十余種,主編“大散文”“獨立文叢”等書系,現居山東濱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