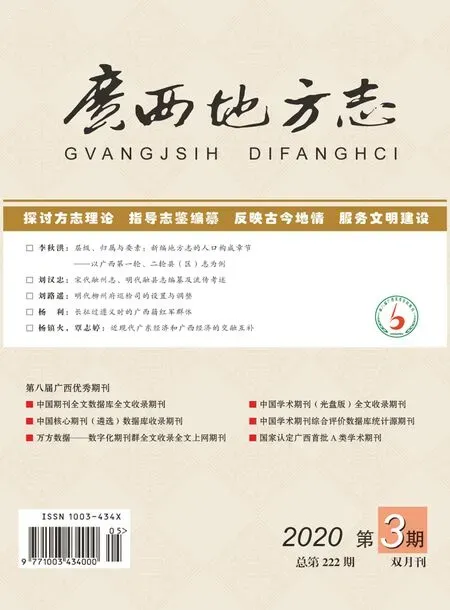近現代廣東經濟和廣西經濟的交融互補
楊鎮火,覃志婷
(廣西壯族自治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廣西南寧530000)
自古以來,廣東和廣西同處于珠江水系,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均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特別是近代以來,隨著開埠通商與內外貿易的擴展,位處珠江上下游的廣東與廣西之間經濟往來日益密切,雙方依據自身經濟發展進程的特點和需求,圍繞著人力、資金、技術、商品物資等方面,建立了長期而頻繁的交流。近些年,學術界多從地緣政治學和經濟地理學對近現代兩廣經濟發展進行研究。如,滕蘭花先生在《明清時期兩廣的地緣政治關系及其影響》中引入地緣政治學的理論分析兩廣地緣政治關系以及對廣西區域開發的影響。黃濱先生在《明清時期廣西“無東不成市”布局研究——廣西城鎮經濟網絡淵源溯探之一》《論近代廣西城鎮經濟的“無東不成市”格局》《“無東不成市”格局獨成廣西原因初探——泛珠三角中兩廣經濟聯系的歷史透視》《城鎮經濟網絡結構“無市不趨東”對近代廣西經濟的影響——粵港商業經濟對廣西經濟輻射研究之四》四篇文章中,對廣西全省性“無東不成市”格局進行多維度的分析和研究,深入地揭示了“無東不趨市”現象對廣西近代經濟的影響。韋國友先生和陳煒先生在《近代珠江流域區域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分工與互補———以兩廣為中心的考察》中認為兩廣依據自身經濟發展進程的特點和需求,共同推動了近代珠江流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本文綜合學術界對兩廣經濟發展的研究,嘗試從兩廣的地緣政治關系、廣東對廣西經濟輻射、廣西對廣東的經濟推動三個方面分析近現代廣東經濟和廣西經濟的交融互補,以求教于方家。
一、廣東和廣西的地緣政治關系[1]
地緣政治是政治地理學中的一項理論,主要是根據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預測世界或地區范圍的戰略形勢和有關國家的政治行為。它把地理因素視為影響甚至決定國家政治行為的一個基本因素。又被稱為“地理政治學”。廣西毗鄰廣東,同屬珠江水系,在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發展過程中,都避免不了區域地緣政治關系方面的影響。
廣東和廣西同屬嶺南,同處珠江水系,地域相鄰,西江在廣西梧州匯集各支流后流入廣東,兩廣之間有西江作為交通紐帶。先秦時期的西甌、駱越先民是兩廣的土著先民。在唐朝中期以前,廣東和廣西被并稱為嶺南,屬于封建王朝的一個政治管轄區域;唐朝中期在嶺南地區分別設立嶺南東道和嶺南西道,嶺南才開始分為廣東和廣西兩個部分。到宋代時,封建王朝在嶺南設置廣南路,直到宋太宗末,以嶺南道為界線,廣東在東邊就叫廣南東路,廣西就叫廣南西路,分為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這是廣東、廣西名稱的來歷。元代時,廣東地區歸江西行省管轄,廣西地區歸湖廣行省管轄,今海南省和雷州半島同屬湖廣行省管轄。到了明朝初年,由于廣西壯、黎、瑤三個民族反明起義猛烈,朱元璋采用分而治之的辦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島、欽廉地區、雷州半島一并劃歸廣東,以便加強控制。一直到1949年廣東解放,“欽廉地區”隸屬廣東省南路專區;1950年欽廉專區成立,下轄合浦縣、欽縣、靈山縣、防城縣等縣;1951年欽廉專區改稱欽州專區,同時欽州專區改隸屬廣西省;1955年欽州專區改稱合浦專區,復改廣東省管轄;1965年恢復欽州專區,再次劃歸廣西管轄,此時的廣西已經正式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至此,“欽廉地區”隸屬廣西終于塵埃落定。
縱觀歷史,廣西和廣東除了在政治上的關系非常緊密外,也由于自然條件上的相似性以及經濟方面的互補性,直到明清時兩廣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東西兩廣,雖分二省,其實共為唇齒之邦。”[2]
二、廣東對廣西經濟的輻射影響
中國政治經濟中心在宋代以前一直在北方,因此,廣西桂北地區因接受到北方的影響而較早得到發展,而且隨著靈渠—漓江—桂江—西江水道的開辟和發展,廣西的經濟開發呈現出自北向南推進的格局,并一直保持到明代。明代時,隨著人類航海事業的繁榮和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廣州憑借港口和外貿成為南方政治經濟中心,并以此為極點輻射周邊,形成區域經濟市場,沿著西江流域向廣西輻射,出現了自東向西的梯級開發格局。
(一)廣東對廣西區域經濟布局的影響[3]
近現代的廣西城鎮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因受廣東的絕對輻射影響而形成“無市不趨東”的布局結構。
西江作為珠江最大的支流,連接著廣東與廣西。西江水系自東向西,匯聚著桂江、賀江、南流江流域、羅定江、新興江等支流,梧州成為各支流的交匯點。各支流里的桂江、潯江、北流江、郁江、黔江、左右江等也就成為了兩廣經濟格局中的支點,形成了以河流放射性分布的經濟輻射格局。廣東商人借助便利的西江航運,以會館為基點,建立起地跨兩廣的商業網絡,形成了影響力很大的一支經商移民隊伍。
由于輻射影響下呈現的“無市不趨東”經濟格局,自然也就出現了廣東商人數量和影響力在廣西境內隨著距離遞減的分布規律。即,明清時期廣西城鎮經濟發育的總體格局只能是:最靠近廣東而且處于兩廣航運交通出入口的東端城鎮經濟的發育程度最高,發展規模最大,而由此往西,隨著地理距離的拉長,城鎮經濟發育的程度和規模則相應遞減,直到廣西西部區域則減至非常微弱的狀態。因此,晚清民國時期廣東商人勢力在廣西的分布情形,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廣東商人絕對占有市場份額的區域。此區域為最靠近廣東且為各支流的總匯的梧州市和航運便利、支流交匯的貴縣以東的潯江西江段城鎮。該區域廣東商人定居或來往的總量最大、比例最高。如,1933年梧州可知籍貫的商家共有795家,其中廣東籍占了505家,為總數的64%。民國時期廣東商人比重在大安鎮占80%以上;在桂平縣的江口鎮占了80%左右;在貴縣縣城約占75%,等等。該區域城鎮不僅是新興的五大行業,而且包括傳統、分散的小行業小商店等,也大多都是廣東商人開辦和經營,本地商人以及其他省商人的勢力微不足道,占有極少的市場份額。
第二類,廣東商人相對占有市場份額的區域。此區域主要包括桂南區、桂西段南區、桂東北區大部分。此區域城鎮中,廣東商人的總人口和比例次于貴縣以東至梧州的潯江西江段城鎮,廣東商人的人數少于本地商人,但由于廣東商人集中開辦和經營近代興起的新的主干行業如經紀、批發、銀號、運輸、新式工廠,在當地經濟領域里仍然起主導作用。因此,屬于廣東商人相對占有市場份額的區域。
第三類,廣東商人占有的市場份額處于弱勢的區域。此區域只限于龍勝三江以東、桂林以北的桂東北少部分地區的城鎮和桂西段北區以及玉林、博白、賓陽的個別縣份。在這類區域的城鎮經濟中,龍勝三江以東、桂林以北的桂東北少部分地區的城鎮靠近江西和湖南,生產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更受湘贛的影響,因此,湘贛商人在該地占有更多的市場份額。桂西段北區距離廣東甚遠,沒有水運到達,交通十分不便利,廣東商人很少到達該地經商。至于玉林、博白、賓陽等部分縣份,當地人民經商熱情高,民營經濟發達,特別是玉林素有“扁擔精神”的經商傳統和美譽,而且沒有大江大河直接連通廣東,因此,廣東商人難以滲透該地經濟領域。
此外,近代新興六大主干行業,也是桂東端城鎮門類最齊、規模最大,而隨著向西移動相應遞減。如1933年,梧州有56個行業,南寧有51個行業,百色只有32個行業;行業規模亦趨遞減,如使用發動機的工廠在梧州有29家,資本額15萬余元,在南寧則減為10家,資本額減為2萬多元,而到了百色則僅有1家,龍州連1家都沒有。經紀、銀號等各行情況也相同。因此,近現代廣西最大中心城市既不是當時的省會桂林和中部的柳州,也不是西南部的南寧和南部沿海的北海,而是各支流的總匯、最毗鄰粵港澳、直接承受經濟輻射的東端城市梧州。[4]
(二)廣東對廣西本土經濟的帶動[5]
“無東不成市”格局對于推動歷史上廣西社會經濟發展曾起到巨大的積極作用。它使落后的廣西與全國最發達的廣東以及香港、澳門直接聯系在一起,使廣西在全國少數民族省區中處于較為優越的經濟區位上,它從廣東向廣西地區輸入了極其重要的勞力、資金、技術、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等生產力要素,以區域分工杠桿,激活了廣西的諸多優勢,推動了廣西市場的初步發育,孕育了廣西作為大西南出海主通道的雛型,為當今廣西區域經濟戰略地位改變奠定了重要基礎。
近代以來,靠近廣東以及西江黃金水道便利優勢讓梧州成為廣西城鎮經濟體系的總中心,同時也就擁有了優良的投資環境:商幫實力雄厚,各類客戶眾多,各種信息靈通,工業機器設備、工料來源豐富,交通網絡發達便捷,產品銷售便捷等,是當時廣西所有城市里所僅有的。因此,晚清民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中,公營(國營)的較大型的現代化企業和事業大多集中在梧州,如光緒三年(1877年),當時的清政府廣西當局就創建了梧州煉銻廠;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桂系政府發起的大規模廣西建設運動中,廣西的公營現代化工業建設進入高潮。梧州市先后于1927年建立梧州電力廠、1928年建立梧州硫酸廠、梧州自來水廠、梧州卷煙廠等,這些工廠無論從資金投入、科技骨干水平,還是動力設備的新建程度和生產規模、管理水平等方面來看,均是當時廣西全省之冠。
廣東對廣西的帶動力還體現在,晚清民國時期,孕育了桂東南商幫、桂南商幫。在過去的廣西一直沒有上規模的商幫,即使是資本主義經濟活躍的明清時期,在桂東南也尚未出現本地商幫的身影。直到晚清民國,廣東經濟的發展和廣東商人的進入,帶動了桂東、桂東南農村商品貿易經濟的率先活躍,農業商品性產品大量增多;新信息、新思想、新觀念、新技術也讓桂東南地區成為廣西思想最開放和接納各種人才的地區。在這種影響下,桂東南、桂南的農民也開始發生較大批量涌入城鎮務工經商的社會現象。勢頭之大,大有超過廣東商人之勢。如,1933年玉林總共有商家436家,廣東商人僅35家,廣西商人卻有400家,其中玉林商人387家。玉林本地人不僅商家數多,而且還把持著新興的主干行業,如蘇杭紡織品行本地人有8家,粵商僅1家。玉林商人又在本地工商業相對飽和的情況下,模仿廣東商人拓展的方式,結成商幫,向桂中、桂西南、桂西北等廣西的邊遠地區輻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南寧、百色、龍州、宜山和忻城、賓陽、柳州等重鎮,都出現了玉林會館或同鄉會。西林、隆林、南丹等極邊的山區,也時常可見玉林商幫的足跡。桂南沿海欽州、廉州、靈山等地商幫的興起也類似于玉林商幫。總之,桂東南、桂南商幫的崛起,在廣西商業史上具有突破意義。它終結了廣西沒有從事長距離貿易的本土商幫的歷史,標志著廣西市場經濟已經開始形成。
此外,在明清時,廣西境內的城鎮經濟行業一般只有傳統的蘇杭、土產收購、典當、手工業作坊、交通運輸、水面六個行業。這六行業屬于簡單商業的三環節(生產者—銷售商—消費者)模式水平,但在受廣東輻射影響最大的桂東南地區,行業發育已逐漸步入較復雜商業的五環節(生產者—代理經紀商—批發商—零售商—消費者)模式水平,甚至在傳統的六個行業之外出現了新行業經紀行和百貨批發行。如道光年間,梧州僅專營柴碳方面的經紀行就有10多間,而且經營規模巨大,每家約年均經銷柴木下廣東多達一百幾十萬斤;桂平江口圩也出現了經紀行而且是當地最大的店鋪。貴縣最大商家粵商林寶昌號是一個大型批發店。經紀行、批發行雖不進行直接的門市經營,卻是商業社會化進一步發展的新行種,具有中介、協調各行商家以及手工業、農業與商業之間的重要功能。它們在廣西的出現較多是進入近代以后的事,但以上桂東南各城鎮在清代中葉即率先形成,反映了靠近廣東的廣西桂東南區域城鎮經濟行業發育在全省具有領先地位,這也正是廣東對廣西本土經濟的帶動作用。
(三)廣東對廣西經濟輻射最強的原因[6]
與廣東毗鄰的省份有湖南、江西、福建、廣西四個省(自治區)。從歷史上看,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興起,近現代的廣東因為毗鄰香港、澳門,因而得到大量的資金和機遇率先發展起來,并以此為中心,輻射周邊4個省(自治區)乃至全國。然而,卻只有廣西接受到廣東最強的經濟輻射。究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天然便利的交通條件。珠江是我國南方的大河,也是我國第二大河流、中國境內第三長河流,流經滇、黔、桂、粵、湘、贛等省(區)及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東北部。在廣東省內,珠江包括西江、北江和東江三大支流,其中西江最長,流量大、落差大(達760米),通常被稱為珠江的主干,航運條件也是最為優越的。而廣東商人需要到鄰省做生意的話,各自的路程便利度各有不同。如,廣東商人進入福建,若走內河,經東江以后,仍要經過陸路才能跋涉入閩,因此一般都只走沿海大道一途。廣東商人進入湖南唯一的一條通道是:由北江—騎田嶺山道—來水—湘江;廣東商人進入江西唯一的一條通道是:由北江—大余嶺山道—章水—贛江。因此,廣東商人進入湖南、江西兩省的唯一通道均需要通過河床淺、河面窄、流量小、航運載重少的北江水路,然后再分別登陸、翻越山嶺,才能分別進入。相比較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商人進入廣西不僅可以通過西江,直接貫透廣西全境,同時還可以通過南海沿海海岸航線直接連通廣西沿海,從北海、欽州、防城登陸進入廣西。特別是,晚清民國時期,基本實現水運輪運化和機電化,進入廣西的水運條件更顯便利,這使得粵港商品經濟的輻射在陸地鄰省中唯對廣西的輻射最為直接、程度最深,使得廣西獨到地形成了“無東不成市”格局。
二是經濟發展的差距最大。廣西由于距離北方政治經濟中心甚遠,再加上歷史、自然和社會等種種原因,歷來都屬于我國經濟開發較晚的地區,直至民國,這一格局基本仍未改變。1949年時,仍被稱為“貧瘠省份”。據20世紀50年代初國家民委調研報告,廣西土著的壯、瑤、苗、侗少數民族人們,生產力仍很低下,在桂林、柳州、南寧一線以西,占廣西面積過半的區域,土著居民的農業仍很原始、粗放,可耕地利用十分有限,刀耕火種,廣種薄收,仍然比比皆是。人口的生息繁衍,也最為緩慢,即使在明清時期由于廣東、湖南、江西三省移民移入一些開發得比較充分的地區,但區域內也仍有不少地方情況類似,如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防城縣志》描述,當時土著居民的農業還處于“旱不求水,澇不疏水,既無糞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的狀況。廣西的農業生產和發展遠遠落后于廣東、湖南、江西、福建四省由此可見一斑。
同樣,在手工業、工業方面也是如此。手工業方面,廣西土著經濟中一直缺乏類似于福建、江西、湖南那樣可與廣東商品相抗衡、具有跨省區輻射能力的商品化手工業大宗產出。“工土之民樸拙,不習奇技淫巧”之類記載,在廣西各縣舊志中比比皆是。在桂西區域的普遍情形是,往往連一個本地專業鐵匠、木匠、泥瓦匠都沒有。即使在手工業較發達的桂東區域,也遠不能與廣東、湖南的手工業相比。據20世紀30年代千家駒等人調查,賓陽的瓷器手工業雖在廣西頗有名氣,但是“因制法笨拙,致其銷場,不惟未能達之省外,即連西江下游,亦無人問津。”現代工業方面,1947年,廣西規模較大的現代化工廠僅有88家,同期廣東則有1117家(尚未含港澳),湖南有405家。廣東的廠數是廣西的12.69倍,湖南廠數也是廣西的4.60倍。
廣西的農業和工業水平低下,自然造成本地商品處于弱勢地位,連帶廣西商人的勢力在本地也弱于其它外省商幫。因此,在毗鄰粵港地區的所有省區中,只有廣西經濟發展水平最落后,與粵港地區形成的經濟差距最大,這使得粵港商品經濟能夠以絕對壓倒優勢推移入抵,廣西也就成為接受廣東經濟輻射最強的地區,廣東商人在廣西成為執掌經濟牛耳的勢力。
三、廣西對廣東經濟發展的推動[7]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西江水系航運發展迅速,兩廣間經濟往來主要依靠西江的水路運輸。據資料記載,當時廣西可通航的河流有937條,納入西江的達748條。馬依、舒瑞萍的《廣西航運史》記述:光緒年間,外商乘船經肇慶抵梧州,認為其航運條件“勝于美國之合順江、德國之黎江也”。西江航運的迅速發展,造就了廣東和廣西頻繁的經貿往來,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互補互動的密切經濟聯系。
(一)廣西土特產品為廣東外貿發展提供貨源
近代廣西與國內外市場的經濟往來中,絕大多數產品均需依存廣東傳輸至國內外。1897年梧州開埠通商后,逐步形成了以梧州為中心的近代廣西城鎮商業市場網絡,梧州發展成為廣西對廣東商品輸出的橋頭堡,起著“兩粵之襟帶”的作用。
據《民國時期廣西對外貿易》及民國時期《廣西經濟》等資料顯示:民國以來,廣西隨著國際市場需求的不斷增大及自身城鎮商業市場網絡的不斷完善,輸出的農貿產品如桐油、礦產品、牛皮、桂皮、桂油及鴨毛等土特產品數額也隨之快速增長。民國元年廣西三關出口值714.52萬海關兩,民國9年增至936.86萬海關兩,民國17年達到1206.22萬海關兩,這些商品中約有40%經廣州、香港等地轉出口國外。
1935年12月,新桂系實施貿易統制政策,成立廣西出入口貿易處,在梧州設立總部,并在八步、平樂、柳州、南寧、香港設分處,統制了廣西桐油、茴油及礦產品鎢、銻、錫、錳的出口,其中梧州總處主管省內購、運、銷三方面業務,香港分處專司對外拋售,省內分處專司收購貿易處所運銷的產品。有關近代廣西向廣東市場提供外貿貨源的情況參見表1:

表1 近代廣西三關部分商品出口貨值統計表(民國16年至20年平均數)
近代廣西與國內的埠際貿易也大多經由廣州、香港等沿海商埠中轉完成。民國22年潘載生《廣西大宗出口貿易調查報告》及廣西省政府統計處《廣西年鑒》第一回記載:廣西運往廣東的商品中,土糖、八角、茶油、茶子餅、火蔴一部分經廣州、香港運往華北各埠。廣西銷往華北各地、天津、上海、青島的食糖(年約350萬斤),銷往華北、東北的八角等都是由各地匯集梧州輸出廣州、香港,再由廣州、香港運往上海,終由上海組織分銷。1933年經由廣西向粵港輸出鮮干果60萬元(毫幣),其中有80%轉運上海;輸出麻4萬元,有70%轉運上海。赤糖60萬元,有50%到穗港后運至上海、華北等地銷售。
廣西各地城鄉土特產經由城鎮商業市場網絡運往廣東,不僅繁榮當地商業與港口貿易發展,連帶推動城鎮原料加工業的發展,同時,對腹地經濟的市場化進程也起到了互相推動的作用。
(二)廣西貨物是廣東居民日常生活消費品的主要來源
廣西谷米運銷廣東其時已久。有史料記載“粵東人稠地窄,谷米不敷,仰賴廣西兼資湖廣”“廣西中歲谷入輒有余,轉輸絡繹于戎(圩),為東省賴”。可見,廣西是近代廣東居民日常生活所需食用品的主要供應地。
清末至民國時期,廣東商人在廣西各江河流域城鎮均設置谷米收購點,收購谷米后匯集梧州運往廣東市場。據孔繁琨的《廣西谷米運銷》、郭松義《清代的糧食貿易》記載:每年的夏秋季節,每天均有5千到1萬石稻米從梧州運往廣州,梧州一個圩市交易量可達20至30萬斤。民國以來,廣西谷米每年途經梧州運往廣東者,年約400萬石。另外根據民國中期的調查:廣西谷米出梧州進廣東的銷售場所,最大為西南,其次為廣州,再次為三埠、都城、佛山、廣利、江門等地。其它比如德慶、悅城、高要、官山、鶴山等埠也是廣西谷米的銷地。民國中期,廣西谷米在廣東各區域的銷量如下:西南地區年銷米60萬擔,谷5萬擔;廣州米22萬擔,谷13萬擔;三埠米10萬擔;都城米8萬擔;佛山米8萬擔;九江米6萬擔,廣利米4萬擔,江門米3萬擔。
除谷米外,廣西每年運往廣東市場的還有大量的食用油和家禽、牲畜等。1921—1931年,梧州專營雞鴨出口廣東的商號有20多家。梁桂青《解放前梧州工商業發展情況及其特點》《廣西地方史民族研究集刊》統計:1923年以來,梧州每日運銷香港的生雞有160籠(每籠100至120只),鴨平均6000至7000只。為縮短雞鴨等家禽運往廣東的時間、提高其質量,民國時期廣東商人還在梧州設置大牲堂,專為江口、平南、大安、濛江、藤縣、梧州等7埠的雞鴨商人服務。這些雞鴨主要供應珠江三角洲地區居民。其它如豬、牛、羊等牲畜產品也輸往廣東、香港等地。據賴彥于《廣西一覽》記述:豬是當時廣西大宗出口之一,每年運銷廣東香港,約值由400萬增至700萬元,廣東占7/10,香港占3/10。產豬最多者為貴縣、平南、桂平、北流等縣。張先辰《廣西經濟地理》載:民國22年,興業、桂平、郁林銷往廣州的生豬有5200頭,貨值約12.32萬元。牛也是廣西大宗出口之一,產牛最多為武鳴、賓陽、上林、那馬、恩隆及左右江流域各縣,多沿水路先運到龍州、百色、南寧等地再匯集至梧州,由梧州出口。《民國25年廣西全省及八大城市(梧、邕、柳、貴、郁、桂、融、宜)出入口貿易概況》載:每年運銷香港者,約值100萬元;香港占9/10,廣東占1/10,全經由梧州輸往廣東、香港。
此外,近代廣西的裝撈業(包括向上裝撈和魚苗培養)主要服務對象也是廣東市場。近代廣東城鎮消費市場快速發展而未出現供不應求的局面,反而實現了工商業經濟的迅猛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廣西長期以來源源不絕的日常生活消費品供應。
(三)廣西為推動廣東工業發展提供市場環境
近代廣東城鎮工業經濟的發展,不僅與廣西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且也有賴于廣西城鎮商業市場網絡發展所帶來的大市場環境。兩廣圍繞工業品的生產協作與銷售,以城鎮商業市場網絡為紐帶和載體建立了廣泛的商貿往來。這不僅為廣東城鎮工業發展提供便利的市場條件,同時也促進了廣西城鎮工商業的發展,形成雙方在經濟上互補互動、密不可分的合作局面。
近代廣東工業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廣西為其輸送原料和提供銷售市場。進入20世紀以來,廣東城鎮工業發展加快,據1912年農商部統計,當時廣東有工廠2426家,其中織造工廠類413家,機器及器具工廠類189家,化學工廠類1154家,飲食品類560家,雜工廠類109家,電氣廠1家。城鎮經濟結構的高速發展,對生產原料的需求量十分巨大,必須不斷通過貿易從外地市場購進。這個外地市場主要的鄰近的廣西市場。如近代廣東城鎮手工業和機器繅絲業需要大量的柴炭,用以燒煉、烤餅、烘蠶繭等,從而刺激帶動了廣西柴炭出口業的急速發展。梧州、南寧、柳州等地的廣東商人紛紛在當地開設燃料收購點,組織柴炭運銷廣東市場。梧州作為商品輸出廣東市場的中心,也是柴炭出口廣東的最大集中地。清末梧州每年有1000多萬斤柴炭運往廣州、江門等埠銷售。
近代廣東城鎮機器繅絲業的發展也助推了廣西桑蠶業的發展。馬丕瑤《酌保桑蠶出力員紳折》《馬中丞遺集》卷三所載:1891年5月,廣西全省種植桑樹約達2.67億株。當時桂東南的平南、容縣、貴縣、蒼梧等地桑蠶業十分興盛。據《平南縣鑒》載:“桑,本縣沿河一帶所植為多,用以飼蠶,蠶繭繅絲,為農民最有利益之副產品”。為了組織生絲出口,廣東的商人不僅在梧州開設大型的絲綢莊,而且在各桑蠶產地市場遍設收購行號,形成了架構嚴密的商品收購系統。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三冊載:在容縣,粵商雇傭幾位育蠶專家,并建立了六家絲店收購生絲,成績甚為良好。絲的品質優良,運到廣東、香港后每擔成本約為340元。清朝末年,桂西鎮安府也出現“遍地皆桑,絲繭廣出”,絲行紛紛開設的景象。此外,近代廣東城鎮電力、船舶制造業及鋼鐵冶煉生產所需的煤、焦碳等原料大部分也是由廣西供給。《平桂礦務局志》載:光緒十年(1884年),廣東官礦局派人組建廣利昌、元亨利等公司,在賀縣西灣用土法開采煤并收購本地人采出的煤,運回廣東供生產之用。直至民國時期,西灣官礦局等機構組織生產和收購的煤仍大部分運往廣東銷售。外銷煤、焦碳主要客戶是梧、穗、港一帶的鋼鐵廠、電力廠及輪船公司。
近代廣西還是廣東工業制造品的重要銷售市場,廣東工業制造品沿西江流域銷往廣西境內城鄉各地。梧州作為近代廣西經濟中心城市,其進口的貨品大部分也是經廣東地區而來。馬依、舒瑞萍《廣西航運史》載:1904年,梧州進口貨物價值751萬余兩關平銀,其中經香港而來者為748萬兩(有150余萬兩為中國沿海各埠的土貨由香港運來),經廣東和三水運來為3萬余兩。張先辰《廣西經濟地理》載:連地處桂西的百色城也是“廂外市肆喧鬧,舟載馬馱,百貨云集,類皆來自東粵……,非土產也”。近代廣東輸往廣西的工業品中,數量最大者為棉布、棉紗。據1932年調查統計:當年廣西部分地區貿易局購買廣東生產棉紗布貨值為:郁博局3469元(毫幣),賀縣局3.48萬元,全縣局1373元,懷集局1.34萬元。南寧經營廣東棉紗業的約30家,以廣東商人最多,資本有3—5萬至數10萬不等。此外,近代廣西城鄉市場上出售的瓷器、火柴、文具、衣著、綢緞等商品大多數均產自廣東。
四、小結
近現代廣西經濟和廣東經濟形成交融互補、密不可分的發展格局,主要得益于兩廣間便利的珠江水系航運系統。兩廣間的經貿交往促使廣西形成了遍及各地的城鎮商業網絡,并逐漸沖破了分散、狹隘、封閉的格局,從而與廣東市場建立起廣泛的商貿往來,促進了雙方的經濟交流。這既為廣東城鎮工業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場條件,也促進了廣西城鎮工商業的發展,促使雙方的經濟聯系向更深層次的互動良性合作方向發展。而兩廣經濟聯系的日益加強,必將在更廣闊范圍內推動廣西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