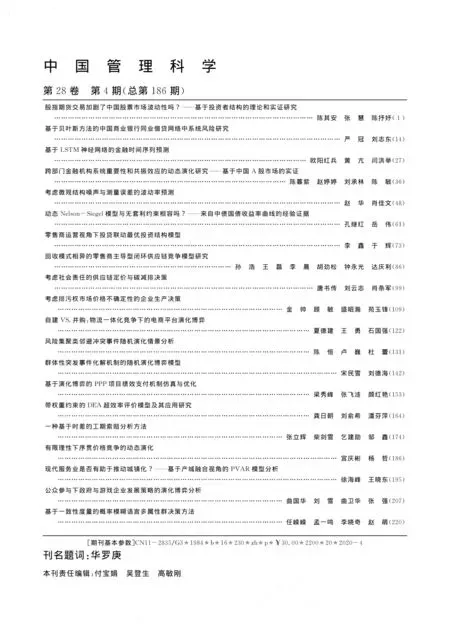考慮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性的企業生產決策
金 帥,顧 敏,盛昭瀚,苑玉鋒
(1.江蘇大學管理學院,江蘇 鎮江 212013;2.南京大學社會科學計算實驗中心,江蘇 南京 210093)
1 引言
隨著排污權交易在全球范圍內的深入推廣,考慮排污權交易的企業生產決策已經成為企業運作管理領域的熱點問題[1-2];特別是,經濟形勢、環境變化、政策導向、技術進步等內外因素的交織影響,決定了排污權交易體系充滿了不確定性;面向不確定情境的企業生產決策更是該領域研究前沿。已有學者在產品市場需求不確定情境下對該問題開展了深入研究。例如,Manikas和Godfrey[3]運用報童模型研究了考慮排污權購置成本和超排處罰成本的企業最優產量問題;Zhang Jingjiang等[4]研究了污染凈化水平確定的排放依賴型企業在污染單次凈化與多次凈化情形下的最優產量決策及多次凈化的最優次數問題;Du Shaofu等[5]進一步研究了初始配額不足的制造商與配額出售方之間的博弈過程機理及其最優決策;Zhang Bin和Xu Liang[6]則立足多產品需求隨機且相互獨立情境,基于報童模型研究了考慮碳排放交易下的多產品最優生產決策問題。
事實上,作為一種基于市場的減排手段,排污權交易主要通過建立環境容量產權市場,在供求機制、競爭機制等的刺激下,使環境容量資源價值以市場價格的形式展現出來,并借助價格的配給與分配功能,指導微觀層面企業做出經濟合理的生產決策,成本有效地實現減排任務的再分配[7];然而,縱觀國際上有關CO2、SO2與NOx等交易實踐不難發現,排污權市場價格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并給企業現實生產決策帶來了顯著影響與障礙[8]。進而,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性被視為該體系下不確定決策的核心特性,逐步受到重視。例如,Gong Xiting和Zhou[9]在市場需求與排污權價格隨機情境下,研究了擁有常規與清潔兩種生產技術的制造商在有限規劃期內實現貼現成本最小化的生產規劃與排污權交易策略;Song Shuang等[10]運用兩階段隨機模型,在需求與碳配額價格隨機情境下研究了考慮碳排放約束的制造商最優產能擴張與生產問題;Pommeret和Schubert[11]在未來總量約束隨機引發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情境下,從跨期污染控制成本最小化視角研究了企業清潔技術投資與污染處理決策以及排污權存儲帶來的影響;易永錫等[12]則運用實物期權法,研究了排污權價格不確定下實現預期成本現值最小化的廠商污染治理投資決策問題。
總體而言,在考慮排污權交易的企業不確定決策研究領域已產生了一些探索性成果,并為企業經營實踐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然而,現有研究以基于期望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 EUT)的分析為主導,而極少考慮到決策者行為偏好對其決策的影響。特別是,EUT所依賴的完全理性假設,由于對現實的解釋力不足,愈發遭受理論界質疑,大量行為科學研究也表明不確定情境下的人類決策行為呈現有限理性特征[13];鑒于此,Kahneman等行為科學家在充分考慮決策者有限理性、重視決策行為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把心理學研究和經濟學研究結合在一起,提出了一種新的不確定情境下決策分析的描述性范式: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 PT)[14-15]。經過30多年的論證,前景理論已經成為行為決策領域的重要研究范式,并解釋了經濟社會諸多領域中的人類決策行為及異象;在企業運作管理領域也得到了廣泛運用,典型的是關于報童問題的系列研究。其中,Schweitzer和Cachon[16]最早將前景理論引入到報童問題研究中,并經實驗發現:需求不確定情境下的決策者實際訂貨行為總是系統性地偏離基于EUT的報童模型最優解。基于此,一些前沿學者從不同方向加以推廣與系統論證,并較好地解釋了報童決策偏差現象。例如,周艷菊等[17]將基于前景理論的報童問題研究拓展到了多產品訂貨決策領域;Nagarajan和Shechter[18]全面應用前景理論論證了前景理論報童最優訂貨量與經典報童最優訂貨量的大小關系;褚宏睿等[19]進一步研究了分別存在回購和缺貨懲罰及二者均存在的報童最優訂貨量問題;丁小東等[20]則通過改進均值前景模型,從理論上深入論證了前景理論對報童決策偏差的適用性。
遺憾的是,目前在考慮排污權交易的企業不確定決策研究領域中鮮有運用前景理論的相關探索。值得一提的,Venmans[21]通過對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TS)下比利時16家制陶、石灰、水泥等制造商經理層的深度訪談來研究配額免費分配及價格不確定性對污染削減投資的影響時發現:與行為經濟學一致,經理觀念顯著影響了投資決策,參考點依賴可更好地解釋“為什么免費分配少于排放量相比多于排放量會對污染削減投資產生更大激勵”,而該現象與基于科斯定理的傳統經濟學分析結果是矛盾的;同時,碳配額價格不確定性對9家企業投資決策具有抑制作用,卻對3家企業產生了明顯的激勵作用。由此可見,運用前景理論研究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情境下的企業生產決策行為更具有現實性。然而,現有基于前景理論的企業決策研究也大多是面向產品需求不確定而展開的,相關成果尚且較難以對此提供有力的理論依據。此外,現有考慮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性的企業決策研究也通常是基于污染治理成本最小化而展開的;而實際上,當排污權被賦予流通性后,其便與勞動力、原材料等一同成為企業的資產與生產要素,有必要在微觀層面上將企業產品生產、污染削減、排污權交易等環節納入實際經營決策中進行綜合考慮[1]。
基于以上認知,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本文探索運用前景理論分析框架,針對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這一客觀情境,從企業運作及其優化層面,建立考慮心理參考點與決策偏好的企業生產決策模型,據此深入提取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情境下的企業復雜決策行為特征。本文引入前景理論分析框架是對現有不確定情境下排污權交易企業行為分析及系統建模研究的重要補充,可為相關決策制定提供更貼近現實的理論依據。
2 基本假設與參數
本文采納文獻[1]、[2]、[4]、[7]等共通的基本模型架構,主要考慮政府初始分配、污染削減和市場交易三種排污權來源,以及單污染物管制、單周期生產的情形;重點從企業生產運作及其優化層面,研究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情境下企業在產品生產、污染削減、排污權交易等方面的決策行為特征,如圖1所示;并結合現實情況,做出如下基本假設:

圖1 所研究問題的基本框架
假設1:排污權可在市場中自由交易,且無交易成本與市場支配力,但不允許排污權存儲與借貸。單位排污權對應單位污染的合法排放權利;企業初始分配獲得的排污權數量,即初始配額,記為l0。
假設2:所慮企業具有污染排放依賴性且守法。在確定技術水平下,企業產污量是其產量的增函數;進而,可將其生產收益(即產量獲利,不包含污染處理成本)記為產污量e的函數B(e),且滿足B(0)=0,B″(e)<0,即生產的邊際收益遞減[22];其中,當B′(e)=0時,企業達到了最大理性生產規模[7]。另外,在削減水平r(0≤r<1)下企業單位污染的削減成本為C(r),由于現實中C(r)會隨r的提高而加速上升,故假定C(0)=0,C(1)=+∞,C′(r)>0,C″(r)>0[1]。
假設3:企業是排污權市場價格的接受者。由于現實中排污權核定與監管均以實際污染排放量為依據,故企業生產計劃制定先于排污權市場交易;進而,排污權市場價格是生產計劃制定的重要依據。
假設4:排污權市場價格P是一個非負的連續隨機變量,其均值與標準差分別為μ與σ,概率密度函數為f(P),累積分布函數F(P)既可微也可逆。
3 基本模型建立與分析
在排污權交易體系下,企業污染主要有兩種處理渠道:污染物削減以及與持有排污權相對應的合法排放。基于假設1與2可知,企業通過選擇削減水平r,付出eC(r)的削減成本,能節約er單位的排污權;進而,為了履行總量控制下的減排責任,企業最終選擇的排污權持有量l不得少于其排污權占用量,即l≥e(1-r)。由于排污權不能存儲與借貸,但可自由交易,故企業理性選擇為l=e(1-r),且若l0>l,將出售剩余排污權,若l0 由此可得,企業的凈收益函數為: π=B(e)-eC(r)-P(e-er-l0) (1) 首先分析在特定排污權市場價格p下的企業決策行為特征。根據以上假設與分析,在該情況下,企業最優決策模型可以描述為: s.t.e≥0,0≤r<1 (2) 由于模型(2)的可行域為凸集,轉化為非線性規劃標準形式后的目標函數關于e和r均為凸函數,因此,若(e*,r*)為模型(2)的最優解,必然存在λ=(λ1,λ2,λ3)使下述Kuhn-Tucker條件成立: (3) 對于模型(3),金帥等[7]已經進行了類似的論證(詳見該文命題1與命題4);鑒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贅述,由此易得本文命題1。 命題1:在特定排污權市場價格p下,企業最優削減決策r*、最優生產決策e*均與p密切相關,且滿足: (4) (5) 命題1的經濟學含義在于:① 僅當C′(0)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清晰發現,在排污權交易體系下,排污權市場價格把企業產品生產、污染削減、排污權交易等環節緊密聯系在一起,并成為衡量企業生產經營決策合理與否的重要標準。這也是排污權交易區別于傳統環境管制手段的顯著特征[7]。 作為價格接受者的企業,盡管無法對排污權市場價格做出完美預測,但是可以根據對排污權歷史價格、經濟發展走勢等的分析,形成對未來排污權市場價格的預判;并以此為依據制定生產決策。 因此,若記x為企業生產計劃制定時對排污權市場價格的預測值,則在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情境下,企業的凈收益函數可以進一步描述為: (6) 從式(6)不難看出,面對排污權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企業存在兩難困境:僅當x=P時,決策是最優化的;而無論是高估或低估市場價格,均會導致不同程度的凈收益損失。 期望效用理論是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于1944年,在公理化假設的基礎上,建立的理性人(rationalactor)不確定性決策分析框架。 基于期望效用理論,可得企業凈收益期望值為: (7) 進而,基于期望效用理論,企業在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情境下的最優決策模型可以描述為: (8) s.t.e≥0,0≤r<1 (9) 綜上分析,可得命題2。 命題2:基于期望效用理論,企業在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情境下的最優決策取決于排污權市場價格均值μ,而與價格標準差σ、初始分配量l0等無關。具體而言,企業對排污權的預測價格為μ時,記為pEU=μ,實現期望效用最大化,且最優決策滿足: Kahneman和Tversky[14]通過大量行為實驗發現,決策者真實決策行為會背離期望效用理論,進而提出了前景理論。前景理論有三個基本觀點: ① 參考點依賴:決策者進行不確定情境下的決策時往往會預先設定一主觀心理參考點(π0),并將策略結果(π)與參考點的相對值(Δπ=π-π0)作為衡量策略效用的重要指標,其中,劣于參考點的結果(Δπ<0)定義為“損失”,反之則為“獲得”。 ② 風險偏好逆轉:決策者風險偏好會在參考點附近發生逆轉,且價值函數呈S型,即決策者在面對“獲得”時傾向于風險規避(riskaversion),而面對“損失”時則傾向于風險追逐(riskseeking)。 ③ 損失規避:決策者對損失的規避程度往往大于對相同收益的偏好程度(λ≥1)。 基于以上觀點,前景理論用最大前景效用原則替代了EUT的最大期望效用原則,并建立了一套包括相對結果、價值函數、決策權重函數等的效用度量體系。具體而言,決策方案的前景效用值U由價值函數v(Δπ)和決策權重函數w(ρ)共同決定,即: U=∑vi(Δπ)w(ρi) (10) 價值函數v(Δπ)反映的是決策者對每個期望結果π相比參考點π0的主觀價值,而非最終財富狀態;參考點的設置取決于實際決策場景。目前廣泛采用的價值函數是Kahneman提出的冪函數形式: (11) 其中,α和β(0<α,β≤1)分別反映決策者對收益和損失的敏感程度;λ(λ≥1)表征決策者對損失規避相比相同收益偏好的厭惡程度。 決策權重函數w(ρ)反映的則是決策者對每個期望結果出現的客觀概率ρ所進行的概率調整,以增加小概率事件的影響,并降低高概率事件的影響。Tversky與Kahneman[15]在吸收等級依賴等思想的基礎上,突破傳統線性權重形式的限制,提出了累積前景理論(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 CPT),將前景理論推廣到具有多種結果的方案前景效用評價,并通過實驗提出了決策權重函數的代數形式: (12) 其中,w(0)=0,w(1)=1,γ為獲得的風險態度系數,δ為損失的風險態度系數。 記π0為企業生產計劃制定時的心理參考點,即預期利潤,根據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情形下的企業收益函數與基本假設,可知企業的心理感知收益為: (13) 1)當Δπ≥0時,企業面臨感知“獲得”。由式(13)可知,企業感知獲得的區間為: 進而,企業感知獲得對應的期望價值函數為: (14) 2)當Δπ<0時,企業面臨感知“損失”。同樣,由式(13)可知,感知損失的區間為:P>max{0,θ}; 進而,企業感知損失相應的期望價值函數為: (15) 1)當Δπ≥0時,企業面臨感知“獲得”;同理,由式(13)易知,該情況下企業感知獲得的區間為:P≥max{0,θ},及其相應的期望價值函數為: (16) 2)當Δπ<0時,企業面臨感知“損失”;同樣,由式(13)可知,感知損失的區間為:P (17) 1)當Δπ>0時,企業面臨感知“獲得”,相應的期望價值函數為: (18) 2)當Δπ<0時,企業面臨感知“損失”,相應的期望價值函數為: (19) 決策權重函數是針對決策者面臨不確定問題決策時所表現出的概率判斷扭曲心理行為特征,把每種期望結果的客觀概率向決策權重轉化而進行的系統性改變。在本文,企業感知事件所對應的客觀概率即為對應的排污權市場價格的分布概率。 (20) (21) 基于Kahneman等在前景理論中所指出的評價階段的效用函數式(10),并參照周艷菊等[17],用期望價值函數替代前景理論中相應的價值函數。 綜合以上三種情況可得,任一排污權預測價格x下企業的前景效用值為: U(x) (22) 根據上述各式,代入各項實際數據及α、β、γ、δ、λ等參數,可以得到前景效用U與排污權預測價格x的函數,運用數值計算,即可找到實現前景效用最大化的排污權預測價格x*PPT;進而,以此為依據,根據式(4)與式(5),可以確定基于前景理論的企業最優生產量和最優削減水平(ePT,rPT)。 為了深入考察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情境下的企業決策行為特征,特別是心理參考點、風險態度、初始分配量等對企業決策的影響,本文進一步開展量化研究。同時,結合現有研究成果,對模型進行細化假設與參數取值如下: 假設5:參照杜少甫等[1],假定企業單位產量所產生污染量為ε;產品價格由其產量q決定,不失一般性,考慮線性逆需求函數pc(q)=k-aq;進而,B(e)=(k-ae/ε)e/ε。另外,企業在污染削減水平r下的單位污染削減成本C(r)=c0r/(1-r)。 假設6:考慮到價格分布通常具有非負、單峰與正偏態等特征,假定排污權市場價格服從Gamma分布,即P~Γ(μ2/σ2,μ/σ2),如圖2所示。這是與現實情況相吻合的。 圖2 排污權價格的Gamma分布示意圖 參照杜少甫等[1],設計企業相關參數取值如下:k=150,a=0.5,ε=1.5,c0=16;基于此,可得企業在不同特定排污權市場價格p下的最優決策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不難發現,e*、l*等與p負相關,而r*則與p呈正相關。 表1 基礎參數取值下的企業最優決策結果 在此基礎上,設定排污權市場價格參數取值為:μ=45,σ=20;由命題2可知,基于期望效用理論,企業在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情境下的最優決策結果與表1中p=45的決策結果的一致的;此時,最大期望效用E(π*)=4371.27+45·l0。 參考Tversky和Kahneman[15]基于行為實驗對前景理論模型相關參數的估計,設定α=0.88,β=0.88,γ=0.61,δ=0.69,λ=2.25。同時,為了深入展現企業的決策特征,在上述參數取值基礎上,設定兩組對照情景:l0=50與l0=150。由表1可知,這兩組情形中企業基于期望效用理論的決策結果為pEU=45,并分別在市場中購買與出售排污權。 此外,鑒于l0不同會直接影響企業的期望收益,為了增強不同情形下結果的可比性,設定企業心理參考點π0=φE(π*);其中,φ為比例系數。進而,當φ=0時,π0=0,該參考點可理解為企業生存點,即零利潤;當φ=1時,π0=E(π*),即參考點轉變為企業最大期望收益;而當φ>1時,則意味著企業心理收益大于其期望收益。數值模擬時,心理參考點依次取0.025·j·E(π*),j=0,1,2…80。需要指出的是,為了表述方便,下文對心理參考點的表述簡化為π0=φ,如最大期望收益參考點為π0=1;與此相似地,下文所涉及前景效用值、心理感知的期望價值等也均以E(π*)為基準進行標準化處理。 圖3展現的是l0=50與l0=150下企業前景最優的排污權預測價格PPT及其前景效用值U(PPT)隨心理參考點π0的變化趨勢。總體而言:既定l0下,π0變動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對PPT的選擇,而且最優前景效用值會隨著π0的提高而不斷下降;同時,對比圖3(a)與3(b)也易知,l0不同時,π0變動對PPT影響的結果也不盡相同。 圖3 心理預期利潤對PPT的影響 1)首先考察l0=50算例下PPT隨π0的變化趨勢。由前已知,該算例下,企業基于EUT的最優決策結果是購買排污權。由圖3(a)可見,隨著π0從0不斷提高,PPT呈現“先逐步高出排污權價格均值,繼而逐步下降并將低于價格均值,其后再回升并最終穩定在價格均值水平”的總體趨勢。具體而言:① 當π0<1.05,特別是在[0.075,1.05)內,PPT>45。這表明,基于PT理論,企業具有高估排污權市場價格的動機,與此相應的是,將在生產中減少產量、提高削減水平,進而其排污權占用量與購買量都將降低;這較好地反映出:當預期利潤相對較低(π0<1.05)時,企業面對排污權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總體表現為風險厭惡。② 當π0>1.05,特別是在(1.05,1.475)內,PPT<45,企業將低估排污權市場價格,與此相應的是傾向于從市場中購買更多排污權。由此則反映出:當預期利潤相對較高(π0>1.05)時,企業面對市場不確定性總體表現為風險追逐的。③ 當π0在1.05附近時,即PPT=μ=45;該預期利潤參考點即是企業風險偏好轉變的臨界點。 2)為了深入闡釋PPT隨π0的變化趨勢,本文繼而提取了l0=50下不同排污權預測價格下企業感知隨π0的變動規律,見圖4。需要指出的是,圖4中用“+”標注的點分別為相應π0下實現企業前景效用值、感知獲得期望價值及感知損失期望價值最大化的預測價格,其中,圖4(c)左側實現感知損失期望價值最大化的預測價格即為左上方感知損失期望價值為0的區域,圖中未再用“+”進行標注。由此可見:① 在特定排污權預測價格下,企業感知獲得的概率與期望價值均將隨π0的增加呈現降低趨勢;感知損失的概率及其期望價值則不斷增加。② 當π0<0.075時,實現感知獲得期望價值最大化的排污權預測價格為45,且企業在該預測價格下感知獲得的概率為1,相應地感知損失的概率及其期望價值均十分接近0;因此,風險態度未對決策結果造成實質性影響。③ 隨著π0從0.075逐步增加,盡管感知獲得期望價值最大化的預測價格依然為45,在該價格下感知獲得的概率卻在逐步減少,相比而言,更高預測價格所實現感知獲得的概率更大;同時,由于感知損失相比感知獲得的期望價值比較低,加之高估小概率、低估大概率的概率扭曲心理行為特征,因此,π0在[0.075,0.825)內,企業總體表現為風險規避,并隨π0的增加而愈發顯著。④ 隨π0進一步增加,感知損失的影響伴隨著感知獲得的概率及期望價值的降低而愈發重要,實現感知獲得與感知損失期望價值最大化的預測價格同步下降,企業風險規避特征逐漸減弱,因此,π0在[0.85,1.25]內,最優預測價格逐步降低,并逐漸從風險規避轉向風險追逐;其后,隨著感知獲得影響的漸趨衰退,感知損失占據主導,低估排污權市場價格的風險追逐行為無法提升其前景效用,進而,最優預測價格又重新回到排污權價格均值水平,亦即實現感知損失期望價值的最大化。 3)結合以上分析,再來考察l0=150算例下PPT隨π0的變化趨勢。由前已知,該算例下,企業基于EUT的最優決策結果是在市場中出售排污權。對比圖3(a)與3(b)易知,l0=150下π0變動對PPT的影響趨勢與l0=50下截然相反:隨著π0從0不斷提高,PPT呈現“先逐步偏低于排污權價格均值,繼而不斷提高并將高于價格均值,其后又下降并最終穩定在價格均值水平”的總體變動趨勢。具體而言:① 企業風險偏好轉變的臨界點為在1.075附近。② 當π0<1.075時,企業具有低估排污權市場價格的動機,與此相應的是,在生產中將增加產量、降低削減水平、增加排污權占用量,最終減少其排污權出售量。③ 而當π0>1.075時,企業通過消耗富余排污權、擴大生產規模已無法滿足其心理預期,進而轉向于高估排污權市場價格,通過縮小生產規模并在市場出售更多富余排污權獲得受益,相應地也增加了其對排污權交易市場的依賴程度。這同樣較好地反映出:當預期利潤在風險偏好轉變臨界點左側(π0<1.075)時,企業面對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性總體表現為風險厭惡特征;而在右側(π0>1.075)時,企業總體表現為風險追逐的。由此可見,盡管l0=50與l0=150算例下π0對PPT的影響趨勢迥異,但本質上反映了相同的影響規律。 以上分析總體表明:面對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性,心理參考點對企業行為決策具有重要影響。毋庸置疑,預期利潤不超過其期望收益是相對客觀的;值得一提的,在該情況下,企業往往表現為風險規避,即排污權潛在需求者會降低其需求量,而潛在供應者則會降低其供應量,進而市場流動性會受到損失;這便較好地解釋了排污權交易市場中“惜買”與“惜賣”現象的根源。然而,當心理預期過高時,企業則更傾向于風險追逐,特別是,配額過量企業具有高額出售排污權的投機動機。因此,以上研究能夠較好地從企業行為層面解釋排污權交易市場中“保守行為”與“投機行為”的產生機理,同時也表明了在構建與完善排污權交易體系過程中引導企業設置合理心理預期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經上分析可見,基于前景理論,初始配額不足(l0=50)與過量(l0=150)時企業表現出的風險決策行為存在差異。鑒于此,本文進一步考察l0變動對企業生產決策的影響及其規律,結果如圖5所示。由于l0變動會影響企業期望收益,不同l0下的心理參考點不具備絕對數量上的直接可比性。盡管如此,圖5清晰表明:與命題2不同,基于前景理論,l0變動同樣會對企業決策產生重要影響。具體而言: 1)在不同l0下企業面對排污權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所表現出風險決策行為特征與上一節的分析結果相吻合:① 當企業初始配額不足(l0<83.63)時,若其心理參考點在風險偏好轉變臨界點的左側,企業總體上表現為風險厭惡,即高估排污權市場價格,以減少其排污權購買量,從而降低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性的影響;而若心理參考點在風險偏好轉變臨界點左側,則企業總體上表現為風險追逐,即傾向于低估排污權市場價格,增加其產量及排污權購買量,因為這樣做有機會博取更多的生產收益。② 當企業初始配額過量(l0>83.63)時,風險行為特征與①類似,只是由于此時企業為排污權出售者,其在價格決策上的行為表現與①恰恰相反,即風險厭惡時傾向于低估排污權價格,減少其出售量,并通過擴大自身生產規模,降低價格不確定性帶來的影響;而風險追逐時則會高估排污權價格,試圖通過以更高價格出售更多排污權來博取更大收益。 2)無論初始配額不足,還是初始配額過量,在任意相同情形下,l0變動對企業生產決策的影響也存在差異:① 當初始配額不足時,隨著初始配額的不斷減少,風險偏好轉變臨界點將右移;而且,無論企業表現為風險厭惡還是風險追逐,相應的心理參考點區間都將逐步擴大,換言之,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性對企業生產決策的影響越明顯。特別是,當l0=0時,企業只能從市場中購買排污權;此時,即便在零利潤預期下也具有強烈的風險規避動機;而且,當π0=2時,過高的預期利潤依然會引發企業風險追逐行為。② 與前類似,當初始配額過量時,風險偏好轉變臨界點則會隨著初始配額的增加而右移,企業表現出風險厭惡與風險追逐的相應的心理參考點區間同樣會進一步擴大。 綜上而言,無論企業初始配額過量還是不足,初始配額與其期望最優排污權占用量的偏離越大,則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性所誘發的風險行為越突出。其根源在于:初始配額數量直接關系到企業對排污權交易市場的依賴程度,該偏離越大則排污權交易對企業決策的重要性越明顯。這也從側面反映了初始分配的重要性與復雜性。當被賦予可流通性后,排污權就具備了經濟價值,并與原材料、勞動力等一同成為企業的必需品;當初始配額不足時,企業生產開展將依賴于排污權交易市場,從而不得不去承擔更多的市場風險;而當配額過量時,企業則會將其作為增加收益的資產,從而誘發借助交易獲得更多利益的投機心理行為。更重要的,無論如何,都會扭曲排污權市場價格的形成。因此,特別是,在我國排污權價格機制本身尚不健全的條件下,如何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求合理的權衡是排污權初始分配實踐中值得充分關注的問題;進一步講,就本研究而言,盡管二級市場交易在理論上能實現排污權的合理化配置,但在初始分配階段就應該盡可能兼顧到企業排污權實際需求,從而更有效地逐步培育建立與完善排污權市場價格形成機制。 描述價格不確定性最常用的兩個屬性是均值與標準差,前者是描述中心趨向性指標,后者則是描述可能結果圍繞中心偏離的指標。而決策風險歸根結底源于企業對未來排污權價格的判斷相對于價格均值的模糊性或偏離。因此,在基礎參數取值下,本部分重點針對排污權價格標準差σ變動的影響進行數值模擬分析,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排污權價格標準差σ變動對PPT的影響 圖6分別描述的是l0=50與l0=150時不同價格標準差σ下PPT隨π0的變化趨勢。由圖6可發現,無論企業是初始配額過量或不足,σ變動不會改變企業風險行為隨π0變動的總體趨勢,但顯著影響了企業風險行為與期望最優決策的偏離程度。 1)先分析企業初始配額不足(l0=50)的情況。由圖6(a)可見:隨著σ的增加,① 企業風險偏好轉變的臨界點有小幅右移,即企業會在更高的心理參考點上表現為風險厭惡;② 無論企業總體表現為風險厭惡還是風險追逐的心理參考點范圍均在明顯增加,總體上企業受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性影響的心理參考點區間也在同步擴大,例如,當σ=5時,風險行為僅產生在區間(0.875,1.1)內,而當σ=30時,則在[0,2]區間上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③ 風險厭惡時最大高估價格所處的心理參考點在左移,而風險追逐時最小低估價格所處的心理參考點則在右移,更重要的,PPT與期望最優決策的最大偏離范圍也在隨σ的增加而不斷擴大。例如,當σ=5時,PPT變動范圍僅為[42,48],相應地,企業排污權購買量在最高、最低估價時分別為28.69、39.10單位,總體變化幅度在10.41單位以內;而當σ=30時,PPT變動范圍則擴大為[27,65],這意味著企業風險厭惡時為了規避價格不確定性帶來的決策風險會最少僅占用57.49單位排污權,相應地只在市場中購買7.49單位,而當企業風險追逐時則會最多占用128.92單位排污權,相應地從市場中購買78.92單位,總體變化幅度達到了71.43單位。 2)再分析企業初始配額過量(l0=150)的情況。由圖6(b)可見:σ變動對企業風險行為的影響規律總體上與前一致。隨著σ的增加,企業受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性影響的心理參考點區間及其前景最優預測價格PPT與期望最優決策的最大偏離范圍均會擴大。只是相對而言,當企業初始配額不足時,風險追逐行為只會加劇其對排污權的需求量,進而σ變動在風險規避階段的影響比風險追逐階段更顯著;而企業初始配額過量時,風險追逐能使其有機會以更高價格出售更多排污權而獲益,進而σ變動的影響更顯著體現在風險追逐階段。 由此可見,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性是造成企業實際決策與理性行為偏差的根源;且不確定程度越高則對企業決策行為的扭曲性激勵越顯著,進而,將在宏觀層面加劇排污權價格的不確定性及其與內在價值的系統性偏離,阻礙價格功能的發揮。因此,作為一種基于市場的減排手段,如何建立相對穩定的排污權價格形成機制是體系構建的重中之重。 前景理論中,用來刻畫決策者風險態度的參數主要有:決策者對收益和損失的敏感系數α和β、風險態度系數γ與δ以及損失規避系數λ。本文采用的Tversky和Kahneman[15]所作經典估計,當然也有學者提出了不同主張[18]。鑒于此,參考Nagarajan與Shechte[18]的做法及主要參數取值,進一步開展相關風險態度參數的敏感性分析,探究其對企業決策行為的影響規律。 1)風險態度系數α和β的分析結果,見圖7。由前景理論的效用度量體系可知,α和β僅分別影響面對獲得與損失時的價值函數:α值越小,獲得部分的感知價值越小,即對獲得的感知越不敏感;β值越小,則對損失的感知越不敏感。 基于圖7(a),固定β為0.88,可見:①α變動對企業決策的影響主要集中在風險規避階段,即風險偏好轉變臨界點左側,而基本不會影響到風險追逐階段。其主要原因在于:α僅決定了對感知獲得的價值評估,并不會改變感知獲得的期望價值,即只是對感知獲得部分的期望價值進行了冪次變換;然而,感知獲得在風險規避階段比較顯著,并隨π0的提高而減弱,在風險追逐階段則相較感知損失已微乎其微,進而α變動的影響在后階段無法體現。② 隨著α的降低,企業對獲得的感知愈發不明顯,企業風險規避行為會加劇,即PPT與價格均值的偏離越大。但是,α越小,則α進一步降低帶來的影響會越趨于不顯著,因為無論企業是出售或購買排污權,一方面,由式(11)知,價值函數是冪函數形式,α越小則感知收益變動越小,另一方面,α較小時企業風險規避的空間已十分有限,如在l0=50與l0=150算例下,從表1知,企業不進行交易的預測價格水平分別為73.23與22.12,而當α=0.37時,PPT已經分別達到了70與25。 圖7 不同α與β取值下的PPT變化趨勢 同理,基于圖7(b),固定α為0.88,可見:①β變動對企業決策的影響則主要集中在風險追逐階段(臨界點右側),而對風險規避階段的影響相對較小,只是當β從0.88降低到0.52時,風險偏好轉變的臨界點從最大期望收益點的右側移動到其左側,進而使得企業會在相比更低的心理參考點上從風險規避轉向風險偏好。② 同時,β越小,則PPT與價格均值的偏離也越大,即所表現出的風險追逐行為會越明顯;但是,與α變動影響不同,由于企業風險追逐行為并不受制于自身初始配額,故當β較小時,其降低帶來的影響依然相對顯著,如在l0=50與l0=150下,從表1知,企業期望最優決策分別為購買33.63、出售66.37單位排污權,而當α=0.37時,PPT分別為24與73,相應地購買量或出售量均大幅增加,并接近100單位;而且,這種風險追逐行為還會隨β的進一步降低而加劇。 以上分析總體表明,當β一定時,α越小,企業對獲得越不敏感,進而,相比而言越偏向于風險規避;相應地,當α一定時,β越小,則企業對損失越不敏感,進而越偏向于風險追逐。 2)由前景理論的效用度量體系同樣可知,風險態度系數γ與δ僅分別影響感知獲得與感知損失時的決策權重函數;二者值越小,決策者越傾向于高估小概率事件,而低估大概率事件,如圖8所示;另外,由式(10)知,各情況下的前景值由其期望價值和決策權重共同決定,不難推測,γ、δ對企業決策的影響規律與α、β的影響大致類似。圖9展示了對γ與δ的敏感性分析結果。 圖8 權重函數與γ(或δ)的關系 圖9 不同γ與δ取值下的PPT變化趨勢 由圖9可見:①γ變動對企業決策的影響集中在風險規避階段,而不會改變風險追逐階段的行為。這是由于γ僅決定感知獲得的決策權重;在前階段,感知獲得是大概率事件,其期望價值也相對較高,進而受γ變動影響明顯;而在后階段盡管感知獲得是小概率事件,γ變動會影響其高估幅度,但感知獲得的期望價值太小,進而γ變動的影響微乎其微。同時,在風險規避階段,隨著γ的降低,企業會表現出更強烈的風險規避行為,因為在該階段感知獲得的概率權重會隨γ的降低而下降,而盡管更高預測價格下的期望價值減少,但概率權重增幅更大,進而加大了PPT與價格均值的偏離。②δ變動對企業決策的影響則集中在風險追逐階段,同樣不會改變風險追逐階段的決策行為。同時,δ越小,則PPT與價格均值的偏離也越大,即所表現出的風險追逐行為會越明顯。③ 無論γ還是δ發生變動,在本算例中,均未對風險偏好轉變臨界點產生顯著影響。 3)風險態度系數λ的敏感性分析結果,見圖10。同理,λ主要影響價值函數,其值越大表明:相比同等數量的收益,決策者對損失具有更高的厭惡程度。由圖10,并結合圖4(b)與4(c)可知:由于感知損失在π0較小時微乎其微,而在π0較大且總體表現為風險追逐時又超過感知獲得并占據主導,因此,λ變動主要影響企業從風險規避到風險追逐轉變的階段。總體而言,在該階段,企業決策制定對損失變動的敏感性比較強,而且隨著λ增大,企業越來越看重損失,其風險規避行為也有明顯的強化,但并不會加劇PPT與價格均值的偏離程度。 圖10 不同損失規避系數λ取值下的PPT變化趨勢 綜上分析可見,面對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性,企業風險態度對其生產決策制定同樣具有重要影響,使得即便相同企業在相同決策場景下也可能產生不同的行為選擇。總體而言,風險態度越接近中性(相關參數趨于1),價格不確定性所誘發的企業風險行為會越趨于緩和。因此,建立相對完善的排污權價格形成機制,除了要規范企業行為,在實踐中還有必要引導企業樹立科學、理性的風險意識。 針對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性普遍存在的客觀事實,從企業運作層面,考察了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情境下的企業生產決策問題。具體而言,首先通過建立特定排污權市場價格下生產決策優化模型,提取了企業在產品生產、污染削減、排污權交易等方面決策行為與排污權市場價格之間的關聯性;基于此,在排污權市場價格不確定情境下,運用期望效用理論分析了企業最優生產決策;重點基于前景理論分析框架,建立了考慮心理參考點與決策偏好的企業生產決策模型,并從企業預期利潤、排污權初始分配、排污權價格標準差、企業風險態度等多個角度進行系統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在理想狀態下,企業可以依據排污權市場價格均值理性地選擇期望利潤最大化的生產決策;然而,由于受信息局限、資源稟賦、心理預期、行為偏好等多方面的影響,企業的實際生產行為是非常復雜的,并使其決策系統性地偏離期望最優決策。正如本文結果顯示心理預期利潤、初始配額、排污權價格波動性、風險態度等會都對企業生產決策產生重要影響。 總體而言,前景理論已經成為行為決策領域的重要研究范式,并深刻解釋了經濟社會諸多領域中的人類決策模式及經濟異象。本研究將前景理論引入排污權交易體系下的企業生產決策問題研究中,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業實際決策偏差的形成機理,從而制定有效的規制與引導策略。算例分析也從多個角度清晰刻畫了企業在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情境下的復雜決策行為特征,所得結果更加貼近現實情景,并充分說明了基于前景理論的模型分析,相較EUT而言,能夠更好地描述企業實際生產決策行為。 本文也存在可改進之處,例如將權重函數引入前景理論決策模型后,模型十分復雜,進而研究結論主要通過大量數值模擬的提煉而形成;同時,也可做深入擴展分析,進一步考慮排污權的有償分配、跨周期使用、產品市場不確定性等問題。3.1 特定排污權市場價格下的企業決策行為分析


3.2 排污權價格不確定情境下企業凈收益分析
4 基于期望效用理論的模型分析





5 基于前景理論的模型分析
5.1 前景理論
5.2 期望價值函數








5.3 決策權重函數
5.4 前景效用函數及評價
6 算例分析


6.1 心理預期利潤對企業生產決策的影響

6.2 排污權初始配額對企業生產決策的影響
6.3 排污權價格標準差對企業生產決策的影響

6.4 風險態度對企業生產決策的影響




7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