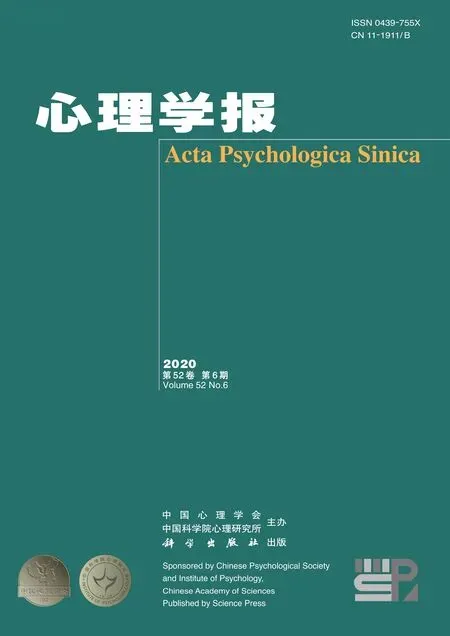他人在場條件下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
張 環 侯 雙 王海曼 廉宇煊 楊海波
他人在場條件下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
張 環侯 雙王海曼廉宇煊楊海波
(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 天津 300387) (國民心理健康評估與促進協同創新中心, 天津 30007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 天津 300074)
在社會互動的提取小組中, 說者的選擇性提取可能會導致聽者對未提及但相關內容的遺忘, 這被稱為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本研究實驗1首先考察了有無真實他人在場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 結果顯示只有在真實他人在場條件下, 該現象才會出現, 說明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受到聽者對自下而上的社會互動情境加工的影響。實驗2進一步考察了在他人在場條件下, 個體的抑制控制能力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 結果顯示該現象只與其作為說者時的個體提取誘發遺忘效應大小有關, 提示了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個體提取誘發遺忘過程類似, 都會受到個體自上而下的排除競爭項目侵入記憶的無意抑制能力的影響。研究結果為理解人際交流情形下個體記憶的形成與改變提供了重要啟發。
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 他人在場; 抑制控制; 無意抑制
1 問題提出
在現實生活中, 人們有大量的機會圍繞著過去的經歷或已獲得的知識與配偶、親人、朋友, 甚至是陌生人在一起交談。在交談過程當中, 談話的內容一般是由話題提出者所選擇的。然而, 由于話題提出者自身的遺忘, 或者其他特殊的原因, 話題提出者會有意或者無意地選擇性提取某些信息。針對信息提出者本人的研究結果發現, 這種對記憶信息的選擇性提取會造成說者本人對特定信息的遺忘, 稱之為提取誘發遺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 Anderson, Bjork和Bjork (1994)認為這是記憶行為固有的性質。以往國內外研究均表明, 說者由于選擇性提取練習而產生的提取誘發遺忘現象具有普遍性(Anderson et al., 1994)。
有意思的是, 在雙人甚至是多人提取小組中, 針對說者之外的其他聽者的研究結果發現, 傾聽他人提取信息, 有可能會造成聽者對特定信息的遺忘(白鷺, 毛偉賓, 李治亞, 2016)。Cuc, Koppel和Hirst (2007)將這種由說者提取某些信息從而導致聽者對相關信息的遺忘, 稱之為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SS- RIF)。關于該現象的認知解釋, 有研究者認為其與說者的提取誘發遺忘現象的認知機制存在著相似性(白鷺等, 2016)。也就是說, 說者在選擇性提取過程中存在著自上而下的控制性提取過程, 這種提取過程同時包括了對目標項目的激活和對競爭項目的抑制, 這種激活與抑制的雙加工模型保證了說者對目標項目的順利提取(Badre & Wagner, 2007); 同樣地, 在社會互動的提取小組中, 研究者推測聽者實時監聽并“內隱地” (covert)發生著與說者相似的控制性提取過程, 進而在隨后的個人提取任務中表現出對目標項目的提取優勢, 以及對競爭項目的長時抑制(Zhang, Zhang, Liu, Yang, & Shi, 2018)。然而, 在社會互動的提取小組中,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并不總會隨著說者的選擇性提取而出現(白鷺等, 2016; Abel & B?uml, 2019)。因此, 探索社會互動提取小組中,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發生條件和背后的認知過程, 對理解這一社會性記憶的發生發展過程來說就顯得至關重要。
為了探討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發生條件, Cuc等(2007)首先在真實互動的雙人提取小組中規定一個成員為“說者”身份, 另一個成員為“聽者”身份, 二人在提取練習任務中以固定的角色完成互動提取練習。此外, 該研究還對互動階段聽者對說者提取練習項目的監聽程度做了控制, 即要求聽者對說者的提取項目分別進行準確性和流暢性監測, 并給出反饋。在最終的個人提取測驗中, 結果發現, 說者在不同實驗條件下均出現了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然而, 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只出現在要求聽者對說者的提取練習項目進行準確性監測的小組中。進一步, Koppel和Storm (2014)的研究發現, 當指導語沒有明確要求聽者對說者的提取項目進行監聽活動時, 大多數的聽者在真實互動提取過程中仍會努力參與說者的提取練習過程, 并“內隱地”與說者一起完成提取任務, 進而在最終的提取測驗中表現出穩定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效應。國內研究者采用中文類別樣例雙字詞作為實驗材料, 同樣發現聽者對提取練習任務的參與程度(詞義或字形準確性判斷)會影響其對特定項目的記憶損害程度(Zhang, Fu, Zhang, & Shi, 2017)。以上以行為學為研究方法的實驗研究, 均操作了真實他人在場這一條件, 結果發現聽者對說者提取項目的監聽程度或者對提取練習任務的參與程度是影響聽者是否產生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重要因素, 這一結果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另外一部分研究者以認知神經科學為研究手段, 試圖探討在實驗室模擬的“社會互動”情境下, “他人”提取內容對個體記憶的影響。在這些研究中, 研究者通常以音頻或者視頻代替真實互動情境下的“說者”, 讓進入到功能性核磁共振設備(fMRI)中的聽者相信自己處于與“說者”實時互動的提取情境下。結果發現, 在這種無真實他人在場(音頻或視頻播放說者的提取內容)的互動提取過程中, 聽者通過認真傾聽而自發產生的與說者類似的神經活動模式, 會對聽者最終的記憶結果產生影響(Zadbood, Chen, Leong, Norman, & Hasson, 2017; 類似研究見Silbert, Honey, Simony, Poeppel, & Hasson, 2014; Stephens, Silbert, & Hasson, 2010)。因此, 這些研究以認知神經科學為研究方法, 均操作了無真實他人在場這一條件, 結果發現只要要求聽者認真監聽“說者”的回憶內容, 聽者的認知過程與神經活動就會發生與“說者”類似的過程, 進而對最終的記憶提取結果產生影響。
由此可以發現, 以往基于行為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為研究手段的研究中, 要么操作真實他人在場, 要么操作無真實他人在場, 去探討在這些“社會互動”情境下, 聽者記憶的認知過程和影響因素。這些研究的先驗假設在于, 有無真實他人在場, 對于社會互動水平的影響不大, 進而對個體記憶的影響就可以忽略。然而, 隨著社會認知神經科學(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發展, 尤其是“第二人稱方法” (Second-person Approach)對社會認知研究的推進(Schilbach, 2019; Schilbach et al., 2013), 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自然情境下社會性互動的基本過程和規律, 以及這種人際間交流對個體記憶和行為的影響。在真實互動的雙人甚至是多人記憶提取過程中, 說者與聽者之間的社會互動始終是“在線”形式的信息傳遞過程(Scholkmann, Holper, Wolf, & Wolf, 2013)。近期的研究已表明, 真實他人在場(如眼神交流、面部表情的表達與識別、有無話輪轉換等等)會影響小組內多個個體在完成合作任務過程中的神經信號同步性, 進而影響其在社會認知任務上的行為表現(Cui, Bryant, & Reiss, 2012; Dai et al., 2018; Jiang et al., 2012; Zheng et al., 2018), 在社會性記憶任務中也有類似的證據(Dikker, Silbert, Hasson, & Zevin, 2014)。因此, 根據社會認知神經科學的新近研究結果可以推論, 是否有真實他人在場會通過改變人際間的社會互動水平, 進而影響個體的記憶過程和結果。
綜上所述, 按照以往基于行為學或者個體認知神經科學為研究手段的結果可以推論, 有無真實他人在場不會改變社會互動水平, 進一步, 也不會影響聽者的記憶過程和結果, 即只要聽者認真監聽“說者”的提取內容, 聽者就應當出現與說者類似的心理和神經活動過程, 進而出現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然而, 按照社會認知神經科學的近期結果可以推論, 相比于無真實他人在場條件, 真實他人在場會通過影響提取小組成員間的社會互動水平進而影響聽者的記憶結果, 也就是說只有在真實說者在場條件下, 聽者才會受到社會性互動的影響, 產生與說者類似的“內隱”的選擇性提取過程, 進而出現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據此, 本研究實驗1基于經典的提取練習范式(Retrieval Practice Paradigm), 操縱了真實他人在場與無真實他人在場(事先錄好的標準化音頻材料)兩種社會性互動水平, 要求聽者均認真傾聽“說者”的提取內容, 旨在探討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產生的邊界條件, 尤其是真實他人在場這一自下而上的社會情境因素是否影響和制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發生。
此外, 在實驗1的基礎上, 實驗2進一步探討在社會互動的記憶提取任務中, 除了他人在場這一社會互動情境因素的影響之外, 是否還有來自個體自身的自上而下的認知調控因素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起作用?以往研究發現,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說者的提取誘發遺忘的認知過程存在著相似性(白鷺等, 2016), 而針對說者的提取誘發遺忘的研究發現, 個體提取誘發遺忘的水平通常與個體的執行控制(executive control)水平有關(Aslan & B?uml, 2012; Aslan & B?uml, 2011; Ortega, Gómez-Ariza, Roman, & Bajo, 2012), 尤其是執行控制系統中的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能力, 被研究者認為普遍與個體的提取誘發遺忘水平(也就是抑制無關信息的能力)有著明顯的相關性(Anderson et al., 1994)。因此, 除了社會互動水平(說者是否在場)之外, 自上而下的、與個體記憶提取相關的抑制控制因素也可能是導致在社會互動情境下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發生的關鍵因素(Abel & B?uml, 2019)。由此, 在本研究實驗2中, 研究者期待進一步探討在真實互動的提取小組內, 聽者“內隱”的控制性提取過程是否與說者外顯的控制性提取過程類似, 都會受到來自個體水平的自上而下的特定抑制控制類型的影響。
2 實驗1:有無真實他人在場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
2.1 實驗假設
在不同實驗條件下, 說者均存在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此外, 按照社會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結果推論, 即便在不同實驗條件下都要求聽者認真監聽說者的提取內容, 然而只有在真實說者在場條件下, 聽者才會出現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
2.2 實驗方法
2.2.1 被試
采用Gpower 3.1軟件, 參考前人關于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研究中(Cuc et al., 2007)采用類別?樣例詞單所得出的項目類型主效應的效應量大小(= 0.5, 實驗1), 并以Cohen (1988)對效應量大中小的界定, 設置中等效應量= 0.3, 即當樣本量達到112時, 項目類型主效應的統計檢驗力在α = 0.05時可以達到0.95。
因此, 本實驗于某高校招募共116名被試(被試年齡在18~26歲, 平均年齡20.21歲,= 1.44, 其中女性79名)。由主試隨機指定其中的60名被試(平均年齡20.33歲,= 1.43歲, 其中女性33名)為真實他人在場組成員; 余下的56名被試(平均年齡20.54歲,= 1.49歲, 其中女性46名)為無真實他人在場組成員。由于無真實他人在場組的一名男性被試在正式的記憶提取實驗中的實驗數據缺失, 故最終該組的有效數據為55名被試(平均年齡20.07歲,= 1.43歲, 其中女性46名)。為了避免社會關系和社交目的等因素對記憶結果可能存在的無關影響, 本研究不同社會互動水平條件下, 均依據同性別陌生人關系原則進行組對(類似操作見Barber & Rajaram, 2011a; Barber & Rajaram, 2011b; Finlay, Hitch, & Meudell, 2000)。
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 裸眼或矯正視力正常, 且母語皆為漢語。在正式實驗開始之前, 所有被試簽訂了知情同意書, 且在實驗結束之后均獲得一定的現金報酬。
2.2.2 實驗材料
由劉旭(2013)的中文類別樣例詞庫中選擇12個語義類別, 每個類別下根據分類頻率(樣例詞與類別的關聯程度), 分別選擇3個高分類頻率項目和3個低分類頻率項目, 一共72個樣例詞作為實驗材料。另外選擇3個類別作為填充材料, 兩個類別作為練習材料。在每個類別中, 所有樣例詞的長度都為兩個漢字, 并具有獨特的首字發音和字形, 此外, 所有樣例詞均為低頻詞。實驗前, 選擇不參加正式實驗的20名心理系研究生按照Battig和Montague (1969)的評定方法對每個樣例詞與其類別的關聯程度進行重新評定, 結果發現每個類別下的高分類頻率項目與低分類頻率項目的類別關聯度存在顯著差異,(70) = ?10.05,< 0.001。此外, 每個類別下的樣例詞在熟悉度、首字筆畫和尾字筆畫上均無顯著差異。
2.2.3 實驗設計
實驗1采用2(互動水平:真實他人在場、無真實他人在場) × 2(互動角色:說者、聽者) × 4(項目類型:Rp+、Nrp+、Rp?、Nrp?)的三因素混合實驗設計。其中互動水平為被試間變量, 互動角色和項目類型均為被試內變量, 因變量為被試在最終回憶測驗中的正確回憶率。
在實驗的提取練習階段, 類別詞與樣例詞均獲得提取練習的項目簡稱為Rp+項目, 只有類別詞獲得提取、而樣例詞沒有獲得提取練習的項目簡稱為Rp?項目, 類別詞與樣例詞均未獲得提取練習的項目簡稱為Nrp項目(白學軍, 劉旭, 2013)。在本研究中, 為了控制樣例詞與類別詞的關聯程度(分類頻率)對實驗結果的影響, 在Nrp類別中, 本研究按照前人研究方法, 分為高關聯度詞(Nrp?)和低關聯度詞(Nrp+) (Wimber et al., 2008), 這一操作亦排除了詞頻效應在提取誘發遺忘中的影響作用。被試在提取練習階段均被要求提取低關聯程度的樣例詞(Rp+)項目, 若Rp+項目的最終回憶率高于未提取練習類別中的低關聯程度樣例詞(Nrp+)項目, 則說明出現了提取練習效應; 若被試對高關聯度樣例詞(Rp?)項目的最終回憶率低于未提取練習類別中的高關聯程度樣例詞(Nrp?)項目, 則說明出現了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2.2.4 實驗程序
正式實驗開始之前, 被試需要先進行練習階段。在被試完全理解實驗程序之后, 開始正式實驗。正式實驗分為4個階段:學習、互動的提取練習、干擾和最終的回憶階段。
本研究的操作中, 真實他人在場實驗條件下的聽說雙方于同一實驗室內, 并排成90°夾角、面對同一被試機而坐。在提取練習階段, 要求說者大聲補全只呈現首字的樣例詞, 而要求聽者緊閉雙眼, 認真傾聽對方的提取內容。提取練習階段進行兩輪, 為了使說者與聽者的角色在兩名被試之間進行輪換。無真實他人在場組的被試獨自在實驗室中面對電腦完成實驗任務, 在提取練習階段, 電腦將播放由同性別實驗助手事先錄制好的音頻材料, 提取練習階段同樣進行兩輪, 要求被試分別扮演說者與聽者的角色, 與“他人”協作完成大聲補全或認真傾聽任務。在不同互動水平的實驗條件下, 均要求作為“聽者”的被試認真傾聽“說者”的提取內容, 并在實驗任務結束后測量所有被試的團體偏好、任務投入度以及共情特質。圖1以真實他人在場條件為例, 說明整個實驗流程。

圖1 真實他人在場組的具體實驗流程
2.2.5 實驗后測任務及工具
正式實驗結束后, 分別對不同實驗條件下的被試進行團體偏好、任務投入度以及共情特質的測量:(1)使用Larey和Paulus (1999)編制的團體偏好量表(Group Preference Scale)測量所有被試的合作傾向性。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數為0.81。(2)使用Xue, Lu和Hao (2018)編制的自我評價模型量表測量所有被試對本實驗的投入度和情感偏好, 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數為0.77。(3)使用Simon和Sally (2004)編制的共情商數問卷(the Empathy Quotient, EQ)作為測量被試共情商數的工具。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數為0.81。
2.3 實驗結果
2.3.1 不同實驗條件下, 后測任務各變量的差異檢驗
分別對真實他人在場與無真實他人在場組被試的團體偏好、投入度和共情商數的量表結果進行分析, 發現兩組被試的團體偏好水平、投入度和共情商數上, 均不存在顯著差異[(113) = 0.18,= 0.855;(113) = 1.08,= 0.282;(113) = 0.38,= 0.704], 說明本實驗的社會互動水平操作是有效的, 即只改變了他人在場因素, 控制了團體偏好、投入度以及共情等其他社會因素對個體記憶提取表現的影響。
2.3.2 不同實驗條件下, 說者的記憶提取成績
對提取練習階段, 說者提取練習的正確率(見表1)進行分析后發現, 在兩種實驗條件下, 說者的正確提取率不存在顯著差異,(113) = 1.38,= 0.170。

表1 不同實驗條件下, 說者提取練習的正確率(M ± SD)
對最終回憶測驗中, 說者的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見表2)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項目類型的主效應顯著,(1, 113) = 618.56,< 0.001, η= 0.846, 95% CI = [0.39, 0.46], 說明在不同實驗條件下, 說者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均高于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互動水平的主效應((1, 113) = 1.79,= 0.184)、以及項目類型與互動水平的交互作用((1, 113) = 1.95,= 0.166)均不顯著。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和前人研究經驗(Anderson et al., 1994; 劉旭, 岳鵬飛, 白學軍, 2019), 采用事前比較的方法(舒華, 張旭亞, 2008)分別對兩種互動水平下的說者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進行配對樣本檢驗, 結果發現, 在不同的互動水平下, 說者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均顯著高于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54) = 15.43,< 0.001,= 2.082, 95% CI = [0.35, 0.46];(59) = 20.02,< 0.001,= 2.580, 95% CI = [0.41, 0.50]) (圖2中的上圖), 說明在兩種實驗條件下, 被試作為說者時均出現了經典的提取誘發促進現象(retrieval- induced enhancement), 即提取練習效應。

表2 不同實驗條件下說者Rp+、Nrp+、Rp?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M ± SD)
隨后, 對最終回憶測驗中, 說者的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見表2)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后發現, 項目類型的主效應顯著,(1, 113) = 9.90,= 0.002, η= 0.081, 95% CI = [?0.08, ?0.02],說明在不同實驗條件下, 說者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均顯著低于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互動水平的主效應((1, 113) = 1.64,= 0.204)以及項目類型與互動水平的交互作用((1, 113) = 0.41,= 0.523)均不顯著。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和前人研究經驗(Anderson et al., 1994; 劉旭等, 2019), 采用事前比較的方法對不同互動水平下的說者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進行配對樣本檢驗發現, 在無真實他人在場的實驗條件下, 說者Rp?項目正確回憶率邊緣顯著低于Nrp?項目,(54) = ?1.87,= 0.067,= 0.247, 95% CI = [?0.08, 0]; 在真實他人在場的實驗條件下, 說者Rp?項目正確回憶率顯著低于Nrp?項目,(59) = ?2.58,= 0.013,= 0.385, 95% CI = [?0.11, ?0.01] (圖2中的下圖)。說明在兩種社會互動水平的實驗條件下, 被試作為說者時, 均出現了經典的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2.3.3 不同實驗條件下, 聽者的記憶提取成績
對最終回憶測驗中, 聽者的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見表3)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項目類型的主效應顯著,(1, 113) = 559.98,< 0.001, η= 0.832, 95% CI = [0.35, 0.41], 說明在不同實驗條件下, 聽者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均高于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互動水平的主效應((1, 113) = 2.39,= 0.125)、項目類型與互動水平的交互作用((1, 113) = 0.90,= 0.346)均不顯著。

圖2 不同實驗條件下說者Rp+、Nrp+、Rp?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
注:= 0.067;< 0.05;< 0.01;< 0.001, 以下同。

表3 不同實驗條件下聽者Rp+、Nrp+、Rp?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M ± SD)
根據本研究目的, 采用事前比較的方法分別對兩種互動水平下的聽者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進行配對樣本檢驗, 結果發現, 在不同的互動水平下, 聽者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均顯著高于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54) = 15.61,< 0.001,= 2.114, 95% CI = [0.32, 0.41];(59) = 17.92,< 0.001,= 2.310, 95% CI = [0.35, 0.44]) (圖3中的上圖), 說明在兩種實驗條件下, 被試作為聽者時也出現了經典的提取誘發促進現象, 即“內隱地”提取練習(covert retrieval)效應(Abel & B?uml, 2019)。
隨后對最終回憶測驗中, 聽者的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見表3)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后發現, 項目類型的主效應((1, 113) = 2.52,= 0.116)、互動水平的主效應((1, 113) = 2.11,= 0.149)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1, 113) = 1.08,= 0.300)均不顯著。

圖3 不同實驗條件下聽者Rp+、Nrp+、Rp?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
因此根據本研究的目的, 采用事前比較的方法, 進一步對聽者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進行配對樣本檢驗發現, 在無真實他人在場的實驗條件下, 聽者的Rp?項目和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不存在顯著差異,(54) = ?0.35,= 0.732; 然而, 在真實他人在場的實驗條件下, 聽者的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顯著低于Nrp?項目的正確回憶率,(59) = ?2.10,= 0.040,= 0.273, 95% CI = [?0.08, 0] (圖3中的下圖)。說明在本實驗操作條件下, 不同的社會互動水平會影響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出現與否, 即真實說者在場條件下, 聽者出現了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
2.4 討論
實驗1的結果表明, 在不同實驗條件下, 說者在最終的回憶測驗中, 均出現了由于選擇性提取練習而導致的對競爭項目的記憶抑制效應, 即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然而, 相比于無真實他人在場的實驗條件, 只有真實他人在場條件下, 聽者在最終的回憶測驗中, 才會出現對說者未練習但相關的競爭項目的記憶抑制效應, 即出現了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這一結果與本實驗假設一致, 即強調了真實說者在場這一自下而上的社會情境因素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 支持了社會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相關推論。
實驗1的結果從社會情境因素角度, 證明了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發生的邊界條件。然而, 若想要真正檢驗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認知過程, 即在真實他人在場條件下, 聽者的“內隱”控制性提取過程是否真實發生這一問題的話, 本研究實驗1并不能給出明確的答案。也就是說, 只有明確辨析在社會互動情境下, 說者的提取練習對說者與聽者所產生的相似的或相異的認知影響, 才能真正檢驗聽者“內隱提取”這一假設, 進而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認知機制提供更為直接的證據。
因此, 在實驗1的基礎上, 本研究實驗2進一步探討來自自上而下的個體抑制控制因素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 實驗結果將推進理解個體差異(尤其是抑制控制)對社會互動情境下的個體記憶過程和結果的重要影響作用。
3 實驗2:不同抑制控制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
3.1 實驗假設
相比于無真實他人在場條件, 在真實他人在場的提取小組內,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該個體作為說者時的個體提取誘發遺忘效應大小存在顯著相關, 即兩種認知過程都會受到個體抑制控制(尤其是有意地抑制來自工作記憶或注意的無關信息的認知抑制能力)的影響。
3.2 實驗方法
3.2.1 被試
實驗2的研究被試同實驗1。本次實驗結束之后所有被試均獲得額外的現金報酬。
3.2.2 抑制控制測驗任務及工具
Nigg (2000)將抑制控制過程分為4種類型, 分別是干擾控制、認知抑制、行為抑制和眼動抑制。與記憶提取任務相關的抑制控制過程主要包含前三種。
(1)干擾控制(interference control)
本研究采用經典的Stroop色?詞范式作為測量干擾控制的工具。參考以往研究, 使用“色?詞”一致和不一致兩種條件下的正確率, 計算Stroop效應量([一致條件下的正確率?不一致條件下的正確率]/一致條件下的正確率) (劉湍麗, 白學軍, 2017)。
(2)認知抑制(cognitive inhibition)
采用定向遺忘研究范式作為測量認知抑制的工具。計算被試的記住率(對“to-be-remembering”, TBR項目的回憶率)和遺忘率(對“to-be-forgetting”, TBF項目的回憶率)。為便于后續的數據分析, 將被試的記住率和遺忘率進行“(記住率?遺忘率)/記住率”運算。
(3)行為抑制(behavioral inhibition)
采用經典的停止信號任務(Stop Signal Task)作為測量行為抑制的工具, 包括反應任務和停止任務。在后續的數據分析中, Stop signal采用了成功抑制率、臨界停止信號延遲時間(SSD)、反應信號反應時(Go RT)和停止信號反應時(SSRT)四個指標(方菁, 朱葉, 趙偉, 張蓓, 王湘, 2013)。其中, 停止信號反應時的計算參考前人研究的方法(Go RT?臨界SSD) (Li et al., 2016)。
3.2.3 實驗程序
為了避免記憶提取任務之間的相互影響, 實驗2中的所有任務在實驗1正式實驗的7天之后進行(類似研究見Finn, Corlett, Chen, Bandettini, & Constable, 2018)。
3.2.4 實驗后測任務及工具
抑制控制測驗完成后, 采用測量工作記憶容量的運算?詞語廣度任務(Operation-Word Span Task, OWST), 對不同實驗條件下的所有被試進行工作記憶水平的測量。
3.3 實驗結果
3.3.1 不同實驗條件下, 抑制控制各變量的描述統計分析
對不同實驗條件下被試的抑制控制各變量(見表4)進行獨立樣本檢驗, 結果發現, 兩組被試的抑制控制各變量均不存在顯著差異[(113) = 0,= 0.997;(113) = ?1.41,= 0.162;(113) = 0.29,= 0.776;(113) = 1.18,= 0.239;(113) = 0.44,= 0.659;(113) = ?0.28,= 0.780]。

表4 不同實驗條件下被試的抑制控制各變量得分(M ± SD)

表5 無真實他人在場條件下, 抑制控制各變量與相對損害值的偏相關

表6 真實他人在場條件下,抑制控制各變量與相對損害值的偏相關
3.3.2 不同實驗條件下, 抑制控制各變量與記憶提取成績之間的相關
分別對不同實驗條件下被試的抑制控制各變量與個體提取誘發遺忘的相對損害值、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相對損害值進行相關分析。表5和表6顯示的是在控制了工作記憶變量后, 不同實驗條件下被試的抑制控制各變量和提取誘發遺忘相對損害值的偏相關。結果發現, 在無真實他人在場的實驗條件下, 除了stop signal變量的內部相關,各變量兩兩之間相關均不顯著(見表5)。而在真實他人在場的實驗條件下, 除了stop signal變量的內部相關, RIF相對損害值與SS-RIF相對損害值呈負向顯著相關(= ?0.31,= 0.018) (見表6)。
3.4 討論
實驗2在實驗1的基礎上, 在不同社會互動水平的提取任務之后, 分別對被試進行了一系列抑制控制任務的測驗, 并將測驗結果與社會互動情境下的個體記憶結果進行了相關分析。結果顯示, 在控制了工作記憶水平變量之后, 只有真實說者在場時,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其作為說者時的提取誘發遺忘相對值呈顯著負相關, 而其他變量之間均無相關關系。這一結果與本實驗假設不符。
按照Nigg (2000)對抑制控制類型的分類及解釋, 個體的認知抑制是指有意地抑制來自工作記憶或注意的無關信息的能力, 如指向性忽略(directed ignoring)、定向遺忘(directed forgetting)和負啟動范式等等。因此有研究者認為, 在個人的提取練習范式中, 被試需要針對所呈現的線索進行定向的選擇性提取任務, 在這種選擇性提取中, 為了能夠更快更準確地提取出目標項目, 被試需要有意地抑制其他起到干擾作用的競爭項目(Anderson et al., 1994; Anderson & Levy, 2007)。據此, 這些研究者認為個體提取誘發遺忘的大小, 應當與其有意抑制無關信息的認知抑制能力有關, 也就是說, 個體的認知抑制能力越高, 其在提取練習任務中產生的提取誘發遺忘效應量就應當越大。然而, 這部分研究大多使用的是特殊群體(研究被試為老年人群體的研究, 見Earles & Kersten, 2002; Zellner & B?uml, 2006; Anderson, Reinholz, Kuhl, & Mayr, 2011; 研究被試為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群體的研究, 見Foa, Feske, Murdock, Kozak, & McCarthy, 1991; McNally, Kaspi, Riemann, & Zeitlin, 1990)。當使用正常成年人作為研究被試, 考察不同的抑制控制任務與個體提取誘發遺忘效應之間的關系時, Noreen和MacLeod (2015)的研究卻發現, 個體的提取誘發遺忘效應與多個抑制控制任務(包括定向遺忘任務、Stroop任務以及Go/No-Go任務)之間均不存在相關關系。
本實驗結果支持了Noreen和MacLeod (2015)的研究, 同樣得到個體作為說者時, 其提取誘發遺忘與多個抑制控制任務之間均不存在相關關系; 進一步, 本實驗發現了個體作為互動提取小組中的聽者時, 其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效應與這些抑制控制任務之間亦不存在相關關系。對于這種抑制控制各任務間無共同變異的結果, 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經被大量討論過(陳麗娜, 2007)。針對這種結果, 研究者普遍認為, 任何普通的抑制能力(common inhibition ability)都有可能被特定任務的異質需求所異化(Kramer, Humphrey, Larish, Logan, & Strayer, 1994; Shilling, Chetwynd, & Rabbitt, 2002)。同樣地, 本研究實驗2的結果發現, 在不同的社會互動水平條件下, 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Nigg (2000)對抑制控制類型分類的各任務之間并不存在相關關系, 這說明伴隨著提取練習任務帶來的對競爭項目的抑制過程與干擾控制、行為抑制以及有意的認知抑制均不同。
本實驗結果還發現, 在真實他人在場的條件下,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效應與其作為說者時的提取誘發遺忘效應大小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這一結果說明, 在特定的社會互動條件下, 兩種認知過程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性。Friedman和Miyake (2004)在Nigg (2000)的基礎上, 將不同類型的抑制與不同的信息加工階段相對應。根據這一理論, 在提取練習的選擇性提取任務中, 說者對無關的競爭項目的抑制更可能屬于前激活干擾抑制(Friedman & Miyake, 2004), 即一種無意水平的認知抑制范疇(incidental memory suppression); 同樣地, 在真實他人在場的提取小組內, 聽者認真傾聽說者的選擇性提取活動時, 亦會受到這種對競爭項目的無意抑制的影響, 因此以個體為單元的分析中, 提取誘發遺忘效應與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效應大小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本實驗研究結果支持了這一推論。本研究實驗2在實驗1的基礎上, 進一步推進了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認知過程的理解。
4 總討論
本研究通過兩項實驗, 首先從自下而上的視角, 考察他人在場的社會情境因素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 隨后從自上而下的視角, 進一步考察在他人在場條件下, 不同的抑制控制因素對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實驗1的結果顯示, 相比于無真實他人在場條件, 只有在有真實他人在場條件下, 聽者才會出現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即在不同社會互動水平的記憶提取小組內,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發生是有條件的, 尤其在于對“他人”(說者)是否真實在場這一自下而上的社會情境因素的加工有關。實驗2的結果表明, 在真實他人在場的條件下,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效應與干擾控制(Stroop任務)、有意的認知抑制(定向遺忘任務范式)和行為抑制(Stop Signal停止信號任務)得分之間均不存在相關關系, 而只與該個體作為說者時的提取誘發遺忘效應大小有關。這一結果說明了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提取誘發遺忘的發生過程類似, 均與個體在互動提取練習任務中, “努力”地排除競爭項目進入記憶提取的抑制過程有關。本研究結果提示, 在社會互動的提取小組內, 至少存在著來自自下而上的對社會情境的加工以及自上而下的來自個體抑制控制的調控, 這種雙向加工過程共同影響著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發生(雙向加工過程的構想見圖4)。

圖4 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雙向加工過程
以往基于行為學和個體認知神經科學為研究方法的研究認為, 只要聽者認真監聽“說者”的提取內容, 就應該出現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也就是說, 只要聽者的參與程度較高, 在傾聽說者進行提取練習時, 聽者亦會自動地進行“內隱提取”, 進而出現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這與是否有真實說者在場無直接和必然的關系(Koppel & Storm, 2014; Coman, Coman & Hirst, 2013; Coman &Hirst, 2015)。然而, 在本研究的實驗1中, 在記憶提取任務之后測量了被試的團隊合作傾向、任務卷入度水平以及共情商數的結果分析表明, 不同實驗條件下被試均認真參與到與“他人”互動的記憶提取的任務中, 認真監聽“說者”的提取結果。然而, 在無真實說者在場的實驗條件下, 即便聽者均認真監聽了“虛擬說者”的提取內容,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卻沒有穩定地出現。這也就是說, “認真監聽”并不是引發聽者“內隱提取”的必要條件, 也就不是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發生的必要條件。
本研究實驗1發現, 他人在場作為一種社會互動水平因素, 對于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至關重要。以往基于社會認知神經科學為研究方法的研究認為, 社會互動水平越高, 兩個人的神經活動過程的相似性會更高, 且這種更高的神經活動相似性能夠預測兩個個體間更好的理解與合作行為(Jiang et al., 2012)。這種不同的互動水平會對人類的認知加工產生影響并且在腦成像研究中得到多次驗證(Cui et al., 2012; Zheng et al., 2018)。此外, 新近發表在上的一項研究使用埃及果蝠(Egyptian fruit bat)作為研究對象, 考察在真實互動情境下兩個果蝠的神經同步性問題, 及其與社會互動行為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 在同一籠內的一對果蝠的神經同步性要高于在不同籠內的果蝠, 這種神經同步性的提高在控制掉了生物節律因素之后, 依然存在; 進一步, 果蝠的神經同步性與其社會性行為的相關顯著(Zhang & Yartsev, 2019)。該研究結果表明, 其他果蝠在場這一社會互動條件會通過調節神經活動趨于同步的方式影響果蝠的社會認知行為(類似研究見Kingsbury et al., 2019)。本研究實驗1驗證了社會認知神經科學的相關研究推論, 即在以人類為被試的研究中, 證明了真實說者在場這一自下而上的對社會互動情境的加工過程對聽者的記憶提取表現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到目前為止, 關于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認知機制, 研究者普遍推測其與說者的提取誘發遺忘的提取抑制假說(retrieval inhibition hypothesis)相類似(白鷺等, 2016; 李治亞, 2017; Abel & B?uml, 2019)。也就是說, 在社會互動的提取小組內, 聽者只有在伴隨著說者的提取活動時, 實時監聽并“內隱地”提取練習了目標項目(而非僅僅“重學”了說者的提取項目時, Raaijmakkers & Jakab, 2012), 才能產生對目標項目的激活與競爭項目的抑制, 進而出現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
因此, 為了進一步檢驗在社會互動的提取小組中,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的發生過程, 本研究實驗2進一步考察了在不同社會互動水平條件下, 多種抑制控制任務與提取誘發遺忘以及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得分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 在不同社會互動水平條件下,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個體水平的干擾控制(Stroop任務)、有意的認知抑制(定向遺忘任務范式)和行為抑制(Stop Signal停止信號任務)各變量得分之間均無相關關系。這一結果與以往研究結果類似, 同樣對提取誘發遺忘中存在的抑制過程與其他抑制控制任務之間的關系提出了疑問, 并進而對不同任務中所引發的抑制心理過程的相似性提出了質疑(類似研究見Noreen & MacLeod, 2015; Shilling et al., 2002)。此外, 在個人記憶提取研究中, 以往有研究提出了個體提取誘發遺忘的雙機制理論(Rupprecht & B?uml, 2017; Schilling, Storm, & Anderson, 2014),比如, 在提取練習任務中, 提取抑制機制(Inhibition)與阻塞機制(Blocking)分別在不同階段對說者的提取誘發遺忘效應起作用。也就是說, 這些研究認為記憶提取的抑制過程并不僅僅受到提取抑制的影響, 因此個體水平的抑制控制各變量與記憶提取的抑制效應量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本實驗2的結果為社會互動情境下, 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可能存在的雙機制甚至多機制理論提供了啟發。
本研究實驗2亦發現, 在真實他人在場的條件下,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其作為說者時的提取誘發遺忘效應存在相關關系, 這一結果支持了在社會互動的選擇性小組內,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其作為說者時的個體提取誘發遺忘效應量大小有關, 即兩種心理過程的內在機制具有相似性, 這與Abel和B?uml (2019)的最近一項研究結果一致, 即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SS-RIF)和個體自身的提取誘發遺忘(RIF)的內在機制是類似的, 二者均基于一定程度的對競爭項目進行長時抑制的心理過程。對于這種對競爭項目的認知抑制過程, Harnishfeger (1995)提出的對抑制控制的二維劃分理論中, 就曾提到抑制控制存在有意和無意兩種認知水平, 無意抑制發生在意識覺醒之前, 而有意抑制發生在當刺激被歸為無關時, 個體進行有意識地抑制(如思維抑制和定向遺忘等)。Friedman和Miyake (2004)的研究也補充了Nigg (2000)對認知抑制的理解, 探討了認知抑制的無意范疇, 即前激活干擾抑制(指無意地排除先前與任務有關的記憶信息侵入的能力)。在本研究中的選擇性提取練習任務中, 說者根據提取線索盡快地口頭補全目標項目, 聽者緊閉雙眼認真傾聽說者的口頭報告, 對于兩者來說, 他們均沒有明確地主動遺忘競爭項目的目的和意圖, 這種對于競爭項目的認知抑制更多地發生在無意識水平。因此, 這種由于選擇性提取而產生的無意水平的認知抑制量之間存在明顯的相關關系, 且二者均與有意遺忘(定向遺忘, directed forgetting)任務所產生認知抑制量無相關關系, 后者是通過指導語明確要求被試有意地主動抑制干擾信息進入記憶。本研究實驗2為理解真實互動的選擇性提取任務中, 個體的抑制控制能力是如何影響和調控個體的記憶提取表現提供了重要啟示。
然而, 需要關注的一點是, 在本研究實驗2的真實他人在場條件下,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與其作為說者時的提取誘發遺忘效應之間存在的是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針對這種行為上的負相關結果所代表的具體含義, 還需要更多的社會認知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加以關注。在本研究的基礎上, 深入探討社會互動和個體差異因素到底以怎樣的方式交互地影響人們的記憶, 以及其背后的神經基礎又如何, 這些問題就顯得至關重要。人類是具有社會性群居屬性的物種, 人類的大腦也是在這樣一個社會性的環境下才得以發展(Dunbar & Shultz, 2007)。此外, 人類大多數的記憶內容亦是在社會互動情境下形成的, 并保存為個體記憶(Csibra & Gergely, 2009)。那么, 在想要真正理解人類記憶這一宏觀問題時, 自下而上的社會互動因素以及自上而下的抑制控制因素就顯得至關重要。由此可見, 未來的研究應當考慮在社會互動提取過程中, 觀察記錄聽者的認知加工并實時測量其神經基礎, 以考察在不同的社會互動模式下, 說者的提取行為是以怎樣的形式對不同抑制水平的聽者的認知加工過程和行為結果產生影響的, 這將對自然情境下人際間社會互動的基本規律及其潛在的臨床和教學應用(尤其體現在司法和教育領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5 結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 相對于無真實他人在場的社會互動水平, 只有真實說者在場時, 聽者才會出現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遺忘現象; 此外, 在真實說者在場條件下, 聽者的社會分享型提取誘發只與其作為說者時的提取誘發遺忘效應量大小有關。研究結果首次從理論層面支持了社會互動因素與個體因素對社會互動情境下個體記憶提取表現的共同影響, 從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上為以認知神經科學為研究手段的未來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
Abel, M., & B?uml, K. -H. T. (2019).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in a social context: Do the same mechanisms underlie forgetting in speakers and listeners?,(1), 1–15. doi: org/10.3758/s13421-019-00957-x
Anderson, M. C., Bjork, R. A., & Bjork, E. L. (1994). Remembering can cause forgetting: Retrieval dynamics in long-term memory.(5), 1063–1087.
Anderson, M. C., & Levy, B. J. (2007). Theoretical issues in inhibition: Insights from research on human memory. In D. S. Gorfein & C. M. MacLeod (Eds.),(pp. 81–102). Washington, DC, U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nderson, M. C., Reinholz, J., Kuhl, B. A., & Mayr, U. (2011). Intentional suppression of unwanted memories grows more difficult as we age.(2), 397–405.
Aslan, A., & B?uml, K. -H. T. (2011).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predict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1), 264–269.
Aslan, A., & B?uml, K. -H. T. (2012).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in old and very old age.(4), 1027–1032.
Badre, D., & Wagner, A. D. (2007). Left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cortex and the cognitive control of memory.(13), 2883–2901.
Bai, L., Mao, W. B., & Li, Z. Y. (2016). A new field of social memory: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5), 707–715.
[白鷺, 毛偉賓, 李治亞. (2016). 社會性記憶的新領域:社會性共同提取誘發遺忘.(5), 707–715.]
Bai, X. J., & Liu, X. (2013). Effects of item competitive intensity on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of the elderly.(11), 2481–2484.
[白學軍, 劉旭. (2013). 項目競爭強度對老年人提取誘發遺忘的影響.(11), 2481–2484.]
Barber, S. J., & Rajaram, S. (2011a). Collaborative memory and part-set cueing impairments: The role of executive depletion in modulating retrieval disruption.(4),378–397.
Barber, S. J., & Rajaram, S. (2011b).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rieval disruption from collaboration and recall.(5), 462–469.
Battig, W. F., & Montague, W. E. (1969). Category norms of verbal items in 56 categorie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onnecticut category norms.(3)1–46.
Chen, L. N. (2007).(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陳麗娜. (2007).(博士學位論文). 華南師范大學.]
Cohen, J. (1988).(2nd ed.).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Coman, A., & Hirst, W. (2015).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The effects of group membership.(4), 717–722.
Coman, D., Coman, A., & Hirst, W. (2013). Memory accessibility and medical decision-making for significant others: The role of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72.
Csibra, G., & Gergely, G. (2009). Natural pedagogy.(4), 148–153.
Cuc, A., Koppel, J., & Hirst, W. (2007). Silence is not golden: A case for socially-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8), 727–737.
Cui, X., Bryant, D. M., & Reiss, A. L. (2012). NIRS-based hyperscanning reveals increased interpersonal coherence in superior frontal cortex during cooperation.(3), 2430–2437.
Dai, B. H., Chen, C. S., Long, Y. H., Zheng, L. F., Zhao, H., Bai, X. L., … Lu, C. M. (2018). Neural mechanisms for selectively tuning in to the target speaker in a naturalistic noisy situation.2405.
Dikker, S., Silbert, L. J., Hasson, U., & Zevin, J. D. (2014). On the same wavelength: Predictable language enhances speaker-listener brain-to-brain synchrony in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gyrus.(18), 6267–6272.
Dunbar, R. I. M., & Shultz, S. (2007). Evolution in the social brain.(5843), 1344–1347.
Earles, J. L., & Kersten, A. W. (2002). Directed forgetting of actions by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2), 383–388.
Fang, J., Zhu, Y., Zhao, W., Zhang, B., & Wang, X. (2013). Stop signal task and the related models of response inhibition.(5), 743–746.
[方菁, 朱葉, 趙偉, 張蓓, 王湘. (2013). 停止信號任務及其相關反應抑制理論模型綜述.,(5), 743–746.]
Finlay, F., Hitch, G. J., & Meudell, P. R. (2000). Mutual inhibition in collaborative recall: Evidence for a retrieval- based account.(6), 1556–1567.
Finn, E. S., Corlett, P. R., Chen, G., Bandettini, P. A., & Constable, T. (2018). Trait paranoia shapes inter-subject synchrony in brain activity during an ambiguous social narrative.(1), 2043.
Foa, E. B., Feske, U., Murdock, T. B., Kozak, M. J., & McCarthy, P. R. (1991). Processing of threat-related information in rape victims.(2), 156–162.
Friedman, N. P., & Miyake, A. (2004). The relations among inhibition and interference control functions: A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1), 101–135.
Harnishfeger, K. K. (1995).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inhibition: Theories, definitions, and research evidence. In F. N. Dempster & C. J. Brainerd (Eds.),(pp. 175–204).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Jiang, J., Dai, B. H., Peng, D. L., Zhu, C. Z., Liu, L., & Lu, C. M. (2012). Neural synchronization during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45), 16064– 16069.
Kingsbury, L., Huang, S., Wang, J., Gu, K., Golshani, P., Wu, Y. E., & Hong, W. (2019). Correlated neural activity and encoding of behavior across brains of socially interacting animals.(2), 429–446.
Koppel, R. H., & Storm, B. C. (2014). Escaping mental fixation: Incubation and inhibition in creative problem solving.(4), 340–348.
Kramer, A. F., Humphrey, D. G., Larish, J. F., Logan, G. D., & Strayer, D. L. (1994). Aging and inhibition: Beyond a unitary view of inhibitory processing in attention.(4), 491–512.
Larey, T. S., & Paulus, P. B. (1999). Group preference and convergent tendencies in small groups: A content analysis of group brainstorming performance.(3), 175–184.
Li, Q., Nan, W. Z., Taxer, J., Dai, W. E., Zheng, Y., & Liu, X. (2016).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rs show impaired inhibitory control and risk taking with losses: Evidence from stop signal and mixed gambles tasks., 370.
Li, Z. Y. (2017).(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李治亞. (2017).(碩士學位論文). 山東師范大學.]
Liu, T. L., & Bai, X. J. (2017). The effect of part-list cues on memory retrieval: The role of inhibition ability.(9), 1158–1171.
[劉湍麗, 白學軍. (2017). 部分線索對記憶提取的影響: 認知抑制能力的作用.(9), 1158–1171.]
Liu, X. (2013).(Unpublished doctorial dissert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劉旭. (2013).(博士學位論文). 天津師范大學.]
Liu, X., Yue, P. F., & Bai, X. J. (2019). The correlated costs and benefits problem in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Evidence from effects of response inhibition and item competitive intensity.(5), 1039– 1046.
[劉旭, 岳鵬飛, 白學軍. (2019). 提取誘發遺忘中的相關代價與效益問題:反應抑制能力與項目競爭強度的影響.(5), 1039–1046.]
McNally, R. J., Kaspi, S. P., Riemann, B. C., & Zeitlin, S. B. (1990). Selective processing of threat cues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4), 398–402.
Nigg, J. T. (2000). On inhibition/disinhibition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Views from cognitive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a working inhibition taxonomy.(2), 220–246.
Noreen, S., & MacLeod, M. D. (2015). 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cognitive inhibition? Task demands and inhibitory effects across a range of memory and behavioral tasks.(8), e0134951. doi:10.1371/journal.pone. 0134951
Ortega, A., Gómez-Ariza, C. J., Román, P., & Bajo, M. T. (2012). Memory inhibition, aging, and the executive deficit hypothesis.(1), 178–186.
Raaijmakers, J. G. W., & Jakab, E. (2012).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without competition: Testing the retrieval specificity assumption of the inhibition theory.(1), 19–27.
Rupprecht, J., & B?uml, K. -H. T. (2017). Retrieval-induced versus context-induced forgetting: Can restudy preceded by context change simulate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259–275.
Schilbach, L. (2019). From one to many: Representing not only actions, but interactions in the brain.(1), 5–6.
Schilbach, L., Timmermans, B., Reddy, V., Costall, A., Bente, G., Schlicht, T., & Vogeley, K. (2013). Authors' response: A second-person neuroscience in interaction.(4), 441–462.
Schilling, C. J., Storm, B. C., & Anderson, M. C. (2014). Examin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inhibition in memory retrieval.(2), 358–370.
Scholkmann, F., Holper, L., Wolf, U., & Wolf, M. (2013). A new methodical approach in neuroscience: Assessing inter- personal brain coupling using functional near-infrared imaging (fNIRS) hyperscanning.813.
Shilling, V. M., Chetwynd, A., & Rabbitt, P. M. A. (2002). Individual inconsistency across measures of inhibition: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inhibition in older adults.(6)605–619.
Shu, H., & Zhang, X. Y. (2008).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舒華, 張旭亞. (2008).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Silbert, L. J., Honey, C. J., Simony, E., Poeppel, D., & Hasson, U. (2014). Coupled neural systems underlie the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naturalistic narrative speech.(43), 4687–4696.
Simon, B. -C., & Sally, W. (2004). The empathy quotient: An investigation of adults with Asperger syndrome or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and normal sex differences.(2), 163–175.
Stephens, G. J., Silbert, L. J., & Hasson, U. (2010). Speaker– listener neural coupling underlies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32), 14425–14430.
Wimber, M., B?uml, K. -H., Bergstr?m, Z., Markopoulos, G., Heinze, H. -J., & Richardson-Klavehn, A. (2008). Neural markers of inhibition in human memory retrieval.(50), 13419–13427.
Xue, H., Lu, K. L., & Hao, N. (2018). Cooperation makes two less-creative individuals turn into a highly-creative pair.527–537.
Zadbood, A., Chen, J., Leong, Y. C., Norman, K. A., & Hasson, U. (2017). How we transmit memories to other brains: Constructing shared neural representations via communication.(10), 4988–5000.
Zellner, M., & B?uml, K. -H. (2006). Inhibitory deficits in older adults: List-method directed forgetting revisited.(2), 290–300.
Zhang, H., Fu, Y., Zhang, X. L., & Shi, J. N. (2017). The effect of item similarity and response competition manipulations on collaborative inhibition in group recall.(1), 11946.
Zhang, H., Zhang, X. L., Liu, X. P., Yang, H. B., & Shi, J. N. (2018). The inhibitory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inhibition: Assessment using an emotional Stroop task.Online. https://doi.org/10.1177/0033294118805007
Zhang, W. J., & Yartsev, M. M. (2019). Correlated neural activity across the brain of socially interacting bats.(2)413–428.
Zheng, L. F., Chen, C. S., Liu, W. D., Long, Y. H., Zhao, H., Bai, X. L. … Lu, C. M. (2018). Enhancement of teaching outcome through neural prediction of the students' knowledge state.(7), 3046–3057.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in a naturalistic collaborative retrieval situation
ZHANG Huan; HOU Shuang; WANG Haiman; LIAN Yuxuan; YANG Haibo
(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Center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Promotion of Mental Health, Tianjin 300074, China)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In our daily life, people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to share their memories of past experience or knowledge with others. In such conversation, the phenomenon which, due to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selective retrieval of speakers, listeners forget the unmentioned but relevant memories, is called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SS-RIF).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of the phenomenon, the curr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bottom-up processing of social interactive situations and top-down cognitive control of inhibition on SS-RIF,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presence of speaker or not, and the listener’s ability of various types of inhibition control would affect the occurrence and scale of SS-RIF.
In Experiment 1, a 2 (interactive level: the presence of the speaker, the absence of the speaker) × 2 (interactive role: speaker, listener) × 4 (item types: Rp+, Rp–, Nrp+, Nrp–) mixed design was adopted, in which interactive level was the between-participants design while interactive role and item type were the within-participants desig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correct recall proportion in the final recall test. A total of 116 healthy volunteers participated in Experiment 1. The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different interactive level conditions. All participants of Experiment 1 were recruited in Experiment 2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hibitory control on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in different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t was found in Experiment 1 that, regardless of condition, the phenomenon of within-individual retrieval- induced forgetting in speakers appeared; however, the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in listeners only aros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peaker condition. Furthermore, Experiment 2,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Experiment 1,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was independent from levels of inhibitory control. Interestingly,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peaker condition, the effect of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in listeners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effect of their within-individual retrieval- induced forgetting as speakers.
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factor of social interactive situation indee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ffect of SS-RIF.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speaker, through monitoring the accuracy of audio material, listener’s SS-RIF do not appear. Moreover, the finding that levels of inhibition control do not affect SS-RIF may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double or multiple mechanisms under SS-RIF in social interactive condition, that is, not only inhibition, but also other mechanisms such as blocking jointly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SS-RIF.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of the same person’s effect of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as listener and within-individual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as speaker, it can be speculated that the inner mechanism of SS-RIF and RIF shares certain similarities. These finding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occurrence conditions and factors affecting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and shed light on the bidirectional processing model of SS-RIF. Further, they contribute to the revelation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SS-RIF in listeners forming collective memory, and provide some inspiring viewpoints for future research.
socially share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presence of the speaker, inhibitory control, incidental memory suppression
B842; B849:C91
2019-07-31
* 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點項目(TJJX15-002)、天津師范大學校博士基金項目(043/135202WW1711)和天津師范大學“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計劃”項目(040/1353P2WX1804)資助。
楊海波, E-mail: yhbps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