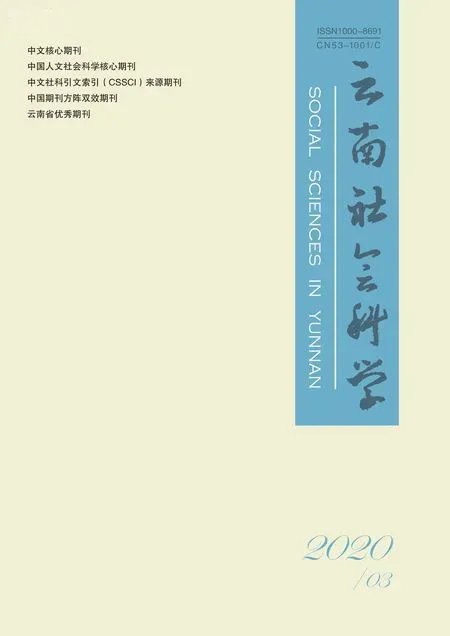次邊疆治理:歷史鏡鑒與實踐意蘊
——以西部邊疆地區為中心的考察
丁忠毅 黃一鑫
疆域是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的基本構成要素,因而國家是一個政治地理空間單位。①周平:《國家治理須有政治地理空間思維》,《探索與爭鳴》2013年第8期。對于擁有較大政治地理空間的國家而言,不同國土空間在國家治理全局中發揮著不同功能。站在國家治理全局,根據國家地理空間結構,把握地理空間互動關系,發揮不同地理空間單元在國家治理全局中的功能,促進不同地理空間功能的互補互促,是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內在要求。中國擁有超大規模的政治地理空間,不同國土空間具有較大異質性,國家治理規模和治理負荷具有超大性特征。②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14—18頁。有效克服國家治理的超大規模和負荷難題的重要方式便是對國家疆域劃分為不同空間單元,賦予不同空間單元以不同功能,并進行差異化治理。在探索治理“由國家政權的統治中心到域外的過渡區域”③馬大正:《中國邊疆治理通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5頁。的歷史進程中,統治者根據國家治理需要,逐漸將疆域的邊緣性部分與核心區或腹地區界分出來,將其界定為“邊疆”④周平:《中國邊疆政治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3頁。,邊疆治理制度隨之應運而生,國家空間治理的“核心—邊緣”二元結構也逐漸被型塑,并對國家治理產生了持續而深遠的影響。受“核心—邊緣”二元空間觀的深刻影響,無論是當前國家對陸地邊疆的治理實踐,還是理論界對邊疆治理問題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次邊疆”地區的重要性。超越國家空間治理的“核心—邊緣”二元結構敘事和思維定勢,在更大的空間尺度范圍把握“主邊疆”治理和“次邊疆”治理的互動、互構關系,更好發揮“次邊疆”治理對“主邊疆”治理的促進作用,是新時代提升邊疆治理乃至整個國家治理效能的內在要求。西部邊疆地區地域廣闊,周邊地緣政治形勢復雜,在國家長治久安和發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本文擬聚焦西部邊疆地區,探討西部次邊疆治理對西部主邊疆治理的重要戰略地位及其實現路徑。
一、國家治理全局中的“主邊疆”與“次邊疆”治理
國家的疆域是“一個被精細界分然后得以組織構成的地理空間”①蘇力:《大國憲制:歷史中國的制度構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28頁。。對國家所占據的地理空間進行合理界分是分解國家治理負荷、提升治理有效性的必然要求。早在先秦時期就存在的“五服”“九服”觀念,已反映出中國古代的統治者以王畿為中心向四周界分地理空間并予以差別化對待的空間觀念和治理實踐,②周平:《我國邊疆概念的歷史演變》,《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正如《三國志·魏志·行?傳》所說:“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此后,王朝國家逐漸將國家的地理空間界分為邊疆和核心兩大板塊,國家空間治理的“邊緣—核心”二元結構被型塑。數千年來形成的這種“核心—邊緣”治理思維和治理模式具有深遠歷史影響和強大的歷史慣性,直接影響國家治理的戰略認知和實踐選擇。然而,國家的邊疆地區和核心地區并非涇渭分明,“邊緣—核心”的二元空間界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在國家的邊疆地區和內地之間存在一個廣袤的過渡地帶和連接地帶,且這一地帶在國家治理的空間結構中具有重要地位。突破國家治理的“邊緣—核心”二元空間思維和模式定勢,亟需對邊疆地區和內地之間的過渡地帶及其在國家治理的空間結構中的作用予以特別關注。
中國陸地邊疆地區的空間尺度包括縣、市、省3個層次。與邊境相鄰的193個縣級行政區域是狹義層面的邊疆;與邊境相鄰的45個市級行政區域是中觀層面的邊疆;陸地邊境9個省區是廣義層面的邊疆。③193 個邊境縣級行政區域包括135 個邊境縣(旗、市、市轄區)和新疆建設兵團的58 個邊境團場。參見周平:《論我國邊疆治理的轉型與重構》,《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如果將陸地邊疆9省區視為主邊疆地區,那么這些地區與內地之間的過渡地帶和連接地帶,便可視為次邊疆地帶。如果以邊疆地區為中心,次邊疆地區可視為邊疆的邊緣地帶,其邊疆性特征仍較顯著;如果以其所在省份的省會城市為中心,次邊疆地帶又可視為內地的邊緣地帶,其經濟發展水平、文化習俗、民族構成在總體上與內地核心區域仍然存在一定差異。在國土空間結構中,次邊疆地帶是內地和邊疆地區的地理、經濟、政治、文化連接地帶,又是一個“雙邊緣”地帶。因而,次邊疆帶既與主邊疆地帶構成一個相互協動的體系,又與內地核心地區構成一個相互連動的體系。④孫勇、王春煥、朱金春:《中國邊疆帶治理重點指向》,《華西邊疆評論》2016年輯刊。
國家的空間治理能力是影響國家治理績效的核心要素。在“核心—邊緣”二元空間視域下,國家的核心區域是其立國的根本,是國家積聚力量的基本條件,⑤周平:《邊疆在國家發展中的意義》,《思想戰線》2013年第2期。邊緣地帶既是拱衛國家核心區發展的重要空間,也是國家外向性發展的依托空間。國家的核心區和邊疆地區雖然在國家治理全局中具有不同地位,發揮不同作用,但并不意味可以厚此薄彼,甚至忽略邊疆治理。邊疆在地理空間上遠離核心區,處于國家權力傳輸的空間末端;市場發育相對滯后,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直接承接境外地緣政治博弈壓力甚至面臨他國入侵的威脅,是國家軍事防御前沿;多個民族集中居住,民族文化多元共存,族際關系尤為復雜。⑥周平:《如何認識我國的邊疆》,《理論與改革》2018年第1期。邊疆治理既面臨與國家核心區治理同樣的一般性客體,也面臨諸多特殊客體⑦方盛舉、王志輝:《我國邊疆治理的一般客體和特殊客體》,《思想戰線》2015年第5期。,其任務更加艱巨、復雜。
古今中外國家發展的歷史反復證明,邊疆治理績效關乎國家興衰。⑧丁忠毅:《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邊疆治理的重要論述研究》,《社會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從“富起來”向“強起來”邁進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陸地邊疆治理在國家治理全局中的地位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邊疆地區正日益成為國家開發開放的前沿,成為國家重大戰略的支撐空間,①丁忠毅:《“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西部邊疆安全治理:機遇、挑戰及應對》,《探索》2015年第6期。成為國家發展的新增長極。②周平:《陸地邊疆:國家發展的新增長極》,《新視野》2017年第5期。然而,與新時代國家發展戰略需要不相匹配的是,陸地邊疆地區往往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典型空間,往往是敵對勢力插手干預的集中區域,往往是非傳統安全問題易發高發區域,往往是社會穩定基礎相對脆弱的空間場域。雖然近年來執政黨和政府站在國家發展全局高度重視邊疆治理,持續實施對口援藏、對口援疆、東西部扶貧協作、興邊富民等重要政策,有力促進了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但加快推進邊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著力補齊邊疆治理短板,仍是國家治理的戰略性課題。
次邊疆與主邊疆唇齒相依、指臂相連。地緣上的鄰近關系決定了主邊疆和次邊疆地帶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建設中的高頻度、常態化、深層次的互動,決定了主邊疆治理和次邊疆治理二者之間既相互促進、又相互掣肘的協同聯動關系。從國家疆域盈縮變遷的歷史來看,主邊疆和次邊疆隨著國家興衰特別是其控制的地理空間的變化而相互轉化。當國家能力強盛,控制的地理空間增加時,曾經的主邊疆地區則可能變成次邊疆;反之,當國家實力衰弱、邊疆治理能力下降,邊疆地區脫離其轄治時,曾經的次邊疆則變成主邊疆。從國家的安全防衛來說,“主邊疆”始終作為國家安全防御的最前沿,負責維護和管控邊境安全穩定,確保國家控制的疆域的完整性,提供國家安全的戰略縱深。“次邊疆”地帶則往往設置重要的軍事基地,和平時期作為戰略威懾,一旦主邊疆地區發生戰事,則可增援主邊疆,為“主邊疆”提供兵力、物資等多方面的后勤補給,成為應對戰事的后方指揮中心和保障中心,屬于國家安全防御的次級地帶。如宋朝便實施極邊、次邊、近里三級制邊疆層級體系,其中“極邊”地帶以寨堡為據點駐守,起到應對邊警的作用;“次邊”地帶為重點防御區,屯駐重兵;“近里”地帶為支援地區。③鄭濤、張文:《極邊、次邊、近里:北宋西北邊疆層級體系三級制界說》,《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從國家對邊疆地區的政治整合來看,國家除致力加強對主邊疆地區的直接轄治外,還注重在次邊疆地區設置相關的政治建制和國家機構,以發揮次邊疆在強化國家政治整合中的前端和前哨作用,從而解決中央權威、權力傳導隨空間距離增加而弱化的梗阻問題,強化中央對邊疆地區的政治轄治和整合。從經濟發展角度看,次邊疆地區往往是主邊疆地區和核心區域經濟互動的連接區域和活躍區域,是內地經濟輻射主邊疆地區,帶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協調發展的重要空間。從社會穩定角度看,由于空間場域的近鄰性、族群關系的親緣性、利益關系的復雜性、交往互動的持續性,主邊疆和次邊疆地帶的安全穩定具有典型的互構性特征,無論是主邊疆地區的安全穩定問題,還是次邊疆地區的安全穩定問題,都具有顯著的“蝴蝶效應”和“連鎖效應”,從而影響邊疆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安全穩定。
總之,國家空間治理的“核心-邊緣”二元結構敘事和治理模式,有其歷史合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次邊疆這一過渡地帶、連接地帶在國家治理的空間結構中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主邊疆治理和次邊疆治理的互動性與互構性。其結果是,無論決策層還是理論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就問題論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等側重于解決局部問題的傾向,而缺乏在更大的空間視野和格局下,對邊疆治理進行全局性、前瞻性和戰略性謀劃。④孫勇:《西藏:思考的維度(下)》,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63頁。在國家治理全局視野下,主邊疆地區治理的重要性凸顯,隨之凸顯了次邊疆治理的重要性。把握主邊疆治理和次邊疆治理的互構關系,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加快補齊邊疆治理短板的同時,著力補齊次邊疆治理的短板,是新時代整體提升邊疆治理績效,逐漸消解國家空間治理的“核心-邊緣”二元結構負面影響,從而促進邊疆地區與內地協調、一體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基本路徑。
二、西部“次邊疆”治理的戰略地位的歷史認知和實踐探索
邊疆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在國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邊疆規模隨著國家占據的疆域規模、治理能力等條件的變化而盈縮,邊疆的層次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主邊疆和次邊疆也可能發生改變。從歷史的彼時彼境來看,今天的次邊疆地區可能是當時的主邊疆,但當下的次邊疆地區在國家地理空間中的絕對位置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因而,用當下的次邊疆和主邊疆結構分析歷史上這些區域的治理問題,依然適用。
中國西部邊疆地區包括與中亞、南亞、東南亞等地區接壤的新疆、西藏、云南、廣西等省區,①羅中樞:《中國西部邊疆若干重大問題研究》,《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既是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支撐空間,又長期面臨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因而既是國家治理歷來高度關注的政治地理空間,又是國家治理的難點空間。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王朝國家的中央政權在經略當前中國西部主邊疆地區過程中,便深刻認識到甘肅、青海、四川等當前西部次邊疆地區治理的重要戰略地位,并付諸大量實踐探索。本文聚焦甘肅、四川兩大次邊疆地區,簡要梳理歷史上關于其戰略地位的歷史認知和實踐探索,為理解當前西部次邊疆治理在主邊疆治理中的戰略地位提供歷史鏡鑒。
甘肅等次邊疆地區在轄治新疆地區的歷史進程中始終發揮戰略支撐作用。甘肅與新疆唇齒相依,河西走廊連接新疆與腹地,在歷史上一直是西北邊疆防御和經營新疆的戰略基地。早在西漢時期,漢武帝通過河西之戰打通河西走廊,設立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河西四郡,奠定轄治西域的重要基礎。此后,河西地區就成為王朝國家經營新疆地區和守衛內地的邊關要塞。清朝歷史地理學家顧祖禹指出:“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②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六),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972頁。在清初建立的西北邊疆防御體系中,甘肅也是西北塞防的重要布防之地。③楊軍民:《清代陜甘總督與新疆軍政治理——以陜甘總督與新疆各軍府關系為視角》,《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左宗棠在收復新疆過程中提出以下戰略謀劃:“關內外用兵雖有次第,然謀篇布局須一氣為之,以大局論,關內肅清,總督應移駐肅州,調度軍食以規烏魯木齊。”④郭文深:《左宗棠用兵策略及其在收復新疆中的應用》,《廣西社會科學》2007年第9期。在收復新疆的軍事行動中,左宗棠以甘肅為軍事基地,籌措糧餉、整頓軍隊和籌備軍備,最終成功收復新疆。清朝在收復新疆之后,劉錦棠上書朝廷,主張在新疆設省。根據劉錦棠的設想,新疆與甘肅形同唇齒的特殊戰略關系,新疆各項事務必須借助甘肅的支持才能順利開展,“若將關內外劃為兩省,以二十余州縣孤懸絕域,其勢難以自存”⑤陳劍平:《清末“甘肅新疆省”省名辨析》,《歷史教學》2013年11期。。劉錦棠的核心理念正是以甘肅作為支撐新疆建省及管理新疆的戰略支撐,以強化中央政權對新疆的轄治和政治整合。1884年,光緒頒布詔書,新疆正式設省,巡撫駐扎烏魯木齊,受陜甘總督節制,⑥郭琪:《晚清新疆設省始末》,《中國檔案》2019年第12期。這一舉措對化解西北塞防危機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甘肅還是聯通邊疆與腹地的國家經貿通道和文化交流通道。“北有絲綢之路,南有茶馬古道”。陸上絲綢之路溝通著王朝國家核心區與西域(今新疆大部)及中亞、西亞甚至地中海各國,河西走廊正是絲綢之路的黃金地帶和樞紐要道。通過河西走廊,新疆與內地得以開展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不僅增強了新疆和內地的經濟粘性,促進了區域一體化和文化融合,還強化其對中央政權的依附性。⑦周平:《中國邊疆政治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189頁。
“治藏必先安康”。四川藏區與西藏指臂相連。傅嵩炑曾形象地指出:“譬之藏為川滇之毛,康為川滇之皮,藏為川滇之唇,康為川滇之齒,且為川滇之咽喉。”⑧傅嵩炑:《西康建省記》,北京:中華印刷公司,1932年,第2頁。丁寶楨也指出:“川省與藏衛唇齒相依,不能稍分畛域。”⑨吳豐培:《丁寶楨藏事奏牘》,《清代藏事奏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4年,第527頁。四川藏區與西藏的地緣關系和族群關系,決定了其在協調漢藏關系、經略西藏上的重要地位。雖然“治藏必先安康”的理念直至清朝末年才被明確提出,但四川藏區一直是西藏與腹地核心區商貿往來的重要通道、人文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場域。興于唐宋的茶馬古道陜康線(川藏線)便將內地的茶葉、絲綢、布匹、僧服、紙張及金銀等物質源源不斷地輸入西藏,并將西藏的馬匹、皮張、藥材、銅佛、舍利等物資輸入內地,①顧祖成:《明清治藏史要》,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濟南:齊魯書社,1999年,第75頁。促進了西藏與內地的聯系。明朝時茶馬貿易進一步繁榮,并成為中央政權間接控制藏區的重要經濟手段。清朝時川藏線上的商業貿易活動更加活躍,催生了雅安、打箭爐(康定)、甘孜等沿線商業城鎮的興起,既帶動了川藏的商貿交流,促進了藏區社會經濟發展,又促進各族群間的互動,為民族融合奠定了良好基礎。金川之戰之后,清朝為強化對西藏地區的轄制,設立成都將軍一職。這是清朝在西南地區設置唯一駐防將軍職務。在駐扎地址的選擇上,最初的選址為康定和雅安,后因地勢原因和與總督所在地較遠而最終選址成都。但成都將軍所轄副將及官兵皆駐扎在康區要沖,其基本考量在于一旦發生戰事,成都將軍可以及時獲得消息,并“就近調度……更足以聲援而資策應”②《清高宗實錄》(卷1311),乾隆五十三年八月癸丑條。。
清朝末年,英國、俄國等侵略勢力都想染指西藏事務,西藏面臨分裂的危局。為避免西藏的分裂和領土的蠶食,清政權基于地緣關系的考量,逐漸著手以川康為政治樞紐加強對西藏的控制。鹿傳霖、錫良、趙爾豐等歷屆四川總督,逐漸形成欲固西藏必先經營川邊的理念,著力在川邊力推改土歸流,逐漸確立了以流官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系,使中央政權的權威真正延伸到西藏地區。為更好實現對西藏的防衛,鹿傳霖、錫良等人逐漸認識到四川藏區的重要地位,甚至對四川藏區的一些重要節點和支點地區的戰略地位都進行了具體的研判。1896年,鹿傳霖指出:“瞻對距藏甚遠,插入內屬土司之中,本系川境內地,一旦棄歸藏中,值此事艱,設西藏有事,瞻對之地不問而屬他人。川省若無門戶可守,危亡可立而待”。③吳豐培:《清代藏事奏牘》,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981頁。錫良一針見血地指出:“邊事不理,川藏中梗,關系至大。征之前事,藏侵瞻對,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聞戰,藏危邊局,牽制全局者,皆邊疆不治,道途中梗所致也。”④錫良:《川督錫良等奏請設川滇邊務大臣駐巴練兵電》,載吳豐培:《趙爾豐川邊奏牘》,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44—45頁。而要改變道途中梗的困境,錫良明確主張改土歸流,“設置川滇邊務大臣,駐扎巴塘練兵,以為西藏聲援,整治地方為后盾,川滇邊藏,聲氣相通,聯為一致,可以一勞永逸。”⑤錫良:《川督錫良等奏請設川滇邊務大臣駐巴練兵電》,第44—45頁。長期處理川藏事務的趙爾豐也強調,川邊必須建行省,以“內屏川滇,外扶藏衛”⑥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編輯組:《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920頁。,實現“以杜英人之覬覦,兼制達賴之外附”⑦吳豐培:《趙爾豐川邊奏牘》,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2頁。的目的。總體而言,鹿傳霖、錫良和趙爾豐等清朝官員已經較深刻地認識到“安康可以促進治藏,而治藏又必先安康”⑧李紹明:《民族學文選》,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年,第587頁。,并付諸大量實踐。在清末傳統王朝國家逐漸瓦解、新的民族國家建構前途未卜之際,西藏地區雖局勢一直動蕩不安,但終究沒有脫離中國而“獨立”,很大程度上與中央政府對四川藏區的經略密不可分。
王朝國家在治理當下的主邊疆和次邊疆地區,已經對兩大地理空間的地緣關系、人文關系有較深刻的認知,并采取大量的實踐措施,從而為當下理解主邊疆治理和次邊疆治理的互動、互構關系提供了經驗借鑒。歷史啟示人們,盡管主邊疆和次邊疆地區因地理結構、資源稟賦、族群關系等因素的差異而互動的方式和側重有所差異,但主邊疆和次邊疆治理的互動、互構關系客觀存在并可能對邊疆治理乃至整個國家治理產生深遠影響。主邊疆治理和次邊疆治理的良性互動,可能帶來邊疆治理績效的事半功倍,反之則可能誘致邊疆治理的失效甚至誘發更大的國家發展危局。邊疆地區的有效治理需要站在國家治理的全局,深刻把握主邊疆和次邊疆兩大空間的互動、互構關系,以整體性治理思維協同推進兩大空間的治理。
三、新時代西部“次邊疆”地區發展現狀難以適應國家發展的戰略需要
國家崛起把邊疆治理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顯了出來。①周平:《國家崛起與邊疆治理》,《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7年第3期。中國西部邊疆及其周邊地區是世界地緣政治博弈的熱點和焦點區域。世界主要大國為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贏得競爭優勢,進一步強化了在中國西部周邊國家的地緣謀劃和博弈,甚至直接介入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的事務,以此遏制中國的發展和崛起,由此給西部邊疆安全與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同時,隨著東中部地區發展達到一定高度,國家向西開發開放的力度進一步增加,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西部邊疆地區成為國家發展的新的增長極,成為國家向西開發開放的重要戰略支撐空間。主邊疆和次邊疆治理的互動、互構關系,決定了次邊疆治理的地位必然隨著主邊疆治理地位的提升而凸顯。
第一,次邊疆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的空間地位日益凸顯。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新疆被定位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西藏被明確定位為中國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云南被定位于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主邊疆地區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的空間定位目標的實現,有賴于次邊疆地區空間支撐作用的發揮。如,甘肅河西走廊作為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道,同樣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戰略通道,且被譽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黃金段”,肩負著進一步推進國家向西開發開放、強化新疆與內地交流合作和經濟聯系的重要戰略使命。根據《“絲綢之路經濟帶”甘肅段建設總體方案》,甘肅將成為建設繁榮絲路、人文絲路、綠色絲路、和諧絲路的中堅力量和重要支撐,成為整個絲綢之路經濟帶實現有效發展的關鍵環節。川滇藏交界的藏彝走廊是古代茶馬互市的必經之路。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藏彝走廊仍然是西藏融入內地市場,加強與川渝經濟圈、長江經濟帶以及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經濟合作的通道,在促進西藏將自身的資源稟賦、政策紅利與內地的資金、技術、人才等優勢相結合,推動環喜馬拉雅經濟合作帶建設,以及推動面向南亞開放的重要通道建設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空間支撐作用。
第二,次邊疆地區在強化國家空間整合、促進國家一體化發展中的空間地位日益凸顯。國家越發展,越需要加強國家空間整合,以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安全。中國在邊疆和內地兩大空間的非均衡發展特征明顯。在區域協調發展已經成為新時代國家重大戰略背景下②2018年11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明確提出了這一戰略,制定了系列政策。,促進邊疆地區和國家核心區均衡發展日益成為重大實踐課題。邊疆地區日益成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后盾③方盛舉、陳然:《現代國家治理視角下的邊疆:內涵、特征與地位》,《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9年第4期。,成為既要對外開放、又要對內開放的雙向開放空間④郝時遠:《中國文化多樣性與“一帶一路”建設》,《今日民族》2016年第10期。。次邊疆地帶作為邊疆地區與內地溝通和聯系的重要空間,在實現邊疆與內地互聯互通和邊疆內地一體化進程中應該起到重要的支撐和帶動作用。一般而言,中心城市在空間互聯互通關系格局中起主導性作用。中心城市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增長極,在強化邊疆與內地經濟聯系、帶動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發揮輻射功能。然而,當前邊疆與內地核心城市、城市群的空間距離遙遠,如新疆天山北坡城市群與黃河上游城市群,拉薩山南城市群與川渝城市群之間在空間上都相隔甚遠,中心城市的經濟輻射帶動作用尚不顯著。在此情況下,次邊疆地帶應該成為聯結邊疆與內地的橋梁和戰略支點,著力培育次邊疆地帶的次經濟中心和增長極,更好發揮其對主邊疆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不斷提高邊疆地區和內地一體化發展水平。
第三,次邊疆地區在國家安全治理中的空間地位日益凸顯。次邊疆地區歷來是守衛主邊疆地區安全的重要戰略基地,在國家安全治理中的地位向來重要。在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相互交織的背景下,主邊疆地區和次邊疆地區在安全風險領域日益共生共衍,一些境外勢力和國內分裂勢力除了在主邊疆地區從事破壞安全穩定的行為外,日益將次邊疆地區作為興風作浪的重要空間,企圖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挑起安全危機。而次邊疆地帶社會動蕩勢又容易在整個邊疆地區引起連鎖反應,甚至對整個國家的安全穩定局勢帶來沖擊。在這一背景下,次邊疆地帶的安全形勢以及安全治理能力對主邊疆地區乃至整個國家安全的影響日益增加。
第四,次邊疆地區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的空間地位日益凸顯。國家的崛起和民族的復興,都要以一個鞏固和強大的中華民族為基礎。①周平:《中華民族:一體化還是多元化?》,《政治學研究》2016年第6期。邊疆治理最關鍵的是民族團結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治國必先治邊——云南邊疆民族地區治理體系建設的實踐經驗》,《求是》2016年第18期。。陸地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區高度重合的國情,決定了維護民族團結、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是中國陸地邊疆治理的重要任務。③丁忠毅:《命運共同體建設視域下陸地邊疆治理現代化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7年第3期。次邊疆地帶因其特殊的空間位置而成為多族群經貿往來、文化交流的重要場域,成為民族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的共生之地,并作為紐帶溝通起多個“歷史民族地區”,是中國各民族交流交融特征最明顯的地區。費孝通先生以宏觀整體視野,從中國“歷史形成的民族地區”④費孝通:《談深入開展民族調查問題》,《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1982年3期。構建出包含“六大板塊”和“三大走廊”的民族格局。“六大板塊”即東北角的高山森林區、北部草原地區、西南角的青藏高原、云貴高原、沿海地區和中原地區。“三大走廊”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嶺走廊”。板塊之間以走廊相聯結。⑤王元林:《費孝通與南嶺民族走廊研究》,《廣西民族研究》2006年4期。民族走廊成為從古到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為頻繁、文化積淀深厚、對中華文明起源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貢獻突出的多民族交融的大通道。次邊疆地帶正處于兩個或多個板塊連接的三大民族走廊地區,河西走廊是西北走廊的核心部分,⑥秦永章:《試議“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圍和地理特點》,《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2011年3期。連接著北部草原地區與青藏高原以及中原地區,四川藏區是藏彝走廊的重要部分,⑦李紹明:《費孝通論藏彝走廊》,《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1期。連接著青藏高原與中原地區以及云貴高原。總結歷史上次邊疆空間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規律和經驗,發揮次邊疆地區特殊空間區位優勢,進一步促進民族團結、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然而,與次邊疆地區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上升形成較大反差的是,次邊疆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還遠不能適應主邊疆治理和國家發展所提出的戰略需要。次邊疆地帶具有明顯的“雙邊緣”特征,在地理空間上遠離所屬省級行政區的省級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心地的輻射影響和帶動作用明顯較弱,加之地理形貌復雜、生態環境脆弱、交通通達性較低,一直是中國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典型空間。如表1所示,從甘肅省域范圍來看,河西五市地區生產總值遠低于省會蘭州,除嘉峪關市外人均GDP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四川省域范圍來看,甘孜、阿壩、涼山的經濟發展水平也遠低于四川省和全國平均水平。其他次邊疆地帶的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上也是如此。

表1 西部次邊疆地帶部分城市GDP 情況
雖然近年來中央政府和次邊疆所在的一些省份已經開始注意到次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滯后帶來的不利影響,并開始在國家層面和省級層面統籌、支持次邊疆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其中最典型的支持政策是全國層面的對口支援四省藏區和在一些省份實施省內對口支援。2010年,中央政府開始實施對口援青政策。2014年,國務院確定廣東、浙江、上海、天津對口支援云南、四川、甘肅藏區。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做出了“加大中央對四省藏區政策支持力度,統籌推進西藏和四省藏區協調發展”,“要在西藏和四省藏區繼續實施特殊的財政、稅收、投資、金融等政策”。①《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步伐》,《人民日報》2015年8 月26 日,第1 版。2012年,四川啟動省內對口支援藏區工作,目前正實施第二輪對口支援工作,有力促進了四川藏區經濟社會發展。但總體而言,針對次邊疆地區的特別支持政策還主要集中在某些焦點區域,還遠未實現對整個次邊疆帶的覆蓋。在全國其他國土空間總體加速發展的背景下,次邊疆地區發展總體滯后的情況可能進一步凸顯,并制約邊疆與內地一體化的推進、主邊疆和次邊疆治理的良性互動,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有效推進。
次邊疆地帶發展滯后影響國家空間整合、阻礙邊疆與內地的一體化發展。次邊疆經濟社會發展滯后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空間結構在邊疆和內地之間形成一個“凹陷地帶”。如不加以強勢改變甚至可能成為“斷裂地帶”,將限制其促進邊疆內地一體化的紐帶和橋梁作用的有效發揮。同時,次邊疆地帶脆弱和復雜的生態環境以及滯后的經濟發展,導致了交通等基礎設施的發展也相對不足,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尚不健全,與邊疆及內地之間的交通銜接水平總體仍然不高,客運樞紐、物流園區等建設也較為滯后,②朱金春:《“一帶一路”視域下的邊疆內地一體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制約了邊疆與內地之間資源、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嚴重制約邊疆與內地的一體化發展,不利于國家的空間整合。
發展是促進安全的物質基礎和基本途徑。③丁忠毅:《“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西部邊疆安全治理:機遇、挑戰及應對》。當前次邊疆地帶整體治理和開發的水平較低,將削弱區域穩定的基礎。次邊疆地帶因發展不均衡而誘致的安全風險,一方面源于與內地較大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另一方面源于主邊疆地區較快發展與次邊疆地區發展相對滯后的反差。由于次邊疆社會相較于內地而言,同樣具有較濃的“邊疆性”和異質性。由此導致因發展滯后而引起的問題和矛盾與民族、宗教等因素相交織,從而產生更為復雜和敏感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對次邊疆社會穩定造成沖擊。次邊疆治理成效不佳時,社會問題和矛盾會出現溢出效應和擴散效應,對主邊疆地區的治理也會帶來負面影響,并為境內外敵對勢力提供可乘之機。
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過程中,次邊疆地帶具有良好的歷史基礎和現實的示范帶動作用。在中央不斷加大對主邊疆地區支持力度的同時,次邊疆地帶則相對被邊緣化,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滯后,可能會讓次邊疆地帶部分民眾產生邊緣化感、不平衡感和被剝削感。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既需要歷史傳統的滋養,更需要系牢民族團結的經濟紐帶,提高各民族間的經濟依存度,真正讓各民族在經濟生活中同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④白利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域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學習習近平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論述》,《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而次邊疆地帶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現狀,不僅容易弱化其與內地和邊疆的經濟聯系,也容易導致生于此長于斯的民眾“五個認同”的弱化。如果次邊疆地帶這一多民族和諧共生的歷史示范區域在國家發展的空間格局中長期被邊緣化,其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間功能將難以發揮。
四、新時代加強西部“次邊疆”治理的實踐意蘊
新的木桶原理啟示人們,只有木桶每塊木板、維系木板成為木桶的配件質量都好,且木板長度都整齊時,木板才能發揮其整體功能。由此延伸,一個系統整體作用的發揮,取決于其功能最小部分,因而系統功能的最大化不僅要學會揚長避短,而且要學會揚長補短。⑤虞崇勝:《補齊短板:木桶原理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運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1期。在國家空間治理過程中,也需要更加關注制約國家發展全局的短板空間,發揮不同國土空間功能的協同發揮。主邊疆治理和次邊疆治理持續的互動、互構關系,決定了加強次邊疆治理對提升主邊疆治理效能的重要性。新時代國家發展進程中邊疆治理地位的凸顯和強化國家整合的戰略需要,更是進一步彰顯了次邊疆治理的戰略地位。而當前次邊疆治理面臨的突出問題及其可能誘致的政治社會風險,則凸顯強化次邊疆治理的緊迫性。從國家發展戰略全局高度,補齊次邊疆治理的短板,是新時代強化國家空間謀劃、促進國家區域協調發展,從而提升邊疆治理乃至整個國家治理效能的重要課題。
第一,在國家空間治理總體格局中強化對次邊疆的空間謀劃。一國的空間想象力和空間謀劃水平既是其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體現,又是改善其國家治理績效的前提和基礎。近年來,中國日益重視對國家治理所處的空間場域的謀劃,無論是國際層面的“一帶一路”倡議,還是國內層面的統籌陸疆和海疆治理、京津冀協同治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都彰顯出國家的空間想象力和空間謀劃力日益提升。但在國家空間治理的總體謀劃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對次邊疆地區的空間功能和空間謀劃不足的問題。由此導致的不利影響將隨著國家的發展逐漸顯現。近年來多項政策有效促進了主邊疆地區的發展和穩定。與之形成明顯對照的是,次邊疆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得到相應重視。特別是,次邊疆既處于主邊疆省區的邊緣地帶,又處在內地省份的邊緣地帶,而省級行政區交界區往往是發展基礎薄弱、自然條件較差的地區,也是省級政府工作容易忽視的地區,由此導致次邊疆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僅滯后于內地,而且相對于主邊疆地區也更容易呈現出不協調不平衡的問題。如四川省藏區總體發展水平曾經長期高于西藏,但現在出現了相反的情況,且發展差距呈逐步擴大趨勢。①楊明洪:《統籌西藏與四省藏區協調發展的戰略意義與實踐》,《開發研究》2017年第3期。著力改變這種狀況,需要站在國家發展全局的高度,從三個層面強化對次邊疆地區的空間謀劃:一是在國家層面統籌主邊疆和次邊疆的空間規劃,有效發揮主邊疆對次邊疆的空間拱衛作用,以及次邊疆對經略主邊疆的空間前沿和戰略后方作用,著力促進主邊疆治理和次邊疆治理的良性互動。二是在區域層面統籌次邊疆地帶的空間謀劃,著力發揮次邊疆區域不同空間的聯動和協同發展作用。三是推動次邊疆所在省域層面的空間聯動,促進省域中心地區和邊緣區域空間謀劃的聯動,帶動省域空間發展的協調均衡。
第二,著力發揮次邊疆在促進西部主邊疆地區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發展中的紐帶作用。強化國家對邊疆地區的經濟整合,促進邊疆與內地經濟一體化發展是新時代國家治理的重要目標。縱觀歷史,一部邊疆經濟開發發展史,主要是邊疆地區在邊腹經濟社會互動過程中實現發展理念創新、制度創新、技術革新和經濟結構再造的歷程。②衣保中:《腹邊互動與我國歷代邊疆經濟開發》,《史學集刊》2012年第2期。在邊腹經濟互動過程中,次邊疆地帶作為內接國家的核心區域、外連主邊疆區域的國土空間,是促進內地與邊疆地區一體化發展的關鍵空間。如果次邊疆地帶的發展既滯后于內地核心區域,也滯后于主邊疆地區,在國家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中就可能形成一條環主邊疆地區的發展“凹陷地帶”,從而制約次邊疆地區作為連接和輻射次邊疆經濟發展的空間功能的發揮,影響國家經濟社會的一體化發展,阻礙國家對主邊疆地區的空間整合。加快次邊疆地帶經濟發展,有效發揮其在促進主邊疆地區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紐帶作用,可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加強對次邊疆地帶經濟發展的特殊支持。針對次邊疆地帶發展基礎的薄弱和歷史欠賬,促進次邊疆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需要中央政府、相關省級政府的強力支持和特殊政策。中央政府有必要在更大范圍的次邊疆地區實施特殊的支持政策,助力次邊疆地帶更好融入國家經濟發展全局;次邊疆地區所在的省級政府有必要借鑒四川省內對口支援的實踐經驗,對緊鄰主邊疆省份的邊緣區域進行對口支援,特別要以此加強對一些集中連片貧困區域脫貧攻堅的支持。二是加強次邊疆地帶經濟發展所需的物質基礎設施和社會性基礎設施建設。在物質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尤其需要重視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在提高次邊疆地區內部通達水平的同時,更好發揮其貫通主邊疆和內地的空間優勢,使商貿物流更加通暢,人員流動更加便捷,打破交通滯后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限制和約束,實現從“瓶頸制約”到“優勢支撐”的跨越發展。在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需從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角度,加大對次邊疆地區基礎教育、公共醫療衛生、基本社會保障的投入力度,著力提高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并將其作為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基本途徑。三是著力打造主邊疆與次邊疆、內地的經濟合作帶。探索將內地的資金、技術、人才等優勢與邊疆地區的資源稟賦、政策等優勢相結合,在次邊疆地帶打造環狀經濟合作帶,發揮次邊疆省區省會城市、省域經濟次中心、交通樞紐和門戶型城市的聯結帶動和經濟輻射作用,進一步加強次邊疆地帶與主邊疆地區的產業聯系和經濟合作,助力內地和主邊疆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發展。
第三,構建次邊疆與主邊疆地區應對安全風險的協同治理體系。主邊疆地區和次邊疆地區在空間上的近距離,族群關系上的親近性,決定了兩個空間的安全風險特別是重大安全風險的共生共衍,決定了傳統囿于行政區劃的屬地管理體制難以完全適應中國主邊疆地區和次邊疆地區日益增多、日趨復雜的各類安全風險,也決定了加快構建主邊疆地區和次邊疆地區安全風險協同治理體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首先,需要協同推進主邊疆和次邊疆地區的安全風險應急管理機制,統籌應急信息分享、應急資源調度、應急輿情引導,推進應急管理機構的聯動和應急力量的互助,有效防止重大突發事件引發更大范圍、更高層級的安全風險和次生危機。其次,針對日常安全維護,主邊疆和次邊疆地區的安全管理部門需樹立合作、共享、共治、共贏的理念,可圍繞信息共享、形勢研判、人員培訓、經驗交流等方面,通過定期舉辦聯席會、聯合執法、聯合演習等方式,加強協同治理機制建設,以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和地方主義藩籬,共同解決區域性安全難題,形成應對邊疆安全風險的合力。當然,協同治理并不等于淡化屬地管理責任,無論是主邊疆地區和次邊疆地帶,都需要積極應對轄區內的安全風險,著力構建區域安全風險防控的第一道屏障,以防止本轄區內安全風險的蔓延和擴散。
第四,發揮次邊疆地區在促進民族團結、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歷史作用與區位優勢。自古以來次邊疆就是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特征最鮮明的地區。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需重視發揮該地區的歷史作用和空間功能。首先,注重對次邊疆地帶多民族共融共存歷史文化的挖掘、闡釋以及傳承和發展。次邊疆地帶悠久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留下了珍貴的文化和歷史遺存,存在著許多民族團結動人事跡,從中可以凝練和總結出民族團結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歷史經驗和總體規律,從而成為當前中國處理民族關系和解決民族問題的寶貴歷史資源和精神財富。其次,發揮次邊疆在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區位優勢。次邊疆地區世代生活著多個民族,且一般連接多個主體民族聚居地,各民族的文化由于遠離其發動源或傳播源,到次邊疆地區集中形成了不同文化圈的切割線,①曲青山:《論青海在穩定發展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青海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多元民族和文化可以更好和平相處、相互交流促進,從而產生了新的民族和文化認同。這種新的民族和文化認同更具多元化和包容性。因而,次邊疆地區既是多民族共同生產生活的場域,也是多元化、包容性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的鍛造地,對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產生重要推動作用。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應發揮次邊疆地區特別是相關民族走廊的空間優勢。國家已經將次邊疆作為促進民族團結的戰略重點。如2010年出臺了《關于進一步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的意見》,將甘肅定位為“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示范區”。黨的十九大后,又提出了把甘肅建設成為“全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省(區)”的要求,有效發揮甘肅在促進民族團結方面的示范和輻射優勢。在其他次邊疆區域,也應更加重視其在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空間區位優勢,建設更多民族團結進步示范空間。
綜上所述,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妥善應對該變局中的挑戰、把握蘊含其中的機遇,并贏得更大的國家發展優勢,內在地要求補齊國家治理的短板,全面提升國家的治理效能。隨著邊疆在國家空間治理中的地位的提升及其治理短板效應的顯現,強化邊疆治理已經成為國家的重要戰略選項。然而,在國家空間治理“核心—邊緣”二元結構敘事和實踐中,連接國家邊緣區域和核心區域的過渡地帶,即次邊疆的空間功能未能得到應有重視。
當前,國家發展的時空條件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國家發展的新的戰略需要,使次邊疆治理的戰略地位日漸凸顯。在這一背景下,審視次邊疆治理與國家發展戰略需要的匹配程度,并提出加強次邊疆治理的對策思路,理應成為理論研究的重點問題。本文展開的更多是宏觀層面的初步思考,旨在拋磚引玉,以期方家繼續深化對這一問題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