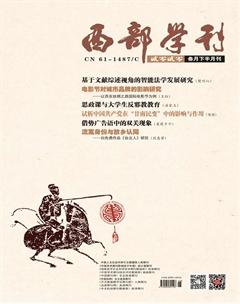精神分析思想中的創造力解讀與探索
張晶晶 黃欣慰 李丹陽 王步遙
摘要:創造力是個亙古亙今的話題。以精神分析流派的視角回顧有關“創造力”的種種學說,可以看到弗洛伊德以升華的角度理解創造性,將其視作最高品質的防御機制:英國獨立學派分析師認為它是一種原始的能力,可以在足夠好的環境中得到培育和促進,或是在有侵犯的環境中受到損害和阻礙;精神分析學派的理論則強調“創造是人人具備的一種內在力量”,提出了“一般創造力”的觀點,并認為這是大眾所需的“創造力”。這種觀點可以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示。
關鍵詞:創造力:獨立學派:精神分析流派
中圖分類號:B84-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20)06-0158-03
創造力是什么,有什么價值與意義,一直以來都是被探索的問題。自亞里士多德以產生前所未有之事物定義創造力后,千年來的研究者們,都對創造力進行了多次的研究與闡釋,希望能夠找尋到打開創造力的鑰匙,來揭示創造力背后的神秘。高爾頓曾通過研究天賦條件與創造力的關系,認為創造性個體是天生的結果。精神分析學派的理論內在地蘊含著“創造是人人具備的一種內在力量”的觀點。本研究將以精神分析的思想為線索,在精神分析視角下,對創造力解讀與探索。
一、弗洛伊德與創造力
弗洛伊德(Freud)將創造力引入無意識領域。當個體在本我、自我、超我與外在現實,這四個層面里體驗到混亂時,為了尋求平衡,不得不通過發揮創造力才能夠找到自由的出路。“本我(id)”是為了尋求快樂而存在,一旦本我轉化成快樂的需求很難被自我所駕馭時,只有升華為“超我(superego)”,才能得到有效的滿足,即轉為創造的需要,當力比多強大的能量轉化為創造動機,外化時便產生了偉大的創造作品。既然創造是“本我”的能量轉化所致,那么,人人都應有“本我”,也就是人人都具有潛在的創造力。弗洛伊德也提出了無意識創造力理論,認為“夢”也是一種創造的思維機制,也談到超越“性本能”驅動的創造動機說。
弗洛伊德發現,假若一件藝術作品不能用他自己的理性和分析的術語來理解,那么他就很難欣賞它。他一直對無意識過程十分感興趣,只要它們是可分析的。精神分析的技術是一個清晰而有紀律的指南,精神分析的真相出現在分析者和病人之間,在理解的那一刻,兩者都發生了變化。要想窺見真理,就必須拋棄兩者的先入之見,因為兩者都有自己的先人之見。但是創造力是散漫的、充滿主觀性的,是自發的。深不可測的創造力偏離既定理論和可靠的臨床技術。所以他對創造力的興趣,伴隨著他面對創造力時的矛盾心理,在弗洛伊德的作品中表現得很明顯,關于藝術和文學的精神分析性寫作一直都很豐富。
無意識的活動對科學藝術創造意義重大。無意識眾多本能中,性本能起著主導作用。他認為性本能的壓抑是神經癥的起因,而性本能沖動的升華,則是文學、藝術創作等創造活動的動因。其次,弗洛伊德用俄狄浦斯情結來解釋藝術家個體的創造動機。創作的原動力就在于藝術家潛意識里一直被壓抑的種種本能欲望,尤其是童年時代被壓抑的俄狄浦斯情結。通過升華使人滿足本能的活動被更高的文化目標所取代,表現為一種對文化與文明事業的創造與追求。“我把想象的領域看成為了提供一種替代物來代替現實生活中的已被放棄的本能滿足、唯樂原則向唯實原則痛苦地轉變期間所產生的一塊‘保留地”藝術家的創造物,藝術產品,是無意識愿望在想象世界的滿足。
弗洛伊德常被指責將創造力病態化。“創作寫作的機制和歇斯底里的幻覺是一樣的。”他認為,藝術家與我們所有人一樣,都痛苦于未實現的愿望,可他們不會承認,因為他們的這些愿望是被禁止的欲望。然而,藝術家卻避免了這種沖突帶來的神經質的結果,除了可以像普通人那樣獲得常規的升華,還因為他們具有一種特殊的天賦,能夠塑造被禁止的、無意識的幻想,從而避免責查,并在視覺上或口頭上表現出來。藝術家從中獲得了快樂,藝術家就像神經病患者一樣,從一個不令人滿意的現實世界中退出,進入想象的世界;但與神經質的人不同的是,他們知道如何從中找到出路,并再次在現實中站穩腳跟。他的作品,是無意識愿望的想象滿足。但藝術所提供的替代性滿足是與現實相對照的幻覺。一個社會越沒有沖突,它對藝術的需求就越少。一個社會,如果它的附屬品是真正的藝術,而不是一味逃避神經質的解決方案,那么這個社會可能根本就沒有藝術家。
弗洛伊德闡釋了幻念與夢、創造之間的聯系。幻念即幻想、白日夢或是想象力等。弗洛伊德談到人人具有幻念、想象。人們總在利用自己的想象力(幻想)來滿足那些在現實中不能被滿足的愿望。
我們時時刻刻都在體驗著我們的想象力(Rycroft)。在過渡空間內,可能會出現更為流暢的思維方式。當我們發現自己在做白日夢時,也許就能識別出這種心理狀態,當我們冥想或者花時間思考時,我們可能會意識到我們心中客體之間的邊界變得更加松弛了,也許它們會融合在一起,產生出新的想法,這樣我們可能會將它體驗為幻想或幻覺。
夢是一個我們熟悉且日常體驗的過渡空間。當我們體驗它們時它們是真實的,當我們回憶它們時,我們卻知道它們不是。有時候,我們能意識到它們有多么有創意,將那些甚至連自已都不知道的圖像和想法放在一起。當我們在分析中談論它們時,我們從自己的內部世界里帶出一些事物進入足夠安全的共享現實中。在咨詢工作時,這個空間讓我們可以冒險讓另一個人(分析師)參與到我們隱秘想法、恐懼和愿望中,玩味它們,并且共同創造新的意義。這當然取決于在這一特定時刻的安全性和質量,以及夢中可能的象征。首先夢本身就是創造,是做夢者的創造物。當代對夢做工作時需要涉及創造性分析工作,就要和分析師共同發現,在分析的背景和治療階段下,做了什么樣的創造。“分析師的反移情不僅是分析性關系中的部分,它還是病人的創造物,是病人人格的一部分”。
二、獨立學派與創造力
米爾納Milner的作品對藝術創造力的理解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闡明了分析性創造力。她的經典論文“象征主義”(Milner,1952)解釋了讓創造性進入分析。Milner反對用符號來代替不受歡迎的現實。她強調分析性創造力是可以被發現和利用的。Milner從她對一個1歲男孩的分析中說明了這在臨床情況中意味著什么。她不得不讓自己成為他的一個“柔韌的媒介”。他需要能夠在腦海中創造她,同時發現并利用她。她的分析活動有一部分是口譯,她清楚地表明口譯始終是一個基本要素,自己的精神狀態是一種特殊的要素。她需要使自己處于一種狀態,使他覺得她是那種容易擺布的媒介。她讓小男孩把她當作自己的一部分來體驗,由他創造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己以外的某種東西反應。事實上,她對他的作用是作為一種反應活動。創造性分析表現在病人身上,也表現在她自己身上。柔韌的媒介,一部分是她的病人方面,一部分獨立于他、被創造、被發現利用,以及Milne自己的回答活動,都具有雙重自我的特質
西格爾Segal(1952)闡述了一種比弗洛伊德更積極的創造力觀。在她認為有必要創造藝術作為一種防御的地方,她把它與一個普遍的發展過程聯系起來。西格爾認為冒險性本能是一種補救沖動的表現,當嬰兒在現實或幻想中尋找補救方法時,就會出現冒險性沖動。西格爾和弗洛伊德都是動機理論。他們假設無意識的需求會激發創造力,但他們并沒有處理創造過程本身。他們都從功能的角度來看待創造力。盡管西格爾的理論根源于正常的發展過程,但它仍然是一個問題,要滿足特定發展階段的需要,找到糾正損害的方法,或讓人們能夠承受這種罪責。這兩種理論都將創造力置于其所服務的發展功能之上。相比之下,溫尼科特的觀點允許一種主要與創造性過程本身性質有關的創造性觀點。這里提出的關于創造力的基本概念是溫尼科特所說的潛力,或者過渡空間。創造性,生命活力和游戲聯系著內在個人現實與外在的、共享的現實游。戲的普遍意義在于在時空的連續維度中作為一種創造性的體驗.發生于過渡空間中。
溫尼科特反復強調,嬰兒創造了客體,但客體卻在那里等待著被創造,并成為被凈化的客體。尊重這一悖論,尊重一個不受主觀或客觀挑戰的經驗領域,正是它賦予了“空間其潛力”。
溫尼科特概念的第二個關鍵方面是,這一經驗領域,以其特殊的精神功能模式,在一生都是可用的。嬰兒期早期的過渡空間可能是其最被認可的表現形式,但童年后期的游戲領域是另一個版本的過渡空間,依賴于對同樣悖論的接受。在成人生活中游戲空間,是精神分析成為可能。這個空間以發現和創造的交融而開啟,嬰兒通過這種交融構成了自己的身份,也構成了嬰兒的身份周圍的世界。這個經驗的過渡空間,不管是內在的還是外部的,它構成了嬰兒經驗的大部分,并且在整個生命中都被保留在屬于藝術、宗教、想象的生活和創造性的科學工作的強烈的經驗中。而過渡空間的本質是客觀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不分離。審美體驗實際上是審美活動的一種形式,它要求觀者進入一個潛在的空間。我們自己的審美活動,就像藝術家的創造力一樣,產生于這個中間的區域,它從嬰兒期的過渡空間直接站在一條發展的直線上。潛在空間的概念提供了一種理解,包括藝術、精神分析和其他形式的創造力,以及審美體驗。弗洛伊德、西格爾和其他人對理解情感需求和沖突做出了貢獻,這些情感需求和沖突可能會激發特定藝術作品的創作。這一觀點是基于溫尼科特的創作過程本身。它不把這個過程看作是次要的,也不把它看作是一種糾正或補償的活動,而是把它看作是對人的意義的一種中心表達。
攻擊性是創造力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不僅僅是因為攻擊性會在現實或幻想中造成損害,然后必須通過一些創造性的補救工作來糾正這些損害。攻擊性在創造空間時起著基礎性的、積極的作用。內化的攻擊性是形成超我的關鍵。如果沒有升華攻擊性的能力就不可能實現持續的客體關系。
三、其他精神分析思想
精神分析學派代表人物阿德勒以自卑與超越為核心闡述著個體心理,認為每個人內在都具有一種追求優越的本能內驅力,用這種“創造之力”,有意識地塑造著自己人格與命運。榮格的理論中亦提出了自己對“創造性”的獨特見解。曾用“情結”和“個體潛意識”這樣的概念闡述了整個人類及個體的創造力來源與心理機制。人類之所以能夠不斷地發揮無限的創造性潛能,正是由于個體潛意識的“情結”,通過強大的集體潛意識的心理能量匯聚并展現出來。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的“自我現實化”概念是最能體現其人格發展或創造力發展的概念,無意識中的自我得到現實化便成為了意識的現實,這一步和創造力密切相關。不同的個體所具備的創造性潛能迥然不同,這種自我獨特的潛在力量就是最原生態的一般創造力。人人都是具有一般創造力的獨特個體,有著“創造性地展現生命”的內在需求。
四、當代創造力觀點
Amabile眼中的創造力并不是獨屬于天才的個體,它是類比于一段連續的“波譜”(spectrum),是每個個體普遍所擁有的特質。“波譜”的頂端可能是所謂的天才的創造力,那么剩余的部分就是常說的一般創造力了,我們的創造力潛能只是處于不同的頻段而已(Amabile,1997)。就像我們都不能否認變廢為寶的創造力和梵高的星空作品中彰顯的創造力。當今關于創造力的研究亦存在著兩種取向,一種是以科學主義為主流取向的實證派,探究創造力產生的機制。另一種則是以人文主義取向的現象學創造力研究,關注到特質個體如精神分裂譜系或雙相情感障礙個體。
特殊創造力使我們對創造力這個概念感到望塵莫及。無數的個案更是為它增添了神秘色彩。假若特殊創造力是天才所獨有的,那么當我不用狹窄的眼光去審視創造力,將注意力從那些音樂、繪畫、寫作等領域的特殊創造力轉移到大眾身上,會發現這個一般創造力才是大眾所需。一般創造力是“健康人”實現完整人格和獨特自我的需要,它呈現一種間斷性的連續,存在于每個人當中,是人人都有的內在潛質。
“積極的幻想,可以促進創造力的提高,并有利于創造性成果的產出。這些幻想不僅可以激發創造力本身,而且還能增強人的動機、堅韌性及表現力。”可是目前關于創造力研究仍舊聚焦于實證主義,探究創造力是個體現象還是社會現象?創造力是所有領域的還是特殊領域的?此時回顧心理學理論流派中探究創造性,對完善理論知識與促進心理咨詢都具有相當的啟迪意義。
五、總結
弗洛伊德從升華的角度理解創造性,將其視作最高品質的防御機制,英國獨立學派分析師認為它是一種原始的能力,可以在足夠好的環境中得到培育和促進,或者在有侵犯的環境中受到損害和阻礙。溫尼克特不同于弗洛伊德,認為嬰兒天生具備的不是破壞性而是創造性,一切后續的創造力都取決于他作為嬰兒時能否有創造力,以及母親、隨后是父親、隨后是整個家庭能否支持、鼓勵這種創造力。如果嬰兒在成為一個人的過程中自然表達出來的攻擊性不被容許的話,如果攻擊性被壓抑、禁止,或被當成是不好的,那么嬰兒可能就會崩潰,生病或者退縮。創造性是一種活力的表現,可以被壓制,被防御的順從取而代之,可以抵御在由不安全的環境所引發的焦慮。溫尼科特假設,創造性的攻擊性是嬰兒與生俱來的權利,是作為人類存在的一部分。他探索了這種天生的創造性的攻擊性如何被破壞、被歪曲而成為破壞性的攻擊性。巴林特在“基本錯誤”書中講到一人關系是創造性的領域。而且客體關系學說認為,“主觀客體”的時期也是原始創造性的時期,具有全能的幻覺。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讀創造力對未來更好地理解創造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作者簡介:張晶晶(1996-),女,漢族,甘肅人,單位為新疆師范大學,研究方向為應用心理學。
黃欣慰(1993-),女,漢族,河南商城人,單位為武警工程大學。
李丹陽(1994-),女,回族,甘肅人,單位為新疆師范大學,研究方向為應用心理學臨床心理與咨詢。
王步遙(1995-),男,漢族,上海人,單位為新疆師范大學,研究方向為具身認知erp理論心理學。
(責任編輯: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