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么脫離凡爾賽-華盛頓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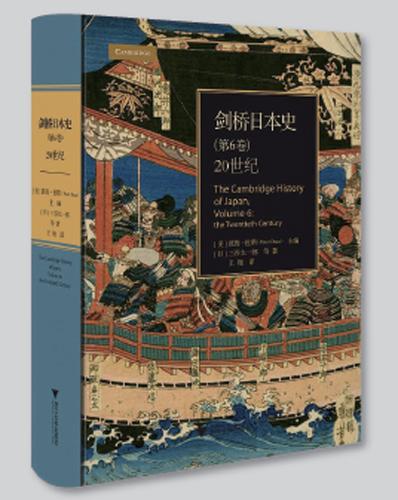
《劍橋日本史(第6卷):20世紀》
[美]彼得·杜斯 主編
[日]三谷太一郎 等 著 王翔 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0年1月
戰爭的硝煙散開之后,在以英、美為主的戰勝國的領導下,新的國際秩序逐漸形成,通常被稱為凡爾賽-華盛頓體系。
它起源于1919年的凡爾賽和平會議,并在1921年到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得到了詳細闡述。在華盛頓會議上,《四強條約》和《九國公約》試圖凍結太平洋上的現狀。
被打破的平衡
這一國際秩序被構建起來,以保護英國和美國這兩個主要戰勝國的利益。這個新的體系也導致了后來成為法西斯國家的不滿,比如德國需要承受巨大的賠償負擔,而意大利和日本盡管是戰勝國,卻感到被剝奪了足夠的回報。
這個體系也將蘇聯排除在外,它曾經遭受過外國聯合武裝干涉,正在建設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蘇聯作為一個強大的局外人,通過共產國際做出特殊努力,支持其他國家興起的民族主義運動,積極尋求擴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則爭相制訂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對策,以捍衛它們的國外勢力范圍,同時防范國內的顛覆性運動。
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三個主要的世界大國集團之間形成了力量平衡,這三個大國集團分別是:華盛頓體系中的領導者—美國和英國;心懷不滿的強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及蘇聯,它的目的是在國際上建立一種社會主義秩序。
在與1929年發生的國際經濟體系上的一場暴風雨—大蕭條作斗爭時,這三個不同集團之間的平衡被打破了。在一系列由法西斯國家顛覆現狀的企圖所導致的危機中,國際政治逐漸向另一場大戰發展演化。巧合的是,正是日本率先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為什么日本最終脫離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和英國在戰爭結束時,開始反過來要求日本放棄大部分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時所得。其中包括:英日聯盟的廢止;日軍從西伯利亞撤離;在《華盛頓海軍軍備限制條約》中以美國、英國、日本主力艦5∶5∶3的比例來約束日本艦隊;將山東半島歸還給中國;終止《藍辛-石井協定》。
這些新動態,許多都是華盛頓會議取得的結果。這次會議結束時,最重要的協定是1922年簽訂的《九國公約》,其中“清算”了列強與中國的所有現有條約,而以美國長時間信奉的“門戶開放”原則取代。毋庸置疑,這一公約是美國外交的一次“勝利”。據惠特尼·格里斯沃爾德所說:“它是美國傳統的遠東政策的典范。”
歡樂又恐懼
日本人對這些協議的感覺,可謂歡樂與恐懼交集。然而,日本政府尤其是外交當局,并沒有被這些負面情緒影響,也沒有把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看作日本利益的徹底失敗。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伍德羅·威爾遜的理想主義中傳達的進步主義與和平主義,也開始在日本起作用了。從實用的角度來看,新的國際體系的好處,特別是華盛頓會議取得的成果,絕不是可以忽略的。
首先,在華盛頓簽署的條約,是當時國際形勢的一種意識形態的產物。這些條約為美國、英國和日本建立聯合防御戰線提供了可能性,共同遏制蘇聯國際共產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
其次,關于3個強國之間的相互關系,原則上可以理解為,施加于日本的種種限制將在未來執行,這些限制并未觸及日本既定的特殊利益,尤其是被日本人視為對自己的生存至關重要的在中國東北和蒙古享有的利益。
再次,由于國際聯盟缺乏執行任何制裁規定的能力,日本顯然能夠輕易地從該體系退出,只要它發現有好處就會這樣做。只要日本仍然能夠通過自由競爭來進行擴張,只要日本在中國東北和蒙古享有的特殊利益沒有遭到中國或蘇聯的威脅,那么,日本對中國作出的讓步—例如,歸還山東半島—就不會被認為是以不合理的價格來支付結束國際孤立的費用。
日本在《華盛頓海軍軍備限制條約》中作出的承諾,也給重新審議軍隊的開支帶來了壓力。首先,1922年的陸軍大臣山梨半造和1925年的陸軍大臣宇垣一成任職時期,軍事撥款的增加受到了查核。軍方權威的下降,似乎為消除“雙重外交”的不良影響提供了一個機會,而這種“雙重外交”給予了軍方在制訂外交政策上與文職外交官一樣多的發言權。這也提供了一個機會,由文職人員執掌的,即由政黨主導的內閣,可以借此恢復對日本外交的真正控制。
“幣原外交”
第一個以通過文官考試的方式擔任外務大臣的職業外交官幣原喜重郎,是忠實信守華盛頓-凡爾賽體系而又不放棄在亞太地區實際考量的代表人物。
他曾在五屆民政黨內閣中任職,擔任過主管外交事務的外務省次官、駐美利堅合眾國的大使,以及日本出席華盛頓會議的全權代表。在他的外交政策中,相互關聯的組件主要是國際合作、經濟外交和不干涉中國內政。
第一,所謂“國際合作”,雖然一般認為這指的是外交活動以國際聯盟為中心,但基本上它涉及有關與美國和英國合作的政策。
第二,所謂“經濟外交”,指的是強調經濟的和平發展,將重心從軍事壓力政策上轉移出來,具體表現在放棄“二十一條”要求、撤出西伯利亞遠征軍、限制對中國軍閥的軍事援助等,因為這些已經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抵抗。實際上,在“幣原外交”下,日本與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額不斷攀升。幣原喜重郎本人相當死板,無法容忍出于“超經濟邏輯”和“非經濟邏輯”而違反經濟合理性或侵犯經濟利益的行為。
第三,所謂“不干涉中國內政”,這是幣原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意味著日本接受了由國民黨統一中國,并且同意了中國關稅自主及取消治外法權。這與經濟外交的原則密切相關。這種政策植根于這樣一種判斷,即一個穩定的、統一的政府在中國建立,對日本經濟利益的推進和市場的擴大是可取的,而輕率的干預政策則會激起民族主義的敵意和對日本貨物的抵制。
“幣原外交”的這些原則與當時的外交環境相吻合。自1925年1月蘇聯和日本恢復正常外交關系之后,日本似乎擺脫了國際孤立,走上了穩固的和平擴張之路。然而,這種穩固的錯覺很快就在民族主義者發起新的進攻時被打破了。由此,朝著中日對抗的突然轉向,導致了整個華盛頓體系的崩塌。
(本文獲出版社授權,標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