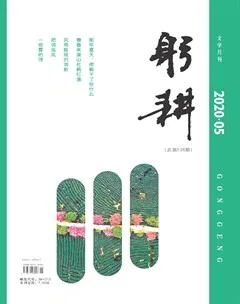大空山溶洞懷古
崔慶云
這是一個隆冬的上午,天色如鉛,四合低垂,原野空曠,雖已是酷寒時節,卻沒有朔風呼嘯,枯葉翻卷,唯有沉寂和冷漠布滿前方的山坡田野,嚴冬的氣息籠罩了山腳下干涸的河道和寂靜的村莊。鋪滿碎石的山坡上黃草低垂,瑟瑟抖動,低矮稀疏的槲葉樹給這座孤山增添了幾分荒涼。山頂灰褐色的巖石突兀翹首,仰視觸手可及的蒼天,似乎想訴說點什么。
四周的一切都蟄伏在一種難以描述的沉寂之中。
上山的坡道布滿形態各異,棱角犀利的沙礫石塊,腳踩在上面不停地仄歪,走起路來有點顛簸的感覺。
目光所及之處一片荒涼凋敝,沒有想象中的古樹參天,林海如黛,不由讓我開始有點懷疑這似乎無人走過的山坡之上,怎么會有遠古人類祖先留下的遺跡呢?
偶爾有幾只喜鵲從頭頂飛過,落在前面的樹上,耳畔便傳來數聲“喳喳喳”的鳴叫,打破了大空山的安寧。
如果不是事先聽帶路村干部簡要的介紹,任我想破腦袋,也難以將這座荒涼的大空山和幾萬年前古人類聯系起來。
隨著腳下海拔的增高,視野也逐漸開闊。佇立山坡,極盡目光,向四周眺望。然而,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片收割后裸露著的黑色的土壤,一條條近乎干涸的河床,或者凝滯或者細小的河流,唯有河面上的冰塊反射著冷白色的天光,加上方才喜鵲的鳴叫,才讓人感覺到一絲絲大地生命的氣息。
望著前面陡峭的大空山,凝重肅穆,矗立萬年,歷經亙古,默默凝視著遙遠而又無法窺透的灰色的天際,像一位飽經風霜敦厚的長者,歷經風吹雨淋,冰刀光劍,風云變幻,天體地殼的移動變幻,始終默默庇護著這一方的生靈。
我用崇敬的目光,細細地審視著一道道山崖,一條條巖縫,還有足跡能夠攀援的山梁坡道,然而,縱使窺破褐色山巖,覽過每一棵樹,也難覓中原人類祖先在此聚集,繁衍后代,棲息生活過的蛛絲馬跡。我沒有特異功能,目光無法穿越時空,去尋覓幾萬年前古人類生活的剪影,只能在腦海里用拼圖的方法去想象他們為了生存,與風云變幻莫測的蒼天斗,與山火洪水肆虐的大地斗,與殘忍兇暴嗜血的野獸斗,聚群而居,茹毛飲血,艱難度日的一幕一幕。
然而,這里的的確確就是中原人類祖先生存過的地方。
此時,大約十點來鐘,天空的鉛云愈加濃重,大有墜落之勢,壓抑沉悶之感仿佛窒息了空氣,方才寧靜的田野不知何時刮起了不疾不徐的西北風,焦黃色的枯葉在山坡上恣意翻卷,然后發出陣陣嗚咽向山下滾落。
俄頃,一片片鵝毛般大小潔白的精靈,稀稀疏疏從天空飄落,親吻著大家的發際、臉頰,飛進露出縫隙的脖頸,雖有絲絲涼意沁入肌膚,但卻給眾人平添無盡的游興。瑞雪兆豐年,飛雪迎春到,吉祥的詩句洋溢在飛雪中,飄蕩在大空山的上空。這一切仿佛是古人祖先們知道我們的到來,特意給我們營造出一種天蒼蒼落飛雪,北風寒原野蔽,鳥獸絕人罕至的意境,讓我們在這種晦暗陰沉壓抑的氛圍中,去體會遠古那種混沌初開,天地昏暗,汪洋淼淼,劍鋒林立,古樹蔽空,百獸肆虐,后人難以想象的境況。
“到了!”向導指著前方一條掩映在一片小樹叢中的灰色小徑。
哦,這就是通往遠古人類棲居生活過的洞穴的唯一小徑嗎?
向導似乎看出我訝然的神色,說:“遠古時代,這里洪荒蠻野,狼蟲虎豹橫行,為了躲避傷害,古人們自然會選擇這種難以攀登,獸跡罕至的地方,入穴而棲。”
是啊,畢竟那時正值新舊石器時代,古人們沒有任何護身利器,只能靠石塊棍棒和一些最原始的東西防身,自然會選擇陡峭險峻,連野獸也難以攀援的洞穴棲身。通往洞穴的小徑尚且如此難行,古人們棲身的洞穴又是怎樣的呢?難以想象的神秘感,想馬上置身其中,一探廬山真面目的迫切感涌上心頭。
“坡陡路滑,雪花鋪徑,大家小心點,腳踏穩,手抓牢,跟著我上山。”向導一邊說,一邊前頭帶路。
大家學著他的樣子,亦步亦趨,腳踩著落滿雪花散松的石粒,繃緊雙腿的肌腱,抓牢兩邊裸露的樹根突兀的巖石,學著向導的樣子,步履維艱地沿著只能容下一人單行的山徑向上攀登,任由朵朵雪花在眼前飛舞。緊張與刺激相伴,渴望與希冀同行。
朔風勁吹,夾裹起團團白霧,迷迷茫茫,天地一色;滿天飛雪,恰似飄落玉麟無數,狂飆亂舞,又如片片梨花。
“到山門了。”向導松了一口氣,說道。
大家抹一把額頭滲出的細汗,緊張的心情頓時輕松下來,回首望一眼身后的山徑,竟早已被雪花覆蓋,難覓其徑了。
向導所說的山門,也就是約兩平方米左右,僅能容下三四人轉身的巖石平臺。平臺靠近巖壁的角落處還能看到尚未被雪花覆蓋的墨綠色的苔蘚,于凄風冷雪中向世人昭示著一點生機。
佇立平臺,轉身回望,遠近景色盡納眼底,霎時只覺心懷一闊,油然滋生一派豪情。
天地相交的地方,隱約是山巒起伏的輪廓,極像寫生者筆下的素描;廣袤平坦的田野,蘊含著無限生機;小路村莊靜謐祥和,正在被雪花披上潔白的盛裝;身側是歷經無數個春夏秋冬,深沉冷漠大空山的灰褐色的懸崖峭壁。
站在這峭壁上的平臺,山下景色一覽無余,偶有風吹草動,樹枝搖曳,鳥雀飛驚,皆避不過值守者的雙眼,而這條僅容一人獨行的山道更是奇險無比,真的是一夫當關,百獸難入。
“這兩個石柱,被咱當地人稱作是兩將軍把關。這個是大將軍,這個是二將軍。”向導指著矗立平臺兩邊一高一矮的兩根光滑的石柱解說著。
太形象了!眾人贊嘆著,也更加佩服古人類選擇巢穴位置的絕佳。
山門尚且如此奇險雄偉,那么洞穴又該是何等的神秘呢?帶著一探洞穴奧秘的迫切心情,一行幾人魚貫進入山洞。
洞內沒有想象中的燈火通明,只是隔三岔五地在巖壁的凹處點著幾根蠟燭,昏黃的光線在這伸手不見五指的洞穴內,顯得是如此的柔弱無力,渺小慘淡,只能于朦朦朧朧中摸索前行,而這,也是得知我們過來采風而臨時置辦的。
雖然光線暗淡,視力不佳,但卻給人一種鉆木取火,洞穴而居,蠻荒時代的感覺。
正當大家磕磕絆絆艱難前行時,幾道突然亮起的手電光束驅走周邊的黑暗,眼前豁然明朗起來。
哇!想不到里面竟然有著如此寬敞的大廳!原來我們駐足的地方有著大約近百平方,高約五六米寬敞的空間,或者稱作大廳一點也不夸張。
目光隨著手電光所及之處,映入眼簾的是怪石嶙峋犬牙交錯的石壁,冰雕般形態各異垂掛著的鐘乳石,置身其中,猶如來到了遠古冰封時代,又好似走進了西游記中描寫的鬼怪妖魔盤踞的洞穴。
“滴答……滴答……”
驀地,一聲聲清脆悅耳的滴水的聲響打破了洞內的寂靜,那水滴的余音在洞穴的石壁回蕩,猶如珠走玉盤,聲聲扣動人們的耳膜,又似一泓涓涓清流,洇潤著大家久居鬧市近乎蒙塵而枯燥的心田。這水滴聲雖然很輕,但在這沉寂了數萬年的洞穴內,顯得是那樣的清晰,那樣的悅耳,猶如深山寺院敲響的晨鐘暮鼓,穿越厚厚的墻壁,飛過林海層層綠波,直達遙遠的山巔,喚起人們心中的那份虔誠。
“咦?想不到這洞內居然還有山泉!”不知誰發出疑問。
“當然了!如果沒有水,古人們咋生存哩。”一位持手電的長者說。
那時古人類雖然思維還不發達,但也知道臨水而居這個淺顯的道理,只不過在這個孤獨并且很是荒涼的大空山的洞穴內,居然還有泉水流淌,怎不讓人稱奇。
“這洞不僅有山泉,有蓄水池,有可睡的石床,有龍虎二窟,還有一條通往山頂的暗道哩,嗨,反正里頭稀罕著哩!”長者繼續介紹著。
哦,想不到這小小的洞穴居然別有洞天哩!聞聽此言,幾位文友顧不上地面石筍的磕絆,高一腳低一腳急急向里探尋。
也許是喜歡泉水的清澈,也許平素就覺得水是有靈性的,而對水有著特別的喜好,我循著水滴聲響發出的地方尋去。
一條狹窄的巖縫,兩側黑黝黝嶙峋的怪石,怪石表面布著黛綠色的苔蘚,苔蘚黑油油的,一定是和這洞穴共同經歷了無數個歲月。那充滿靈性的水源呢?我的目光從高低凸凹的巖石上仔細地看著,又抬頭從縫隙的頂處向下尋覓。終于,我找到了,那閃著磷光那充滿靈性而滑動著的汨汨的細細的水線,對,只能用水線來形容,正從油黑的苔蘚身側流動,雖細卻不停歇,像一條生命之源,經久不息,從遠古流到如今,并且還將繼續流下去。細細的水線匯聚在一處斷崖,而后凝成一顆顆珠子,從崖尖跌落。
我并攏雙手,接一捧清泉,用舌尖去親吻這冷冽甘甜的泉水,頓覺一股清流游走周身,久居塵世而紛擾的心緒剎那間變得通靈清澈,雜念全無。如果可能的話,我多想在這清凈的洞穴內生活一段時間,冥想,看書,寫字。困倦時站在洞口,極目遠眺,一任目光和思緒在眼前這片廣袤的田野躍動。晨迎朝霞看鳥起露消,暮觀云卷云舒夕陽西下,晚執一杯佳釀與月同飲,該是何等的愜意豁達。
“咱這里不知從啥時候留下一個傳說。”那位長者看我發呆的樣子,好像看出了我那一點念想,給我們講了一段流傳此地的故事。
據傳,光武帝劉秀的同窗好友,第一謀士嚴子陵,在輔佐劉秀登基之后,不戀高官厚祿,遂不辭而別,只身微服出洛陽南門,沿宛洛大道一路南下來到云陽,拜訪他一位表弟,因見這里山清水秀,景色旖旎,民風淳樸,再加上表弟熱情挽留,又有這座冬暖夏涼隱蔽清凈的洞穴,既躲避劉秀派人尋找,又可在洞內開課育人,便欣然應諾……
噢,想不到這里還有這么一段美好的傳說。幾位文友興致更加高漲起來。
“這大空山原名富春山,山上風景很美,山下那條河叫富春河,是白河的支流,常年水流不斷,富春河里的魚兒肉質細膩,味道鮮美,這讓喜山樂水,酷愛垂釣的嚴子陵不忍離去,便在此隱居下來……”老者繼續說著。
“你們看,這里還有一張石床,自然形成,床下是空的,冬天可在下面點燃干柴取暖,不僅幾萬年前生活在這洞里的古人類的頭兒在這張石床上睡過,當年嚴子陵一定也在這張石床上睡過,那下邊還有柴火燒過的痕跡哩。”老者把我們領到一塊凸起的石質平臺邊。
順著老者手電筒的光亮,果然看到一塊呈長方形凸起的平臺,數尺見方,酷似一張石床,那下面天然空洞,俯身望去,果然有煙火熏染過的燒痕。
想前輩先賢肯定居于此,那自然是看中了這里山水清秀人杰地靈,且扼守京都洛陽和帝鄉宛城之咽喉,消息靈通,交通便利,劉秀怎么也不會想到,苦苦尋找的嚴子陵居然隱藏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嚴子陵每天授課與子,閑暇時游玩于山水間,執三尺釣竿于富春河邊,月上東山酌一壺美酒,觀眼前無限美景,是何等的逍遙自在。眾人聽后,皆唏噓不已。
隨后,眾文友又看了龍虎二洞,欲探那條直達山頂的密道,只因尚未開發,連當地人也從未爬過,遂憾然作罷。
不知不覺,時已過午,向導家人來電話催促大家回去用飯。
臨別時,那位長者把大家叫到一塊殘缺的鐘乳石下,指著斷口說道:這塊垂下來的石頭原本可達地面,光滑靈巧,甚是好看,只是無人看守,被一些缺德游人敲斷帶走,如今只剩下這半截斷壁,讓人看著心痛。俺這幾個老頭也是自發來守護這洞穴的,得把這里保護起來,免得祖先留下的東西毀在咱這輩人手里呀。
老者話語中透著無奈、憤慨,還有渺茫的期待。
洞內溫暖如春,風雪難入,洞外卻早已是蒼茫一片,鵝毛大的雪片從遙無邊際的九天繽紛而至,如落英,如梨花,落滿了大空山、富春河,還有遠處的山巒。腳下的田野、村莊,天地一色,整個世界被一層潔白覆蓋。
走出好遠,我又回首望去,洞口早已隱于山石后,只能看到尚未開發的荒涼的大空山在寒冬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