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與作品的互證研究
周松芳
一
探討文藝創作規律的傳統途徑,是在創作的基礎上,不斷加以系統化、理論化的總結提升,并以期指導提高創作實踐水平。總結提升的方式,在西方,主要體現為文藝理論與批評及其理論化和系統化;在中國古代,則常常體現為印象式的評點。評點之學,也正是近些年來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研究的重點之一。中國古代之所以盛行印象式批評,竊以為未必是因為理論思維與術語不發達,而是在幾乎人人能詩的士人世界,以詩一般的語言做出評點,更符合特定的氛圍乃至對優美的追求,而且在當時的語境中,無論批評者還是創作者,皆可會心。再則,當時的批評或研究者往往同時身兼創作者,批評、研究與創作有著良好的互動關系。
與此相較,我們當下的批評和研究,與創作分離的趨向比較明顯,更出現了批評的批評與研究的研究,甚至后退幾層至于批評的批評的批評、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等等。如此,則不僅于創作難以有補,于接受也頗感困難。于署名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的研究,可謂典型。雖然陳尚君和汪涌豪于一九九六年提出《二十四詩品》作者并非司空圖,而是明人偽作,但無害于其經典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更能增強其經典力,因為它實可視為中國詩學發展到明代所形成的一個偉大的結晶;明代以來的種種研究成果及其意義,并不會因為作者的關系而受到否定或質疑,反而應該有助于研究的進一步深化與拓展,因為其總結的對象和基礎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和拓展,也理應有更多更好的成果加以體現。羅韜新著《移花就鏡:廿四詩品詩書畫印通釋》,就是這樣一部建基于《二十四詩品》,涵蓋詩書畫印各門類各時期的不可多得的文藝評論和理論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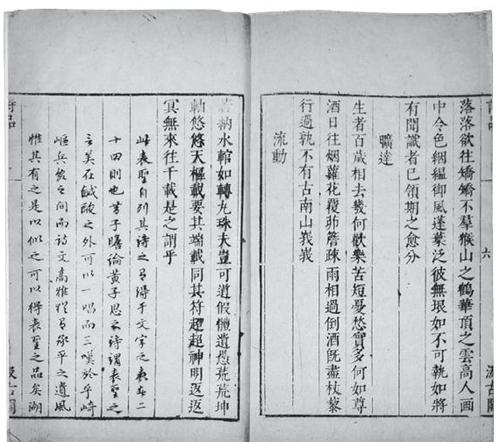
《二十四詩品》,明代汲古閣毛晉刻本
受羅韜影響,我頗找了些時人關于《二十四詩品》研究的著述來研讀,但多數著述都很難避免前述與文藝創作相疏隔之弊,長篇累牘,回不到文學,回不到藝術,仍如鏡中花、水中月,猶在“鏡”中,猶在“水”中,于事無補,且不說于文藝創作和研究都無甚裨益,即便于文藝批評與研究的促進作用,也非常有限。其實錢鍾書先生早已指出《二十四詩品》存在從抽象到抽象的問題,如在《談藝錄》中大贊清人李元復《常談叢錄》中批評《二十四詩品》是“以鏡照鏡”(中華書局1998年,第371頁);又在《管錐編》中批評其“縱極描摹刻畫之功,僅收影響模糊之效,終不獲使他人聞見親切”(第二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410頁);也曾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給汪榮祖的信中說,談藝而無實例,“大類盲人之有以言黑白,無以辨黑白也”。所以有關《二十四詩品》的研究方向,不是一個向上做抽象尋繹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向下與經驗做互證的問題。

《管錐編》(全五冊)錢鍾書著中華書局 1991 年版
羅韜說他是服膺錢鍾書所說的“現象學”研究(見錢氏1983年7月23日《致朱曉農》)的,這個“現象學”當然不是胡塞爾那個現象學,而是警惕馳騖于稀薄的抽象理論,而重視文藝具體現象,以作品為基本出發點的研究。有鑒于此,羅韜便發憤要變“以鏡照鏡”為“移花就鏡”,不僅以恰切的詩例釋證各品,更兼推之于書畫印等其他藝術門類,于是乃有此作,因之也可名之為《二十四詩品》的“現象學”研究。
的確,《二十四詩品》雖然主要從詩歌風格上來總結、區別與評價及指導詩歌創作,這種風格論的特征,在中國古代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傳統之中,如果學力修養足夠,當然是可以移諸書畫及印刻的。而現實中的風格學研究,卻往往并不是指向對文學作品與文學風格之間關系的討論和研究,即便如此,因其研究殊為不易,故歷來佳作甚少,且重點仍多屬批評的批評,令人不饜于心。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來討論羅韜新著《移花就鏡:廿四詩品詩書畫印通釋》,就覺得真是創見迭出,彌足珍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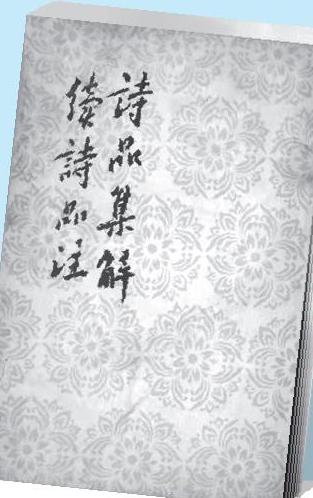
《詩品集解·續詩品注》郭紹虞集解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版
羅韜少年時書法篆刻即得到過錢君匋先生的指教,詩文作品也得到錢鍾書先生、劉逸生先生、余英時先生的贊賞。我把他的作品呈吾師黃天驥教授閱讀,也深得黃師激賞。他是一個有創作實踐的研究者,研讀《二十四詩品》,常常自覺不自覺地聯想到相應的具體的文藝作品,久之,至于表達純熟,常常語驚四座,令人嘆為觀止;“移花就鏡”——以具象可感的詩歌及書畫篆刻相印證——實證目的也日益自覺,歷來一直困擾讀者和研究者的抽象困惑,也將在羅韜的筆下渙然冰釋。
二
《二十四詩品》之模糊感,緣于它除了一些核心性描述,更有許多邊緣化描述。而羅韜對每一詩品的詮解,每每先抓住一些關鍵描述加以評說,然后又在例舉具體作品時加以深化。從第一品“雄渾”的詮解,即可窺其功力。作者對開篇第一句“大用外腓”的“腓”的新解,確實令我們對雄渾風格有進一步的感悟。他說,他所見各家注本都解錯了這個“腓”字,包括郭紹虞《詩品集解》,而此字的正確詮解又十分關鍵,幾乎可以視為理解傳統美學的一個密碼。“腓”,諸家多解作“改變”,甚至有解為“腓肌”的,實不能通;“腓”應該解釋為“病弱”的樣子。再聯系次句“真體內充”,體與用乃是一對概念:“體”為內質,屬陰,“用”表現于外,屬陽;既有充實的內質,而其外表,又何妨示弱?《周易》說“潛龍勿用”,蘇軾說“守駿莫如跛”,都是這個意思。夫如此,下面各句才能通釋。“積健為雄”,雄無疑是積極剛健的。但《二十四詩品》對剛健之道的理解深了一層。老子說“大直若屈”“大辯若訥”,這是老子的“守柔示弱”之道;當其充分表現,發揚蹈厲,具備萬物,無所不在,到最后,又復歸于“非強”,力量不盡用、不盡顯,回到“守柔”之義,也即“腓”弱同義。所以,雄渾不是雄悍、不是雄放,而是知雄而守雌,能強而知斂,“大用”而“外腓”。
了解“腓”字的底蘊,不僅有利于我們了解《二十四詩品》的底蘊,乃至有利于了解中國美學的底蘊。中國傳統美學講“無往不復”,注重美是復合體,不能單向思考。錢鍾書曾說,中國的詩與外國的詩相比,聲音不高,色彩不濃,氣勢不夠,即便是最豪放的部分,在外國人看來還是含蓄的,其原因就在中國美學都存在“大用外腓”式的矛盾思維,兼涵作用力與反作用力,而不會一往而不復。如“綺麗”品說“濃盡必枯,淡者屢深”,也是這個道理。
再則,羅韜的例證,也不僅止于詩歌的風格,像曹操的《觀滄海》,固能較好地例證雄渾,但在魏晉南北朝這一“文學的自覺時代”,更有文學史轉捩的考量。羅韜認為,正是這個時代奠定了中國南北文化的二元結構——如漢魏文學與齊梁文學、建安體與永明體、魏碑與晉帖、幽燕氣象與江南風韻,于是,近兩千年以還,北雄南秀,北氣南韻,二者從互異、互補到互轉,衍化出無窮精彩。方此之際,曹操無論是政治還是文學都是“收束漢音,振發魏響”的關鍵人物,是漢魏文學中幽燕之氣的最好體現者。這首《觀滄海》,在他先于“官渡之戰”戰勝河北強手袁紹,然后北伐烏桓,掃平袁氏余孽,肅清北方,班凱旋之師,途經碣石,一覽滄海,橫槊賦詩,歌以詠志,“開三百篇未有之奇”。
更進一步,羅韜于每一品均選取了從古到今各個時期的代表性詩篇以為例證,縱向的史的觀念是非常自覺的,所引近百首詩,其中多有不常見詩,也可見作者對傳統詩歌浸淫之深廣。又每一詩,必知人論世,及于其特定的時代背景以及寫作的特定事件與特別心緒,更顯作者識見之高明。為了能更清晰透徹地說明,作者還時時舉出反例或旁例。比如講到唐詩之雄渾,或會令人想起李白的“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云,諸侯盡西來”,喜其氣勢懾人,雄風拂面。但一仔細辨讀,就覺得未免虛張落俗,雄而不渾,終是騎驢的想象騎馬的,畢竟隔了一層;由此而引出的杜甫雄渾氣象的七律《登高》,則參差對照之妙,自不待言。再如他論纖秾,認為桃源主題適合纖秾表現,便舉王維、劉禹錫、王安石、汪藻的《桃源行》以及韓愈《桃源圖》,異代同題比較,也是另一種詩史意識的體現。
三
論詩如此,移書法、繪畫、篆刻之“花”以就各品風格之“鏡”時,作者也無不站在各體藝術史的高度,以胸次通觀而得精見卓識。只此,前賢也早有論斷。如劉熙載《藝概》說:“司空表圣之《廿四詩品》,其有益于書也,過于庾子慎之《書品》。蓋庾《品》只為古人標次第,司空《品》足為一己陶胸次也。此惟深于書而不狃于書者知之。”故詩品之所以同時為畫品、書品、印品,其根本不止是詩之風格,乃人之胸次投射。羅韜迥出時流,目顧愷之《洛神賦圖》為高古之代表,就是這個道理。
他在解釋顧愷之的這幅名作的過程中,對于“水不容泛,人大于山”這一著名畫評做了全新的詮釋,尤為令人耳目一新。所謂“水不容泛,人大于山”,這一評價來自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后世多以為是對畫作不成比例的批評。但羅韜認為這是一個肯定性評價。從《洛神賦圖》是一幅“戲劇連環圖”來看,它是以曹植《洛神賦》故事來展開的,人物和情節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山水動植,都是背景,是次要元素,不必強調,理應弱化。所以作者大膽取舍,人物顯得最突出,山與水都弱化處理,這類手法,后來只在京劇中保留和發展。京劇憑一桌一椅,代替繁縟的廳堂;一鞭代鞍馬,一槳代船艇,四丁演千軍,這種“達意高于狀物”的價值觀,是“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內在依據。

《歷代名畫記》〔唐〕張彥遠著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4 年版
后世的美術史家常把“人大于山”作為貶詞來看,這是不對的;張彥遠隨即解釋:“詳古人之意,專在顯其所長,而不守于俗變。”——對“人大于山”的評價是很高的。這正是一切藝術所要謹記的要訣,知所隱才能知所顯。唐宋兩代的山水的最大“俗變”,就是向寫實靠攏了,合比例了,“狀物高于達意”了,這確是一個重大的轉變。而能得古人之意,不徇俗眼,顯其所當顯,隱其所當隱,就是顧愷之此畫的“高古”之妙;后來的京劇,再后來關良戲劇人物畫同此妙諦。這樣就為“高古”開出別徑,從某種意義上堪稱對中國古代美學的一種新貢獻。
羅韜論書法與篆刻的雄渾,也是別具只眼。比如說論隸書的雄渾,《魯峻碑》與《張遷碑》《衡方碑》等都稱得上,而尤以《魯峻碑》為最——此碑用筆豐腴,而刀法峻整,橫筆與捺筆則舒展而有逸氣,形成了雄渾而寬綽的風格。這種雄渾風格的呈現,是書者、刻者和千年風雨共同作用而成的,人力與自然力結合,自覺與不自覺交替,與晉唐以后書法之成,皆憑一筆完成,趣味頗異。這就是所謂金石味的魅力所在。那后人何以重開雄渾之境?以何紹基臨《魯峻碑》為例,他除了通過想象力追摹原書者的筆道外,還領略蒼莽的刀味、石味和滄桑感,以思補筆,以筆追刀,以紙師石,以墨見千年風雨,這就為書法史開出了前所未有的雄渾新境界。
書法如此,刻印亦然。像漢“朔方長印”,是處于今天山西地區的朔方郡的官長之印,氣勢雄渾,與其地氣悉相呼應,幾乎可以作為印學“南北印風不同論”的最佳例證。唐人所謂“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這方印真有河朔氣象。它的線條以方為主,方中寓圓;方則易見雄樸,而圓則使之免于板滯,故稱之為雄渾。雄渾作品的一大特點是,即使把它放大了,氣勢也不會弱,反而越大越好,越大越壯,這方印可以說足以當之。鄧石如篆刻,其實多從這一路中來。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詩書畫印,的確可以合論,也實在應該合論,特別是對于《二十四詩品》這種表面形象而實質抽象的議論,本是建立在綜合藝術之上的,如果確為明人偽作,更是如此。而且,羅韜不僅匯通詩書畫印來例證每一品,也不僅僅是每一例均具體而微到技法特征,更從其歷史發展的規律上來引申拓展,因而也就不僅增強了論證說服的力度,還能給我們以藝術史和藝術理論等多方面的真知灼見與創新啟迪。比如他釋“沉著”,繪畫則以錢松喦《泰山六朝松》為例。錢松喦的作品有兩大得力點,一是線條厚拙沉實,有如鐵鑄;二是設色奇艷脫俗,真幻相生。這令他的作品,既有北派山水之渾厚壯美,又有南派山水的秀逸自然,二者圓融一體,成就獨特風貌。這幅《泰山六朝松》,一松占滿全部畫面,如蒼龍盤屈,氣勢非凡。松樹的線全是以點和短線積成,這既反映了千年老松的鱗甲質感,更表現了筆墨的沉郁奇崛之致,這是“屋漏痕”的極致性表現。而錢松喦山水技法,得力于石溪處最多,而其對古法的真正悟入,是在登上牛首山之后,借江山自然之助始得,并能自出風格——就像董其昌過洞庭看到秋湖暮云,大悟米家點法,王原祁目睹伊洛山色,才真正領略黃公望勾勒之妙一樣。古人之法,必源于造化,不從造化之中去理解古人,是未真知古人。

錢松喦《泰山六朝松》
羅韜由此更進一步的理論上的思考是,中國古代文藝發展的一個規律,正在于以復古為革新。這種對高古的崇尚,前人論之甚詳。羅韜則更廣泛細致地探討下去,便先發現“古”或曰“高古”本身,又可一分為二,有“自覺”與“不自覺”之別:“不自覺的高古”,如上古壁畫,上古詩“斷竹,續竹,飛石,逐肉”等,它們多產生于文藝的起源點,充滿了人類心靈的稚拙之趣;“自覺的高古”,則產生于文藝自覺之后,屬于作者對抗時俗、返璞歸真的主動選擇。古質而今妍,高古往往與樸拙、稚拙相表里。文化進程總是文質交勝的,樸久思華,華極反樸;高古,就是樸對華、質對文的反撥,也即“自覺”地向“不自覺”回歸。
高古必新,復古以開新,乃扭轉時風的開新之法。它有不俗之韻,有獨往之懷,在文學上,更有憤時之氣。高古之高,在于它俯視時俗,或自我作古,有意無意都采取遠交近攻之策:近攻,反抗時下風氣;遠交,從古老的源頭上尋找可以生新的基因。像韓愈《琴操·將歸操》、孟郊《吊國殤》、章太炎《題亡國慘記》,讓我們看到,從孔孟,到韓孟詩的風骨,經過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到章太炎的千年之問,復古主義是包含著一種革命基因的。這種高古之風不僅僅是藝術形式問題,所謂“古”,更多是寄予一種理想。它并非復陳腐之古,而是借復古以開新,這其中有不滿于當下、桀驁不俗的胸懷在。高古的“高”,都有一種孤獨感,有一副硬骨頭。高古必新,這是一種孤獨的新。“以復古為革新”,在羅韜的這種論述中,便有了新的面目。
而羅韜把“曠達”一品由第二十三品移作結穴一品來論述,則別具深意。這是由于經過雄渾沖淡,經過綺麗豪放以后,最終面對人生的終極問題,面對困苦死亡,也面對終極思考的超越,中國人不寄托于彼岸的拯救,而仍歸于在世的曠達境界,無論儒、釋、道三家,都同以此為結穴。他經過對陶潛、蘇軾等人的詩的品賞,對巨然、齊白石山水畫的贊嘆,對陳白沙、王陽明書法的揣摩,最后歸結到對馬一浮“廓然無圣”印的解釋,他說:“馬一浮先生印風寬博靜穆,刻‘廓然無圣四字,境界全出。此語為菩提達摩名言,意即一旦覺悟,一掃執著,無一切生死、高下、圣凡的分別。無差別心,是為廓然、豁然。”并再對馬一浮學行做了簡括通明的總結,最后,以“廓然無圣,大道甚夷”八字結束全書。其實,這是提醒讀者,既從文藝作品的差異去理解美的多樣性,最后也要以無差別心去理解美的境界之匯通。讀罷,掩卷而有廓然澄明之感。
于己亥酷暑中
《移花就鏡:廿四詩品詩書畫印通釋》,羅韜著,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