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司之迷與奧斯丁的解藥
書玉
小說家在作品里展現(xiàn)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當(dāng)?shù)恼Z言,向世人表達(dá)他對(duì)人類最徹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樣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繪,筆下閃耀著機(jī)智和幽默。
—簡·奧斯丁《諾桑覺寺》

一、簡·奧斯丁的魅力
在世界文學(xué)史上,簡·奧斯丁可以說是一個(gè)神奇又獨(dú)特的存在。她創(chuàng)作的七部“浪漫小說”在她自己的時(shí)代就擁有大量讀者,從以攝政王子為代表的貴族到中產(chǎn)階級(jí)女性。即便二百年以后,那個(gè)時(shí)代大量的流行小說早已被束之高閣,她的幾部小說卻依然流行。出版商視簡·奧斯丁為大眾市場制造浪漫小說的祖師奶奶,她的作品還成為好萊塢電影、BBC戲劇和各國女性讀書俱樂部的最佳選項(xiàng)。最不可思議的是,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以來,受女權(quán)主義、解構(gòu)主義及后現(xiàn)代主義各種的理論沖擊,許多經(jīng)典都遭受質(zhì)疑,許多文學(xué)大家因種種政治不正確被拉下神壇,奧斯丁的作品卻依然被作為大學(xué)課堂的文學(xué)經(jīng)典來討論。這種長久不衰的魅力究竟源自何處?各國的研究者和讀者都對(duì)此迷惑不解又津津樂道。
關(guān)于奧斯丁的中文評(píng)論,我讀到的最好的一篇是楊絳先生寫的《有什么好:讀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據(jù)說是因?yàn)楫?dāng)時(shí)社科院文學(xué)所某些人質(zhì)疑西洋文學(xué)這種資產(chǎn)階級(jí)的小說對(duì)我們“有什么好”,楊先生就以奧斯丁這部小說為例,寫了這篇看似普通卻大顯行家功力的文章。她不扯理論大旗,也不借權(quán)威話語,而是從“我們不能單憑小說里的故事來評(píng)定這部小說(優(yōu)劣)”這一基本文學(xué)道理說起,一層層剝洋蔥似的,從布局到人物,從題材到文字,循循善誘地把奧斯丁小說的種種好處一一道來。“可以說,奧斯丁所寫的小說,都是從戀愛結(jié)婚的角度,寫世態(tài)人情,寫表現(xiàn)為世態(tài)人情的人物內(nèi)心”。真是說得又實(shí)在又透徹。最后又以外國人吃鐵蠶豆不得其趣的笑話幽了那些文學(xué)外行一默。這樣通透的評(píng)論也算配得上奧斯丁那樣睿智的小說了。
這里斗膽接著楊絳先生的話題,繼續(xù)探究奧斯丁的小說是憑什么傾倒眾生,并有如此長久的生命的。我特別地想在浪漫小說(romance novel)這一文類的背景下,通過為什么要讀奧斯丁來討論小說的人文價(jià)值及其自身要面對(duì)的倫理挑戰(zhàn)。
以浪漫小說為例,討論文學(xué)的人文價(jià)值及其自身面對(duì)的倫理挑戰(zhàn),可能非常有代表性。一方面,浪漫小說的兒女情長,是人類經(jīng)久不衰的主題,提供了文學(xué)娛樂和教化功能。但另一方面,浪漫小說也是最被文學(xué)教授看不上的文類,因?yàn)樗奶茁罚驗(yàn)樗鼘?duì)人心尤其是對(duì)女性的蠱惑。古今中外,一般的文藝女青年容易迷陷于愛情小說,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人物,不能自拔。十九世紀(jì)法國作家福樓拜就借筆下的包法利夫人指出流行小說對(duì)涉世未深的女性的毒害。“結(jié)婚以前,她原以為心中是有愛情的;可是理應(yīng)由這愛情生出的幸福,卻沒有來臨,她心想,莫非自己是搞錯(cuò)了。她一心想弄明白,歡愉、激情、陶醉這些字眼,在生活中究竟指的是什么,當(dāng)初在書上看到它們時(shí),她覺得它們是多么美啊。”(《包法利夫人》第五章)剛剛結(jié)了婚的包法利夫人或準(zhǔn)確地說修道院教育培養(yǎng)出的愛瑪已經(jīng)對(duì)婚姻生活和鄉(xiāng)村醫(yī)師包法利先生感到了厭倦,因?yàn)檫@跟她看到的愛情小說中描寫的完全不一樣。少女時(shí)期的她在修道院讀書,那些小說充滿了“愛情、愛人、受壓迫的女人孤單地昏倒在涼亭中……場景永遠(yuǎn)是幽暗的森林,糾結(jié)的心,呢喃的誓言,啜泣,眼淚與吻。月夜中乘船聽著樹叢的夜鶯,如獅子般英勇的紳士卻對(duì)女主角溫柔似綿羊”。婚后的愛瑪很快就借完租書店所有類似的小說,一心想經(jīng)歷小說中男女主角刻骨銘心的“愛戀、激情、癡迷”,而無法面對(duì)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巨大落差,最后鋌而走險(xiǎn),終致身敗名裂。因此,在福樓拜眼中,愛瑪或包法利夫人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因?yàn)槌粤四切┝餍形膶W(xué)的迷藥而不自知。
浪漫小說這種給女性讀者的迷藥配方至今依然屢試不爽。當(dāng)代的言情小說從英美的禾林系列到中國的女性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之所以成為巨大的文化產(chǎn)業(yè),很大程度上就依賴于這種讓讀者從現(xiàn)實(shí)中逃離到幻想之鄉(xiāng)的范式。這也成了浪漫小說為人詬病的地方。
然而,奧斯丁小說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她把浪漫小說的軟肋變成文學(xué)教化的盔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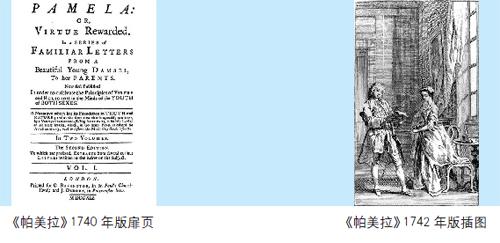
二、羅曼司之迷
簡·奧斯丁寫作的時(shí)代,十八世紀(jì)末的英國,也是長篇小說最為繁榮的時(shí)代。
如伊恩瓦特在《小說的興起》中所描述的,十七世紀(jì)小說這種文體在英國迅速興起,與工業(yè)革命帶領(lǐng)的資本主義、對(duì)個(gè)體獨(dú)特經(jīng)驗(yàn)的重視以及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思維形成都有關(guān)聯(lián)。從物質(zhì)基礎(chǔ)上看,印刷術(shù)帶動(dòng)了報(bào)紙雜志業(yè),使得商品社會(huì)把文化閱讀出版活動(dòng)都納入大規(guī)模的創(chuàng)造利潤的商業(yè)活動(dòng)。當(dāng)時(shí)循環(huán)圖書館(circular library)流行,人們通過訂閱、公共分享,形成大規(guī)模的讀書活動(dòng)。而中產(chǎn)階級(jí)尤其商人階層的興起,也使文學(xué)消費(fèi)有了社會(huì)基礎(chǔ)。尤其是中產(chǎn)階級(jí)女性閱讀量出現(xiàn)巨幅增長。十八世紀(jì)中期,小說取代了伊麗莎白時(shí)代的主要文藝形式戲劇而成為社會(huì)上最流行同時(shí)也是最重要的文體。在這一過程中,女性作家,“涂鴉上癮的藍(lán)襪子才女”(弗吉尼亞·伍爾夫語)充當(dāng)了重要角色。“開始寫作”,如程巍在《倫敦蝴蝶與帝國鷹》中所述,與當(dāng)時(shí)女性在經(jīng)濟(jì)來源和婚姻市場上的困境有關(guān),對(duì)很多晚婚甚至終生未嫁的文學(xué)婦女來說,寫作是唯一可以不離開家又體面的謀生之道。中產(chǎn)階級(jí)婦女構(gòu)成閱讀與寫作的主要群體,文學(xué)是她們娛樂消遣、了解外面世界甚至學(xué)習(xí)“如何在婚姻市場出奇制勝”的重要手段,這也促成了浪漫小說的興盛。“也許主要是通過資產(chǎn)階級(jí)家庭女性成員的白日夢,浪漫主義才得以進(jìn)入中產(chǎn)階級(jí)文化。”(E. J.霍布斯鮑姆語)
在這一時(shí)期的小說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浪漫小說或者羅曼司(romance novel)成為一大重要類型。(與中世紀(jì)傳奇羅曼司不同,此類型小說特指以男女求愛及至婚姻的故事為情節(jié),以婚姻快樂的大團(tuán)圓結(jié)局為結(jié)尾,并多從女主人公的角度講述的愛情故事。)

英國小說的三大鼻祖之一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1689-1741)的書信體小說《帕美拉》(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和《克拉麗莎》(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開創(chuàng)了這種題材和情感類型,被稱之情感小說(sentimental novel)。其主人公都是具有美德的女性,抵御種種欲望的誘惑,最后修成正果,贏得婚姻。在它似乎感傷艷情的表面下,實(shí)質(zhì)是大量倫理道德的說教。理查遜的小說與這個(gè)時(shí)期的女性教育理念有關(guān),也因此《帕美拉》成為英語文學(xué)史上最早的一本暢銷書,出版十一個(gè)月就有五個(gè)版本同時(shí)印刷發(fā)行,而且招來形形色色的模仿者。
哥特小說是十八世紀(jì)英國流行的另一種浪漫傳奇。以黑暗的古堡、詭奇的地景與神秘的氣氛為特征。其中以女作家雷德克里夫(Ann Radcliffe,1764-1823)的作品最為知名。她筆下拜倫式的英雄和長途旅行的場景使得浪漫故事別有一番驚心動(dòng)魄。代表作《舞多佛的秘密》(The Mysteries of Udolpho)曾掀起十八世紀(jì)末英國哥特羅曼司的寫作和閱讀的熱潮。簡·奧斯丁的小說《諾桑覺寺》中,女主人公凱瑟琳和她的女伴們,從虛榮膚淺的伊莎貝拉到寬容溫雅的艾麗諾都在討論《舞多佛的秘密》,可見這本小說當(dāng)時(shí)有多熱。大概與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中國的瓊瑤小說或前幾年北美少女讀者中流行的“暮光(Twilight)系列”一樣。
十八、十九世紀(jì)幾位重要的英國女作家,包括簡·奧斯丁和勃朗特姐妹,都為浪漫小說發(fā)展成為一大文類做出了貢獻(xiàn)。雖然今天的文學(xué)史稱她們的小說是文學(xué)作品(literary novel),以示與當(dāng)年大量的流行小說(pulp fiction,如哥特小說)之間的區(qū)別。但她們當(dāng)年卻未必嚴(yán)格劃定自己寫作的界限,所受影響也非常復(fù)雜。從接受情況看,她們當(dāng)時(shí)都是暢銷作家。奧斯丁在生前就有大量粉絲,她一八一五年的小說《愛瑪》就是被迫“獻(xiàn)給”攝政王子也就是后來的喬治四世的。勃朗特姐妹寫《簡·愛》《呼嘯山莊》,都受到了當(dāng)時(shí)浪漫主義文學(xué)觀念尤其哥特小說的影響,她們的男主人公都是一個(gè)個(gè)狂野的拜倫式的心靈孤兒。
但是,簡·奧斯丁與勃朗特姐妹在對(duì)激情的理解以及小說該如何表現(xiàn)處理女性的情感上大相徑庭。
當(dāng)年有名的評(píng)論家李維斯(George Henry Lewes,1817-1878)曾經(jīng)非常積極地支持和推動(dòng)女性寫作。這個(gè)后來成為女作家喬治·艾略特伴侶的男人,在《簡·愛》出版后,給默默無聞的夏洛蒂寫了很好的書評(píng)。但是他也直言小說中的戲劇性情節(jié)(melodrama)比較“適合那種流動(dòng)圖書館的趣味”。他還給夏洛蒂提建議,讓她去讀簡·奧斯丁,因?yàn)樗男≌f顯現(xiàn)了“用自然的語言和形式來達(dá)到一種冷靜與平衡的智慧”。夏洛蒂讀了當(dāng)時(shí)最有名的《傲慢與偏見》后,卻并不欣賞奧斯丁筆下的“那些住在優(yōu)雅又封閉隔絕的鄉(xiāng)村大屋中的紳士淑女們”,而且非常怨憤地說,“她根本不懂得激情為何物”(the passions are perfectly unknown to her),因此她的人物也缺乏性格深度。而下文也要提到,奧斯丁對(duì)勃朗特姐妹偏愛的哥特小說也是冷嘲熱諷。
對(duì)于持有浪漫主義人文觀念的勃朗特姐妹,小說就應(yīng)該像烈酒、像迷藥。個(gè)人的原始激情的力量是對(duì)維多利亞時(shí)期矯情虛飾的公共道德和所謂理性文明的反叛與警醒。故事中荒涼敵對(duì)的環(huán)境,主人公在追求真愛時(shí)遇到的重重障礙,表達(dá)了早期女性作家在表達(dá)自己越界的激情欲望時(shí)內(nèi)心深處的恐懼和矛盾。而奧斯丁的“冷靜與平衡的智慧”,則是在不動(dòng)聲色的英式家庭故事中,借助筆下的女主人公們探索女性經(jīng)驗(yàn)和智識(shí)成長的種種可能和問題。通過浪漫小說的形式來探索小說這一新文類的倫理責(zé)任也就別有一番用心。

三、小說與女子教育
從各種回憶文字和研究資料可以了解,奧斯丁的閱讀寫作從少女時(shí)代就已開始,而且是她的家庭教育的一個(gè)重要部分,這在當(dāng)時(shí)的中產(chǎn)階級(jí)女性中很有代表性。
十八世紀(jì)開始快速上升成長的資產(chǎn)階級(jí),已逐漸躋身紳士階層并修正其定義。與以往強(qiáng)調(diào)世襲身份的貴族不同,紳士不僅是一種社會(huì)身份,也是一種具有責(zé)任感的品質(zhì)和形象。所以紳士不是天生的。紳士教育,以及與之相應(yīng)的淑女教育,是佐治亞時(shí)代以及后來的維多利亞時(shí)期重要的社會(huì)和倫理話題。啟蒙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及如洛克、休謨等提出的以意識(shí)為主的自我理論,強(qiáng)調(diào)教育對(duì)于成人的重要作用,以及人類心靈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必要反省。而小說這一新興的文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教育職能和倫理重任,尤其是對(duì)于女性的教育。當(dāng)時(shí)英國女性教育事業(yè)處于不上不下的狀態(tài),一方面社會(huì)意識(shí)到教育的重要性,很多鄉(xiāng)紳階層的女子都在家門之外有過不定期的學(xué)習(xí),比如去女子寄宿學(xué)校,還有上流社會(huì)的社交;但另一方面,女性還沒有獲得像男性那樣的正規(guī)、系統(tǒng)的教育機(jī)會(huì),家庭教育構(gòu)成其教育的主要部分,包括閱讀和家庭教師。因而,小說成了女子教育的重要讀本。
簡的父親喬治·奧斯丁在牛津大學(xué)接受神學(xué)教育后,娶了同是牧師家庭出身的卡桑德拉,他們結(jié)婚后搬到漢普郡鄉(xiāng)間小鎮(zhèn)斯蒂文斯頓(Stevenston),在那里養(yǎng)育了六個(gè)兒子兩個(gè)女兒。牧師是當(dāng)時(shí)英國社會(huì)一個(gè)比較獨(dú)立特殊的階層。一方面他們受過良好教育,從事有社會(huì)責(zé)任的職業(yè),通常還管理他們教區(qū)的世俗事務(wù),在地方上享有一定威望。他們的經(jīng)濟(jì)收入通常也有保障—教區(qū)提供鄉(xiāng)間住宅和農(nóng)地,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稅金和教區(qū)保護(hù)人的饋贈(zèng)。但他們屬于有產(chǎn)鄉(xiāng)紳階層中靠近底層的一族。所以喬治·奧斯丁一家并不寬裕,老奧斯丁還要管理農(nóng)莊,找了三四個(gè)男生在家里開寄宿補(bǔ)貼家用。家中的兩個(gè)女孩簡和卡桑德拉,沒有多少嫁妝遺產(chǎn)可以繼承,而她們所有的正規(guī)教育只是不到兩年的女子寄宿學(xué)校。她們的未來就決定于自己的婚姻,跟當(dāng)時(shí)大部分中產(chǎn)階級(jí)家庭的女孩一樣。
奧斯丁的父親雖然未能在經(jīng)濟(jì)上給孩子們提供優(yōu)裕的條件,卻給她們帶來了別的優(yōu)勢,包括教育和社會(huì)交往,這是她們比其他女子多出的一筆財(cái)富。父親讓她們學(xué)習(xí)他為男學(xué)生編的教材,家里有庋藏豐富的圖書館可以使用。最重要的是她們的家庭氣氛非常開放,父母鼓勵(lì)孩子在藝術(shù)文學(xué)上的興趣。少女時(shí)代的簡喜歡閱讀,對(duì)歷史戲劇尤感興趣。她還有很多機(jī)會(huì)接觸家里來來往往的親戚朋友,包括那個(gè)嫁到印度的姑媽和與法國人結(jié)婚的表姐。她們帶她到倫敦、巴斯,讓她看到上流社會(huì)的交往,聽到冒險(xiǎn)的異域故事。年輕的簡最愉悅放松的生活就是跟家人一起,表達(dá)自己對(duì)周圍事物的看法,朗讀討論她剛剛閱讀或?qū)懢偷男≌f—她從十四歲時(shí)就開始創(chuàng)作,早年創(chuàng)作的兩部作品,一部關(guān)于愛情與友誼,另一部關(guān)于英國歷史。
所以奧斯丁從少女時(shí)代就開始通過閱讀和寫作來觀察評(píng)論周圍的人情世故,尤其是女性的愛情婚姻與家庭經(jīng)濟(jì)的關(guān)系。十八世紀(jì)英國階層急劇變動(dòng),從地主鄉(xiāng)紳到銀行家、暴發(fā)戶,以及那些在社交場合出入、待價(jià)而沽的女子,使她看到十八世紀(jì)英國工業(yè)革命后興起的資產(chǎn)階級(jí)對(duì)社會(huì)觀念的改變,以及女性社會(huì)地位及經(jīng)濟(jì)保障是如何赤裸裸地與婚姻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些構(gòu)成了她小說的主要內(nèi)容和人物故事的中心。但同時(shí),她的人文教育和牧師家庭背景,包括這種家庭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位和文化修養(yǎng),給了奧斯丁看待女性婚姻與命運(yùn)的一個(gè)獨(dú)特而堅(jiān)定的角度,也形成了她的文學(xué)倫理觀念的基石:女性的幸福,包括幸運(yùn)的婚姻,必須建立在個(gè)人高度發(fā)展的理性與情感之上。

四、《諾桑覺寺》與女性成長
相對(duì)奧斯丁其他作品,《諾桑覺寺》較少為人所知,是在作者去世后才出版的。其實(shí)這是她最早醞釀構(gòu)思的作品。一八○一年隨家人搬去巴斯的前兩年,簡完成了一部叫《蘇珊》的小說,然后在巴斯進(jìn)行修改。兩年后,簡最親近的兄弟亨利把《蘇珊》的版權(quán)賣給了出版商考斯比。但考斯比一直沒有將之印刷成書,直到一八一六年簡·奧斯丁又把它買回來,再次修訂。一八一七年底,改名《諾桑覺寺》后與《勸導(dǎo)》合集出版。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部見證了作為作者的奧斯丁逐步成熟的作品。
跟奧斯丁其他作品一樣,《諾桑覺寺》也是一部女性成長小說。尤其獨(dú)特的是,這也是奧斯丁公開探討小說形式與倫理的作品。奧斯丁借敘事者和人物之口發(fā)表了很多關(guān)于小說的討論,比如第五章完全就是一篇小說家的獨(dú)立宣言,包括了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感傷小說和哥特小說的針砭,以及對(duì)小說倫理的辯論。更重要的是,作者把女主人公凱瑟琳心智上的成長與她對(duì)小說的認(rèn)識(shí)編織在一起,成為小說的主要母題。

凡是在凱瑟琳·莫蘭的幼年時(shí)代見過她的人,誰都想不到她命中注定會(huì)成為女主角。她的家庭出身、父母的性格、她自己的品貌氣質(zhì),統(tǒng)統(tǒng)對(duì)她不利。
她的相貌不過如此,她的智力似乎同樣不適宜做女主角。她不喜歡音樂繪畫法文寫字算術(shù)。
在十四歲上居然寧可玩板球、棒球、騎馬和四下亂跑,而卻不喜歡看書,至少不喜歡看那些知識(shí)性的書。假如有這么一些書,里面不包含任何有益的知識(shí),全是些故事情節(jié),讀起來用不著動(dòng)腦筋,這樣的書她倒也從不反對(duì)看。(孫致禮譯本)
這是小說《諾桑覺寺》開篇,敘事人向我們介紹了女主人公凱瑟琳,鄉(xiāng)村牧師的十個(gè)孩子之一。她天真,沒有見過世面,閱讀興趣和能力堪憂。因?yàn)橐粋€(gè)偶然的機(jī)會(huì),被好心的鄰居阿蘭夫婦帶到巴斯去長見識(shí),其實(shí)也是為未來的婚姻探路。這個(gè)人物與其他女主人公不同,她幾乎是單槍匹馬,一個(gè)人走在尋找幸福的路上。

奧斯丁對(duì)凱瑟琳這個(gè)人物的設(shè)計(jì)其實(shí)大有深意,她在家信里說,小說里那種十全十美的女主角看著惡心,使她忍不住要調(diào)皮搗蛋。從一開始,作者就給我們看一個(gè)天性有待通過合適的教育進(jìn)行改造的“問題少女”。而這教育由兩個(gè)部分組成,一是有頭腦的閱讀,二是辨識(shí)人情世故的經(jīng)歷。
小說的上半部分主要發(fā)生在巴斯。巴斯是十八世紀(jì)英帝國上升時(shí)期的社交中心,代表了佐治亞時(shí)代的豪奢氣息和精致品位。一八○一年到一八○六年,奧斯丁與退休的父母一起在悉尼街四號(hào)住了五年。據(jù)研究者說,她在那里的歲月并不愉快,她的寫作幾乎沒有什么進(jìn)展。可以想象這樣一個(gè)膚淺夸張、虛榮奢華的城市,給生長在漢普郡鄉(xiāng)間,習(xí)慣了田園簡樸生活的奧斯丁帶來的震驚和不適。“在六個(gè)星期以內(nèi),巴斯是令人愉悅的;但是超過六周,它是世界上最令人厭倦的地方”。這是《諾桑覺寺》里男主人公亨利·蒂爾尼向剛來到城里的凱瑟琳介紹巴斯時(shí)的尖刻的評(píng)價(jià),你幾乎可以看到作者寫下這幾句話時(shí)那種帶著嘲諷的表情。

但是巴斯在簡的生活和小說中都留下了很深的痕跡。簡的幾乎所有小說,都有提到巴斯。巴斯成了上流社會(huì)或希望躋身上流社會(huì)的男女們展示自己,尋找獵物的地方(《理智與情感》),經(jīng)濟(jì)上困窘的父母,把鄉(xiāng)下的莊園出租出去,帶著女兒來尋找有錢的丈夫的地方(《勸導(dǎo)》),女友們喝茶打探消息或者逛街購買婚紗的地方(《諾桑覺寺》)。這樣一個(gè)讓人眼花繚亂的名利場無疑為浪漫故事里的女主人公提供了一個(gè)意味深長的背景。鄉(xiāng)村姑娘凱瑟琳要在這個(gè)名利場里找到自己的Mr. Right,并且能俘獲他的心,無疑需要過人的觀察識(shí)人能力和逐步成熟的心智。
小說的敘事是全知有限的。小說的意識(shí)視角是凱瑟琳的。頭幾章都是她在監(jiān)護(hù)人艾倫太太陪伴下,進(jìn)入巴斯社會(huì)的描寫。我們看到凱瑟琳初次參加舞會(huì)時(shí)的尷尬與失望,希望被人關(guān)注的虛榮與喜悅,生活每天是眼花繚亂的“娛樂”,而隱藏在這一娛樂活動(dòng)之下才是女性的真正目的和她們內(nèi)心的盤算和焦慮。“巴斯是個(gè)多么快活的地方。他們匆匆趕往新月大廈,想在那里呼吸上流社會(huì)氛圍的新鮮空氣。”
的確,凱瑟琳不久就進(jìn)入比自己以前鄉(xiāng)村生活大得多的社交圈子。她在舞會(huì)上遇到亨利·蒂爾尼,在溫泉房遇到索普兄妹一家,她很快交到兩個(gè)女友,伊薩貝拉和艾麗諾。隨后章節(jié)表面上是這些青年男女們的交往和郊游,但故事的內(nèi)核還是凱瑟琳如何增長見識(shí),包括她如何辨認(rèn)出誰才是真正可以托心的朋友。雖然索普兄妹最初以他們的老練世故、時(shí)髦有趣吸引迷惑了凱瑟琳,但在睿智的男主人公亨利·蒂爾尼的引導(dǎo)下,她逐漸看出他們不過是金玉其外的渣男渣女,自私、無知,會(huì)在關(guān)鍵時(shí)刻背叛。
當(dāng)凱瑟琳離開巴斯時(shí),“她見了世面,看到了各種各樣的樂趣”。最重要的是,她贏得了蒂爾尼一家人的喜愛。被邀請(qǐng)到他們家所在的諾桑覺寺小住。
上卷結(jié)束時(shí),主人公凱瑟琳很幸運(yùn),她走在嫁入豪門的路上。但凱瑟琳能否成功地把自己嫁出去,最重要的考驗(yàn)卻在書的下卷,取決于她能否突破哥特小說為她設(shè)置的認(rèn)知障礙,辨別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的不同。
五、小說的迷藥
在書的第一部分,第六章凱瑟琳和她那個(gè)看上去精明實(shí)際上是繡花枕頭的女友伊薩貝拉之間有一大段討論哥特小說的對(duì)白。作者用她們無知又做作的對(duì)話,表達(dá)了她對(duì)那些喜歡讀哥特小說卻對(duì)小說的毒性毫無抵抗能力的女性讀者的看法。
第十四章凱瑟琳與蒂爾尼兄妹出游時(shí),她們又一次討論當(dāng)時(shí)流行的哥特小說。這次,男主人公亨利代作者出面。
“難道你不認(rèn)為《尤多爾弗》是世界上最好的書嗎?”
“最好的?我想你是指最精致的吧。那得看裝幀了。”
“亨利,”蒂爾尼小姐說,“你真不客氣。莫蘭小姐,他待你就像待他妹妹一樣。他總是挑剔我措辭不當(dāng),現(xiàn)在又在對(duì)你吹毛求疵了。你用的‘最好這個(gè)字不合他的意,你最好趁早把它換掉。不然他會(huì)拿約翰遜和布萊爾把我們奚落個(gè)沒完。”
“的確,”凱瑟琳大聲嚷道,“我并非有意要說錯(cuò)話。可那確實(shí)是一本好書。我為什么不能這么說呢?”
“很對(duì),”亨利說道,“今天天氣很好,我們進(jìn)行一次很好的散步,你們是兩位好姑娘。哦!這的確是個(gè)好字眼!什么場合都適用。最初,它也許只被用來表示整潔、恰當(dāng)、精致、優(yōu)雅,用來描寫人們的衣著、感情和選擇,可是現(xiàn)在,這個(gè)字眼卻構(gòu)成了一個(gè)萬能的褒義詞。”
作者又一次用了非常微妙的反諷語言表明了她對(duì)哥特小說、對(duì)輕信的年輕女子們的看法。你幾乎可以看到她與亨利會(huì)心地相視一笑。
奧斯丁對(duì)哥特小說的嘲貶并不代表她認(rèn)為閱讀小說是無用甚至愚蠢的。恰恰相反,奧斯丁認(rèn)為小說對(duì)心智的培養(yǎng)非常重要。書中的反面教材無知而又傲慢的索普先生就是一個(gè)不屑于讀小說的花花公子,他在情感方面,遲鈍而粗魯,沒有感知美與共情的能力。因此凱瑟琳很快就把他從候選人中剔除出去。
與約翰·索普不同,凱瑟琳心儀的對(duì)象亨利不僅喜歡讀小說,他還為小說辯護(hù)說:“一個(gè)人,不管是紳士還是淑女,只要不喜歡小說,一定愚蠢。”在他看來,讀書不只是娛樂,而且能很好地修正人們的狹隘與無知。“少男少女應(yīng)該接受折磨,”亨利說道,“這是但凡對(duì)文明國度的人性多少有點(diǎn)了解的人所無法否認(rèn)的。”閱讀廣泛,但有自己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而且能選擇最合適的詞句來表達(dá)自己的判斷,做到頭腦與語言的精確合一,這似乎是奧斯丁心目中理想的讀者。
奧斯丁在《諾桑覺寺》里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是她對(duì)哥特小說的批判不只是通過人物之嘴進(jìn)行的抽象的評(píng)論,而是用故事本身來表達(dá)她對(duì)小說可能產(chǎn)生的人生誤導(dǎo)的認(rèn)識(shí)。
凱瑟琳進(jìn)入宛如哥特小說背景的諾桑覺寺后,迫不及待地用小說思維解釋現(xiàn)實(shí)。一開始,亨利并沒有直接戳穿她的想象,告訴她生活是什么樣子。作者只是用戲仿小說的語言,呈現(xiàn)女主人眼中所看到的現(xiàn)實(shí)。
凱瑟琳只掃視了一眼便發(fā)現(xiàn),她的房間與亨利試圖嚇唬她而描繪的那個(gè)房間截然不同。它絕非大得出奇,既沒有掛毯,也沒有絲絨被褥。墻上糊著紙,地板上鋪著地毯,窗戶和樓下客廳里的一樣完備,一樣光亮。家具雖則不是最新的式樣,卻也美觀、舒適,整個(gè)房間的氣氛一點(diǎn)也不陰森。
但是中毒甚深的凱瑟琳依然執(zhí)迷不悟,試圖用哥特小說的情節(jié)來解釋主人一家的生活,以至懷疑將軍把妻子謀殺。這時(shí)亨利才出面告訴她這種認(rèn)知有多么可笑:
“如果我沒理解錯(cuò)的話,你臆測到一種不可言狀的恐怖……親愛的莫蘭小姐,猜想想你疑神疑鬼得多么令人可怕。你是憑什么來判斷的?請(qǐng)記住我們生活的國度和時(shí)代。請(qǐng)記住我們是英國人,是教徒。請(qǐng)你用腦子分析一下,想想可不可能,看看周圍的實(shí)際情況。”
傳奇的夢幻破滅了。凱瑟琳完全清醒了。亨利的話語雖然簡短,卻比幾次挫折更有力量,使她徹底認(rèn)識(shí)到自己近來的想象之荒誕。她羞愧得無地自容,痛哭得無比傷心。她不僅自己覺得無臉,還會(huì)讓亨利看不起她。
不過奧斯丁對(duì)她的女主人公一如既往地偏愛。雖然凱瑟琳幼稚,但是她的誠實(shí),以及自省能力使她具備在經(jīng)驗(yàn)面前幡然醒悟的可能。
夜晚慢慢過去了……她仍在聚精會(huì)神地思索她懷著無端的恐懼所產(chǎn)生的錯(cuò)覺,所做出來的傻事,所以很快就明白了,這完全是她想入非非、主觀臆斷的結(jié)果……其實(shí),沒來等院之前,她就一直渴望著要?dú)v歷風(fēng)險(xiǎn)。她回憶起當(dāng)初準(zhǔn)備了解諾桑覺寺時(shí),自己懷著什么心情。她發(fā)現(xiàn),早在她離開巴斯之前,她心里就著了迷、扎下了禍根。追本窮源,這一切似乎都是因?yàn)槭芰怂诎退棺x的那種小說的影響。
奧斯丁在《諾桑覺寺》中表達(dá)的不只是對(duì)哥特小說的嘲諷和批判,而且是關(guān)于女性能否對(duì)小說做出自己的判斷的問題。
現(xiàn)在回頭再來看他們討論小說時(shí),亨利說的那句有點(diǎn)接續(xù)的話就顯得意味深長了:“莫蘭小姐,沒有人比我更尊重女人的理解力了。據(jù)我看來,女人天生有的是聰明才智,她們一向連一半都用不上。”
他信任她們的智力和頭腦。也正如此,在凱瑟琳痛心疾首改變之后,他接受了她。“以后無論判斷什么還是做什么,全都要十分理智。”她從寫作之初對(duì)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的區(qū)別就有清醒的頭腦。
六、簡·奧斯丁這個(gè)女友
奧斯丁從來不是浪漫主義者。她的主人公們都活在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和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中,婚姻成為階層進(jìn)退的重要砝碼。她的作品中那種睿智和諷刺的力量,來自她對(duì)鄉(xiāng)紳階層物質(zhì)的批判,以及對(duì)上流社會(huì)虛偽的交易的揭穿。在奧斯丁的筆下,最聰明、最讓我們同情的女主人公并不屈從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和社會(huì)壓力,她們有能力用自己的教養(yǎng)、智慧和心靈在錯(cuò)綜復(fù)雜的社會(huì)和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中為自己的愛情找到一個(gè)平衡。伊麗莎白、凱瑟琳、安妮,她們經(jīng)濟(jì)地位都不太美妙,但靠自己的頭腦,靠她們對(duì)自我與周圍世界的認(rèn)知,掙出了好婚姻。所以奧斯丁的小說表面上看是浪漫愛情故事,寫待嫁閨中的女人們?nèi)绾螕衽迹瑢?shí)際上她寫的是女性的成長。通過閱讀,通過世事觀察,獲得心智的成長,是她小說中那個(gè)在個(gè)人與階級(jí)的“傲慢與偏見”中,尋找“理智與情感”之間平衡的女性主人公的特色。
正因?yàn)樗≌f中的正面人物都有能力去感受情感,也能理智地判斷反省,所以即使其小說是一種皆大歡喜的結(jié)局,也是建立在對(duì)人性樂觀的態(tài)度和可信的基礎(chǔ)之上,而不是戲劇性的偶然或幻想。
韋恩·布斯在《我們的朋友:小說倫理學(xué)》(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1989)中,從倫理學(xué)的角度討論奧斯丁小說經(jīng)久不衰的魅力。他以《愛瑪》一書為例:“(它)里面包含針對(duì)其自身毒性的解藥。這部小說并不剝奪讀者從常規(guī)形式中得到的娛樂,但同時(shí)幫助細(xì)心的讀者培養(yǎng)一種雙重視野,把享受浪漫情節(jié)帶來的樂趣和對(duì)書中各色男女人物的精致觀察結(jié)合起來。”他把這種特質(zhì)稱為“奧斯丁的專利解藥”(Austens patented antidote)。
雙重視野,這正是奧斯丁小說魅力的關(guān)鍵。從小說中得到娛樂,但仍然能辨別幻象,是奧斯丁為其小說讀者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作為作者,她希望與讀者建立的關(guān)系是一種平等、尊重的關(guān)系。她用表面上看來俗套的浪漫小說的故事與結(jié)構(gòu)吸引讀者。但同時(shí)更讓她們看到這種結(jié)構(gòu)和情節(jié)本身的問題,通過敘事人的反諷語調(diào)的引導(dǎo),通過現(xiàn)實(shí)主義細(xì)節(jié)本身的內(nèi)容,以及對(duì)女主人公的成長過程可信的呈現(xiàn)。
小說的興起與發(fā)展,是資本主義上升時(shí)期人性覺悟的體現(xiàn),同時(shí)建立在人道主義及其對(duì)理性、自由、情感與想象的尊崇之上。簡·奧斯丁的小說自信完整地表達(dá)了這一信念。她的小說都可以讀成女性在理性與情感上的成長史。同時(shí)奧斯丁作為一個(gè)小說家,她對(duì)小說的功用與陷阱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shí)和警惕。以哥特小說為例,她提醒讀者小說的虛幻,以及它與現(xiàn)實(shí)的差異。這種提醒是善意的,是建立在她對(duì)讀者的智力和理解力的信賴與依靠之上。也就是說,一個(gè)有道德感的小說家,會(huì)用小說自身的形式,在提供給讀者這劑迷藥的同時(shí),也交給她們一服解藥。這才是小說敘事和閱讀的倫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