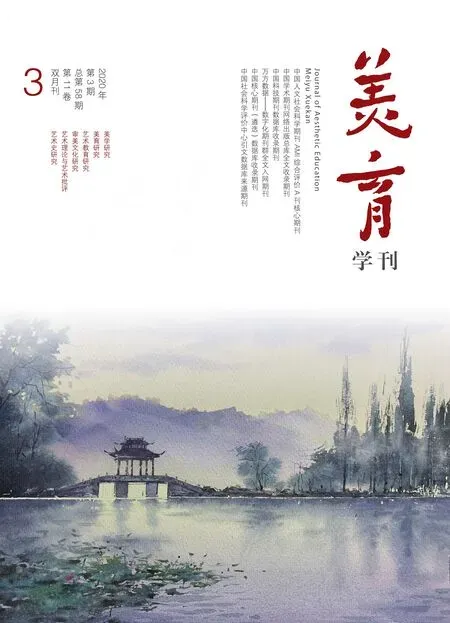美學史前史考察
——古希臘“美”的概念之詞源學辨析
李 創
(西安工業大學 文學院,陜西 西安 710021)
一、“美”的辭源學考辨


而“美”在古希臘語境中的用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二、Kállos在古希臘作家文本中的使用
美國學者大衛·康斯坦(David Konstan)在《美:這一古希臘概念的命運》(7)David Konstan, Beauty:The fortunes of an Ancient Greek Id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一書中,對“美”在古希臘不同文本中的使用情況作了詳細的分析,我們根據他的重要提示,對“美”在古希臘作者文本中具體的用法,以表格形式進行更為細致的區分與辨析。

古希臘作家出處及使用情況女詩人薩福(Sappho)在現存薩福殘篇⑧第16篇第3行“”中用了的最高級(形容最美好的事情,這里指征討特洛伊的軍隊);第7行用Kállos形容海倫的美,在其他地方也用它形容月亮:“”(“星星圍繞著美麗的月亮”,殘篇34第1行)和“”(“所有星星中最美的”,殘篇104,b1行),在殘篇132中她又用kála形容少女的美“”(我有一個美麗的孩子);在殘篇50中又用kalós形容男子外表的美和內在的美好。詩人阿爾基洛科斯(Archilochus)阿爾基洛科斯現存殘篇(196A段,第34行)中用kalê形容一個女子擁有“無暇的外表”(eidos)和“美麗的身體”(a kalón body):“”⑨。古希臘哀歌詩人彌涅墨斯(Mimnermus)在殘篇1中,他說:“誰能將美的人與無價值的事物放在一起呢?”(原文為:,[4]31此處參考Archibald Allen的意見將譯為worthless即“無價值的”)。他曾感嘆最美者(kállistos)隨著時光逝去而容顏逝去,青春是“愉快和美的”(,殘篇第3篇,第1行[4]51)。詩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他在詩中表達,“死于溫泉關戰役中的人的命運是美的”,這里的“美”可以理解為高尚;對于年輕的奧林匹克獲勝者特奧革奈特(Theognetus)來說,西蒙尼德斯認為他是看起來較美的(kalliston),而他的運動技巧則超越了他的外表;再如,說“這是一座美好的米蘭(kalós Milo)的美的(kalón)雕塑”。政治家、詩人索倫(Solon)Kállos不僅具有道德善的意義,有時也指太陽的能量:“”(索倫殘篇:Theognidea 933行)[5],太陽這個例子中,光輝是它最顯著的特征。索倫觀察到,一般怯懦的人比較善良,而kalós的人并不必具有好的外形。這里性格和外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哀歌體詩人提爾特奧斯(Tyrtaeus)建議說話美好、做事富于教養,也就是做正當的事。在戰斗前線犧牲是“美好的”(kalós,殘篇10第1行,引用自阿爾凱奧斯Alcauus殘篇400)可見,這里美與善是同義的。對他來說,美的(kalós)更偏于道德意義。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最好”()的獎勵是德性()。一個男人具有的最燦爛美好的青春,成為男人贊賞、女人愛慕的對象,是當他倒在戰爭的前線時(殘篇10第26-30行)。⑩挽歌體詩人忒奧格尼斯(Theognis)描述太陽神(Apollo)是不朽者中最美的(,忒奧格尼斯殘篇1第7行)。最正當的事就是最美的事,健康是最好的事(,殘篇1第255行)。
⑧此處原文及翻譯參考的是Sappho,Ifnot,Winter,FragmentsofSappho,trans. Anne Carson, Vintage Books. 2002。
⑨轉引自Archilochus 196A (West),Haverford College & Bryn MawrCollege,June(2012),http://www.aoidoi.org/poets/archil/Archilochus-196A-Aoidoi.pdf。
⑩轉引自GreekLyricPoetry, M.L.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24。
見洛布叢書古典網站:https://www.loebclassics.com/view/theognis-elegiac_poems/1999/pb_LCL258.211.xml?result=1&rskey=YbaOQm。

續表
William J. Slater,LexicontoPindar. Berlin. De Gruyter. 1969. 見perseus古典網站:http://www.perseus.tufts.edu/hopper/text?doc=Perseus:text:1999.04.0072
以上參見洛布古典叢書,希洛多德:《歷史》第四卷(全四卷),8-9章,哈佛大學出版社,1938年。(Herodotean,Herodotus,bookⅧ-Ⅸ, trans. A.D. Godle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經過前人對美的樸素思考,在柏拉圖哲學中,“美”才成為一個獨立的理性思辨概念進入了哲學視野,他也因此成為真正的美學意義上的開創者。柏拉圖從其“理式論”(Eidos)出發,堅持世間美的事物存在絕對的“美本身”,感性可見的美來源于超感性的永恒的美的理式。在《大希庇阿斯篇》中,他苦苦追問的是“美本身”(τò καλòν),堅持認為:“依靠美本身,美的事物才成為美的。”(《斐多篇》)[7]在《會飲篇》中他說:“這時他憑臨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觀照,心中起無限欣喜,于是孕育無量數的優美崇高的道理,得到豐富的哲學收獲。如此精力彌滿之后,他終于一旦豁然貫通唯一的涵蓋一切的學問,以美為對象的學問。”[8]而美對于他就如《斐德若篇》所說:“因為只有美才被規定為最能向感官顯現的,對感官來說,美是最可愛的。”[9]164海德格爾譯為:“但只有美才分得了這種命運[亦即在存在之照耀的本質秩序中],就是成為最能閃耀的、卻又最令人出神的東西。”[3]216這與歌德認為美乃是一種“原現象”(UrPh?nomen)含義基本相同。在柏拉圖哲學里,美的理式具有本體論的地位,與“存在”類似,是人類認識終極的歸宿和最高的境界,且與“光”有著本源的關聯,它深刻影響了中世紀基督教美學以及黑格爾、尼采及海德格爾的美學思想。

在柏拉圖筆下,名詞Kállos主要指人的美,尤其是直接表現外在的吸引力,而形容詞Kalós的含義寬泛一些,Kalós經常指事物的視覺表象,尤其是閃爍著光輝而對人產生吸引的事物,希臘城邦的保衛者、阿伽門農和阿基里斯,被認為是Kalós,對于男性使用Kállos加以修飾,指具有好的外表的青年人,如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伽倪墨德斯(Ganymede)及被黎明女神愛著的克利托斯(Clitus),奧德修斯的兒子忒勒瑪科斯(Telemachus),又如王子帕里斯和柏勒洛豐(Bellerophon),他們都對女性有著外表上的吸引力。拜占廷古典學者認識到,對于男子來說,Kállos和Kalós之間的區別大致在于前者略傾向于表達英俊、漂亮,而后者著重表達英雄般的氣概,而對女性而言,Kállos主要用來形容海倫和阿佛洛狄忒以及奧德賽的妻子珀涅羅珀(Penelope),作為形容詞的Kalós雖然也表達好看的外表,但并不與誘惑關聯緊密,它可以更寬泛地指一些物品,如戰車、盾牌、面包籃以及行為和聲音等。在柏拉圖的形而上學中,Kállos也可指精神的美或形式。在古希臘,Kállos的外延不僅指視覺和身體外表,而且在古典時期與語言相關。在《會飲》篇中,蘇格拉底說:“我承認,他的發言各個部分都挺精彩,特別到了快要結尾的時候,他的用詞尤其美妙(Kállos),使我們全都聽得入了迷。”[9]237但在之后,蘇格拉底又談到了身體的美(第210 A5-6行)與作為美本身的永恒的美(211 A1-3行)。這也為美學學科的哲學屬性作了界定。“再進一步,他應該學會把心靈美看得比形體美更為珍貴,如果遇見一個美的心靈,縱然他在形體上不美,也會愛上他,并且珍視這種愛情。他會期待著與這樣的心靈對話,加速養成自己高尚的品質。經過心靈之美,他會被進一步導向思考法律和體制之美。等他發現了各種美之間的聯系與貫通,那么他就會得出結論,形體之美并不是最重要的。”[9]253

三、美的后續流變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美”在古希臘的使用情況大致包括以下幾種:
一是廣義的美,從美的人,到美的物,發展到抽象的社會制度、靈魂、美德等,與善同義,但尚沒有用于自然風景。自然風景作為美的對象,在西方直到18世紀才開始出現。
二是人的美,尤其是涉及人的身體以及外在形式。可以看出,美學從其古希臘開端就具有人本主義傳統。

總體來看,現代美學意義上的“美”(以英語的beauty為例),與古希臘的Kállos本質區別在于,古希臘美的含義更為廣泛,不僅包括美的事物、形式、身體、人,也包括制度、法律以及靈魂與道德等。現代美學意義上的“美”可用于藝術作品,也關系到自然世界。而古希臘人通常不用Kállos去形容這種藝術作品及自然風景的美。在現代英語中,“beauty”更多地形容女人的美,男子則可用“handsome”(英俊)來表示,而Kállos可以用來形容男人、女人、男孩及女孩的身體、姿態、面容、外表等,“beauty”及“beautiful”往往不能用于修飾行為、慣例、美德等,而Kállos則適用,而繪畫、作曲、日落等可以用我們現在的詞語beautiful來表示。因此,我們可以看出,美(beauty)與Kállos是存在差異的,美(beauty及beautiful)主要用于感性領域,而Kállos、Kálos也可用于智慧、美德等領域,在這一用途上將其譯為“美”是有一定誤導作用的,與善、好基本同義。
古希臘藝術家與哲人對美的思考成為西方永恒的典范,在羅馬取代古希臘后,拉丁語“美”(pulcher,其異體為pulcer)也取代了古希臘的Kállos,主宰了羅馬時代及整個中世紀。經過文藝復興,伴隨著民族國家及民族語言的興起,由此派生出意大利語pulcro、葡萄牙語pulcro、西班牙語pulcro等,而由pulcher的同義詞bellus派生出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bello,法語的beau以及英語的beautiful等,而德語sch?n、俄語krassivyj、波蘭語piekny等則是由本國語言派生而來。
德國古典美學的奠基者康德顯然否定鮑姆嘉登將對美的批評性判斷納入理性原則之下從而建立美學學科的努力,因為他認為鮑姆嘉登的aesthetics其來源是感性的,而不是出自先驗理性原則。
眾所周知,黑格爾作為一個古希臘崇尚者,試圖以古希臘整體觀彌合現代性造成的一系列二元分裂,他的美學仍然從美的“理式”出發,基于概念的流動性與藝術發展的歷史性,發展出象征型、古典型與浪漫型三種藝術形態,古希臘古典型藝術為真正的藝術、美的藝術,古希臘宗教為美的宗教。他認為,伴隨著浪漫型藝術取代古典型藝術,真正的藝術和美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只在中世紀晚期(文藝復興時期,如拉斐爾等的繪畫)中留下一抹余暉。美學(the philosophy of fine art)的建立與“藝術的終結”是同步的過程。正如海德格爾所說:“在希臘人那里,惟當他們偉大的藝術以及與之同步的偉大的哲學走向終結之際,才有美學的發端。”[3]86而古典學者出身的尼采也認為:“沒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這一簡單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學,它是美學的第一真理。”[15]他們的美學充滿了對古希臘輝煌的藝術與美的崇敬與眷戀,由此凝結為一種對于古希臘的鄉愁意識。
古希臘尤其是柏拉圖對美與光之間關聯的強調,對于黑格爾“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尼采“日神”與“酒神”分別對應“美”與“真”等思想產生了深刻影響,也影響了海德格爾對美的思索。海德格爾通過向前蘇格拉底哲學思想的回溯,試圖克服自柏拉圖哲學肇始所建立的主體性法則,因而在他的美學思想中排除了人的美,他從古希臘女詩人薩福關于星星、月亮的美的詩句得到啟發,得出“顯現”(Schein,照耀)乃是月亮的顯現,從而與西方形而上學如尼采所說的“日神精神”形成區別,而與中國古典美學,尤其是道家美學有了深層次的相通。

四、結語
一門學科,只有扎根于傳統的深厚土壤之中才能茁壯成長。美學這門產生于西方思想傳統的學科,中國美學研究者要深入地研究美學,就必須對“美”這一概念的來源及發展做出一個清晰的認識與梳理。通過對古希臘作家、哲學家對美的用法與思考的探討,我們可以深入了解“美”在古希臘作家、哲學家文本中的使用情況,對于我們深刻把握美的含義及美學的產生與發展,理解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的美學思想,以及當代學者舒斯特曼的“身體美學”等種種美學思想,都有有益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