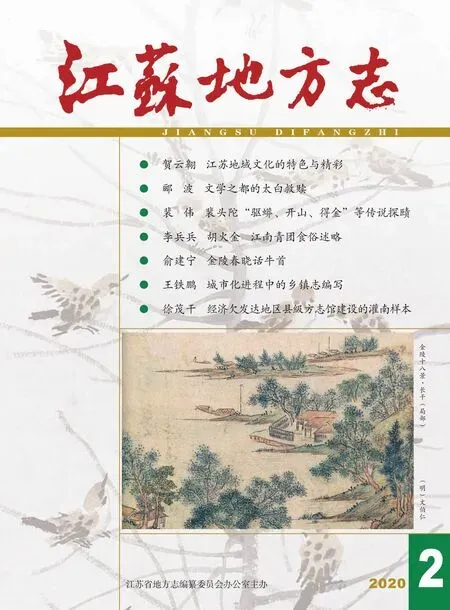江南青團食俗述略
◎ 李兵兵 胡火金
(蘇州大學歷史系,江蘇蘇州215006)
提 要:清明節前后吃青團在江南食俗文化中獨具特色,極強的時令性和祭祀功能讓青團在江南地區品目繁多的食物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與江南地區“不時不食”的飲食文化相契合。青團食俗至遲在明代嘉靖年間已經產生,至今綿延不衰,承載了深厚的文化內涵。

清明節前后吃青團是江南地區特有的一種食俗。江南青團食俗從誕生之時起延續至今,益發受到人們的喜愛,這與青團具備的中國飲食文化的某種意蘊相契合。青團既是寒食節的冷食,又是人們清明前后上墳祭祀的祭品,其文化意蘊同時包含了食俗文化與祭祀文化。另外,在青團食俗中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人與自然的交互。青團的時令性極強,只有在清明節前后食用才能獲得最佳口感。本文著意于厘清青團的源流,探索青團食俗背后的文化內涵,以期推動這一食俗的進一步發展。
一、青團的起源
關于青團起源的探討,目前未見真正有說服力、有價值的成果。有學者認為“‘青團’之稱大約始于唐代”[1]。還有學者根據《夢粱錄》的記載,認為南宋臨安的“三色粉團”是今青團的前身,“它是用米粉、青草汁拌和作團,加糯米粉和糖作餡心,但當時人們未給它定名為青團”,進而認為在南宋時期青團食俗業已形成,到了清朝將“三色粉團”便稱為“青團”[2]。其實,認為青團起源于唐朝或者宋朝,主要原因是將“粉團”錯認作“青團”。粉團可能很早就有了,唐代時粉團是端午節宮中普遍食用的節日小食,宮中還用粉團做游戲,“唐宮中每端五造粉團、角黍饤金盤中,纖妙可愛。以小小角弓架箭,射中粉團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3]。另外,《夢粱錄》記載的并非“三色粉團”,而是“五色水團”[4]。“水團”其實指的是湯圓。其做法為“秫粉包糖,香湯浴之”[5]。在宋代,湯圓不只是元宵節的節食,也是人們平常會吃的一種食物,“水團”“白團”都是其別稱[6]。這里記載的“五色水團”與后來有特指意義的青團顯然不同。《武林舊事》中確實提到了端午“彩團”:“大臣貴邸,均被細葛、香羅、蒲絲、艾朵、彩團、巧粽之賜。而外邸節物大率效尤焉。”[7]這里“彩團”也是端午節的一種小食,做法不得而知。至于記載中的“粉團”,則是沒有經過染色的。《了凡四訓》中記載:“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取即與之,無倦色;一仙化為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8]這日日相與的粉團,顯然不可能是時令性極強的青團。由此可知,將“青團”的出現時間定于唐朝或者宋朝都是不妥的。將“五色水團”“彩團”定為“青團”的前身更合適些。
關于青團的記載,最早出現在《七修類稿》和《嘉靖吳江縣志》中。明代郎瑛所著《七修類稿》在“饅頭青白團”一條中記載:“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之征孟獲,命以面包肉為人頭以祭,謂之蠻頭,今訛而為饅頭也。古人寒食采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而為青白團子,乃此義耳。”[9]郎瑛大約生于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卒年大約在隆慶年間,甚至萬歷初年,住處在杭州東城永昌門景隆觀附近。《七修類稿》全本的成書時間為隆慶元年(1567)[10]。而在田汝成在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告病回鄉后創作的《西湖游覽志余》中,關于時令節俗部分的記載并無青團[11],說明當時在杭州地區吃青團這一風俗并未形成。郎瑛記錄“饅頭青白團”一條的具體時間不得而知,但能夠作為《事物類》的一條,可以確定在他生活的年代,青白團子已經廣泛作為當地寒食節用于祭祀的祭品。據此,杭州地區青團食俗的形成可能是在嘉靖二十六年到隆慶元年之間。
《嘉靖吳江縣志》記載:“清明前兩日謂之寒食,人有新亡者,其家必倍悲痛,名新寒食。至歲則往祭其幾筵,俗呼排座。清明插柳滿檐,青蒨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言: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士女并出祭墓,俗呼上墳。排座上墳必用蛤蜊、蟛螖、角粽、青團諸品,牲醴隨宜。”[12]徐師曾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已完成該書除水利、武略之外的部分。[13]由此,可知,在嘉靖二十七年之前,在該地區青團已經出現,并用作上墳的祭品。另外,《弘治吳江志》記載:“寒食、清明日則插柳于檐,多做稠餳、冷粉團以祭墓。人有新亡者,值是日必倍悲痛,謂之‘新寒食’。迨春和景明之際,用樓舡載蕭鼓先至上方謁廟,然后以祭物為山水之游。”[14]此書于弘治元年(1488)才由知縣孫顯捐俸集資付梓。[15]也就是說直至弘治元年時吳江地區還沒有青團。由于粉團已經具有“祭墓”的功能,青團出現之后,便代替粉團繼承了這一祭祀功能。據此可確定吳江地區青團是在弘治元年至嘉靖二十七年之間出現并成為受人們歡迎的祭品和食物。青團最早出現可能是在吳江地區,杭州地區隨后出現。
青團的出現與青精飯(即后來的烏飯)的流行是分不開的。《真誥》載東漢龍伯高“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方”[16],霍山中學道者鄧伯元、王玄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17]“青方”或“青精石飯”是道教為修仙而服食的一種方劑,與節令無關,制此方劑要用到南燭,“取莖葉,搗碎,漬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暴,米粒緊小,正黑如瑿珠,袋盛之可適遠方……能行,取汁炊飯,名烏飯。”[18]在唐代,青精飯已經廣為人知。許多詩歌中提到了青精飯,其中陸龜蒙對青精飯記述甚夥,“舊聞香積金仙食,今見青精玉斧餐”[19],“青精飯熟云侵灶,白袎裘成雪濺窻”[20],“烏飯新炊藜藿香,道家齋日以為常”[21],從陸龜蒙的記載來看,江南地區青精飯也是非常盛行的。到了宋朝,青精飯成了浴佛節的齋食。《嘉泰吳興志》載:“《統記》云:‘夏至日,以南燭草染糯作烏飯,僧道尤高此食’。南燭草即今黑飯葉也。今俗四月八日造以供佛,因相饋送。”[22]葛勝仲在《丹陽集》中對浴佛節吃青精飯有所記載[23],可見佛道二家都將青精飯作為了齋食。另外,寒食節人們也吃青精飯,“楊柳葉,細冬青,居人遇寒食采其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干石飯。”[24]青精飯已進一步融入了時人的生活。明朝《大明會典》將烏飯納入了南京光祿寺“薦新”祭品之中[25]。
佛、道兩教對青精飯的推崇,以及青精飯在清明、寒食節成為節食,使人們大都熟知了青精飯的制作方法。而青團的制作方法為“抱青草為汁和粉作糕團,色如碧玉”[26],“以蔣麥汁染粉為青色”[27],“以米粉和艾汁制青團”[28],“取蓬蒿揉米粉作團”[29]。當我們對比一下青精飯與青團的制作方法,再考慮一下青精飯當時的流行程度,以及青精飯作為寒食節冷食的功能,便可知道青團的出現可能受到了青精飯的影響。明高濂《遵生八箋》:“用楊桐葉,并細葉、冬青葉,遇寒食,采其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道家謂之青精干食飯。今俗以夾麥青草搗汁,和糯米作青粉團,烏臼葉染烏飯作糕,是此遺意。”[30]郎瑛在《七修類稿》中的記載也持此說。《(嘉慶)直隸太倉州志》也記載道:“寒食節,搗穱麥葉汁溲米粉作團食,謂之青團子,即古青飯遺意。”[31]青團的出現受到了青精飯的啟發是有其合理性的,其制作理念、基本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相吻合,在粉團的基礎上,用穱麥葉、艾葉等搗汁溲米粉即成,只是取汁原料和染色對象發生了變化而已。
二、青團的分布
青團最早出現在吳江縣和杭州府,而同時期的其他方志中并未見到相關記載,可能當時只有這兩個地方將青團作為掃墓的祭品以及食用青團是比較流行的,因而被當時人記錄了下來。《(萬歷)杭州府志》記載:“清明,門檐遍插柳枝,亦戴于首。家各設奠祖先,出郭掃墓,以紙錢掛墓樹上,其米食用青白團子。”[32]
但是在明朝,青團出現的區域似乎并不大,較大范圍的出現是在清朝。《昌化縣志》(二十卷·清乾隆三十年刻本)載:“清明日,家插柳于檐端,亦戴于首。各具時饈墓祭,以楮前掛樹上,名曰‘掛錢’,取古孝子遺意。其米食用青白員子,盛者多設羊豕、盤核及鼓樂以侑,前后累日不絕。”《海寧縣志》(十三卷·清康熙十四年修、二十二年續修刻本)載:“清明日,插柳枝于檐戶,各祭祖塋,其米食用青白團子。”《古禾雜識》載:“寒食節,有青團灰粽。”[33]《(嘉慶)直隸太倉州志》載:“寒食節,搗穱麥葉汁溲米粉作團食,謂之青團子,即古青?飰遺意。”《昆新兩縣志》(四十卷·清道光六年刻本)載:“新喪未逾年者設箬葉粽(又名‘長粽’)及青團子(搗嫩草汁,入粉令青)以祭,新喪者亦然。”《景寧縣志》(十四卷·清同治十二年刻本)載:“清明,插柳于門,掃墓掛楮錢。食青螺。用蓬葉和米粉揉作團(俗呼蓬餣,即禁火遺意),祀先、饋戚皆用之。”《同治蘇州府志》(卷三風俗)載:“清明插桃柳枝于戶上,食青苧團。”《石門縣志》(十一卷·清光緒五年刻本)載:“清明,遍插柳于門檐或戴之首,各祀祖先,掃塋墓。……家制作青粉團供祀,分食之,亦古寒食遺意。”《平湖縣志》(二十五卷·清光緒十二年刻本)載:“清明,祀先祭墓,以青草汁揉粉作寒具,折竹插地掛紙球,曰‘標墓’。”《太平縣志》(十八卷·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載:“清明,采菁雜米為團,及做烏飯、£(餌)。門前插柳枝,小兒發辮中亦戴柳球。”《富陽縣志》(二十四卷·清光緒三十二年刻本)載:“寒食,不禁火,前后數日家家取蓬蒿揉米粉作團。”《浙江新志》(三卷·民國25年杭州正中書局鉛印本)載:“以米粉和艾汁制青團,曰‘清明團’。”從這些記載可清晰看出,青團的分布區域在清朝有了較大的擴展,現在的臺州、麗水的一些地區也出現了青團。不過,總體來看,青團的分布區域集中在蘇杭地區,而且呈點狀分布,并非一個區域所有下屬區域都是如此,這也體現出即使在比較小的范圍內也存在著風俗的差異化。青團進一步流布到其他地區要到民國以后。
三、青團食俗的盛行:自身特色與懷祖追遠
青團自明中后期產生以來便一直流行于江南地區,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上海每年在清明供應的青團總數達800多萬個,按市區常住人口計算,平均每人要吃一個多。”[34]近年來,隨著城市人口的進一步增加,青團的產量也隨之增長。關于食品添加劑亮藍能否用于青團的問題,衛生部給予了否定意見,“青團在GB2760食品分類系統中屬于糧食和糧食制品類別的米粉制品,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劑亮藍。”[35]能得如此關注,青團在當地飲食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由此也可見江南地區青團食俗盛行之一斑。一種食俗的形成不僅食物本身要獨具特色,也要符合當地人的某種精神需求,惟此才能獲得長久的生命力。
青團的特色在于制作原料、獨特的口感和審美感受。青團起初是作為一種冷食的。“清明,遍插柳于門檐或戴之首,各祀祖先,掃塋墓。……家制作青粉團供祀,分食之,亦古寒食遺意。”[36]這里“古寒食遺意”即指寒食節不生火、吃冷食這一由來已久的風俗,青團便是當時人們可選擇的冷食之一。寒食習俗的出現當在“介子推傳說”形成之后,是紀念介子推的方式逐漸演化的結果。寒食禁火吃冷食的習俗由來已久且影響深遠,青團又有極強的時令性,只能寒食清明前后來做,因而產生之后很自然便成為寒食節的一種冷食。
青團的時令性是由其制作原料決定的。如今我們可以吃到許多反季節蔬菜、水果,粽子、糍粑制作時間也非常隨意,但是青團還是保持在3月中旬到4月中旬上市,有極強的時令性,體現的是自然時序的約束,只有在這段時間,所采的艾葉或蔣麥葉等才剛好青嫩,榨出的汁才給人最清新的香味,從而造就青團“色澤碧綠,清香軟糯,甜而細膩”的美妙感受[37]。時間提前了,艾葉或蔣麥葉等還沒長好;時間一過,便又長老了,榨出的汁都有殘渣,沒了新鮮的味道,正所謂過時不候,這是人們長時間經驗的總結。現在即使可以冷凍儲存,但是口感上還是會差很多。人與自然的交互在這樣的時間段以青團為載體得以完成。就蘇州地區而言,“蘇幫菜”是極講究時令的,隨時節交替,菜色便生出許多變化。人們對青團的喜愛,也是這種“食隨時變”“不時不食”觀念影響的結果。
另外,蓬蒿、蔣麥葉、青草以及艾草都有一定的藥用功能,尤其是艾草,《證類本草》記載:“艾葉,味苦,微溫,無毒,主灸百病,可作煎,止下痢、吐血、下部瘡、婦人漏血,利陰氣,生肌肉,辟風寒,使人有子,一名冰臺,一名醫草。生田野,三月三日采,暴干作煎,勿令見風”[38]。《天臺山全志》載:“鳳凰山,在天臺縣東十里,《志要》云:‘山形似鳳者三,故其地亦名鳳林。崖上有仙人掌,跡甚鉅南有釣魚臺及呂洞賓所游之地,名為呂道岸,其地夏日蚊蠅不入,所產艾草入藥最佳’。”[39]現在研究也證明,“艾葉的主要化學成分為揮發油、黃酮、多糖、鞣酸、萜類及微量元素等,其藥理作用較廣,具有抗菌、抗病毒、抗氧化、保肝利膽、止血及抗凝血、抗過敏、免疫調節、抗癌等多種活性。對于艾葉的產品開發已涉及藥品、食品、保健品及生活用品等方面,但某些方面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入”[40]。藥食同源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個方面,食物的藥用功能深受人們關注,這樣的藥理作用為青團逐漸受到人們的追捧提供了一定的科學依據。
青團碧綠瑩潔的外表也頗惹人喜愛。綠色象征自然、清新、寧靜以及青春等,給人以希望。根據《嘉靖吳江縣志》中的記載,清明插柳滿檐,街巷之中綠意濃濃,給人舒適自然的感覺,這是人們的一種普遍感受,也表達了對“紅顏”常駐的期求。詩歌中人們經常表達對春天綠意盎然的喜愛之情,如“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等。綠色帶給人們的舒緩感受是非常獨特的,讓人沉浸其中,和諧自處。青團的碧綠外表在人們的色彩審美中無疑較其他食物是占了優勢。
青團除了作為一種時令食物供人們自食或贈送親朋好友之外,也是江南部分地區人家在家祭和上墳祭祀時所用祭品之一。《嘉靖吳江縣志》的記載顯示,以青團諸品上墳,祭祀結束后,分與眾人食用。現在,“家祭時,吳地人家必用的祭品之一是‘青團子’”[41]。在昆山周市鎮,“清明祭祖款客,一般都做青白兩種團子,飯后,大家小戶都上墳‘掃墓’‘掛墓’”[42]。在蘇州市吳中區,“清明節前后,有用草汁做的青團子和以糯米塞藕孔的焐熟藕上市,此為居民祭祀祖先之物”[43]。青團自出現以來,其祭祀功能一直保留至今。青團作為一種祭品,與我國古老的“薦新”習俗有關。“徐達源《吳門竹枝詞》云:相傳百五禁廚煙,紅藕青團各薦先。熟食安能通氣臭,家家燒筍又烹鮮。”[44]這里提到的“薦新”是將新收的或者新鮮的食物薦獻給神靈或者祖先的一種古老而又世代相延的禮儀,是中國古代祭祀祖先的一種常規祭祀活動。青團的時令性完美契合了“薦新”所需之物的要求,因而被賦予了懷祖追遠的文化內涵。對祖先的追思是人們普遍的精神寄托,“薦新”即是對此的一種表達方式。寒食或清明時節,人們都會上墳掃墓,“寒食時看郭外春,野人無處不傷神,平原累累添新冢,半是去年來哭人”[45]。青團承載了這樣深厚的文化內涵,更是讓人們在欣賞食用之余完成了一種精神寄托。
青團食俗發展至今愈加受到人們的喜愛,每到青團上市,人們都排隊爭相購買,足見此食俗生命力之強大。民俗的集體性是民俗的本質特征,“民俗文化不是個人行為,而是集體的心態、語言和行為模式。”[46]就青團食俗而言,青團的產生可能是個人行為,但形成一種民俗是人們集體的選擇,從中可以窺得人們的飲食習慣、審美傾向以及祭祀文化等。現在青團的祭祀功能已然弱化,但作為時令性極強的美食越發受到人們的追捧,這樣的趨勢也反映出現代人的飲食理念:清淡、綠色、健康。《衛生部關于食品添加劑亮藍不得用于青團的批復》中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讓青團保持其時令性,使其顏色為天然之色,是讓青團食俗健康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