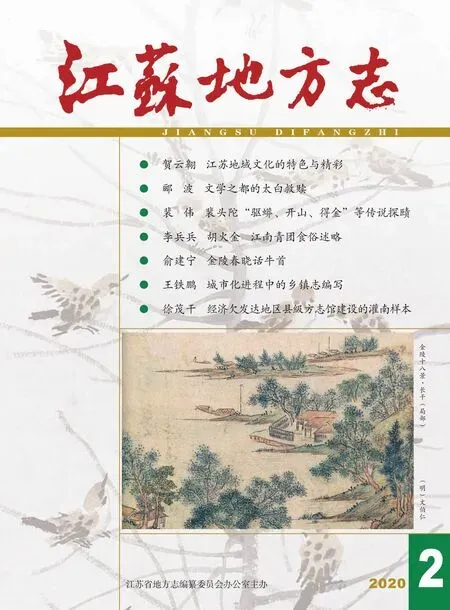文學(xué)之都的太白救贖
◎酈 波
(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南京210046)
2019年,南京榮獲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頒發(fā)的“世界文學(xué)之都”稱號(hào)。這是中國(guó)第一個(gè),迄今為止也是唯一的一個(gè)。當(dāng)時(shí)記者采訪我,我說(shuō)不僅作為現(xiàn)在的南京市民我很激動(dòng),我想曾經(jīng)的那些南京市民,比如說(shuō)謝安、謝玄、王導(dǎo)、顧愷之,包括李白、王安石,包括曹雪芹、湯顯祖,他們可能不是生于南京,卻和很多人一樣,從遠(yuǎn)方來(lái)到南京,可是在這個(gè)城市里,他們生活過(guò),他們高興、悲傷,他們傾吐心聲,他們留下傳世之作。
那些詩(shī)文、那些杰作,他們?cè)谶@里寫(xiě)就,無(wú)論是《牡丹亭》還是《紅樓夢(mèng)》,不僅是他們?nèi)松木融H,也是今天我們所有人在紅塵中心靈的救贖。比如說(shuō)李白,李白在南京完成了人生的救贖。
李白經(jīng)常來(lái)南京,寫(xiě)關(guān)于南京的詩(shī)。在他留下的所有的詩(shī)作中,關(guān)于南京的詩(shī)占據(jù)了將近十分之一。在所有李白的詩(shī)里有一個(gè)重大的主題叫“金陵懷古”,包括后來(lái)劉禹錫寫(xiě)的著名的“舊時(shí)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都屬于這一主題。
在李白所有詩(shī)中,《長(zhǎng)干行》是我個(gè)人最喜歡的一首詩(shī)。因?yàn)橛袃蓚€(gè)著名的成語(yǔ),來(lái)自這一首詩(shī),一個(gè)叫“青梅竹馬”,一個(gè)叫“兩小無(wú)猜”。
妾發(fā)初覆額,折花門(mén)前劇。郎騎竹馬來(lái),繞床弄青梅。同居長(zhǎng)干里,兩小無(wú)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kāi)。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塵與灰。常存抱柱信,豈上望夫臺(tái)。十六君遠(yuǎn)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mén)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fēng)早。八月蝴蝶來(lái),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yù)將書(shū)報(bào)家。相迎不道遠(yuǎn),直至長(zhǎng)風(fēng)沙。
“郎騎竹馬來(lái),繞床弄青梅”,這兩句非常重要,不僅產(chǎn)生了兩個(gè)成語(yǔ),后來(lái)它對(duì)中國(guó)文化史產(chǎn)生的影響,直到今天還有紛爭(zhēng)。有關(guān)這個(gè)話題爭(zhēng)得最厲害,2007年、2008年“百家講壇”還比較火的時(shí)候,當(dāng)時(shí)有一個(gè)新聞,就因?yàn)樵?shī)中的一個(gè)字“床”,但不是因?yàn)檫@首詩(shī),而是李白寫(xiě)的另外一首詩(shī)《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床”作為生活器具我們太熟悉了,但是,詩(shī)中的“床”是不是我們現(xiàn)在所理解的床呢?這是一個(gè)很值得探討的問(wèn)題。
在六朝時(shí)期就有這樣一個(gè)典故: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shí)。遇桓于岸上過(guò),王在船中,客有識(shí)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shí)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chē),踞胡床,為作三調(diào)。弄畢,便上車(chē)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說(shuō)新語(yǔ)》)
王徽之應(yīng)召赴京師,行舟停泊在青溪側(cè)。桓伊與王徽之素不相識(shí)。桓伊從岸上路過(guò),舟中客人稱桓伊乳名道:“此人就是桓野王。”王徽之便叫人上岸對(duì)桓伊說(shuō):“聽(tīng)說(shuō)足下善于吹笛,請(qǐng)?jiān)嚍槲掖狄磺!被敢廉?dāng)時(shí)已經(jīng)顯貴,也曾聞知王徽之的聲名,便默默下車(chē),坐在交椅上,為王徽之吹奏三調(diào),吹罷,便起身上車(chē)離去,主客之間一句話也未交談。而桓伊當(dāng)時(shí)吹奏的就是《梅花三弄》。
桓伊下車(chē)取的床,是像“小馬扎”一樣的坐具,通過(guò)研究,古人把支撐的器具叫做床,睡覺(jué)是支撐,叫床,我們這里的坐具是支撐,也叫床。
那么,李白當(dāng)時(shí)深秋的夜晚,看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這個(gè)床,又是什么床呢?這就要從另一個(gè)詞說(shuō)起“背井離鄉(xiāng)”,古時(shí)候我們有一個(gè)詞,叫“井床(指井欄)”。
如果是在屋子里的月光照進(jìn)來(lái),怎么會(huì)疑是地上霜呢?只有在院子里,尤其是深秋時(shí)節(jié),再加上井欄又是銀色的,所以他才會(huì)在院子里疑是地上霜。更重要的,因?yàn)檫@個(gè)井還代表了一種背井離鄉(xiāng),所以他才會(huì)“低頭思故鄉(xiāng)”。
所以,“郎騎竹馬來(lái),繞床弄青梅”,是什么景象?是一對(duì)三四歲的小男孩小女孩,拿著竹棍,兩個(gè)人在井欄上奮力地打著青梅樹(shù)。當(dāng)時(shí)小女孩站在他身邊,看著小哥哥的臉的那一刻,這一幕畫(huà)面成為小姑娘一生永恒的記憶。
《長(zhǎng)干行》這首詩(shī)對(duì)商婦的各個(gè)生活階段,通過(guò)生動(dòng)具體的生活側(cè)面的描繪,在讀者面前展開(kāi)了一幅幅鮮明生動(dòng)的畫(huà)面。詩(shī)人通過(guò)運(yùn)用形象,進(jìn)行典型的概括,開(kāi)頭的六句,宛若一組民間孩童嬉戲的風(fēng)情畫(huà)卷。“十四為君婦”以下八句,又通過(guò)心理描寫(xiě)生動(dòng)細(xì)膩地描繪了小新娘出嫁后的新婚生活。在接下來(lái)的詩(shī)句中,更以濃重的筆墨描寫(xiě)閨中少婦的離別愁緒,詩(shī)情到此形成了鮮明轉(zhuǎn)折。“門(mén)前遲行跡”以下八句,通過(guò)節(jié)氣變化和不同景物的描寫(xiě),將一個(gè)思念遠(yuǎn)行丈夫的少婦形象,鮮明地躍然于紙上。最后兩句則透露了李白特有的浪漫主義色彩。這闋詩(shī)的不少細(xì)節(jié)描寫(xiě)是很突出而富于藝術(shù)效果的。如“妾發(fā)初覆額”以下幾句,寫(xiě)男女兒童天真無(wú)邪的游戲動(dòng)作,活潑可愛(ài)。“青梅竹馬”成為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語(yǔ)。又如“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寫(xiě)女子初結(jié)婚時(shí)的羞怯,非常細(xì)膩真切。詩(shī)人注意到表現(xiàn)女子不同階段心理狀態(tài)的變化,而沒(méi)有作簡(jiǎn)單化的處理。再如“門(mén)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八月蝴蝶來(lái),雙飛西園草”,通過(guò)具體的景物描寫(xiě),展示了思婦內(nèi)心世界深邃的感情活動(dòng),深刻動(dòng)人。
從漢到魏晉到唐,很多人寫(xiě)長(zhǎng)干行,李白之前公認(rèn)寫(xiě)《長(zhǎng)干行》第一的是誰(shuí)呢?是崔顥。
崔顥的“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wèn),或恐是同鄉(xiāng)”也是非常的著名。但是李白寫(xiě)完《長(zhǎng)干行》以后,成為當(dāng)時(shí)以及后世公認(rèn)的第一。我們還可以把崔顥和李白的另外兩首詩(shī)作為對(duì)比。一個(gè)是崔顥的《黃鶴樓》,還有就是李白的《登金陵鳳凰臺(tái)》
李白第一次登臨黃鶴樓時(shí),本來(lái)是滿腔詩(shī)緒要抒發(fā)的,但看到崔顥的《黃鶴樓》之后,被崔顥的詩(shī)給壓服了,于是說(shuō):“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shī)在上頭”。僅憑這兩句我們可以推斷,李白當(dāng)時(shí)心里是服氣的。
但不久,李白就不服氣,寫(xiě)了一首詩(shī),詩(shī)名《鸚鵡洲》,全詩(shī)是:“鸚鵡來(lái)過(guò)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shù)何青青。煙開(kāi)蘭葉香風(fēng)暖,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shí)徒極目,長(zhǎng)洲孤月向誰(shuí)明。”顯然,這時(shí)候的李白還太年輕,盡管他在心里已經(jīng)存著跟崔顥比高低的心,盡管他極盡遣詞造句之能事,任憑他窮盡創(chuàng)作手段,但這首詩(shī),顯然要比崔詩(shī)弱一些,氣量、格局都弱了許多。
過(guò)了若干年之后,李白再次南游金陵,此時(shí)的李白在盛唐的社會(huì)背景之下,已經(jīng)接觸到了悲涼丑惡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在沉浮起落之間已有相當(dāng)深厚的生活閱歷,也由此產(chǎn)生了只有經(jīng)歷了滄桑才會(huì)生出的人生思考。于是,他終于寫(xiě)出了“總為浮云能蔽日,長(zhǎng)安不見(jiàn)使人愁”的千古名句。這是真真正正跟崔顥的“較量”,僅以最后兩句來(lái)衡量,似乎比“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還要高明一些。
這時(shí)的李白,已經(jīng)從游俠少年變成了詩(shī)歌名家,他已歷經(jīng)歲月的淘洗,歷盡命運(yùn)的坎坷,登上過(guò)朝堂,流落過(guò)江湖,李白很少寫(xiě)律詩(shī),而《登金陵鳳凰臺(tái)》卻是唐代律詩(shī)中膾炙人口的杰作。
比較《黃鶴樓》與《登金陵鳳凰臺(tái)》兩首詩(shī),崔顥寫(xiě)出了一種深情,可是李白卻寫(xiě)出了一種不朽——雖然他在人生窮途末路之際,在人生孤家寡人之際,在當(dāng)時(shí)的金陵晚年蕭索之際,在人生什么都沒(méi)有的時(shí)候,他撿起心中不放棄的一種精神,在鳳凰臺(tái)上流出“總為浮云能蔽日,長(zhǎng)安不見(jiàn)使人愁”的時(shí)候,李白不就是在南京完成了他的人生救贖嗎?
我好想站在鳳凰臺(tái)上,站在李白的身邊,站在賞心亭上,站在辛棄疾的身邊,去見(jiàn)證一個(gè)歷史時(shí)刻,見(jiàn)證一種平凡生命的偉大不朽。雖然時(shí)光不能穿越,可是我們可以通過(guò)詩(shī)詞、通過(guò)文學(xué)、通過(guò)藝術(shù)給予我們現(xiàn)實(shí)紅塵中最后溫暖的角落,溫暖每一個(gè)人的心靈,去穿越去守候,在這座城市去見(jiàn)證救贖,同時(shí)也是完成了我們每個(gè)人平凡生命的抒寫(xiě)與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