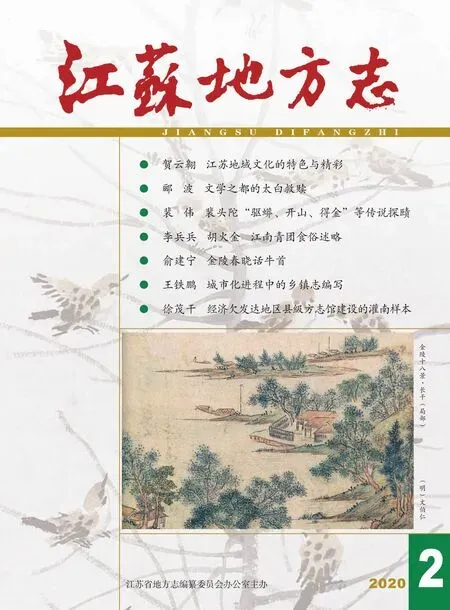清末民初南京地區的水災、兵災、疫災
◎經盛鴻
(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江蘇南京210097)
提 要:近代以來,由于長江上游地區生態平衡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長江下游包括南京地區在清道光年間連續遭遇特大水災,數年的災荒以及由此造成的災民遍地、民變四起、社會動蕩,為太平軍進入南京并在長江流域地區迅猛發展提供了條件。太平天國戰爭時期,南京地區成為清軍與太平軍激烈戰爭的最重要戰場,長期的戰爭給南京人民帶來多次可怕的疫災,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戰爭后期,攻入南京的湘軍對太平軍與南京人民殘酷的屠殺與劫掠焚燒造成“兵災”,給南京留下巨大創傷,歷經數十年未能恢復。1913年,北洋軍在鎮壓孫中山、黃興領導的“二次革命”后,攻入南京,南京再次遭到浩劫。這些水災、兵災與疫災,對南京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與近代化進程造成慘重的破壞。
清末民初,南京從清政府的兩江總督衙門所在地,先后成為太平天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首都所在地,時間長達數十年,地位更形重要,成為全國名列前茅的大都市之一。同時,在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斷加劇的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尤其是嚴重的水災、兵災與疫災,對南京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與近代化進程造成慘重的破壞,給南京人民帶來極大的災難與痛苦。
一、近代南京地區災害頻發的原因
南京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城市緊鄰長江,所轄區、縣分布于長江南北兩岸,自古以來就與長江水情有密切的關系。清代乾、嘉以前,長江上游兩岸山巖矗立,原始森林覆蓋嚴密,植被保存完好,水土流失現象難以發生,因而江水清澈,長江自宜昌出三峽以后,進入廣闊的中下游平原地區,水流比較平緩,兩岸有洞庭湖、洪湖、鄱陽湖等湖泊,吸納與調節水量,此時的長江不易發生水災,即使偶有發生,與北方幾乎連年泛濫的黃河相比,則是輕微的。南京更是水災較少,且不嚴重。據《中國歷史大洪水》一書記載,從明萬歷十一年(1583)到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258年間,長江流域僅發生兩次大水災。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以后,中國進入動蕩與多災多難的近代社會,長江中下游流域的災情迅速加劇,特別是水災更加嚴重。據《中國歷史大洪水》記載,自清朝道光二十一年(1841)到1949年的109年間,長江流域發生大水災9次,超過同一時期黃河重大災害性洪水的次數;至于范圍與危害較小的水災則次數更多。
長江中下游在近代以來水災增多的原因很多,除了天氣異常等自然因素外,人為破壞的社會因素則更為重要。
首先,明、清以降數百年來,長江流域生態平衡逐漸遭到日益嚴重的破壞。1644年清朝入關統治全國以后,歷經200多年的承平時期,人口激增,土地不足,大量移民進入人煙稀少的長江上游流域,開山毀林,開荒種地,安家落戶,破壞了大量植被,既削弱了上游水源的涵養功能,洪水無所阻擋,滾滾而下,洪峰不斷增大,又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使江水含沙量劇增,由清變渾,河床不斷墊高,河道逐漸淤升,在中下游部分江段形成高出兩岸陸地的“懸河”,迫使長江兩岸的護堤不斷加高,風險加劇。而在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官府與民眾為擴大耕地面積,大興圍湖筑圩造田,使洞庭湖、洪湖、鄱陽湖等大小湖泊面積日益縮小,失去吸納與調節長江水量的功能,堵塞了水路,使各河、湖不能順暢其流。到了鴉片戰爭以后更趨嚴重,引起的巨大危害日漸暴露。
對于此種人為破壞長江流域生態平衡而引起長江水患不斷加劇的情況,有識之士早有覺察。清初,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就指出,山地墾殖使“山谷泥沙盡入江流”,造成江河湖泊的淤積之狀。道光年間長期在南京擔任兩江總督的陶澍也指出:長江下游的水患,是“因上游川、陜、滇、黔等省開墾太多,無業游民到處伐山砍林,種植糧食,一遇暴雨,土石隨流而下,以至停淤接漲”[1]。鴉片戰爭時期的啟蒙思想家魏源更深刻地指出:“歷代以來,有河患無江患”,但到鴉片戰爭前后,長江水患卻日益加劇,“乃數十年中,告災不輟,漂田舍,浸城市,請賑緩征,無虛歲,幾與河防同患,何哉?”就是因為在長江上游大量移民盲目伐木墾荒,使得“泥沙隨雨盡下,故漢之石水斗泥,幾同濁河”;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官府與農民在江湖洲渚上大量筑圩墾田,“澤國盡成桑麻”。[2]他們的分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第二,中國君主專制社會在清朝到了末世,統治者日益腐敗,內政不修,官吏貪黷,經濟落后,生產力低下,水利荒蕪,控制、駕馭與利用自然的能力日益減弱,越來越被自然界的野性力量所壓服與支配。近代著名思想家薛福成揭露清代“河工”(水利工程)的官場黑幕,說:“每歲經費銀數百萬兩,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應酬、過客游士之余潤……”[2]孫中山更尖銳地指出:“中國所有一切的災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統的貪污。這種貪污是產生饑荒、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3]
而從晚清鴉片戰爭的爆發到民國初期孫中山領導“二次革命”失敗的70余年間,中國人民在飽受清朝和北洋軍閥統治壓迫之時,屢遭外國侵略與蹂躪,各種自然災害和人為災害更加頻繁與慘重。南京地區地處長江之濱,控扼南北東西交通要沖,作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和軍事戰略重鎮,更是成為長江流域乃至全國遭受各種災害最嚴重的地區,多次遭受嚴重的洪水侵害以及戰爭與瘟疫等人為災難。
二、鴉片戰爭后南京連續三年的大水災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在南京與英國侵略軍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古城南京蒙受巨大的恥辱。與此同時,以洪水為代表的自然災害接連向南京肆虐。1840年、1841年與1843年,南京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水災,其中一年甚至江潮短期涌灌入城,但造成的災害尚不重。1848年至1850年,即道光皇帝統治的最后三年,東南各省與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連續發生特大水災。
道光二十八年(1848),長江中下游流域的蘇、皖、浙、鄂、贛、湘六省及豫、魯兩省,發生大面積水災,史稱“東南八省之水”,以江蘇災情尤為嚴重。此年夏間,連降暴雨,長江盛漲,加之海潮洶涌上托,高達丈余,使蘇南、蘇北地區圩破堤塌,遍地皆水,南京受害最深。時人姚瑩(桐城派大師姚鼐之孫)記載說:“道光二十八年七月,霖雨,湖南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濱江海諸郡縣患水……而江寧被水尤甚。”[4]《上元江寧兩縣志》記載:“道光戊申大水,金鰲家桐樹灣門扉不沒者只三板,人無過問者。”洪水進入南京城,居民家的門扉已大半淹沒,大街上可行船。當時在北京做官的儀征人張集馨接到家信后,記道:“接南中家信,金陵、儀征一帶,居民皆架木棲止。余家天安橋宅亦復水深數尺,哀鴻遍野,百姓其魚。”[5]直到第二年(1849年)春,姚瑩來到南京,仍處處看到、聽到前一年南京水災的慘痛遺跡:“見城中門扉水跡三四尺不等,咸相告曰:某某市中以船行也。”[6]
1848年水災給南京與江蘇各地民眾帶來沉重的經濟困難。據次年上任江蘇巡撫的傅繩勛在1849年四月給朝廷的奏章中所說:“上年江海湖河并漲,各壩齊開,江(寧府)、淮(安府)、揚(州府)、常(州府)等屬,被災地方較廣,商販稀少,糧價日增。”[7]
1849年,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生更加嚴重的三江(江蘇、浙江、江西)、兩湖(湖南、湖北)與安徽大水災。長江暴漲,破堤淹沒兩岸城鄉。當時人記載:“己酉,江水泛漲……沿江飄胳如麻……”[8]南京與蘇南的水災災情超過蘇北,在南京地區,“江寧省城已在巨浸之中”[9],而且時間長達數月之久。南京城南夫子廟旁的貢院,水深三四尺,導致原定農歷八月舉行的科舉鄉試被迫展期舉行;城中的兩江總督衙門(今長江路“總統府”所在地)也有一二尺深的積水;糖坊橋一帶平地“水深三尺”,許多居民被迫舉家遷居到鐘山、清涼山上。
關于此年南京大水災,當時人留下生動而凄慘的記載。姚瑩《江寧府城水災記》寫道:“閏四月,久雨不已。五月,復大水,阛阓深六七尺,城內自山阜外,鮮不乘船者,官署民舍胥在水中,舟行刺篙于人屋脊,野外田廬更不可問矣……連年船行市上。”南京著名的地方文化人士陳作霖在其所著《炳燭里談》中寫道:“道光己酉,金陵水災為數百年所未有,通城行船。東花園、王府園等處,水逾屋脊者數尺。船行其間,為水中樹枝所掛,輒至覆。”魏源則在《江南吟》一詩中,用沉痛的語言描述了南京的水災慘景:“江潮挾淮城倒灌,一閘難回萬馬奔。城南移家走城北,月華照城如澤國。船撐橋頂雞棲樹,父老百年未傳說。一歲潦尚可,歲歲淹殺我。南北六朝都江左,幾見金陵之城水中坐?”1850年,江蘇許多地方包括南京,仍有水災,雖較上年為輕,但造成很大損失。
連續數年的災荒使南京地區與江蘇南北各地“民情困苦異常”,農村不斷發生“搶大戶”“借荒”等群眾自發斗爭,社會動蕩不安,為太平天國起義軍進入南京并在長江流域地區迅猛發展提供了條件。
三、戰禍、疫災與湘軍、北洋軍血洗南京
1853年初,太平天國起義軍沿長江而下,經過戰斗,攻入南京并在此建立政權,向全國進軍。清政府先后調重兵圍攻南京。南京地區成為清軍與太平軍激烈戰爭的最重要戰場。長期的戰爭給南京民眾帶來多次可怕的疫災,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太平天國戰爭
1853年3月,太平軍攻入南京。接著,清軍在孝陵衛建江南大營,在揚州城外建江北大營,包圍南京地區,與太平軍多次作戰。南京城四周山野間,到處裸露著大量的雙方陣亡官兵與牲畜的尸體,來不及掩埋,恰又遇上“天大旱,赤地千里”,很快造成“疫氣流行”,各種傳染病在城內外迅速傳播,使得太平軍與清軍官兵以及南京當地百姓大量感染,“均多死者”。[10]
十余年間,南京地區的戰爭綿延而激烈,并在1860年、1862年、1863年、1864年多次發生瘟疫。同治元年(1862),曾國藩的湘軍對南京形成合圍之勢時,湘軍官兵染瘟疫而死者眾多,“秋八月,江南大疫,南京軍中尤甚,死者山積”[11]。“溧水大疫,時寇亂方劇,民皆乏食,死者無算”[12]。軍營中人員集聚,生活衛生條件更差,最易感染瘟疫。同年曾國藩奏稱:“大江南岸各軍,疾疫盛行。……近日秋氣已深,而疫病未息。寧國所屬境內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師及上海各軍,亦皆繁興,死亡相繼。”[13]曾國藩后來記述湘軍在南京城下遭受疫災情形,說:“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殕……”[14]官兵的大量染疾與死亡,影響軍隊的戰斗力和軍事部署的順利實施。曾國藩在奏折中說:這年七八月間,“金陵賊匪未撲官軍營盤,曾國荃因營中病勇過多,亦未進攻”[15]。他無可奈何地感嘆:“今歲夏秋以來,疾疫大作。昔時勁旅,頓變孱軍。”[16]湘軍如此,太平軍與南京民眾感染疫病的嚴重情形就可想而知。當時清廷在對相關奏折的答復中,就指出:“至天災流行,必無偏及,各營將士,既當其阨,賊中豈能獨無傳染?”[17]確實,在這一年,太平軍中同樣疫癘流行。
與疫災相比,清政府官兵對太平軍與南京民眾殘酷的屠殺與劫掠焚燒造成的 “兵災”更為可怕。
太平軍初入南京時,軍紀嚴明,“并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18],但圍剿太平軍、包圍南京的清政府軍隊,抱著對起義軍民的強烈仇恨,在曾國藩發出的“雖使周孔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19]的號召下,對南京太平軍與民眾進行長期殘酷野蠻的燒殺搶掠,他們打勝仗時這樣,打敗仗時也是如此。咸豐十年(1860)四、五月間,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從南京東進,一直打到上海郊區。戰敗的清軍自南京東郊向東潰敗時,對沿途的民眾燒殺搶掠,形成所謂的“庚申之難”。家住南京東郊江寧縣的一個名叫李圭的士紳,憤恨地寫道:“至官軍一面,則潰敗后之虜掠,或戰勝后之焚殺,尤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其慘毒實較‘賊’又有過之無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20]湘軍在1864年7月19日攻破南京后,對全城進行血洗屠殺。據曾國藩向清廷上奏所說:湘軍攻入南京后,“……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21]被湘軍殺死的,絕大多數是南京本地的民眾,其中又多是老弱婦幼。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當時隨湘軍入城,他在日記中記載:“老弱本地人民……盡遭殺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余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于四遠。其亂如此,可為發指。”[22]湘軍蕭孚泗等部在劫掠天王府、忠王府等地后,“取出金銀不貲,即縱火燒屋以滅跡。”[23]結果,“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24],壯麗的古城南京經此浩劫,變成了一片瓦礫。一年后,到南京就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所看到的是:“金陵一座空城,四圍荒田,善后無從著手……實則無屋、無人、無錢。管、葛居此,亦當束手……似須百年方冀復歸也。”[25]李鴻章的友人竟勸他將兩江總督衙門移往揚州。

晚清的流民一家
經此浩劫,南京城居民銳減。到1867年,朝天宮以北的南京廣大地區,“極目百里,不復見一民一物,惟瓦礫滿前,荊榛塞道,天陰鬼哭,正不待夕陽時也”[26]。20年后,南京所轄各郊縣,耕地仍有一半以上荒蕪。1882年2月,左宗棠到南京就任兩江總督,他描繪當時的南京:“江南克服廿年,而城邑蕭條,四野不辟,劫竊之案頻聞。金陵向非貿易埠頭,人煙寥落,近則破瓦頹垣,蒿萊滿目,雖非荒歉之年,而待賑者恒至二萬數千之多,較之四十年前光景,判若霄壤。”[27]1897年,距湘軍屠城已30多年,湖南的維新志士譚嗣同因任江蘇候補知府來到南京,他見到的南京仍是一片破敗凄慘景象。他氣憤地寫道:“頃來南京,見滿地荒寒氣象。本地人言……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于湘軍,而金陵遂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28]湘軍洗劫南京,給南京留下巨大創傷,歷經數十年未能恢復。然而舊傷未平,新傷又起。1913年9月2日,袁世凱部北洋軍在鎮壓孫中山、黃興領導的“二次革命”后,攻入南京,各部按照其長官們大掠三日的許諾,立即劃分地盤,肆意進行搶劫、殺戮、奸淫、焚燒,連續三天。據上海《時報》報道:“北軍進城后,即肆行淫掠,幾乎無兵不搶。馮國璋兵在下關搶,雷震春兵在南門搶,張勛兵在太平門搶。馮國璋且在下關縱火焚燒,全埠化為焦土”;北洋軍“搶掠后所有贓物皆運往浦口,由火車直運天津、北京或運至上海矣”;劫掠后的南京,“被劫一空,雖家具什物,亦搬運全盡。各等人民皆體無完衣,家無一餐之糧”[29]。三日后,北洋軍稱有軍令到,嚴禁擾民,違令者斬。此時,南京全城居戶已經十室九空,省行政公署瞻園內,死人倚樹,軍馬倒地,到處血跡斑斑。所有婦女人等,或死或逃,掠無可掠,淫無可淫,自然應令即止。據事后江蘇省警察廳調查核定,南京兵燹,共使商民4萬余戶受損,價值高達1600萬銀元。
北洋軍在南京燒殺淫掠時,南京城內的美國傳教士、鼓樓醫院院長馬林(William E. Macklin)、金陵大學校監韋理生(William F.Wilson)與其夫人、金陵中學任教的Mary Rowley,以及寶珍三、夏偉師等西方人士,一起救護和幫助了許多的中國難民。由于教會學校與醫院中有許多外籍人士,北洋軍有所顧忌,因此成為難民的聚集地。“各教會雖有兵士入內,概未擾及,各教堂及各醫院均改作留養婦孺之所,避難金陵大學者數逾千人,圣經學校亦有六七百人,鼓樓紅十字會醫院,庭無隙地,蓋近段居民皆逃入,以求庇護也,各醫院避難者亦為人滿,皆席坐露宿,家中雖有巨廈,不愿居也,西人亦均竭力保護婦孺,每一宅內概容留五六十人不等”[30],文中提到的“鼓樓紅十字會醫院”,即金陵大學附屬醫院,南京民間俗稱鼓樓醫院,當時被紅十字會借用;此時金陵大學校址是現在的金陵中學,校區面積有限,收留千余名難民,亦屬難能可貴;“圣經學校”是指金陵神學院。1913年11月,金陵大學校刊《金陵光》第4卷第6期,刊登此次難民救助活動的親歷者侯寶璋的文章《二次革命聲中之金陵大學》,比較完整地記述了金陵大學在南京陷落后救助難民的情況,原文如下:
避難:自二次宣布獨立,徐州戰爭,消息不佳,寧人以孤城可危,將被兵禍,故避居本校者,絡繹不絕。
停課:本校洪、陳諸君,曾開夏日學以餉學者,一時俊秀之士,負笈來游者,實繁有徒,嗣以徐州失敗,張軍進逼,學生恐兵禍將及,乃相率歸家,學校亦因之停課。
人滿:張軍進逼,炮聲隆隆徹晝夜,城軍無糧,岌岌不支,人心乃大亂,于是避于本校者益眾,校中所有各房皆滿,且有臥于地上者,有坐以待旦者,蓋是時已達千二百人矣,本校以擁擠難容,恐有礙衛生,乃禁止續入,門前萬頭攢動,幾欲破門而入,司閽者竟不敢啟閽,有本校學員友人劉、董二君立待竟日,卒不得入。
調查:人多易雜,洪君乃訂立章程,以為范圍(如夜間不準外出,禁止燈火等條)。而又恐宵小間入,乃制出入憑證,凡已入本校者,人給一張,有此方得出入……
匿名書:當二十八夜十一句鐘時,忽有匿名書由墻外傳入,大意謂本軍隊無糧難支,聞貴校儲財甚多,望借用一二,其早籌出,免致臨時動手云云,比時人已喪膽,哪堪更聞是語。及夜深,而槍聲又大作于四周,難人心膽俱裂,竟有膝行入禮堂地道下者,其居房中者,已呆若木雞,惟坐聽天命而已,次日難民中之有聲望者,聯名請兵保護,司令部乃發兵一隊于前門,以資防守……
絕糧:當馮、張諸軍未入之先,避難者亦不過以饘食充饑已耳,而猶系千辛萬苦,自外間送來者也,比兵已入城,其留于家者皆逃匿無余,堂中又無宿糧,人盡饑,計不得食者凡二日,其苦可想見矣。
雨絕:天氣酷熱,難人需水孔多,堂中僅有三井,即不旱而水亦不豐,況又月余未雨,以此三井均涸,日惟乘隙外出,取水一二次,以資飲焉。
巷戰:張軍入城,本堂附近各處,如北門橋等街,皆有兩軍互相搏擊,槍聲如施連珠炮,竟日始息。該時適有東洋人某,由城南赴該領事署,取道本校門首,為張軍所見,乃發槍射擊,死其一,其他則由五臺山后繞道,至該領事署始免。蓋倭人與我,原系同種,張軍以為漢人而西裝者,故殘之。倭人被殘后,張軍乃群集門首,欲斬關而入,難者聞此,驚駭萬狀,不知命在何時也,嗣由本校監學韋理生君,親至門首,謂此系美國學堂,幸勿攔入等語,始各行散去,然亦險矣。
彈裂:當時城軍猶未盡出,仍于虎山施彈,本校適當戰線內,其險何如,午時,倏有一彈落校舍外,入地約尺許,隆然一聲,塵土紛飛,地為之震,難者心驚膽悸,莫知所措,以為不死于兵,亦將死于彈也,正亡魂間,又有一彈,瞥如飛鳥,自西南來,沖空氣作嗤嗤聲,越二校舍而射至墻外,崩然大聲以裂……
攝影:寧垣秩序稍整,難者乃同拍一照,以志不忘。
展期:平定后,本校乃遍請避難者歸家,以將開課也,嗣以避難者之請緩,不肯重違其意,姑展限半月,然外間搶掠一空,其中戶而變為赤貧者,不知凡幾,當軸者若無善后之法,將見餓殍載途,不知伊于胡底,本校乃頒面以赤貧者,自此餓者得食,而秩序又為之一變矣。
贈匾:難者盡出校后,復同贈一匾,上顏“慈云普護”四字,以垂紀念。
開師范:此次受難,惟文人為最苦,蓋家既被搶一空,而事業又難圖,本校蒲洛克君有(鑒于)此,特開師范專科于陶園,并每月津貼學者三元,以作零用,才士聯袂而來,除甄別外,計得八十一士,可謂盛矣。
文中還寫道:“繼又得上海紅十字會函,謂有輪舟一艘來寧,專載無依之難民及老弱不能自衛者赴申,其健者留焉。”這是指上海紅十字會租用“大通號”輪船,兩次到南京,運送難民及傷員3000余人,到上海救治。
一部中國近代史,是中國人民不斷蒙受災難與恥辱的歷史,但同時也是中國人民英勇奮斗、前赴后繼,與各種災害作斗爭并最終取得勝利、走向民主、繁榮與近代化的歷史。南京地區的近代史也是這樣。難忘的1949年4月23日,南京人民終于擺脫了漫漫長夜,迎來了她光輝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