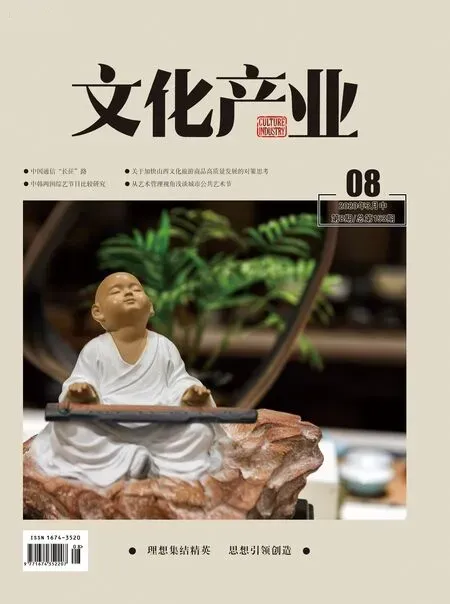淺析抗戰時期《野草》在桂林的成長要素
◎萬玉琴
(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紀念館 廣西 桂林 541001)
1940年8月20日,《野草》在桂林創刊,它是抗戰時期中國國內占有重要地位的左翼文藝月刊,刊物的編輯主要有夏衍、秦似、宋云彬、孟超、聶紺弩等人。從第3卷第一期起(1941年9月15日),增設國外版總經銷。《野草》在桂林發行近三年,共出版了五卷二十九期。1943年6月,國民黨政府以“節省紙張”為借口強制停刊;1946年10月1日在香港復刊,歷時兩年,共出十二期。
《野草》文風短小精悍,筆調明快犀利,深刻反映了抗戰前后中國的真實面貌。由于它針砭時弊,非常富有戰斗性,成為當時全國僅有的一份以雜文為主的文藝月刊。筆者從《野草》成長所不可缺的幾個方面:現實需要、人力資源和內容的繼承與發展三個方面進行挖掘和闡述。
一、《野草》創辦是民族斗爭形勢的迫切要求
1940年,法西斯氣焰囂張,汪精衛投降日本,國內輿論萬馬齊喑,充滿悲觀論調。這時一大批進步文化人士站了出來成為先遣隊,大力宣傳反法西斯主義,反投降、反分裂;他們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宣傳團結、進步,堅持抗日的呼聲此起彼伏,極大激勵了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夏衍時任《救亡日報》主編,雜文高手聶紺弩時任《力報》副刊主編。由于雜文篇幅可長可短、文字可深可淺,引古論今,可隱晦、可鮮明,容易引發讀者共鳴。在抗戰總體形勢尚未明朗,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尚未對日正式宣戰的情況下,國內新聞審查還頗為嚴格,即便桂系大本營也不敢隨意作仗馬之鳴。雜文的文體,頗為適合當時的時局,所以撰寫雜文的文學前輩非常之多,熱愛雜文的讀者也不少。作家們努力發揮著雜文的戰斗力和投槍匕首作用。
在特定時期、特定環境中,雜文的大量出現和被接受、被喜好,是當時抗戰時局的需要,是民族革命斗爭形勢的迫切要求。面對時局變化和形勢需要,作家秦似和孟超均向夏衍提出了創辦一份以雜文為專刊的建議。在夏衍的邀請下,秦似來到桂林,經過對文化環境的考察,發現當時文化市場新鮮活潑的文章極少,不能滿足市場和人們的需要,當時的文化產品可以說是百廢待興,于是有了創刊雜文的設想,并且是要傳承魯迅風的那種有戰斗力的雜文。對于聶紺弩來說,雖然《力報》的副刊《新墾地》比較受觀眾喜愛,但新聞性、時效性比較強,故對于文字的內涵深度無法深度挖掘,就算深度挖掘,讀者也未必充分閱讀領會,所以無法淋漓盡致地展現文學性。特別是夏衍,對文章有極強的洞察力,熱愛創新,喜歡有新意、活潑幽默的文字。秦似向夏衍提議想辦一個專刊短文的雜文雜志,要有戰斗力,能針砭時弊、議論時政,而且有新意。這個提議立馬得到了夏衍的贊同和支持。

《野草》
夏衍的《復刊私語》和秦似的《發刊詞》,潑辣尖銳、諷刺弊政、含義深邃,表達了在戰時背景下文人戰士們創刊《野草》的現實需求和強烈愿望。
二、“野草作家群”是思想一致的戰斗集體
《野草》創刊和存活,主要是憑借這一批大腕作者群體,巧妙規避國民黨新聞檢查,借助社會關系解決各種問題,再加上深入抗戰生活,下筆有神,倚馬可待,自然得到各方面重視。這群社會層次高、文學功底好、思想統一、團結進步、稿源穩定的作家群體,擎起雜志的大旗。在《野草》雜志上發表作品的重要作家被稱為“野草作家群”,最突出的代表是《野草》雜志的五個編輯:秦似、夏衍、宋云彬、聶紺弩和孟超。《野草》的作家群用文字和圖形進行著各種各樣的戰斗,運作《野草》雜志的定位和發行。善于戰略謀斷的秦似是提倡者,善于組織話題的夏衍是組織者,善于抒發胸中塊壘的聶紺弩是踐行者和集大成者,而孟超、宋云彬是堅定的支持者。這五位編輯成了《野草》期刊的核心成員。
《野草》在當時惡劣的戰時環境下得以成長,也得到了國統區許多進步作家和美術家的大力支持。左翼力量從敵占區撤來,也有的在重慶、廣州、香港搜集新聞信息。在《野草》編輯部的帶動下,聚集了郭沫若、茅盾、田漢、胡愈之、陳此生、柳亞子、馮雪峰、胡風、秦牧、荃鱗 艾蕪、司馬文森、林林、華嘉、黃藥眠等左派人士或趨同左派人士,形成了陣容強大的“作家群”。《野草》的社團成員,在政治、文化、人脈以及組織關系上錯綜復雜,和各個組織如中共中央長江局、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以及中共地下組織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出自黃埔系的聶紺弩和宋云彬,都與周恩來關系密切;國民黨左派中,有南社的柳亞子、太陽社的孟超等。雖然每個人出自的社團不盡相同,但他們都有著反對分裂、支持抗戰的共同政治趨向;他們都希望團結一致,保衛家園,用手中的筆做抗日的先鋒。
當時在桂林的茅盾,極為關心《野草》的編輯出版工作,努力擠出時間為其撰寫連載多期的《雨天隨筆》,每次都認真閱讀編者新送來的剛出版的《野草》,并從內容到編排上提出很多寶貴意見。秉性剛直、被蔣介石開除國民黨黨籍的柳亞子,當時與桂林政黨及文化界交往頻繁且身體欠佳,即便如此他對《野草》的約稿還總是有求必應。《野草》剛出滿一卷,“皖南事變”爆發,國民黨反動派在全國范圍內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在此情況下,夏衍在不得不離開桂林的前一個晚上,盡管“雨橫風狂”“波浪翻屋”,他仍深夜未睡,處理著許多事情,其中包括把即將發排的《野草》稿子看完。
《野草》的文章小型、敏銳、迅速、及時、切中時弊、富有戰斗力,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同志的關注。當時正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對《野草》雜志特別關心,就如何辦好雜志作了重要指示,要求該刊編輯要特別注意斗爭方式,在斗爭中保存實力,文章可以稍微寫得含蓄些,不要太露。當時遠在延安的毛澤東同志,曾囑人將每期《野草》各寄兩份給他。雜志還被介紹到其他國家,莫斯科出版的《國際文學》就曾專文介紹過桂林的《野草》雜志①。
許多美術家、畫家與《野草》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其中包括新波、余所亞、周令釗、陳煙橋、劉建庵、溫濤、丁聰、郁風等。他們用手中的畫筆揭露黑暗,刻畫人間丑態,歌頌愛國熱情,體現了《野草》的風格和特色。在《野草》創刊號的首頁,刊出的是余所亞的《前方馬瘦,后方豬肥》漫畫,猛烈抨擊了那些不顧國家危難而過著奢淫生活的現象;《野草》第一卷的封面設計是從一幅舊墻的縫隙中頑強長出一支生氣蓬勃的草芽,這是周令釗饒于意趣而引人深思的創作。
《野草》雜志為這些作者們提供了一個能表達真情、實話、反映民心的平臺。作者們都愿意為健康、積極、正義的社會輿論做出貢獻,因此能夠充分發揮作家的能動性和創造性。
三、在內容上繼承并發揚了魯迅雜文傳統
抗戰文學的發展、文學內容所承載的形式是順應社會形勢發展,并由現實社會和戰時特點決定的。
30年代,魯迅去世之后,投槍匕首般的雜文已經不多見。而時勢造英雄,抗日烽火激發了左翼愛國作者群的激情。在時代的要求下,《野草》順應而生,這些作者們都自覺繼承魯迅傳統,所以大家一致贊成刊物取名為《野草》,作家們希望《野草》雜志能替廣大愛國人士和人民大眾傳達自己的心聲,能為抗戰勝利做出應有的貢獻。他們強調:《野草》不是“供給若干悠閑者們乘涼”的,而是戰士們“歇息的處所”②。
據秦似回憶,夏衍為籌辦刊物曾多次邀約其他四個編輯商議刊物的名稱、宗旨和辦刊方針。經過醞釀和思考后,夏衍列出了兩個書刊名供大家商討,一個是“短笛”, 寓有“短笛無腔信口吹”之義;另一個是“野草”。大家一致認為,“野草”這個名稱不單單是傳承魯迅,更重要的是在當時持久抗戰的態勢和八股文風盛行的文學形勢下,“這個刊名可能給社會和文壇帶來一點生氣,引人略有所思”。夏衍同志說:“魯迅那時寫文章,往往說出了大家心里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文章一發表,便與讀者心里的想法有一種契合和默契,所以大家都喜歡都愛讀。”“野草作家群”認為魯迅是他們很好的榜樣,應責無旁貸地把魯迅的戰斗旗幟接過來,把這個文學武器充分發揮起來,為抗日服務、為當前的革命斗爭服務③。為此,夏衍等人決定《野草》以刊登短小生動、活潑辛辣的雜文為主,主要學習魯迅先生的雜文風格,即文章的外表看上去帶點“柔和與軟性”,內容卻是“幾根難啃的骨頭和難以下咽的魚刺”,寓政治風云于社會風月之中,用筆和紙在借古論今、談天說地的隱晦形式中為苦難的人民傳達呻吟和呼喊。
《野草》外“軟”內“剛”成為了這個刊物最大的特點。如聶紺弩的《早醒記》《歷史的奧秘》《蛇與塔》《血書》等,為了改變廣大民眾的精神面貌、增強民族意識,他激烈抨擊黑暗現實和腐朽事物,批判舊的倫理道德,提倡積極上進的新思想。當時《野草》的作家群就是在國統區艱苦的環境下,堅持發揚魯迅散文的現實主義精神,針砭時弊,議論時政。后期的《野草》在繼承魯迅雜文思想和精神的基礎上,做了新的嘗試和改進,呈現出新的特點,文風由消沉、諷刺漸漸地走向了輕快和光明。雜文中更多地體現了人民勝利的喜悅,民眾的歡歌笑語和對勝利充滿的必定信心。
四、結語
在當時環境錯綜復雜的戰爭時期,《野草》雜志只是一個以刊登雜文為主的小型刊物,但卻能比較順利地創刊,且在桂林存活了近三年,這與當時的三個要素是密不可分的:革命形勢和文學需要;有著一群身份比較特殊的龐大的作家群;刊物內在選擇文學表現的形勢即繼承魯迅的雜文傳統。這是當時戰時環境下天時、地利、人和相互作用下的共同結果,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注釋】
①蔡定國、楊益群、李建平:《桂林抗戰文學史》,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頁。
②秦似:《〈野草〉月刊發刊語》,《野草》創刊號。
③秦似:《回憶〈野草〉》,《新文學史料》,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