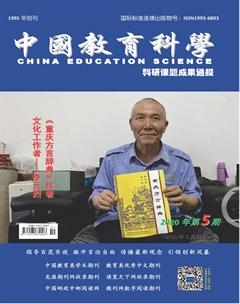中國英語的語音界定討論
馬蘭萍
摘? 要:中國英語的語音界定既要正視和反映大多數接受過良好英語教育的中國人的英語發音實際情況,更需要在中國英語的標準認定上的人為干預和選擇。中國英語的語音界定應該既是規定性又是描述性的,且規定性先于描述性。中國英語的語音界定應視中國的電臺、電視臺英語節目播音員、主持人的實際發音為典范和描寫對象,由此避免中國人紛繁的英語發音。
關鍵詞:中國英語、語音、發音、界定
1. 研究回顧
雖然“中國式英語”(Chinese English)作為學術意義上的一個術語不太容易說明,但由于它的含義主要為貶義,所謂“中國英語學習和由于使用者受母語的干擾和影響,硬套漢語規則和習慣,在英語交際中出現的不合規范英語或不合英語文化習慣的畸形英語”。因而人們對之研究觀察的目的主要出于英語學習和掌握運用的匡正或補救。
“中國英語”(China English)的出現距今不過20多年。一般認為是葛傳榘首先把“中國英語”作為一個嚴肅的概念提出來的。他在指出Chinese English 和China English 的區別時認為:“各國有各國的情況。就我國而論,不論在舊中國或新中國,講或寫英語時都有我國所特有的東西要表達”。從此,“中國英語”的提法已漸為中國學者接受并不斷的引起關注。依筆者檢索所及,汪榕培的“中國英語是客觀存在”的論斷在先,李文中的旨在區別“中國式英語”和“中國英語”的文章“中國英語和中式英語”稍后。再后,杜瑞清、姜亞軍又撰文討論“中國英語”問題。同時,刊載該文的《外語教學與研究》的編者在該期“新年的話”中稱:“中國英語已不是學者們虛構的概念,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了。”該文預言,隨著學習英語的中國人越來越多,英語有可能成為許多中國人的第二語言,最終“中國英語”也許會成為英語最大的一種變體。如此,針對“中國英語”的各個層面進行客觀的定義、描寫和解釋都是不可或缺的。按照杜瑞清和姜亞軍的看法,英語的迅速國際化引起了英語的本土化(nativization)。至此似可確認,帶有中國地域色彩的一種英語變體在對內對外的交際活動中的存在是客觀的。然而迄今為止,尚缺乏對“中國英語”各層面的普遍接受的定義和描寫。李文中曾提到有人認為“中國英語”的定義應包括三部分含義:“中國人在本土上使用的”;“以準英語為核心的”;“具有中國特點的”。李氏認為這種解釋有一定見地卻不免狹窄、粗泛,他對“中國人在本土上使用的”定義更有質疑而舉證。杜瑞清、姜亞軍的研究指出了英語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并以音位、詞匯、語篇層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語音方面的論述較之李文中更有所進展。李文中對“中國英語”的觀察主要從詞匯、本地化詞義獨特句式以及篇章結構入手,其中涉及到的“中國英語”的語音特征部分并非專論,也未能明確“中國英語”的語音規范問題。事實上,他們更多地注意了“中國式的語音失誤”,而姜亞軍曾指出“中國英語在音位層面的特征,如英美發音混雜和源于中國英語教學和詞典編撰體系的保守型發音等”。
2. 中國普通話推廣的語音障礙與英語發音在中國的本土化
中國的普通話推廣普及過程與英語在中國的本土化存在某些可類比的情況。很久已來,普通話發音與英語發音的關系也是英語教育工作者所關注的。眾所周知,普通話在中國的推廣并非一帆風順。其他層面的困難暫且不論,這里只觀察普通話的發音。一方面,由于普通話的更加普及,各地方言也迅速發生變化,其語音變化越來越貼近普通話發音。這一傾向在職業人群、接受良好教育者和年輕一代中更為顯著。例如,“上海方言的語音……明顯向普通話靠攏”。這種現象意味著各地方音有與普通話語音存在著“互動”,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由于各地不同方音(accent)的影響,也出現了不少普通話變種。比如,對相當數量的中國人而言,很容易感受到上海人所講的普通話和廣東人所講的普通話在語音方面的差異。
普通話關于語音的定義和不同地方中國人實際上所操的普通話發音“背離”現象也許能為中國英語的語音界定帶來某些啟示。“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范白話文著作作為語法規范”。依然單就語音而論,幾乎各地方言的語音系統中都有需要糾正的方音。試想,如果某人在講普通話時未能克服其方音系統中的不諧音素,那么他必然從語音方面對其所操的普通話進行“修正”。換言之,他使用了其語音系統某些已經存在的音素來替代應有的音素。讓我們姑且將其看作是普通話在推廣進程中的”本土化”現象。
英語語音在中國“本土化”的成因與此相仿佛。一些英語學習者在把握某些英語音素時感到困難。他們對此的應對策略是:使用語音替代,即使用母語系統中已有的最為相似的音素來替代目標音素。還有學者指出,漢語中缺少的英語音素正是中國人感到困難的音素。事實上,音素帶來的困擾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對中國為數可觀的英語學習者而言,另一方面的麻煩來自超音段音位層面,如重音、弱化、同化和連讀等。確實,在實際的言語統一體中,上述要素都是在我們稱之為“語流”中體現的。例如,通常的情況是單個音素的克服容易些,在單詞的發音中正確地體現這些音素就困難些,更難的是在語流中對這些音素的正確把握。然而,它才是最有價值的。可以想象,如果一個人該層面的問題得不到或尚未解決,其后續對策必然是求助于母語系統的相應部分。如此,英語語音在中國的被“修正”則是難以避免的。
3. 關于中國英語語音的討論
就英語在不同國家的語音特征而論,使我們很容易想到古人“生于齊者,不能不齊言,生于楚者,不能不楚言”的論斷。這表明,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同操漢語的人們實際發音表現為多種地區口音(regional accent)并存的語音特征。就發音而言,英語的多樣性不斷被人們所認識。今天,大多數人已習慣了英國英語、美國英語、澳大利亞英語等英語的存在。英語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人們能夠不費氣力地將它們從發音方面加以區別。另外,我國一些學者也曾指出區域性變體如印度英語,尼日利亞英語,和新西蘭英語的某些語音特征。那么,作為另一變種的中國英語必有其相應的語音特征。這是因為,不少人在學習英語發音時,母語發音的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是必然會發生的。現實的情況是,漢語中的多種地區口音使中國不同地區的英語學習者的發音更為紛繁。我們認為,一方面分別對其語音進行描寫不容易進行;同時其中任何一種英語發音也缺乏普遍意義。
到目前為止,已經提出的中國英語概念未能明確涉及它的語音界定規范。出于學術意義上的便利和作為實踐意義上的規范的考慮,我們主張:應視中國電臺的界定英語播音員、主持人的實際發音為中國英語的典范和描寫對象。主要理由如次:眾所周知,中國的英語學習和使用者人口之眾,恐怕是除英語國家之外所僅見,由于多種因素的作用,中國人英語發音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分別對其進行描寫既耗時費力又缺乏廣泛意義。其一,以主持人的實際發音為中國英語的語音典范將避開實際發音的紛繁而有助于專注于具有廣泛意義者。其二,中國英語的語音界定必將對中國英語學習者的英語發音產生一定的影響并對語音層面的描寫帶來推動。我們相信,主持人的發音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英語教育在英語發音方面的最高成就。可以想象,他們獲得主持人職位的重要條件是具有英語發音方面的相對優勢。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們在英語學習方面是成功的,他們的成功影響著未來的英語學習者。簡言之,將他們所操英語的語音視為中國英語的典范具有某種英語語音教學的導向引領意義。其三,在國際上非英語國家的對外英語節目、廣播的播音員、主持人一般都是各國自己培養的,鮮有雇用母語為英語者或本民族語為非英語者但從小生長于英國國家者充任的例證。這種國際通行做法也許一定程度上關乎民族感情、尊嚴和一個國家的英語教育實力的象征。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我們專注于某一國家的對外英語廣播一段時間,不必等到播音員自報家門,我們就能辨別出是哪個國家的英語廣播節目。我們姑且把這種現象視為英語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本土化”效應。也許,濃厚的民族特色和強烈的民族意識在客觀上助長了英語發音在不同國家的“本土化”。應當承認,所有這些不同的英語發音盡可能與native speaker的發音接近,顯示了對英語正確發音的熱烈追求和殷切向往。
目前在中國,即使電臺、電視臺播音員的普通話發音有時也偏離了純正的、正統的、符合定義的普通話標準。一些具有地區特色的普通話發音被廣泛接納,在一些廣告、娛樂節目中尤為顯著。這說明在實際交際活動中,公眾對一些語言變體的態度越來越寬容。故盡管中國的電臺、電視臺英語欄目主持人、播音員所操的英語與英美播音員的發音尚有差距,但仍應視為中國英語的語音典范和被描寫對象。實際上,任何標準語音的確定都具有一種人為的選擇或干預印記。例如,Jones曾多次宣稱RP本身并不比其他發音模式“優越”或“漂亮”,他之所以把RP作為詞典記錄的對象,是因為他恰好能夠充分地、正確地取得有關這種發音的知識。他無意成為語音改革者或決定語音好壞的評判者。
4.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中國英語的語音界定既要正視和反映大多數受過良好英語教育的中國人英語發音的客觀實際,又要有在語音標準認定上的人為干預和選擇。就其實質而言,定義中國英語的語音應是認定一種英語變體的語音標準。我們認為,該標準應該是既有廣泛的代表性,又具備學術意義上的可描述性。為此,中國英語語音層面的界定既是規定性的,又是描述性的,且規定性先于描述性。換言之,其描述性是以規定性為前提的。其規定性的意義:避開了中國英語學習和使用者發音的紛繁,專注于具有代表性者;其描述性的價值體現在反映中國英語的語音現狀,以發現英語教學的問題,而后尋求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