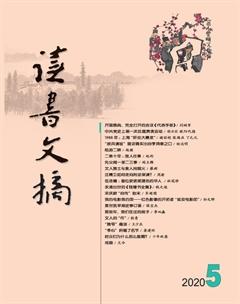我的電影我的團
孫文曄
《馬路天使》的導演為何在當紅時突然消失?白求恩大夫手術場景是如何被記錄下來的?南泥灣事跡是怎么傳揚開的?說起紅色延安的記錄者,我們總想起埃德加·斯諾,想起那些沖破封鎖的外國記者,卻往往忽視了延安自己的攝影攝像機構—— 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習稱延安電影團)。
當膠片成了歷史,延安電影團成員也大多離世了。為了填補這段電影史上的空白,他們的后人,兩位退休老人吳筑清(吳印咸之女)和張岱(錢筱璋之女),重新拾起記錄的力量,努力還原了這段傳奇。
《風云兒女》
抗日戰爭初期,在周恩來親自安排下,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等幾位左翼電影精英,從大城市奔赴陜甘寧邊區,成了紅色延安記錄者。
從1938年抗戰到1946年挺進東北,電影團在延安拍攝了整整8年,留下了厚重的影像資料,但記錄他們自己的照片卻屈指可數。
不過,也許正因為跨越了幾十年,很多歷史文獻已經公開,回憶錄也相繼出版,延安電影團的故事反而越來越清晰。在吳筑清家,當兩位老人對記者講起這段故事時,一個個人物、事件又變得栩栩如生起來。
“我倆的父親,一個是電影《馬路天使》的攝影師,一個是剪輯師,當時在上海,月薪150大洋,他們到延安去,是有袁牧之、許幸之這樣的引路人。”吳筑清和張岱對歷史的追尋,是從左翼電影運動開始的。
1931年,戰爭的陰影投向中國東北,即使是在紙醉金迷的大都市上海,神怪武俠、風花雪月也不再受觀眾歡迎。中國當年最有影響的電影公司—— 明星公司,窮則思變,向幾位新文藝工作者伸出了橄欖枝。
明星公司經理周劍云先找到安徽蕪湖的同鄉錢杏邨(阿英),邀請錢杏邨和夏衍、鄭伯奇三人加入明星公司。
要不要幫資本家拍電影呢?夏衍一時拿不定主意,最后,還是當時在上海領導共產黨文化工作的瞿秋白拍了板。他說:“在文化藝術領域中,電影是最富群眾性的藝術,將來我們取得了天下,一定要大力發展電影事業。現在有這么一個好機會,何不利用資本家的設備學一點本領?”
為了把這件事辦好,中共中央“文委”還特地成立了一個電影委員會。別看這個小組才5個人,但不同凡響的新內容和形式,卻給當時奄奄一息的電影業,帶來了生機。1933年,上海的“明星”“聯華”“藝華”“天一”等公司共攝制50余部影片,其中左翼影片或受左翼影響的影片就有43部。
左翼電影在民眾中越來越有影響力,國民黨打壓的手段也越來越沒底線。1935年,田漢、陽翰笙等被捕,夏衍、阿英、鄭伯奇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
不過,電影小組沒有氣餒,他們又另起爐灶,成立了“電通影片公司”,這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第一個商業電影公司。為了辦好“電通”,“左聯”把在戲劇界嶄露頭角的袁牧之輸送到了電影界。
袁牧之本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但他從小癡迷戲劇,甚至不惜跟家里斷絕關系,也要闖蕩上海。有一次,一家照相館要拍櫥窗,袁牧之只用一套西裝,一條領帶,一頂禮帽,就創造出卓別林等西方十位電影大師的形象,一時成為新聞熱點。因為善于化裝造型,袁牧之在戲劇界有了“千面人”的綽號。
電通公司成立之初,陷入無戲可拍的境地。這時,剛從戲劇轉入電影行業的袁牧之,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僅用幾天時間,就創作出了《桃李劫》。
許多青年唱著其中的《畢業歌》,“去擔負起天下的興亡”,主演袁牧之和陳波兒也因此一炮而紅。
1935年,《風云兒女》上映。值得一提的是,該劇作者田漢在拍攝期間被捕,他在獄中寫出了該片主題曲歌詞,由探監的女兒偷偷帶出,又由聶耳譜曲,這才有了《義勇軍進行曲》。26歲的男主角袁牧之,明知很危險,仍用意氣風發的聲音在電影中首唱了這首歌。
同樣臨危受命的還有吳印咸,因為對光影特別敏感,又是美術科班出身,沒有任何電影經驗的他,被導演許幸之推到了攝影師的位置上。
演而優則導,在電通公司,袁牧之還編導了中國第一部音樂喜劇片《都市風光》。別看電通公司雖然只存在了兩年,正式出品的也僅有四部影片,但這四部影片中,袁牧之擔任主創的就有三部,還把攝影師吳印咸等新人培養成了業內高手。
1937年,山雨欲來,上海電影業也遭遇了空前危機。不僅電通公司辦不下去了,就連明星公司也難以為繼,重組,欠薪,陷入破產邊緣。就在此時,《馬路天使》橫空出世,成了20世紀30年代的巔峰之作。
雖然“七七事變”剛剛發生,但《馬路天使》首映后仍席卷上海灘,創下了連放21天,10萬人次觀看的票房奇跡,片中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
這部電影不僅是當年最賣座的影片,在藝術上也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從誕生至今的80多年里,它奇跡般地經歷了各個時期,始終為人喜愛。
著名演員周璇曾經說過,她一生沒有什么滿意的電影,除了《馬路天使》;趙丹也曾經說過,他真正的演員生涯是從《馬路天使》開始的。
這部電影如此經典,其實不僅是周璇和趙丹主演,更是因為有袁牧之編劇、導演,有吳印咸掌機,有賀綠汀編曲,有田漢配樂,有錢筱璋剪輯,如此鼎盛陣容,怎能不好看?
世界著名影評家喬治·薩杜爾曾在《世界電影史》中不無驚訝地寫道:“誰要是看過袁牧之的《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該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個對法國電影一無所知的年輕導演之手,他一定會以為這部影片直接受讓·雷諾阿或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
年僅28歲的袁牧之,用實力證明自己不僅是演藝明星,更是集編劇、導演、文藝評論于一身的天才電影人。
不過,《馬路天使》是袁牧之導演的第二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抗戰爆發后沒多久,這位鼎盛一時的大明星就“失蹤”了。等到他再次回到大眾視線中,身份已經變成了創立延安電影團、擔任新中國電影局第一任局長的袁牧之。如今,在中國電影博物館,有五尊“中國電影開拓者”的塑像,其中一位就是他。
《延安與八路軍》
1938年8月,袁牧之和吳印咸化裝成普通的八路軍戰士,登上了北去的列車。
素有“千面人”之稱的袁牧之,自從雙腳踏上黃土高坡那一刻起,“千面”全都轉變成了“一面”。他把自己只當成革命隊伍里的一位新人,打著綁腿,過起了供給生活。
由于正式加入了八路軍,袁牧之每月有5元邊幣薪金,這是延安干部中的最高標準。吳印咸是特邀攝影,部隊每月給他老家發120大洋,供其家用。這個安排雖然周到,不過,比起吳印咸過去的工資水平,并不算多。
1938年9月,八路軍政治部電影團,正式成立。
吳筑清說,電影團與當時延安的自發社團完全不同,是按八路軍正規編制建立的軍事機構,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正規電影和圖片拍攝機構,而且直接隸屬于八路軍總政治部,并由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兼任電影團團長。
成立之初,全團只有6人,參加過長征的干部李肅擔任政治指導員,袁牧之負責藝術指導,吳印咸和徐肖冰擔任攝影,另外又從抗大學員中調來葉蒼林和魏起擔任劇務。
他們當中,從事過電影工作的只有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三人。徐肖冰抗戰爆發前曾給吳印咸做過攝影助手,后來參加了八路軍,進入抗大學習,沒想到這次又在延安相遇,他還是吳印咸的攝影助手。
他們的全部家當被稱為“兩動三呆”。“兩動”是指兩臺能拍電影的機器,35毫米的“埃姆”,是伊文思所贈;16毫米的“菲爾姆”,購于香港。“三呆”是指三架拍照片的相機,其中一臺是徐肖冰的,另外兩臺是吳印咸拿出自己的積蓄購置的。膠片共有16000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藥品,這就構成了延安電影團的全部生產資料。
雖然條件遠比不上上海,但是他們卻執著地相信,即將產生的是一部立意高遠、無愧祖先的作品。吳印咸在拍攝手記中寫道,“從祖先墳上開始我們的工作。”
1938年10月1日這一天,攝影機的轉動打破了古柏林中的寂靜。在莊嚴的黃帝陵前,剛剛成立不久的延安電影團開機了。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部紀錄電影,在此拍攝第一組鏡頭,可謂意義深遠。
鏡頭一轉,又轉到黃土高原崎嶇的山道上。1938年夏秋之間,2000多名愛國青年風餐露宿,從這條路奔向延安。延安為什么會有如此魅力?延安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八路軍的抗日斗爭是如何展開的?在導演袁牧之的計劃中,人們將在《延安與八路軍》中得到答案。
戰爭的殘酷很快顯現出來。兩個月后的一天,尖銳的警報聲驟然響起,延安遭到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轟炸,造成41人死亡,100多人受傷。當時,吳印咸和徐肖冰正在窯洞里對攝影機做維護,一顆炸彈剛好在窯洞一角落下,屋子里頓時布滿了灰塵。幾乎是同時,吳印咸撲到桌子上,用自己的身體掩蓋住了所有零件。奇跡般的,他沒有受傷,一桌子的攝影機零件,連一顆細小的螺絲釘都沒有丟。
延安的拍攝順利結束,電影團將前往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毛澤東特意為他們送行,還語重心長地說,你們現在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不能充分發揮能力,但將來的工作是很多的。比如,現在拍長征不可能,過幾年你們就能拍了。
在炮火硝煙、危險與忙碌中,戰地拍攝轉眼進行了一年,所拍攝的素材急需進行后期制作。于是,袁牧之攜帶拍好的底片返回延安,留下吳印咸、徐肖冰各帶一組,分赴平西游擊區和晉東南八路軍總部拍攝。
電影的后期制作工序復雜,延安不僅沒有設備和器材,就連電都沒有,該怎么辦呢?在蘇聯的解密檔案中,張岱發現了一份中共中央給季米特洛夫、周恩來和任弼時的絕密電報,其中介紹了片子的來龍去脈,袁牧之和冼星海的身份,以及這部片子的重要性:
原打算把這些膠卷寄往美國或香港,但據我們得到的消息說,這些膠卷在寄往美國和香港的途中因海關警察的監督和檢查有受損或被沒收的危險。經過認真討論后,我們決定將這些膠卷送往莫斯科顯影,以使這些復雜的照片能正確地剪輯成影片。……請你們盡快解決這一問題,因為時間一拖延,電影膠片就有損壞的危險。這將是第一部真實反映中國人民、共產黨和八路軍反對日本侵略者英勇斗爭的戰斗影片。它對國際和中國國內宣傳有著不尋常的意義。
1940年3月26日,延安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歡迎會,迎接從蘇聯歸來的周恩來。那一天,周恩來約見了袁牧之,告訴他黨中央已安排妥當,讓他和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冼星海同行,前往蘇聯完成電影《延安與八路軍》。離開延安時,組織上還安排把底片放在周恩來的車上,免受國民黨檢查,保證了絕對安全。
在莫斯科,蘇聯方面很快將底片洗印出來,冼星海的配樂也完成了,正當準備進行剪輯時,一場風暴卻不期而至。
1941年6月22日,德國向蘇聯發動閃電戰,莫斯科電影機構紛紛向后方撤退。袁牧之和冼星海聽從蘇聯方面的安排,輾轉抵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然而,就在他們互祝平安時,一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 裝有《延安與八路軍》所有底片的箱子竟然不知去向。
袁牧之盡最大努力打聽和尋找,可是沒有任何線索,他的呼喚在戰爭的轟鳴聲中被淹沒了,所有理想和創造都在瞬間灰飛煙滅。
更令人痛惜的是,因為戰爭原因,袁牧之被困在蘇聯長達五年三個月之久。冼星海因為長期勞累、貧病交加,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蘇聯,年僅40歲。
《延安與八路軍》真就全部散失在了遙遠的莫斯科嗎?吳筑清苦笑著說:“未必,可是找回來很難。”
1950年,在中蘇合拍的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解放了的中國》中,中國的電影工作者意外看到了《延安與八路軍》中部分彌足珍貴的鏡頭,并且聽到了熟悉的冼星海風格的配樂。
1952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成立后,曾派人去蘇聯找回一些《延安與八路軍》的片段,這些資料后來大多用在中央新影的影片《延安散記》等紀錄片中。
1959年,中央新影的編導高維進到蘇聯搜集材料時,曾正式向蘇聯方面查問過這部影片的下落。蘇聯有關方面答,在蘇德戰爭期間已將這部影片的全部底片和素材交給了當時在“第三國際”工作的一位同志帶回中國,至于下文如何,無從查究。那時,中蘇關系惡化,到底是不想給,還是懶得找,或者壓根沒有,也就不得而知了。
《延安與八路軍》這部中共自己拍攝的第一部新聞紀錄片,終究無法以全貌的形式呈現出來,這是電影團永遠的遺憾,更是黨的重大損失。
不過,不幸中也有萬幸。離開延安之前,袁牧之曾和吳印咸商量,已經拍攝的幾千英尺膠片,是冒著生命危險搶拍下來的,而且膠片體積大、分量重,背著這些寶貝遠赴蘇聯,漫漫路途之中一切都難以預料,萬一有閃失,將會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幾經斟酌,最后將一部分內容相近的16毫米的底片暫時留在了延安。更為難得的是,有關白求恩大夫的影像素材因為沒有在拍攝提綱中,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南泥灣》
隨著《延安與八路軍》拍攝結束,吳印咸又一次面臨人生選擇,他已經實現了當初的諾言,現在該往何處去呢?這兩年來,延安展現出令人“著迷”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吳印咸,他請求組織停發每個月120塊大洋的安家費,轉而領取每月1塊錢的邊幣。
吳印咸留在了電影團,卻不知電影團正面臨著被精簡的危機。
1941年后,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的階段。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曾這樣描述延安的困難,“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延安難,電影團就更難了,膠片來源斷絕,完全沒有補給,剩下的膠片只能精打細算地使用。電影團沒有膠片,就像戰士沒有槍,還能打仗嗎?
為克服困難,延安實行“精兵簡政”,不少文藝機構或合并或精簡,但看似無用的電影團卻被保留下來。在總政治部宣傳部長肖向榮心里,攝影隊的8個人和放映隊的6個人,是好不容易集結起來的精英,散伙容易,想再聚起來可就難了。
為減輕政府負擔,吳印咸帶領電影團的人開荒種地,當年就做到糧食自給有余。他們還開辦照相館,舉辦了攝影展覽,自主解決了辦公費用和生活開支。
經費解決了,但電影團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沒有作品怎么行?再難也要拍電影,當中央提出要拍南泥灣的時候,吳印咸把目光投向了最后的2000英尺正片上。
作為專業人員,他當然知道,拍電影需要用負片,正片是翻拍拷貝用的,而且這些正片都過期四五年了,感光度差,只要照明條件稍差,或者是移動的物體,就很難保證成像質量。可是條件如此,電影團已經別無選擇。
1942年秋,在359旅進入南泥灣屯墾一年后,攝制組也開進了南泥灣。為了不浪費一格膠片,吳印咸全程掌鏡,最終用1500英尺正片完成了拍攝。如今觀眾看到的挖窯洞、揮镢墾地、紡線織布、馱鹽運輸的鏡頭,洋溢著勃勃生機和獨特的藝術氣息,都是因為出自大師之手。“可惜沒有照明設備,晚上熱火朝天的開荒場面沒留下來。”吳筑清說出了父親的憾事。
在延安進行后期制作本不可能,這個問題在拍《延安與八路軍》時就遇到過了。但袁牧之幾年未歸,電影團哪敢再重蹈覆轍。
越是艱難,越需要榜樣,為了盡快把南泥灣的事跡傳揚出去,電影團決定因地制宜,用最原始的土方法,手工進行后期制作。
影片的沖洗,水是不能少的,而且需要流動水,延安是缺水的地方,更沒有自來水,但是上天助人,駐地就在延河邊,山腳下尚有幾個深水井。電影團的小伙子們背水上山,又弄了幾個大缸,反復澄清。沒有燈,就用自然光曝光,房頂開個洞,肉眼觀察陽光,尋找曝光的時機。
沒有電影編輯機,甚至連一塊放大鏡都沒有,剪輯自然不易。18歲就剪出《馬路天使》的錢筱璋開動腦筋,找來一面鏡子,把日光反射到膠片上,在方寸之間尋找著剪接點。最后,拍攝的1500英尺素材用上1300英尺,折損率降到了最低。
1943年2月4日,紀錄片《生產與戰斗結合起來》(俗稱《南泥灣》)在延安首映。放映效果比我國早期有聲電影還要好,畫面與音樂、解說互相烘托,大大增強了影片的藝術感染力。許多不明底細的觀眾還以為延安能制出“有聲電影”,一面驚訝,一面自豪。
他們哪里知道銀幕后面演的“雙簧”呢! 配樂用的留聲機和唱片是從毛主席那里借的,解說是工作人員通過小喇叭,現場向觀眾講解。放映隊帶著這部片子和手搖發動機,走遍了陜甘寧邊區,所到之處,都跟過大年似的熱鬧。
這一時期,延安電影團還為許多中共領導人拍過肖像。這些照片極為準確地捕捉到了人物的個性:溫厚淳樸的朱德,靈活灑脫的周恩來,內向持重的董必武,心胸寬闊的林伯渠……這些以陜北窯洞為背景的照片,為后世留下了領袖們的延安形象。
為了盡可能多地將延安的火熱生活記錄下來,電影團本著“寧精毋濫”的原則,有選擇地拍攝一些具有重大史料價值的素材。不過,不論多么重要的題材,也只能拍攝有限的幾個鏡頭。
這樣,他們相繼拍攝了延安慶祝百團大戰勝利大會和追悼會、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等一系列大事件。現在看來,這些影片具有不可估量的歷史價值。
新中國沒有忘記《南泥灣》,延安電影團的成員們更沒有忘記他們親手制作的第一部紀錄片。錢筱璋是《南泥灣》的剪輯和解說詞撰稿人,也曾長期任中央新影廠長,在他的主持下,《南泥灣》成了真正的有聲電影。
《電影先鋒》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為了開辟東北解放區,中共中央抽調10萬名干部派往東北。延安電影團也接到命令,去長春接收遠東最大的電影拍攝基地—— 日偽的“滿映”。
電影團在東北找到了新的使命,而遠在阿拉木圖的袁牧之,竟然與延安的同志們不謀而合了。
1946年春,在撫順大街上,電影團派到東北的先遣隊員錢筱璋猛然看到了一個熟悉的面孔,這出乎意料的相逢,令雙方都愣住了。袁牧之,這位被延安電影團苦盼了整整五年的人,竟然出現在眼前,錢筱璋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袁牧之也沒有想到,錢筱璋會到戰火中的東北來。他在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備嘗困苦。直到戰爭結束,黨中央開始安排留蘇人員陸續回國,他才得以從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出發,經過莫斯科和西伯利亞,和李立三等人回到祖國。這次趕到撫順,是到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報到。
這是多么不尋常的相逢!上海淪陷時,兩人曾相約到延安去拍紀錄片;奔赴延安時,錢筱璋曾為袁牧之送行,此后整整七年半,天各一方,卻又在這關鍵時刻走到了一起。
袁牧之的到來,使接收工作有了帶頭人。但接收工作剛開了個頭,國民黨就把大批軍隊運抵東北,內戰一觸即發。作為戰略撤退的一部分,東北局決定將接收的“滿映”器材運往后方,并動員職工一起前往。
張岱感嘆道,“東北局宣傳部就三個半人,卻要說服廠子里的上百號人一起撤,我到現在都想不出,他們是怎么做工作的,竟然把廠里的日本人都說動了。離開長春,連顆螺絲釘都沒給國民黨留下。”
“滿映”整體遷往興山市后,延安電影團的大部隊也隨東征縱隊來到這里,建起了新中國第一個電影生產基地—— 東北電影制片廠。
袁牧之任廠長的“東影”創辦時雖然艱苦,但成績卻非常突出,從1947年到1949年,他們創下了中國人發展電影事業的六個第一:第一部木偶片《皇帝夢》,第一部科教片《預防鼠疫》,第一部動畫片《甕中捉鱉》,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蔣》,第一部長故事片《橋》和第一部譯制片《普通一兵》。
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東影”又派出32個攝影隊,陸續南下。一個攝影隊,就是一臺攝影機,一個攝影師,一位助理,他們不是戰士,卻永遠沖鋒在前。在這當中,有15批攝影隊成員來自延安電影團,有三位同志不幸在戰斗中犧牲。
所有的犧牲與苦難,最終都凝結在膠片上。為延安電影團寫書作傳之后,吳筑清和張岱又有了新的期盼,她們說,“我們現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延安與八路軍》這部失散的片子找回來。”而中央新影把紀念延安電影團的紀錄片取名為《電影先鋒》,是因為這批人以超越時代的先鋒精神,開創了新中國的電影事業。
(選自《北京日報》202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