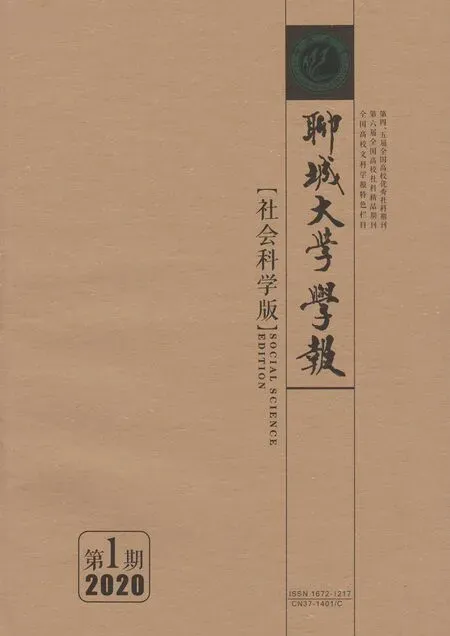安大簡本《螽斯》章次探賾
趙海麗
(山東交通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山東 濟南 250023)
清代學人方玉潤曰:“《六經》中唯《詩》易讀,亦唯《詩》難說。”①[清]方玉潤:《詩經原始?凡例》(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頁。《詩經?周南?螽斯》堪為此說之例證。這是一首用語顯豁,彌足珍貴的詩歌之作,為一直以來的三章體。安徽大學收藏新發現的戰國楚簡《詩經》(簡稱安大簡本《詩經》),為目前所見最早的先秦抄本(包括《周南?螽斯》文本)。其本存在與《毛詩》本章次不同的情況,即安大簡本《螽斯》與《毛詩》本的二、三章相校,章次相互錯置。情況如下:
《螽斯》章次何者更為合理?筆者以為這需要從《螽斯》詩旨的確定,重言詞之義及詩意表現,用韻及聲情特征等諸多因素加以綜合考察分析。這不但直接影響到對《螽斯》詩意的正確解讀,同時也影響到《詩經》文獻的準確傳承。故不揣淺陋,略加考論,以期對《螽斯》篇之章次原貌作進一步的解讀。
一、《螽斯》詩旨簡說
《螽斯》這首詩篇幅短小,內容簡單,但前賢后生對此詩的主旨理解始終存在分歧,主要有五說:一是傳統說。以《毛詩序》為代表,《小序》謂“后妃子孫眾多”,《大序》因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眾多。”①[清]方玉潤:《詩經原始》(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81頁。韓詩認為“言賢母使子賢也”。②[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06頁。亦有“眾妾相安相樂”③[明]朱謀?:《詩故》卷一,第551頁。之詞。諸家之說對螽斯所比的對象有些差別,實質上意旨為主歌頌的。毛亨、鄭玄、孔穎達、朱熹等均從此說。二是諷刺說。以高亨為代表。他認為《螽斯》“是勞動人民諷刺剝削者的短歌。詩以蝗蟲紛紛飛翔,吃盡莊稼,比喻剝削者子孫眾多,奪盡勞動人民的糧谷,反映了階級社會的階級實質,表達了勞動人民的階級仇恨。”④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8頁。三是祭祀說。以張巖為代表。他認為這是一首以螽斯為圣物的祭祀禮辭。⑤張巖:《簡論漢代以來〈詩經〉學中的誤解》,《文藝研究》1991年第1期,第66頁。季康華等學者同意其觀點。⑥季康華:《一曲圣物祭祀的歌舞禮辭——〈詩經?螽斯〉中六個重言詞的解析》,《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報)》2007年第3期,第10-12頁。四是君子說。上博簡《孔子詩論》第27簡后半段內容,孔子曰:“《蟋蟀》知難。《中氏》君子。《北風》不繼人之怨。《子立》不……”李零、何琳儀、李守奎將“中氏”讀作“螽斯”。⑦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0頁;何琳儀:《滬簡詩論選譯》,引自《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55頁;李守奎:《楚簡〈孔子詩論〉中的〈詩經〉篇名文字考》,引自《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342-349頁。廖名春、季旭升、鄭玉姍均同意李零的說法。⑧廖名春:《上博〈詩論〉簡的形制和編連》,簡帛研究網站2002年1月12日;季旭升主編,陳霖慶、鄭玉姍、鄒濬智:《〈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一)〉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60-61頁。王小盾、馬銀琴也認同“中氏”實即《周南》的《螽斯》,只是把“君子”釋為“群子”,即“中氏君子”為“《螽斯》群子”。⑨王小盾、馬銀琴:《從〈詩論〉與〈詩序〉的關系看〈詩論〉的性質與功能》,《文藝研究》2002年第2期,第45-48頁。五是祝賀說。即認為這是一篇贊頌子孫眾多的祝辭。諸家之論說將《螽斯》詩旨定作“祝賀說”是最有影響的。當代治《詩經》學者多從此說。袁愈曰:(《螽斯》這首詩)是“祝人子孫眾多。”⑩袁愈:《詩經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11頁。姚小鷗認為:“本篇祝賀人多子多孫。古人認為人丁繁衍是家族興盛的保證。螽斯繁殖能力強,所以,本篇用螽斯多子來比喻人之多子。”[11]姚小鷗:《詩經譯注》,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9-10頁。黃典誠論《周南?螽斯》是一篇向男家祝賀新婚的頌詞,愿人將來“百子百孫,傳之無窮”[12]黃典誠:《詩經通譯新詮》,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52年,第7、13頁。。趙會莉言:“在《詩經》中新婚的祝詞中,祝福新人多子多孫的賀辭成為當時的主旋律,一曲《周南?螽斯》唱出了人們的心聲。”[13]趙會莉:《〈詩經〉里的賀婚習俗及其文化意義》,《文學教育》2014年第5期,第46-47頁。蕭兵也說:“螽斯多子而且群飛,可以暗喻后裔繁盛。”[14]蕭兵:《孔子詩論的文化推繹》,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6-227頁。
綜合以上學人對《螽斯》主旨的認識,筆者認為《螽斯》是一首用于祝禱子孫眾多儀式的樂歌頌詞。該詩吟唱,文辭簡樸質實,充滿土氣和天性。
二、安大簡本《螽斯》重言詞之義及詩意的遞進
“詵詵”與“振振”;“揖揖”與“蟄蟄”;“薨薨”與“繩繩”,此類重言詞是由兩個相同的音節構成,都是實詞,有具體的詞匯意義。《詩經》中的重言詞應用廣泛。清人王筠言:“《詩》以長言詠嘆為體,故重言視他經為多,而重言之不取義者尤多。或同言而其意義迥別,或異字而義則比附。”①[清]王筠:《毛詩重言》全一冊影印本,第1頁。這些詞兩兩構成了三組疊句,是理解《螽斯》詩意的關鍵點。現以安大簡本為例來探討《螽斯》篇中重言詞之義。
(一)螽斯之形容——“詵詵”“揖揖”“薨薨”
詵詵:《毛傳》:詵詵,眾多也。今本《說文》:“詵,致言也。”這里“詵”沒有“眾多”之義。然《釋文》云:“詵詵,《說文》作,音同。”《廣雅》:“,多也。”《玉篇》:“,多也。或作兟。”《五經文字》:“兟,色臻反。見《詩》。”莫子偲校刻唐寫殘本《說文》,“”下引《詩》作。《文選》班固《東都賦》注、左思《魏都賦》注各引毛《傳》作“莘”。袁梅認為:“‘先'‘辛'雙聲,互通。《詩》之古文疑作‘兟兟'或‘',二字重文。《釋文》所云《說文》作,或據彼時傳本。今本《說文》‘詵’下注引毛《詩》作‘詵詵兮',用假借字也,與《文選》注各引毛《傳》作‘莘'同例。”②袁梅:《詩經異文匯考辨證》,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11頁。王安石認為:“詵詵,言其生之眾。”③[宋]王安石著,邱漢生輯校:《詩義鉤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頁,第15頁,第15頁。故所謂“詵詵”,為眾多之義。
揖揖:《毛傳》:“揖揖,會聚也。”今本《說文》“揖”無“眾多”之義。《魯詩》與《韓詩》“揖”作“集”,因此應“揖”為“集”之假借。“揖”與“戢”以及“輯”是同一個語根的字,語源上和“集”也有關系。劉釗認為:“‘集’的本義應該有‘降落(下落)’‘棲止(停留)’‘聚集(集合)’等三個意思,這三個意思正好對應‘集’字一詞的三個早期義位。”④劉釗:《“集”字的形音義》,《書馨集——出土文獻與古文字論叢》,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第241-261頁。清王先謙認為:“‘揖'‘輯'‘集'古字通用。《書?舜典》‘輯五瑞',《史記?五帝紀》《漢書?郊祀志》作‘揖五瑞'。《漢書?兒寬傳》‘統楫群元',注:‘輯、楫、集三字同。'是‘揖'‘集'互通之證。它書‘集集'無連文,明是此詩魯韓訓。”⑤[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0頁,第40頁。王安石曰:“揖揖,言其聚之眾。”⑥[宋]王安石著,邱漢生輯校:《詩義鉤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頁,第15頁,第15頁。綜合來看,“揖”為“集”之假借,又見“集”的本義是“降落”“棲止”“聚集”三義,由是,“揖揖”取第三義“聚集”之義為妥。
薨薨:《毛傳》:“薨薨,眾多也。”今本《說文》“薨”亦無“眾多”之義。韓詩“薨”作“”。《毛詩傳箋通釋》:“薨與聲近而義同。”《釋訓》《釋文》引舍人本“薨薨”作“雄雄”,“雄”為“翃”之誤,“翃”同“”,如此,“雄”即“翃”的假借。《廣雅》《釋訓》:“,薨薨,飛也。”《集韻》《十七登》:“《博雅》:,飛也。或作,通作薨。”據此,“”“”一字。高亨《詩經續考》:“薨薨”“形容它羽翅的聲音”。亦見《齊風?雞鳴》中“蟲飛薨薨”。王安石認為:“薨薨,言其飛之眾。”⑦[宋]王安石著,邱漢生輯校:《詩義鉤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4頁,第15頁,第15頁。由此,“薨薨”,眾飛之義。
(二)子孫之形容——“振振”“蟄蟄”“繩繩”
振振:《毛傳》曰:“振振,仁厚也。”今本《說文》:“振,舉救之也,從手辰聲。一曰奮也。”段注:“此義則與震略同。”《釋言》“振,迅也”,郭注:“振者,迅也。”《太玄》“振,動也”。《詩序》言:“子孫眾多。”王先謙認為:“言后妃子孫受賢母之教。莫不奮迅震動,有為之象也。”⑧[清]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0頁,第40頁。陳奐以為“振振”與《中庸》篇所謂的“肫肫其仁”的“肫肫”同義。他說:“鄭注云:肫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忳。忳忳,懇誠貌也。今《詩》作諄諄,并與振振聲同義近。”①[清] 陳奐:《詩毛氏傳疏》,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22頁。亦見《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召南?殷其雷》“振振君子”。《魯頌?有駜》“振振鷺”。嚴粲說:“振振共有二訓:盛也,信厚也。《詩》言‘振振’者三,此詩當如‘均服振振’之訓為‘盛’,《麟趾》《殷雷》當為‘信厚’。”②[宋] 嚴粲:《詩輯》(36冊),嶺南述古堂影刻明味經堂本。《左傳?僖公五年》“均服振振”,杜預注曰:“振振,盛茂。”“振”又通作“震”,《文選?藉田賦》“震震填填”,李善注:“震震,盛貌。”“振振”又作“軫軫”,《文選?羽獵賦》“殷殷軫軫”,李善注:“殷、軫,盛貌也。”綜上所述,見“振”有多義:仁厚,奮迅震動,懇誠貌,盛貌。此處“振振”取“奮迅震動”與“盛貌”兩者,為興旺、強盛之義。
蟄蟄:今本《說文》:“蟄,臧也。”段注:“臧者,善也。善必自隱。故別無藏字。凡蟲之伏為蟄。”《毛傳》:“蟄蟄,和集也。”三家《詩》將“蟄蟄”作“卙卙”之假借。《說文?十部》云:“卙卙,盛也。從十,甚聲。汝南名蠶盛曰卙。”在此,“蟄蟄”有“伏藏”“和集”“盛”之義,“和集”最能說明“螽斯”之狀,取“蟄蟄”為和諧與歡暢之義。
繩繩:《毛傳》:“繩繩,戒慎也。”今本《說文》:“繩,索也。”《集韻》:“繩繩,無涯際貌。一曰運動不絕意。”《爾雅?釋訓》:“憴憴,戒也。”意與毛同。《玉篇?系部》引《韓詩》說:“繩繩,敬貌。”袁梅認為:“《爾雅》作‘憴憴',乃‘繩繩'之借字。‘繩繩'為正字,嗣續相承之意。”③袁梅:《詩經異文匯考辨證》,濟南:齊魯書社,2013年,第11頁。亦見《大雅?抑》“子孫繩繩”。綜觀,“繩繩”有“戒慎”“索”“無涯際貌”“敬貌”“嗣續相承”之意。《螽斯》所見“繩繩”,更接近于“繩”之本義“索”,而“無涯際貌”“嗣續相承”乃是其引申義。此處“繩繩”為綿長之義。
(三)邏輯和詩意的層層遞進
上文對《螽斯》篇中六個重言詞進行了釋義。無論“螽斯”之物是“詵詵”,或是“揖揖”,或是“薨薨”,最終還是希望歸屬到“人之子孫”的“振振”“蟄蟄”“繩繩”這種繁衍狀態上來。亦無論是“振振”之“子孫眾多而興旺”④[瑞典]高本漢:《高本漢詩經注釋》(上),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第16-20頁。,或是“蟄蟄”之“子孫聚集而歡暢”⑤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10頁。,終歸還是追求永恒的“繩繩”,即展示“子孫不絕世代綿長”這一人類繁衍的文化愿景,此為重點更是核心。像安大簡本《螽斯》篇這樣使用重言疊唱的藝術手法,表達主題,抒發情感,一章比一章的感染力得以加強,形成了邏輯和詩意的層層遞進,給人留下深刻鮮明的印象。因此,就安大簡本《螽斯》之章次而言,首章側重子孫眾多興旺;次章側重子孫聚集歡暢;末章側重子孫世代綿長。此為十足的生命精神演進,惠及詩歌意境提升之例。
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一書中曾將“詵詵”與“振振”;“揖揖”與“蟄蟄”;“薨薨”與“繩繩”這六個重言詞進行了綜合釋義,其中他認為:“振振,謂眾盛也。振振與下章繩繩、蟄蟄,皆為眾盛。”⑥[清]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1-53頁。這一說法雖然通過通假,也可以找到例證,但是三章同義,并不是最好的解釋。據本文綜合歷代注釋,“振”“蟄”“繩”三字的本義是有差異的,而馬氏將之混為一義,毫不區分,失去了詩意的層層遞進,足見這一觀點不可取。朱熹《詩經集傳》釋:“繩繩,不絕貌。”⑦[宋]朱熹:《詩經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頁。就與馬瑞辰的觀點不同,恰恰與筆者“末章側重子孫世代綿長”的觀點相一致。如此看來,今本《毛詩》以“蟄蟄兮”作結,其邏輯和詩意的遞進性就遠不如安大簡本“繩繩兮”收尾合理了。
三、安大簡本《螽斯》用韻及聲情特征
古人作詩,循天籟之自然,這一點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有精辟論述:“上古之時,先有語言,后有文字。有聲音,然后有點畫;有謠諺,然后有詩歌。謠諺二體,皆為韻語。‘謠',訓‘徒歌',歌者,永言之謂也。‘諺',訓‘傳言',言者,直言之謂也。蓋古人作詩,循天籟之自然,有音無字,故起源亦甚古。”①劉師培:《論文雜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110頁。語言不但表達意義,而且也表現聲與情,詞義與聲音情感是緊密相連的。《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毛詩正義》卷一之一《周南?關雎》,《十三經注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9-270頁。循天籟之自然產生的最早詩歌由不入韻,到像《螽斯》這種以韻文表達形式的出現,是與音樂的使用和發展有莫大的關系。
(一)安大簡本《螽斯》的用韻特征
從語言由簡到繁的發展看,出自《吳越春秋》、相傳黃帝時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兩句句式,語法結構簡單,這首歌可視為四言詩的雛形。③陳良運:《中國史學批評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頁。如安大簡本《螽斯》篇在詩句上,以二字(“詵”、“振”等六個疊字)四字(“螽斯之羽”“宜爾子孫”)為主組成三言,具有早期詩歌的特點。周嘯天認為:“在原始歌謠中,二言、三言曾經是主要的句子,由此發展到《詩經》的四言句式,……從二言到四言,看起來只是一步之遙,但實際上卻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④周嘯天:《先秦八代詩賦欣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商、周時代,以四言句作為一種語言逐漸規范,并開始向五、六言發展,則是有甲骨、鐘鼎上的文字可考。據王力的擬音,《周頌》無韻的詩有《清廟》《昊天有成命》《時邁》《噫嘻》《武》《酌》《桓》《般》⑤王力:《詩經韻讀 楚辭韻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48-358頁。。而《時邁》《我將》《賚》《酌》《般》《桓》《武》七篇為《大武》樂章的歌詞。⑥姚小鷗:《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的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72頁。從這些無韻詩篇中,足以想象早期詩的吟唱,純發乎于天然之性。陳致認為《詩經》中的詞語在兩周金文中都有對應的辭例,有時學者或以為是金文引用詩句,但實際上,并非引詩,而是金文和詩經都在用當時成語,如“以雅(夏)以南”“日就月將”“出入王命”等,這些成語實際也是在周人早期宗教活動中逐漸形成的。《周頌》諸篇在使用祭祀成語的過程中,也是句子由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的雜言逐漸變得規則,向四言形式發展,同時又有一種入韻化的傾向,而這種入韻的傾向,又與金文銘辭,特別是編鐘銘文逐漸變得規則,并且入韻,幾乎可以說是同步的。⑦陳致:《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陳致:《詩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頁,第3頁。他又以實例進一步解釋:“‘永寶用享'一詞正是金文韻文化過程中的自然產生的一個語詞,在西周早中期,銘文最后的祝愿詞一般都是‘永寶'‘永寶用'‘永用',另外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形式,之所以出現‘永寶用享'一詞,很可能是為了入韻,因為金文在韻文化時,最常見的是以陽部韻收結。……西周懿、孝時期的組及夷厲時期的眉縣楊家村逑組銅器上,最常見的格式是銘文最后以‘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的祝嘏之辭收結,其用韻的特點很明顯。”⑧陳致:《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陳致:《詩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頁,第3頁。“以陽部韻收結”也就是多以祝愿詞這種美好情懷的陽聲為尾音來表達。
整理者認為:“安大戰國楚簡《詩經》是目前發現的抄寫時代最早、存詩數量最多、保存最好的《詩經》抄本。”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新書發布會在合肥召開》,《古文字微刊》9月23日發布。杜澤遜認為安大簡是“戰國早中期”寫本。⑩杜澤遜:《如何認識安大簡〈詩經〉的價值——在安大簡發布會上的發言》,《文博山西休休文庫》9月23日發布。相應的雖安大簡本《螽斯》成篇的年代較早,但用韻是顯而易見的。首章詵、振,文部陽聲;次章揖、蟄,輯部入聲;末章薨、繩,蒸部陽聲。各章句數相等,字數相等,韻腳的位置相同,韻在篇中的位置整齊。其次章與末章順序:“眾斯之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輯部,入聲)。眾斯之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蒸部,陽聲)。”上文所言,金銘韻文多以陽聲收結,即具有多以祝愿詞這種美好情懷的陽聲為尾音表達的特點,與安大簡本《螽斯》篇末章以“繩”陽聲,表達“子孫世代綿長”這種美好期盼的情懷來收結完全一致。
《周南》中以陽聲收結的情況除了《螽斯》篇外,還見《樛木》耕部陽聲,一首祝賀新郎的詩;《桃夭》真部陽聲,一首祝賀新娘的詩;《兔罝》侵部陽聲,一首贊美獵人的詩;《漢廣》陽部陽聲,一首情歌;《麟之趾》真部陽聲,一首贊美子孫繁盛多賢的詩,計六篇。這些“祝賀”和“贊美”的詩篇,與《螽斯》一樣,均表達出一種美好的情懷。并且這種暢陽盎然的尾音韻律,出于天籟,是天真興致,不假于安排的。如此來看,安大簡本《螽斯》篇的章次排序比《毛詩》合理。
韻屬于形式層面,既與語篇意義密不可分,也是韻體詩的文體學特征,符號學特征。《螽斯》雖篇幅短小,內容簡單,但用韻整齊,詩意遞進,為其“聲情并茂”之體現做了很好的鋪墊。
(二)安大簡本《螽斯》的聲情表達
上博簡《孔子論詩》開篇就是孔子言論:“詩亡(無)隱志,樂亡(無)隱情,文亡(無)隱意。”①季旭升主編,陳霖慶、鄭玉姍、鄒濬智合撰:《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頁。可知春秋時期詩、樂、文是融為一體的,三者僅是一個事物的三個不同方面而已。②蔡先金等:《孔子詩學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第59頁。《尚書?堯典》亦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③江灝、錢宗武譯注,周秉鈞審校:《今古文尚書全譯?舜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頁。說明詩歌不但與音樂關系密切,而且在演唱時需要符合音調的要求。這時的詩歌,其實有著音樂藝術與文學藝術的雙重身份。
安大簡本《螽斯》入樂韻文“觸物寄情”。謝肇淛言:“詩者,人心之感于物而成聲者。風拂樹則天籟鳴,水激石則飛湍咽。夫以天地無心,木石無情,一遇感觸,猶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況于人乎!”④[明]謝肇淛著,江中柱點校:《小草齋詩話》卷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詩歌、音樂、舞蹈,都是屬于聽官,是“直接表情”的。⑤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22頁。《詩經》中收入的早期詩歌,或用以表現喜、怒、哀、樂性情;或表現耕作、衣食生活;或事鬼神,表現人類的虔誠、祈求風調雨順。“它們基本上處于自發的、隨機的狀態,往往是個人有感而發,表現個人的思想或感觸”⑥孫旭培:《華夏傳播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頁。。《周南》之詩都是入樂的韻文,安大簡本《螽斯》也是一樣:這是一首用于祈禱子孫眾多儀式的樂歌頌詩。詩人用螽斯多子,比人的多子。⑦程俊英:《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10頁。《禮記?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⑧《禮記正義》卷三七《樂記》,《十三經注疏》(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27頁。音樂的發生是建立在心物感應的基礎之上的。見該詩之開篇:“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禮記?仲尼燕居》載鄭注之言:“振羽,皆樂章也。”⑨《禮記正義》卷五O《仲尼燕居》,《十三經注疏》(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14頁。可見《螽斯》中的振羽是富于節奏樂感的情態動作。以“螽斯”隱喻繁育,是一種象征符號,人們在捕捉詩中“螽斯”這一生動形象的同時,用“宜爾子孫,振振兮;蟄蟄兮;繩繩兮”這樣一種具體的情感狀態,即“觸物寄情”,來領略詩人于字里行間洋溢著的,期盼子孫繁盛的情感寄托與表現。《螽斯》二、四句用六個虛詞“兮”為和聲來虛化聲腔,“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⑩[東漢]班固:《漢書?禮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038頁。,使得整篇誦讀起來,雖節拍簡單,無多變化,但似邊舞邊唱的風謠,熱情活潑,令人心動,回味無窮。
安大簡本《螽斯》樂歌頌辭“聲情并茂”。錢鐘書曾言:“詩者,藝之取資于文字者也。文字有聲,詩得之為調為律;文字有義,詩得之以侔色揣稱者,為象為藻,以寫心宣志者,為意為情。及夫調有弦外之遺音,語有言表之余味,則神韻盎然出焉。《文心雕龍?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聲文,情文。'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詠歌者,則論詩當如樂;好雕繪者,則論詩當如畫;好理趣者,則論詩當見道……。”①錢鐘書:《談藝錄》(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30-131頁。這里錢氏的形文、聲文、情文之論,實際上就是詩“辭情與聲情”②劉方喜:《聲情說——詩學思想之中國表述》,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第138頁。之表達方式,即“辭情”涉及語言之“義”,“聲情”則涉及語言之“音”。勞孝輿在《春秋詩話》中言:“樂與詩存,則樂為有聲詩。”③[清]勞孝輿:《春秋詩話》五卷,據嶺南遺書本排印,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黃志浩、陳平亦言:“詩歌最初本是可以演唱的歌辭,在演唱之時,歌辭受音樂曲調與節拍的制約,要符合音樂樂章的規定”;“當‘韻'和‘聲調'在藝術表現中成為人們共同遵守、約定俗成的某種規定與模式時,‘律'也就產生了”④黃志浩、陳平:《詩歌審美論》,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第172頁。。陳致認為:“《詩?周頌》諸篇與金文在西周中晚期都有韻文化的傾向,這是因為音樂的發展,樂鐘(按:有雙音效果)的規范化和定型化,使祭祀禮辭不斷朝著詩歌的方向發展所致。”⑤陳致:《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陳致:《詩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第28頁,第3頁。他還以西周晚期的豐白車父簋(集成4107)一例來證明其觀點,其銘文曰:“豐白車父作尊簋,用匄眉壽,萬年無疆,子孫是尚,子孫之寶,永孝用享。”五句中一、四以幽部為韻,二、三、五以陽部為韻,韻文所帶來的效果,令人回味。⑥陳致:《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陳致:《詩書禮樂中的傳統——陳致自選集》,第28頁,第3頁。
這里所言“二、三、五以陽部為韻”,宛如安大簡本《螽斯》篇二、四句各三字,六個重言詞連用,后加上“兮”,三字總的音長比前后四字的音要短。重言詞振振——蟄蟄——繩繩,本身讀來就極富節奏感,再與之相對應的韻腳陽聲——入聲——陽聲,全詩用這樣高低起伏,輕重相間,快慢不同的聲音和節奏,回還復沓,重章疊唱,聲情頓挫⑦[南朝宋]范曄:《后漢書?鄭孔荀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范曄評價漢末孔融:“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音情”即“聲情”。。這種歡快的節奏,既易配樂和演唱,又可施于禮儀,最能表達人們祝禱人子孫繁盛的美好情懷。“音樂為物,直接訴諸感情”⑧朱謙之:《中國音樂文學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第23頁。;“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⑨[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樂略·樂府總府》(全二冊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883頁。;“詩者聲教也,出于情性”⑩[宋]鄭樵:《詩辨妄?國風辨》,《六經奧論》卷三。。郭紹虞言:“舞必合歌,歌必有辭。所歌的辭在未用文字記錄以前是空間性的文學;在既用文字記錄以后便成為時間性的文學。此等歌辭當然與普通的祝辭不同;祝辭可以用平常的語言,歌辭必用修飾的協比的語調。”[11]郭紹虞:《韻文先發生之痕跡》,見《中國文學史綱要》,《國粹學報》第三十四期。轉引自朱自清:《中國歌謠》,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4頁。音樂與文學都是感情的自發表現。安大簡本《螽斯》篇聲韻宛轉,章意遞進,可以說這首詩從“語義”上能提供給我們的信息(即辭情)不多,但通過和諧的“語音”偏以“聲情”取勝,即以聲傳情,以情帶聲,聲情并茂,實現聲音跟情感的完美結合。正如《毛詩序》的“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12]《毛詩正義》卷一之一《周南?關雎》,《十三經注疏》(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70頁。,自然和諧。《螽斯》篇尤其以“繩”字陽聲結尾,“詩言盡而意長,歌止而音不絕”[13][明]顧炎武:《詩本音》卷一,《欽定四庫全書》經部十。,悠然聲于天地,暢然情于遐思。整個祝禱就似處在一種音樂性極強的氛圍中,且歌且舞的情境中,或用以他祝,或用以自祈。如此,感情單純,情緒事態單線發展,適宜于口頭傳唱。發乎天然,聲腔樂調悅耳動聽,給人以無限的遐想。很是應合了姚小鷗所言:“樂的自然屬性和功能(節律、音響、發乎人性、感于人心)。”①姚小鷗:《詩經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的演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4頁。
再來看《毛詩》中《螽斯》振振——繩繩——蟄蟄的用韻:陽聲——陽聲——入聲,以入聲收結,入聲字“蟄”有塞音韻尾[-P],塞而不破的發音特點,使得整篇詩的語音,由高亢快速下墜戛然而止,即聲腔被快速關閉,結束了詩的吟唱,爾無了聲音的張揚與闊放。反而具有了滯澀、頓挫感,表達出的情感是沉悶的,缺失了吟唱中的意猶未盡與淋漓盡致。這種情況亦見于《邶風?日月》篇,這是一位棄婦申訴怨憤的詩。寫一位婦女被丈夫遺棄,憤怒控訴其“逝不古處”“逝不相好”“德音無良”“畜我不卒”之罪過。其尾句:“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以“述”字物部入聲收結,該詩表達出的是一種悲切、怨憤、孤寂的情感。
上述對比《毛詩》以“蟄”入聲收結音調是沉悶的,在情感表達上遠沒有以“繩”陽聲收尾的音調暢陽;在聲情關系上就不那么悅耳和諧;在作品表現上與聲情配合有度的自然屬性也有了距離。由此看來,安大簡本的章次排序比《毛詩》合理。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提出如下一些認識。
第一,筆者認為《螽斯》是一首用于祝禱子孫眾多儀式的樂歌頌詩。該詩文辭簡樸質實,充滿土氣和天性。
第二,安大簡本若與《毛詩》中《螽斯》相比較,使用重言疊唱的藝術手法,表達主題,抒發情感,形成了邏輯和詩意的層層遞進,給人留下了深刻鮮明的印象。因此,就安大簡本《螽斯》之章次而言,首章側重子孫眾多興旺;次章側重子孫聚集歡暢;末章側重子孫世代綿長。此為十足的生命精神演進,惠及詩歌意境提升之例。如此排序,無論是邏輯還是詩意都富有層遞性。
第三,金銘韻文多以陽聲收結,即具有多以祝愿詞這種美好情懷的陽聲為尾音表達的特點,與安大簡本《螽斯》篇末章以“繩”陽聲,表達“子孫世代綿長”這種美好期盼的情懷來收結完全一致。這種暢陽向上的韻律,出于天籟,是天真興致,不假于安排的。
第四,振振——蟄蟄——繩繩,陽聲——入聲——陽聲,聲情頓挫,以聲傳情,以情帶聲,聲情并茂,自然和諧,實現聲音跟情感的完美結合。知《螽斯》篇以“繩”陽聲結尾,悠然聲于天地,暢然情于遐思。發乎天然,聲腔樂調悅耳動聽,給人以無限的遐想。對比《毛詩》以“蟄”入聲收結音調是沉悶的,在情感表達上遠沒有以“繩”陽聲收尾的音調暢陽;在聲情關系上就不那么悅耳和諧;在作品表現上也是不符合聲情配合有度的自然屬性。
總之,通過對《螽斯》詩旨簡要梳理以及章次順序的綜合考察分析,知安大簡本的章次排序比《毛詩》更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