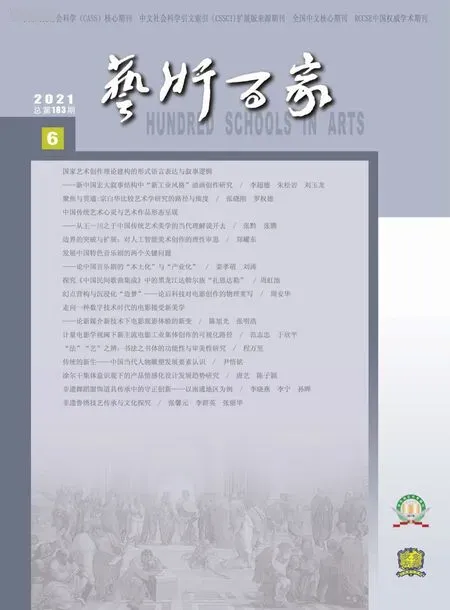建陽(yáng)刻書(shū)的輻射效應(yīng)?
宋文文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0013)
建陽(yáng)素有“圖書(shū)之府”之稱(chēng),所刻書(shū)籍“上自六經(jīng),下及訓(xùn)傳,農(nóng)桑牧醫(yī)、居家必備無(wú)所不包”[1]38。清代福建學(xué)者陳壽祺云:“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鄉(xiāng)鋟板以達(dá)四方,蓋十之五六。”[2]可見(jiàn)建陽(yáng)刻本發(fā)行量之大,傳播影響之深遠(yuǎn)。由于刻書(shū)從業(yè)者眾多,地理位置優(yōu)越,傳播面廣,建陽(yáng)刻本從八閩地區(qū)發(fā)源,進(jìn)而輻射到全國(guó)乃至國(guó)外。
一、建陽(yáng)刻書(shū)對(duì)福建地區(qū)的輻射效應(yīng)
兩宋時(shí)期,全國(guó)刻書(shū)官刻、家刻、坊刻三大系統(tǒng)均已形成。福建地區(qū)刻書(shū)以建陽(yáng)為中心,而建陽(yáng)的刻書(shū)以坊刻為主,官刻、家刻較少。建陽(yáng)地處閩北山區(qū),武夷山脈南麓,地勢(shì)蜿蜒險(xiǎn)要,自古為閩北要地。此地山高林密,緊臨浙江、江西,成為閩、浙、贛三地水陸往來(lái)的主要線(xiàn)路;福建與內(nèi)陸地區(qū)的交通路線(xiàn)主要經(jīng)過(guò)浦城、邵武、崇安、建陽(yáng)、建安、南平,而建陽(yáng)、建安、南平處于閩北走廊中心[3],而且早在唐代元和年間就開(kāi)通了閩北與閩東南的交通線(xiàn)路。唐末茶業(yè)重心由江蘇宜興轉(zhuǎn)移到福建,閩北建陽(yáng)一帶成為全國(guó)茶業(yè)貿(mào)易的集散地,高度發(fā)達(dá)的經(jīng)濟(jì)帶動(dòng)了其他文化事業(yè)發(fā)展,刻書(shū)業(yè)也借此發(fā)達(dá)起來(lái)。
福建為理學(xué)的重要發(fā)源地,朱熹就出生于建陽(yáng),并在此學(xué)習(xí)講學(xué)多年,故此地讀書(shū)人多,讀書(shū)風(fēng)氣濃厚,成為福建刻書(shū)業(yè)興盛的土壤。當(dāng)?shù)氐淖匀毁Y源優(yōu)勢(shì)為理學(xué)的迅速發(fā)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因此,建陽(yáng)刻書(shū)的影響作用也與閩學(xué)的展開(kāi)有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
(一)福州
受地理位置的影響,建陽(yáng)的坊刻在不同程度上對(duì)福建地區(qū)的坊刻、官刻、私刻均產(chǎn)生輻射效應(yīng)。福州自古為福州八閩中心城市,其經(jīng)濟(jì)繁榮,刻書(shū)業(yè)也比較發(fā)達(dá)。北宋時(shí)期,福州寺院刻書(shū)已經(jīng)很發(fā)達(dá),福州東禪寺、開(kāi)元禪寺等刊刻了大規(guī)模的毗盧藏、崇寧藏等大藏經(jīng)。南宋以后,由于建陽(yáng)刻書(shū)業(yè)發(fā)達(dá),具有寫(xiě)刻雕版紙張優(yōu)勢(shì),許多福建的官私刻本也是委托建陽(yáng)坊刻刊行的。紹興十二年(1142),汀州寧化縣刻本《群經(jīng)音辨》后有序:“寧化號(hào)稱(chēng)多士,部屬臨汀,新葺縣庠,衿佩云集。是書(shū)初下,繕寫(xiě)相先,字差毫厘,動(dòng)致魚(yú)魯。且患不能周給諸生,固請(qǐng)刻本藏于黌館,以廣其傳。嘯工東陽(yáng),閱月方就。……鏤版于學(xué)。”[4]“東陽(yáng)”為宋代建陽(yáng)的別稱(chēng),以上文字記載了從建陽(yáng)書(shū)坊招募刻工,為福建官府刊印書(shū)籍的史實(shí)。
還有不少書(shū)籍是委托建陽(yáng)書(shū)坊刊刻的,如宋淳祐年間福建常平提舉趙師耕在麻沙刊刻的《河南程氏遺書(shū)》[5]388,委托建陽(yáng)書(shū)坊刊行的《大元圣政國(guó)朝典章》。崇禎十五年(1642),福建巡按御史李嗣京等命建陽(yáng)知縣黃國(guó)琦刊刻《冊(cè)府元龜》一千卷,李嗣京《揭帖》載:“職昨奉命按閩,閩有建陽(yáng)縣,乃宋賢朱熹等講道之鄉(xiāng)。縣有書(shū)坊,自宋迄今,皆為刊刻古書(shū)之所。職因取家藏舊本,行分守建南道胡維霖,轉(zhuǎn)行建陽(yáng)縣知縣黃國(guó)琦厘訛補(bǔ)闕。職與道、縣和蠲嶄稟,爰付棗梨。二月始事,十月告成。”①
南宋時(shí)期,福州刻書(shū)中心地位逐漸被建陽(yáng)所替代,因此,官刻本亦多是延請(qǐng)建陽(yáng)書(shū)坊的刻工來(lái)刊刻,或直接交付建陽(yáng)書(shū)坊刊刻,其官刻本與建陽(yáng)刻書(shū)聯(lián)系緊密,相互影響。《張子語(yǔ)錄》中的牌記內(nèi)容為“后學(xué)天臺(tái)吳堅(jiān) 刊于福建漕治”。官刻本不以營(yíng)利為目的,一般不存在帶有宣傳性質(zhì)的牌記,但福州官刻本中卻有帶牌記的刻本,這也充分說(shuō)明福州刻書(shū)所受建陽(yáng)刻書(shū)影響之大。(圖1)

圖1 宋代福建漕治刻本《張子語(yǔ)錄》
(二)邵武
邵武古稱(chēng)昭武,兩宋時(shí)期,此地文風(fēng)鼎盛,名家輩出,與建陽(yáng)麻沙、崇化相距不遠(yuǎn),約30多公里。咸豐年間《邵武縣志》卷一《山川志》載:“樵城之西有山曰金鰲,郡治主山也。……正脈出龍山,……下鼓子嶺、崖嶺,通建陽(yáng)書(shū)坊。”②由于此地與建陽(yáng)相鄰,其刻書(shū)活動(dòng)及刻本風(fēng)格深受建陽(yáng)刻書(shū)影響。《中國(guó)版刻圖錄》著錄有邵武刻本《東萊標(biāo)注老泉先生文集》十二卷[6],目錄后有紹熙四年(1193)吳炎刻書(shū)咨文。著錄文:“十四行,行二十五字。注文雙行,行字同。目錄題東萊呂祖謙伯恭編注、若峰吳炎濟(jì)之校勘。[7]宋諱缺筆至慎字。吳炎校勘后,建陽(yáng)書(shū)肆為之梓行。”[8]37著錄不僅揭露出此書(shū)的版式特點(diǎn)與建陽(yáng)刻本極為相似,而且其刊行之地就在建陽(yáng),此地的刻書(shū)活動(dòng)與建陽(yáng)關(guān)系緊密。
又如余聞中于宋嘉泰二年(1202)刻印《儒學(xué)警悟》四十卷,此刻本目錄后有嘉泰辛酉(1201)建安俞成元德父跋。俞成是崇化書(shū)林云衢人,曾為建陽(yáng)蔡夢(mèng)弼校書(shū),因此,此刻本極有可能是在建陽(yáng)刊刻的。[9]106
(三)南劍州
南劍州古稱(chēng)南平,北宋太平興國(guó)四年(979)更命為南劍州,此地距建寧府60公里,距離建陽(yáng)約120公里,是閩北通向省城的必要之地。南宋時(shí)期,南劍州刊本《龜山別錄》的刊刻者為劉炳,此人是朱熹門(mén)人,曾受朱熹委托于建陽(yáng)刊刻此書(shū)。③
(四)建寧
建寧古稱(chēng)建安,今是建甌,南宋為建寧府,而建陽(yáng)由建寧府管轄,故建寧府的官私刻本基本都在建陽(yáng)刊刻。此外,還有福建路駐守在建寧的派出機(jī)構(gòu),如福建轉(zhuǎn)運(yùn)司、福建常平司等也在建陽(yáng)刻書(shū)。[9]55
鄰府縣刻書(shū),雖不完全是在建陽(yáng)刊刻,但有一部分刻本是與建陽(yáng)書(shū)坊有關(guān)系的。明代王瓚在建安楊允寬刻印的文集中有序云:“公集曰《兩京類(lèi)稿》、曰《玉堂選稿》者,公冢子允寬符卿梓行已久,板藏書(shū)坊,燬于回祿。”[9]378文中的書(shū)坊是指建陽(yáng)書(shū)坊,建安的家刻本是委托建陽(yáng)書(shū)坊刊刻的。
(五)泉州、漳州
宋元時(shí)期,泉州港為著名的國(guó)際貿(mào)易港,北宋黃祐年間(1049—1054),泉州人口已達(dá)80萬(wàn),經(jīng)濟(jì)繁榮,相較于福建其他地區(qū),其圖書(shū)貿(mào)易活動(dòng)更為繁榮。這里的官私刻本也有不少是在建陽(yáng)刊刻的。如宋淳熙七年(1180),學(xué)者程大昌出守泉州,泉州市舶彭椿年得到程大昌的《禹貢論》《演繁露》等,到元明兩代一直有官刻交給書(shū)坊承刻的傳統(tǒng),如明代晉江蔡清《易經(jīng)蒙引》亦由朝廷下旨發(fā)往建陽(yáng)書(shū)坊刊刻。
泉州的刻書(shū)業(yè)也受朱熹影響,據(jù)說(shuō)泉州的刊工密布在涂門(mén)城外的田庵村一帶,而田庵村的版刻技術(shù)就是朱熹傳授的,按照田庵村舊俗,每年的農(nóng)歷二月十五都要祭祀“祖師朱文公”[10]74。
漳州位于閩西區(qū)域,與廣東省相連,此區(qū)域還包括廈門(mén)、泉州等地。漳州與朱熹考亭派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在這之前此地幾乎無(wú)刻書(shū)記載。
朱熹于紹熙元年(1190)任漳州知府。任職期間對(duì)漳州刻書(shū)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推動(dòng)作用。朱熹在漳州不到一年的時(shí)間里,主要刊刻《易》《詩(shī)》《書(shū)》《詩(shī)經(jīng)》《大學(xué)》《中庸》《論語(yǔ)》《孟子》《近思路》等十幾種書(shū)籍。
朱熹對(duì)漳州、泉州等地的刻書(shū)事業(yè)影響巨大,清代有名的泉州洪氏書(shū)坊便是受他的影響而發(fā)展壯大的。“他們?nèi)鍙氖驴贪婕夹g(shù),與朱熹來(lái)泉講學(xué)有關(guān)。……一世祖洪榮山,從朱熹學(xué)習(xí)金石鐫刻,初以鐫刻私章,逐漸發(fā)展到木刻乃至?xí)妗!盵11]301漳泉刻書(shū)的繁榮,得益于朱熹早期在建陽(yáng)書(shū)坊的刻書(shū)實(shí)踐。[12]因此,福建漳州、泉州的刻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建陽(yáng)書(shū)坊的影響。
二、建陽(yáng)刻書(shū)對(duì)全國(guó)的輻射效應(yīng)
(一)朱熹弟子對(duì)建陽(yáng)刻書(shū)事業(yè)的促進(jìn)作用
朱熹從事刻書(shū)的主要地點(diǎn)在建陽(yáng),他在閩北山區(qū)居住幾十年,為滿(mǎn)足教育和研究需要,他充分利用當(dāng)?shù)貎?yōu)越的刻書(shū)條件,刊刻了大量儒家經(jīng)典及自己的著述。[13]朱熹開(kāi)創(chuàng)的考亭學(xué)派是眾多學(xué)派中與刻書(shū)關(guān)系最為密切的學(xué)派,他在武夷精舍還刊有《小學(xué)》六卷等,他本人也考訂撰寫(xiě)《韓文考異》十卷、《周易參同契考異》一卷。這些書(shū)籍曾多次被建陽(yáng)書(shū)坊翻刻。朱熹大半生都在閩北度過(guò),在建陽(yáng)撰寫(xiě)的著作絕不在少數(shù),據(jù)嘉靖《建陽(yáng)縣志·書(shū)坊書(shū)目》中所列出的書(shū)目,朱熹的著作為建陽(yáng)書(shū)坊提供了大量書(shū)稿,如《四書(shū)集注》《小學(xué)》《近思錄》等。朱熹在建陽(yáng)長(zhǎng)期從事教學(xué)與刻書(shū),門(mén)人也受到他的影響,既從事學(xué)術(shù)研究,也從事刻書(shū)事業(yè)。他的許多門(mén)人弟子如蔡元定、蔡沈、黃干、劉爚等都有書(shū)稿為建陽(yáng)書(shū)坊所刊刻。[14]96-98
朱熹也在浙江、江西、湖南等地?fù)?dān)任過(guò)地方官,所到之地,皆有刻書(shū),而他在閩時(shí)間最長(zhǎng)。建陽(yáng)的刻書(shū)技藝在當(dāng)時(shí)堪稱(chēng)一流,其所刻書(shū)籍必帶有明顯的“建本”特征。可以說(shuō),朱熹對(duì)建陽(yáng)刻書(shū)在全國(guó)的輻射效應(yīng)發(fā)揮了較大作用。[15]
江西也是文化發(fā)達(dá)、刻書(shū)興盛的地區(qū),朱熹從福建到江西,很大程度上也將建陽(yáng)刻書(shū)傳到了江西地區(qū)。如朱熹于淳熙六年(1179)擔(dān)任南康知軍,刊刻《周子通書(shū)遺文遺事》;同年又刊刻胡明仲《敘古千文》;次年在白鹿洞書(shū)院刊刻包拯的《包孝肅詩(shī)》。④李致忠《宋代刻書(shū)述略》:“坊肆遍及全國(guó)各地,特別是浙、蜀、閩、贛、皖尤盛。”[16]145-174盡管當(dāng)?shù)爻霭鏄I(yè)也比較發(fā)達(dá),但與建陽(yáng)相比,江西地區(qū)刻書(shū)地點(diǎn)雖多,但顯得較分散,不像建陽(yáng)刻書(shū)那么集中。在刻書(shū)人才方面,建陽(yáng)的幾大刻書(shū)家族,保障了專(zhuān)業(yè)人才的資源供給,而江西在此方面則不如建陽(yáng)。但在朱熹及其門(mén)人弟子的推動(dòng)下,江西刻書(shū)事業(yè)有了一定的改觀。端平二年(1235),朱熹之孫朱鑒將《楚辭集注》《易學(xué)啟蒙》等書(shū)刊行于南康,其中《楚辭集注》后有“南宋槧初刊本,鐫刻精善,裝池古雅”之贊譽(yù)。此本無(wú)論從版式還是字體上看,皆與同時(shí)期建陽(yáng)刻本十分相似。
原刊本《楚辭集注》與建陽(yáng)刻本余仁仲《禮記》字體皆有南宋建陽(yáng)刻本風(fēng)格,即“多似柳體,方正嚴(yán)謹(jǐn)、瘦勁疏朗”[8]36,版式基本遵循南宋建陽(yáng)官刻本的特點(diǎn),一般以半頁(yè)十行為主,字大行疏(圖2)。私刻坊刻多在十行以上,并且行密字細(xì)。

圖2 宋代原刊本朱鑒《楚辭集注》(北京國(guó)家圖書(shū)館影印本)(左);
建陽(yáng)對(duì)江西贛州、南昌、廬陵等地的刻書(shū)影響最為明顯,其字體與版式都與建陽(yáng)刻書(shū)十分相似,廬陵刊本《皇元朝野詩(shī)集》《資治通鑒綱目》,無(wú)論字體還是版式其特征都與同時(shí)期建刻風(fēng)格極為相近。(圖4、圖5)從流傳后世的刻本中不難發(fā)現(xiàn),古代江西刻本所受建陽(yáng)刻本影響最深。究其原因,不僅是閩學(xué)的推動(dòng),而且是在江西地區(qū)許多建陽(yáng)刻工被雇傭從事刻書(shū)業(yè),還是建陽(yáng)書(shū)商在江西開(kāi)設(shè)書(shū)坊,印售書(shū)籍。朱熹的許多建陽(yáng)籍弟子門(mén)人在江西從事刻書(shū)行業(yè)。(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在下文中有敘述)同時(shí),朱熹培養(yǎng)了大批閩學(xué)門(mén)人,不斷吸引著外地文人到此地學(xué)習(xí)。這些學(xué)者來(lái)自五湖四海,他們的匯集對(duì)建陽(yáng)刻書(shū)意義重大,不僅大大提高了刻書(shū)的銷(xiāo)售量,而且這些朱熹門(mén)人更是刻書(shū)事業(yè)的直接參與者。

圖3 建陽(yáng)余仁仲萬(wàn)卷堂刻本《禮記》(右)

圖4 廬陵刊本《皇元朝野詩(shī)集》(左);

圖5 廬陵刻本《資治通鑒綱目》(右)
據(jù)臺(tái)灣學(xué)者陳榮捷統(tǒng)計(jì),朱熹門(mén)人467人,其中福建人164人,居全國(guó)首位,浙江80人左右,江西79人。[17]106還有來(lái)自廣東、湖南、湖北等地的學(xué)子,他們學(xué)成歸鄉(xiāng)后,在各地又陸續(xù)刊行儒家經(jīng)典。朱熹學(xué)派從事出版業(yè),形成學(xué)派刻書(shū)之效應(yīng),其刊行的書(shū)籍在版式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也帶有建陽(yáng)刻本的風(fēng)格特征。
朱熹所收的建陽(yáng)本地門(mén)人弟子中,還有不少在外地刊刻儒家經(jīng)典,如劉爚在浙江杭州刊刻“四書(shū)五經(jīng)”,閩縣黃榦在江西刻書(shū),建陽(yáng)蔡杭等在廣東刻書(shū)。[13]所刻書(shū)籍皆出自建陽(yáng)的朱熹門(mén)人之手,故或多或少帶有建陽(yáng)版刻的特點(diǎn)。
朱熹所收的“外地”學(xué)生中,有些也在學(xué)成之后將閩學(xué)及刻書(shū)帶到了各自的家鄉(xiāng),他們利用書(shū)籍來(lái)宣傳理學(xué)思想。如曾在浙江刻書(shū)的朱門(mén)弟子呂橋年,字巽伯,浙江金華人,于嘉泰四年(1204)刊刻呂祖謙《東萊呂太史文集》十五卷、《別集》十六卷、《外集》五卷[18]344,還刻有呂祖儉《麗澤論說(shuō)集錄》十卷、《附錄》三卷、《拾遺》一卷[19]。
建陽(yáng)所處之地水路繁復(fù),這些水路還貫穿湖南、廣東等地,故這兩地也有不少朱熹門(mén)人從事刻書(shū)事業(yè)。湖南刻書(shū)的朱門(mén)弟子葉武子,字成之,福建邵武人,在嘉定期間官至郴州教授,曾刻印朱熹《四書(shū)集注章句》。廣東刻書(shū)的朱門(mén)弟子張洽(1161—1237),字元德,江西清江人,于紹定二年(1229)刻印朱熹《韓文考異》十卷[13]。廣西刻書(shū)的朱門(mén)弟子詹儀之,字體仁,淳熙十一年(1184)任官于靜江府,刊行朱熹《四書(shū)集注》[19]。在安徽刻書(shū)的朱門(mén)弟子張洽(1161—1237),字元德,曾任池州通判,于紹定二年(1229)刊刻《韓文考異》十卷[13]。李道傳(1170—1217)曾提舉江東常平,于嘉定八年(1215)在池州刻印《晦庵先生語(yǔ)錄》四十三卷[13]。此外,在湖北刻書(shū)的朱門(mén)弟子劉清之(1134—1190)于淳熙十三年(1186)在鄂州任通判,刊《小學(xué)》六卷、《文集》卷五十、《鄂州小集》等;趙師夏,字致道,嘉定九年(1216)任知興國(guó)軍,與軍學(xué)教授聞人模一同刊刻晉杜預(yù)《春秋經(jīng)傳集解》三十卷(圖6);吳仁杰,字斗南,慶元六年(1200)任湖北羅田知縣,刊刻《兩漢刊誤補(bǔ)遺》十卷、《離騷草木疏》四卷[13]。

圖6 趙師夏、聞人模刊刻《春秋經(jīng)傳集解》(宋刻本,現(xiàn)藏于南京圖書(shū)館)
趙師夏、聞人模同刊的《春秋經(jīng)傳集解》刻本,不論字體還是版式特點(diǎn)都與同時(shí)期建陽(yáng)刻本十分相似。從留存于世的朱熹門(mén)人在各地的刻書(shū)情況來(lái)看,江西、湖南、廣東等地的刻本明顯帶有建陽(yáng)刻的書(shū)風(fēng)格特征。
(二)建陽(yáng)人氏到外地刻書(shū),版刻風(fēng)格輻射全國(guó)
除了朱學(xué)門(mén)人在全國(guó)各地刊書(shū)外,也有許多建陽(yáng)人在外地刻書(shū)。如熊克在乾道年間任鎮(zhèn)江教授期間,刻印了晉王弼《老子注》等[9]76;宋慈在湖南刊刻了自己所著的《洗冤集錄》;朱鑒在任江西興國(guó)軍期間刊刻了朱熹著的《楚辭集注》。這些活動(dòng)不僅促進(jìn)了建陽(yáng)與全國(guó)各地版刻技藝的交流,而且也推動(dòng)了建陽(yáng)刻書(shū)文化的傳播,為建陽(yáng)刻書(shū)輻射全國(guó)及海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
元明時(shí)期,建陽(yáng)刻書(shū)世家如余氏、劉氏、熊氏等有到外地刻書(shū)的經(jīng)歷。如蕭騰鴻師儉堂葉貴近山書(shū)舍刻本《新刊名儒舉業(yè)分類(lèi)注釋百子萃言》六卷,題有“金陵三山街建陽(yáng)近山葉貴梓”[9]357(圖7);建陽(yáng)朱桃源遷居北京,與金陵書(shū)林晏少溪合刊書(shū)籍;還有建陽(yáng)著名的刻工、版畫(huà)家劉素明,也為刻書(shū)經(jīng)常往來(lái)建陽(yáng)、金陵、杭州等地。

圖7 蕭騰鴻師儉堂葉貴近山書(shū)舍刻本《新刊名儒舉業(yè)分類(lèi)注釋百子萃言》(建陽(yáng)人氏葉貴于金陵三山街書(shū)坊刊刻)
明代成化年間永順堂刊刻的說(shuō)唱詞話(huà)刻本中,九處牌記都印有北京順書(shū)堂刊,但觀其刻本版刻風(fēng)格、插圖、字體等,與元至治建安虞氏刻本《全相平話(huà)五種》十分相似,有關(guān)此刻本的來(lái)源問(wèn)題,已有學(xué)者對(duì)此進(jìn)行研究,如俞子林在其《明成化永順堂刻本說(shuō)唱詞話(huà)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20]23一文中,根據(jù)其中一篇《包龍圖斷歪烏盆傳》的牌記內(nèi)容“書(shū)林永順堂刊行”,就“書(shū)林”的來(lái)源作了細(xì)致分析,稱(chēng)將成化說(shuō)唱詞從“北京刻本”改為“建安刻本”比較合理,并說(shuō)明此書(shū)應(yīng)為“書(shū)林永順堂”刊刻,而“北京新刊”只能說(shuō)明此本的來(lái)源,并非永順堂的地點(diǎn)。筆者認(rèn)為,北京永順堂地處北京,又刊刻有“北京新刊”,因此此刻書(shū)應(yīng)該是北京刻本,從此套唱詞刻本的牌記及版式特點(diǎn)可以看出建陽(yáng)刻書(shū)的影響,這說(shuō)明建陽(yáng)刻書(shū)字體影響了北方,北京、太原前期刻書(shū)都是建陽(yáng)的顏體字,如成化年間山西太原善敬堂刊刻的《論語(yǔ)集注大全》,字體版式完全與建陽(yáng)刻本相同。這種情況可以看作是建陽(yáng)刻書(shū)的輻射影響,當(dāng)然從中也可推測(cè)出,建陽(yáng)的書(shū)商可能到北京刻書(shū)。
(三)建陽(yáng)刊刻的通俗文學(xué)書(shū)籍行銷(xiāo)全國(guó)
目前所見(jiàn)宋代私刻本書(shū)目,以經(jīng)史子集與各種名人詩(shī)文集為主。在古代傳統(tǒng)文人眼中,小說(shuō)戲曲通俗類(lèi)書(shū)籍向來(lái)不登大雅之堂。隨著南宋經(jīng)濟(jì)的繁榮發(fā)展,市民階層對(duì)精神文化層面有了更高需求。就在這一時(shí)期,善于經(jīng)營(yíng)的建陽(yáng)書(shū)坊主結(jié)合自身?xiàng)l件,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商機(jī)。與當(dāng)時(shí)處在政治、經(jīng)濟(jì)中心的其他出版地不同,建陽(yáng)位于偏遠(yuǎn)地區(qū),出版書(shū)籍的客觀條件較為寬松。于是,建陽(yáng)書(shū)商們從原本有限的文人學(xué)士文化圈中突破出來(lái),將刊印的目光擴(kuò)大到市民階層,為了迎合市民的喜好和需求,他們大量刊行尺牘、酬世大全、小說(shuō)故事等實(shí)用和消遣類(lèi)通俗文學(xué)書(shū)籍,以滿(mǎn)足民間需求。建陽(yáng)書(shū)坊刊刻了大量通俗筆記小說(shuō),如《山海經(jīng)圖》《龍城錄》《揮麈錄》《括異記》《四朝聞見(jiàn)錄》等七種;通俗話(huà)本小說(shuō)有《宣和遺事》等三種[21]160。同時(shí),平話(huà)小說(shuō)盛行,宋代的麻沙書(shū)坊刊發(fā)過(guò)《五代史平話(huà)》五種,元代至治年間(1321—1323)建安虞氏刊刻的《新刊全相平話(huà)武王伐紂書(shū)》三卷、《新刊全相平話(huà)樂(lè)毅圖齊七國(guó)春秋后集》三卷、《新刊全相秦併六國(guó)平話(huà)》三卷、《新刊全相平話(huà)前漢書(shū)續(xù)集》三卷、《至治新刊全相平話(huà)三國(guó)志》三卷,統(tǒng)稱(chēng)“元至治刊平話(huà)五種”,這是繼南宋末年《五代史平話(huà)》之后的又一套平話(huà)小說(shuō)[22]40-41。元代建安虞氏刻過(guò)《樂(lè)毅伐齊》《全相平話(huà)》,今藏于日本內(nèi)閣文庫(kù)。
元人喜歡寫(xiě)曲,散曲更多。元代北人散曲和民間通俗文學(xué)的評(píng)話(huà)小說(shuō)也在建陽(yáng)書(shū)坊刊行。建陽(yáng)書(shū)坊刊有《朝野新聲太平樂(lè)府》《樂(lè)府新編陽(yáng)春白雪》等,其中有一本《新編紅白蜘蛛小說(shuō)》,雖然只有殘頁(yè)遺存下來(lái),也可見(jiàn)其通俗文學(xué)的特色。
明代著名文學(xué)家徐渭曾這樣描繪建陽(yáng)書(shū)坊:“其圖籍書(shū)記,輻輳錯(cuò)出,坊市以千計(jì),富商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不能周也。”⑤建陽(yáng)書(shū)坊所刊的大量戲曲小說(shuō)、故事唱本、應(yīng)用酬世等迎合中下層百姓讀書(shū)興趣的通俗類(lèi)書(shū)籍,皆為當(dāng)時(shí)圖書(shū)市場(chǎng)所不屑,但卻能被建陽(yáng)書(shū)坊經(jīng)營(yíng)成為全國(guó)暢銷(xiāo)之書(shū),這些書(shū)籍品種齊全,無(wú)所不包,價(jià)格低廉,當(dāng)?shù)乇憬莸乃方煌l件,也為建陽(yáng)書(shū)籍行銷(xiāo)全國(guó)提供了便利。
三、建陽(yáng)刻書(shū)對(duì)海外的輻射效應(yīng)
日本、朝鮮與中國(guó)毗鄰,與中國(guó)文化交流密切。他們都鐘愛(ài)中國(guó)的書(shū)籍,在唐代,來(lái)自朝鮮的和尚、留學(xué)生就有一百多人,他們用自己國(guó)家給的購(gòu)書(shū)費(fèi),購(gòu)買(mǎi)帶回了許多佛家、儒家經(jīng)典。日本有堪稱(chēng)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寶龜本《無(wú)垢凈光經(jīng)根本陀羅尼》(770)等四種,這些書(shū)籍也是日本與中國(guó)有書(shū)籍文化往來(lái)的最好見(jiàn)證。元初建陽(yáng)學(xué)者熊禾在《上梁文》中言:“書(shū)籍高麗日本同……萬(wàn)里車(chē)書(shū)通上國(guó)。”[23]804-805根據(jù)相關(guān)著述,宋元時(shí)期建陽(yáng)刻本書(shū)籍,現(xiàn)在日本、美國(guó)、英國(guó)等許多國(guó)家圖書(shū)館均有收藏或翻刻。
朱子學(xué)從高麗末期開(kāi)始傳到朝鮮,其中最關(guān)鍵的媒介就是圖書(shū)。高麗忠烈王十五年(1289),高麗使臣安珦從元大都帶回一批朱子著作,如《朱文公文集》《四書(shū)集注》《朱子語(yǔ)類(lèi)》等[24],并在高麗講授,安珦也因此成為將朱子學(xué)術(shù)傳入朝鮮的第一人。此后,其門(mén)人權(quán)溥(1242—1326)刊行《四書(shū)集注》,對(duì)朱熹學(xué)說(shuō)在朝鮮的傳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dòng)作用。[25]227
明成祖賜給朝鮮一批珍貴物資,其中包括建陽(yáng)刊刻的《十八史略》《山堂考索》《諸臣奏議》《春秋會(huì)通》《朱子成書(shū)》等書(shū)籍。[26]369除了朱子學(xué)說(shuō)書(shū)籍外,元明建陽(yáng)小說(shuō)刻本也為數(shù)不少,在朝鮮也十分受歡迎,如瞿佑的《剪燈新話(huà)》、羅貫中的《三國(guó)志通俗演義》、熊大木的《南北宋志傳》《武穆王精忠傳》、余象斗的《新刻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等。[27]18
建陽(yáng)刻書(shū)傳入日本大約始于南宋時(shí)期,清代楊守敬《藏書(shū)絕句足利本》有言:“秘書(shū)流播海天東,訪(fǎng)古遺文島國(guó)通。讀罷七經(jīng)開(kāi)寶笈,傳來(lái)足利闡儒宗。”[28]15可見(jiàn)中國(guó)書(shū)籍在日本傳播傳統(tǒng)儒家學(xué)說(shuō)起到重要作用。明清時(shí)期,從中國(guó)流傳到日本的書(shū)籍已經(jīng)成為海外貿(mào)易商品之一,這些書(shū)籍多為建陽(yáng)刊刻的《水滸傳》《三國(guó)志演義》《西游記》《西廂記》《萬(wàn)錦情林》等通俗類(lèi)讀物[25]226。
除了購(gòu)買(mǎi)書(shū)籍外,日本、韓國(guó)還翻刻了許多建陽(yáng)刻本圖書(shū),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日韓各國(guó)公藏單位的書(shū)目,多是從建陽(yáng)流傳到日本的(日、韓覆刻過(guò)的建陽(yáng)刻本多達(dá)約幾百種,但尚無(wú)人對(duì)此做過(guò)認(rèn)真統(tǒng)計(jì))。日本國(guó)立公文書(shū)館“內(nèi)閣文庫(kù)”藏有日本南北朝時(shí)期(1336—1386)覆刻的元代至正年間翠巖精舍元刻本《聯(lián)新事備詩(shī)學(xué)大成》刊本,字體與元代建本字體非常接近,刻書(shū)版式甚至牌記都照原版覆刻,幾乎與原本無(wú)甚差異。此外,朝鮮也翻刻了不少建陽(yáng)刻書(shū),如宋代建陽(yáng)刻本《杜工部草堂詩(shī)箋》、元代建陽(yáng)余志安勤有堂刻本《銅人腧穴針灸圖經(jīng)》、明代劉文壽翠巖精舍刻本《增修附注資治通鑒節(jié)要續(xù)編》,均有朝鮮銅活字印本。[25]228
四、結(jié)論
兩宋時(shí)期,建陽(yáng)成為福建刻書(shū)業(yè)的中心,并成為全國(guó)三個(gè)刻書(shū)中心地之一,其優(yōu)越的自然資源條件和深厚的人文環(huán)境使得建陽(yáng)刻本對(duì)福建其他地區(qū)以及江西地區(qū)產(chǎn)生重要影響。宋代是閩學(xué)發(fā)展的興盛時(shí)期,朱熹久居建陽(yáng),在此地參與建學(xué)、撰書(shū)、刻書(shū)等活動(dòng),其門(mén)人弟子學(xué)成后也在閩、浙、贛、粵、湘、鄂等地參與刻書(shū)。這種以鑄造新儒學(xué)為目標(biāo)的群體性刻書(shū)活動(dòng),對(duì)整個(gè)建陽(yáng)的出版業(yè)在全國(guó)的傳播與發(fā)展,無(wú)疑產(chǎn)生了極大的推動(dòng)作用。
宋元時(shí)期,我國(guó)已經(jīng)同世界近十個(gè)國(guó)家開(kāi)始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貿(mào)往來(lái),而泉州等地正是我國(guó)對(duì)外貿(mào)易的重要港口,建陽(yáng)書(shū)籍就是通過(guò)這種方式傳播到海外的,從海外留存的建陽(yáng)刻書(shū)數(shù)量以及當(dāng)時(shí)各國(guó)的刻書(shū)情況可知,建陽(yáng)刻書(shū)為這些國(guó)家?guī)?lái)了重要文化影響。因此,古代建陽(yáng)刻書(shū)在保存和弘揚(yáng)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促進(jìn)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
① 宋代王欽若在《冊(cè)府元龜》(明鈔本)第10頁(yè)中記載了李嗣京的《揭帖》,此本為南京圖書(shū)館影印本。
② 清代王琛修、張景祁纂的《光緒重纂邵武府志》中記載了通往建陽(yáng)書(shū)坊的地形描述。此本為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本第30卷,南京圖書(shū)館影印本,第59—60頁(yè)。
③ 朱熹《續(xù)集》(卷四下)《答劉韜仲》記載:“《山記》乃煩重刻,愧甚。不知所費(fèi)幾何?今卻勝前本矣。《龜山別錄》刊行甚善,跋語(yǔ)今往,幸附之。”
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記載,這是其擔(dān)任南康知軍所刊刻的書(shū)目。此本為景上海涵芬樓藏明刊本2卷,南京圖書(shū)館影印本,第3847頁(yè)。
⑤ 明代徐渭《青藤書(shū)屋文集》中有此記載。此本為清海山仙館叢書(shū)本30卷,南京圖書(shū)館影印本,第398頁(yè)。
- 藝術(shù)百家的其它文章
- 非對(duì)象性美學(xué)的建構(gòu)與藝術(shù)學(xué)理論知識(shí)的有效增長(zhǎng)?
——評(píng)趙奎英等著《美學(xué)基本理論的分析與重建》 - 音樂(lè)與詩(shī)歌的繾綣?
——評(píng)《音樂(lè)文化與盛唐詩(shī)歌研究》 - 論《清河書(shū)畫(huà)舫》的體例創(chuàng)新?
- 《歷代名畫(huà)記》的繪畫(huà)史價(jià)值與影響?
- 三極貫通的影像之橋?
——2020北京師范大學(xué)“看中國(guó)·外國(guó)青年影像計(jì)劃”十周年國(guó)際學(xué)術(shù)論壇綜述 - 聚焦影視藝術(shù)新前沿 共譜影視教育新華章?
——中國(guó)高等教育學(xué)會(huì)影視教育專(zhuān)業(yè)委員會(huì)2020中國(guó)影視藝術(shù)高峰論壇綜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