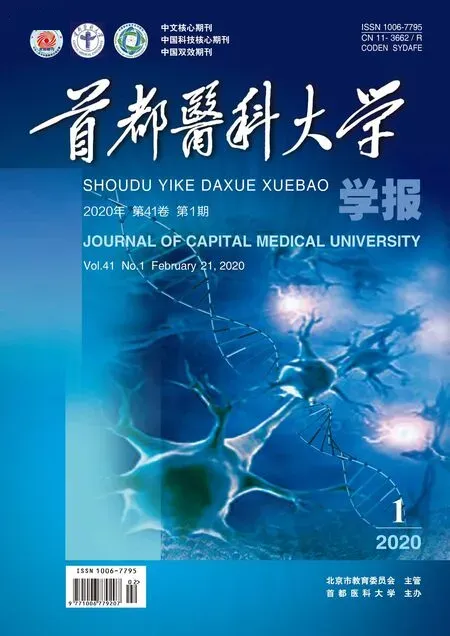ICU中心靜脈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的危險因素及病原菌分析
喬 莉 曹 洋 袁宏勛* 王 瑤
(1.北京大學國際醫院重癥醫學科,北京 102206; 2.北京大學國際醫院感染控制部,北京 102206)
近年來,中心靜脈導管(central venous catheter,CVC)在重癥醫學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得到了廣泛應用,適應證為需要進行血流動力學監測、快速擴容補液、全腸外營養、血液凈化等治療的患者。北京大學國際醫院成立于2014年12月,隨著醫院的發展,各科患者數量日益增多,綜合ICU收治危重癥患者數量逐年上升,中心靜脈引起的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catheter-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CRBSI)發生率亦隨之上升。本文旨在通過對在北京大學國際醫院ICU中留置CVC及已發生CRBSI患者的調查,分析CRBSI的相關危險因素,了解CRBSI患者病原菌的分布情況,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以減少CRBSI的發生,降低病死率。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本院綜合ICU留置過CVC的患者674例,結合臨床資料回顧,明確診斷CRBSI的28名患者,共培養36株病原菌。
1.2 方法
1)CRBSI的診斷標準:根據美國感染學會(Infectious Disease Society of America,IDSA)指南[1],使用半定量方法培養留取導管的尖端5 cm,菌落數在15 cfu以上或定量培養菌落數大于102cfu且排除其他部位感染所致的符合以下條件之一:(1)導管尖端處有至少1處與外周血培養出相同病原菌;(2)分別從不同的兩個導管腔留取血培養,而其中的一份至少是另一份菌落計數的3倍以上;(3)經過導管留取血培養的菌落計數大于外周靜脈血培養的3倍以上;(4)在導管留取血培養比外周靜脈血培養出現陽性結果的時間要提前至少2h。
2)排除標準[2]:(1)未滿18周歲者;(2)入ICU前已出現可疑的CRBSI患者;(3)收入ICU未滿48 h轉出、死亡或放棄治療者(包括短期外科術后麻醉復蘇者),或ICU內CVC放置時間未滿48 h者;(4)多次收入ICU者;(5)臨床資料不全者。
3)調查內容:患者姓名、性別、年齡、病歷號、入院診斷、基礎疾病情況、入院時間、出院時間、住院天數、入ICU時間、出ICU時間、ICU住院天數、預后轉歸,置管部位、置管醫師、留置導管時間、中心靜脈置管次數,是否進行外科手術、是否建立人工氣道,是否免疫力低下,是否大劑量使用抗生素,入ICU時是否動脈血乳酸≥2.0 mmol/L,入ICU后24 h內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評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II評分),發生CRBSI過程中是否存在消化道出血、低蛋白血癥。患者基礎疾病指:循環系統疾病,包括高血壓、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心力衰竭等;肺部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氣管哮喘、間質性肺病等慢性疾病;糖尿病,包括1型及2型糖尿病;腎臟疾病,包括慢性腎功能不全、終末期腎病及慢性腎小球疾病等;肝臟疾病,包括慢性活動性肝炎、肝硬化等;惡性腫瘤,包括各種實體瘤晚期、血液系統惡性腫瘤等。大劑量使用抗生素指患者同時使用3種及3種以上抗生素,且使用上述抗生素時間超過7 d。
4)儀器:采用美國Becton Dickinson公司的BACTEC FX血培養儀及該公司Phoenix100全自動微生物分析系統。
1.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CRBSI發生率分析
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綜合ICU收治總人數為2 677人,中心靜脈置管總例數674例,置管總天數6 197 d,發生CRBSI者28例,感染例數率為4.15%,感染率為4.52‰。
2.2 CRBSI危險因素分析
將患者分為感染組與非感染組,以是否發生CRBSI為因變量,將患者的性別、是否高齡(年齡≥75歲)、此次入院是否進行外科手術、意識狀態、基礎疾病情況、激素使用、大量使用抗生素、免疫力低下、消化道出血、低蛋白血癥、入ICU時乳酸≥2.0 mmol/L、入ICU時間、住院天數、人工氣道、中心靜脈穿刺次數、置管部位、置管醫師、留置導管時間等單因素篩選后P<0.05的因素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見表1~4)。可以看出,經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后,大量使用抗生素、留置導管時間為CRBSI的獨立危險因素。
2.3 CRBSI病原菌種類、藥敏試驗及臨床用藥分析
菌株:28例感染病例中,共檢出病原菌36株。其中革蘭陽性菌18株(占50%),病原菌分別為:表皮葡萄球菌(5株),屎腸球菌(3株),糞腸球菌(D群)(3株),金黃色葡萄球菌(2株),溶血性葡萄球菌(2株),人葡萄球菌(2株),腐生葡萄球菌(1株)。革蘭陰性菌16株(占44.4%),病原菌分別為:鮑曼不動桿菌(5株),肺炎克雷伯桿菌(4株),銅綠假單胞菌(2株),粘質沙雷菌(2株),大腸埃希菌(1株),布氏檸檬酸桿菌(1株),陰溝腸桿菌(1株)。真菌2株(占5.6%),均為白色念珠菌。感染單一菌株者22人,占78.6%,復數菌感染者6人(占21.4%)。
病原菌藥敏結果分析:18株G+菌中12株(占66.7%)為產β內酰胺酶菌株,G+菌對苯唑西林、青霉素、環丙沙星、紅霉素、復方新諾明耐藥率較高,分別為92%、89%、83%、83%、75%,對利奈唑胺、萬古霉素、利福平普遍敏感;16株G-菌中多重耐藥菌(multiple drug resistant bacteria,MDR)10株(占62.5%),超廣譜β內酰胺酶(extended-spectrum beta-lactamase,ESBL)陽性菌2株(占12.5%),G-菌對氨芐西林耐藥率為100%,對美羅培南、亞胺培南耐藥率均為50%,對阿米卡星耐藥率為37%,對多黏菌素無耐藥;2株真菌藥敏結果均顯示敏感。

表1 中心靜脈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單因素分析

表2 置管部位、置管醫師與中心靜脈導管相關性血流感染的相關性分析 Tab.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atheter site, catheter surgeon an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 n(%)
ICU:Intensive Care Unit.
表3 感染組和非感染組在導管留置時間、年齡、乳酸濃度、APACHE II評分、中心靜脈置管次數、入ICU時間及住院天數的差異


Factors Infected group(n=28)Non-infected group(n=646)tPCatheter indwelling time/d13.43±8.417 9.01±9.429-2.4370.015Age/a 66.29±14.89962.11±18.736-1.1640.245Lactic acid/(mmol·L-1)2.032±1.3942.665±2.7212.2270.032APACHE II score20.82±6.41218.27±7.182-1.8480.065Frequency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ization 1.93±0.858 1.62±0.803-1.9710.049Time in ICU/h731.54±626.183454.28±550.605-2.5930.010Length of stay/d50.18±33.31840.36±31.364-1.6180.106
ICU:Intensive Care Unit;APACHEII: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表4 CRBSI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Risk factorsInfected group(n=28)Non-infected group(n=646)OR(95%CI)PHeavy use of antibioticsNo7(25.00)315(48.76)1.00Yes21(75.00)331(51.24)2.662(1.112-6.376)0.028Catheter indwelling time/d13.43±8.4179.01±9.4291.028(1.000-1.057)0.048
Unconditioned Logistic regression, regression screening, inclusion =0.05, exclusion =0.05. The initial variables of the model were: circulatory system disease, heavy use of antibiotics,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rtificial airway, lactic acid, number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ization, time of catheter indwelling, and time of ICU admission;ICU:Intensive Care Unit;CRBSI:catheter-related blood stream infection.
3 討論
目前CRBSI已經成為院內感染中病死率最高的感染來源之一,有報道[3]指出,ICU內血流感染的病死率為20%~60%,CRBSI是導致患者高病死率和增加住院成本的主要原因[4-6]。CRBSI的發生率逐漸增高的態勢及高病死率的現狀,使如何防治CRBSI已成為院內感染防控研究中的首要問題[7]。北京大學國際醫院成立于2014年12月,作為一所新建成的三級綜合性醫院,綜合ICU收住患者逐年增加,同時中心靜脈導管在ICU中的應用普遍化,CRBSI日益引起我們的關注。為了有針對性的控制感染發生,對感染患者血內病原菌調查,同時將血標本與導管尖端培養共同分析[8],有利于后期針對病原菌選擇藥物治療,對降低感染的發生率及病死率提供幫助。
本研究監測了674例留置中心靜脈導管的患者,置管總天數6 197 d,發生CRBSI 28例,感染例數率為4.15%,感染率為4.52‰導管日(千日導管感染率為4.52)。經多元Logistic回歸分析后,大量使用抗生素、留置導管時間為ICU內CRBSI的獨立危險因素。
本研究顯示,影響ICU內CRBSI感染的獨立危險因素有:大量應用抗生素及留置導管時間。在此筆者定義的大量應用抗生素指同時使用3種及3種以上抗生素,且上述抗生素使用時間超過7 d,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大量應用抗生素的患者,其CRBSI風險增加2.662倍。陶真等[9]研究發現CRBSI發生前抗菌藥物應用≥3種、中心靜脈置管次數>1次是CRBSI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本研究與其結果部分一致。隨著留置導管時間延長,操作次數會相應增多,范潤平等[10]、王敏[11]等分析研究結果均顯示,導管留置時間是ICU患者CRBSI的危險因素。根據本研究,導管多留置1 d,其CRBSI風險增加1.028倍,故臨床中應每日評估留置導管的必要性及拔除中心靜脈導管的可行性,盡量減少中心靜脈導管的留置時間。
有文獻[12]報道,外源性定植的細菌是導管感染的主要來源,而急診及ICU環境中存在大量的多重耐藥菌和條件致病菌,故一般認為,由麻醉醫師置管發生CRBSI的概率低于非麻醉醫師(包括ICU醫師、急診科醫師及其他病房或護理人員)置管,但本研究中顯示,置管醫師不是發生CRBSI的獨立危險因素,提示嚴格規范的操作流程及護理更加重要,與有報道[13]指出操作過程中最大無菌化屏障、嚴格無菌操作和導管護理可減少感染的發生相一致。關于置管部位的選擇,有研究[5,14-16]表明,鎖骨下靜脈導管發生血栓或感染的概率明顯低于頸內靜脈及股靜脈導管,其中股靜脈置管是最容易感染的部位。但也有多項匯總研究[8]顯示,無論股靜脈、頸內靜脈還是鎖骨下靜脈,只要技術熟練,操作規范,CRBSI的發生率并無差異,本研究與此結果吻合。
本研究中,檢出菌株36株,革蘭陽性菌占50%,產β內酰胺酶菌株共12株,革蘭陽性菌中以表皮葡萄球菌最多;革蘭陰性菌占44.4%,其中MDR 10株,革蘭陰性菌中以鮑曼不動桿菌、肺炎克雷白桿菌為主;真菌占5.6%。國內有研究[17]顯示,最常引起CRBSI的病原菌為革蘭陽性球菌,其中表皮葡萄球菌所占比例最多,革蘭陰性菌中以鮑曼不動桿菌比例略高,本研究均與之相符。因表皮葡萄球菌在皮膚廣泛存在,故表皮葡萄球菌感染較多可能與此有關,而ICU患者通常留置人工氣道及導尿管等有創操作,也增加了病菌的定植概率。對菌株的藥敏分析中發現,檢出的菌株耐藥率均較高,同時真菌感染率較高,有研究[18-19]顯示,真菌與MDR的出現均與廣泛使用廣譜抗菌藥物有關。本研究中感染復數菌患者占21.4%,國外已有報道[20]顯示,復數菌感染增加血流感染患者的死亡風險,故對于復數菌感染的患者,應引起重視。
對于預防及控制CRBSI,有研究者[21]提出,多學科協作、精良的置管技術和中心靜脈導管的維護對預防CRBSI相當重要,可總結歸納為:正確的手部消毒,評估留置中心靜脈的必要性,選擇正確的中心導管,正確的皮膚消毒,堅持無菌操作、最大無菌屏障化以及加強置管后護理[22-23],上述措施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好的思路和指導。
本次調查尚存在以下不足:作為回顧性、單中心調查研究,可能造成研究結論的局限性,另外,北京大學國際醫院作為新建醫院,本科為綜合ICU病房,受限于樣本量有限,無法按照入院診斷進行分組,有可能造成多因素相互作用導致分析的偏倚。
綜上所述,ICU內CRBSI的發生與大量使用抗生素及留置導管時間有關,CRBSI仍主要以革蘭陽性球菌感染為主,ICU留置中心靜脈導管操作時需經過嚴格培訓,規范操作,加強日常導管護理,對于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應提前予以重視,預防為主,改善預后,盡量做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從而最大程度上減少因操作及護理不當導致的CRBSI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