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控往事
季敏華 莫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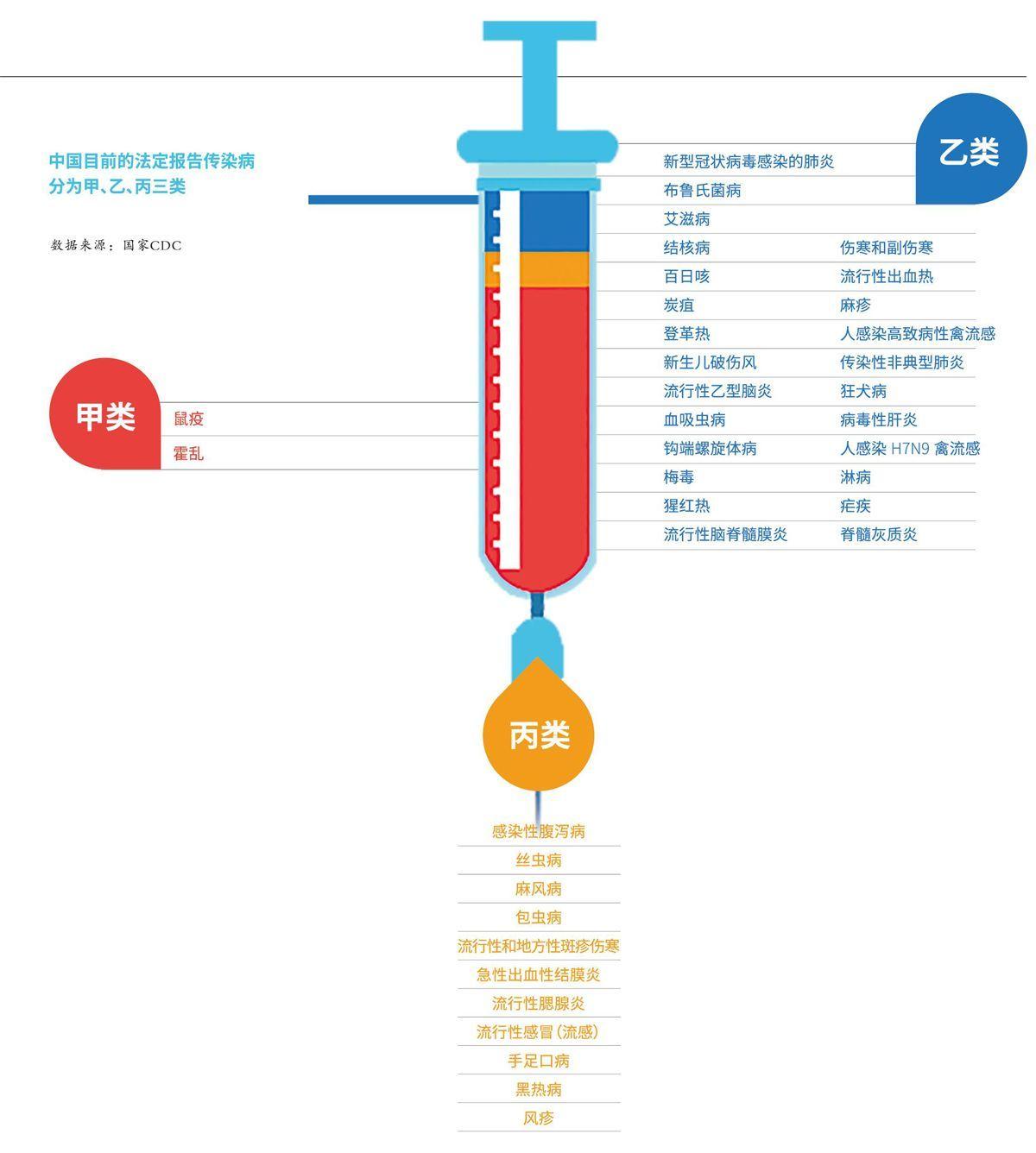
坐落在京郊昌平的國家疾控中心是一個平時不引人關(guān)注,而一旦關(guān)注就必有驚天動地大事發(fā)生的機構(gòu)。2003年,在它成立僅幾個月時,中國發(fā)生了非典疫情;2020年,在它成立的第18年,中國又發(fā)生了新冠肺炎疫情。
在過去一個月內(nèi),失責、只顧發(fā)論文、傳言掌門人高福被調(diào)查……國家疾控中心(CDC)經(jīng)歷了成立18年以來公眾最激烈的質(zhì)疑和信任危機。不過,在質(zhì)疑聲最激烈時,一些有公信力的經(jīng)濟學家和專家卻站出來為國家疾控中心及高福發(fā)聲。
2020年2月27日,鐘南山在一個新聞發(fā)布會上表示,此次疫情蔓延,是因為“我國CDC地位太低,只是衛(wèi)健委領(lǐng)導下的技術(shù)部門。在美國,CDC可以直通中央,不需要逐級申報,甚至在特殊情況下可以直接向社會公報。這是需要改變的,CDC的地位要提高,要有一定的行政權(quán)。”
鐘南山說出了一個對于國家疾控中心角色日漸清晰的認知——盡管受“國家疾控中心”這一名稱的影響,公眾一度認定它是重大疫情的吹哨人和第一責任人,但實際上,國家疾控中心名實不副,無論從機制還是從實權(quán)上都難堪重責。國家疾控中心更像是一個研究中心,成立18年中也曾有機會拓展邊界,卻因長于研究而不善政策執(zhí)行錯過了轉(zhuǎn)型機遇。
疫情仍在膠著。然而追尋中國疾控往事,籌劃未來,已經(jīng)開始。
“后來者”國家疾控中心
2002年1月,當國家疾控中心設(shè)立時,外界更習慣叫它的英文簡稱——CCDC(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或稱為“中國CDC”。在很多熟識中國疾控往事的人士看來,當年之所以取英文名CCDC,正是為了效法美國CDC,希望構(gòu)建一個強大的中央公共衛(wèi)生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