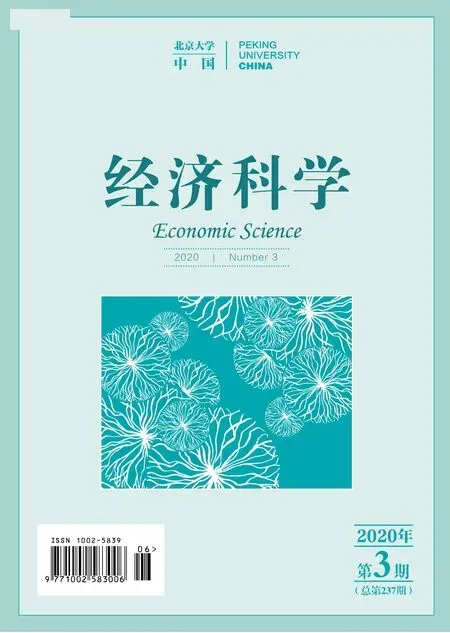城鎮化與中國農村減貧*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山東濟南 250199)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城鎮化日益被視為21世紀最重要的問題之一。目前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鎮,預計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到75%,大部分城市增長主要集中于亞洲和非洲地區(United Nations,2015)。1978年,中國城鎮人口只有1.7億,占總人口的17.9%,到2016年該比例上升到57.3%。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中國城鎮化發展歷程回顧,感興趣的讀者可在《經濟科學》官網論文頁面“附錄與擴展”欄目下載。與此同時,按當年價現行農村貧困標準衡量,1978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約97.5%,2017年末農村貧困發生率為3.1%,農村貧困發生率下降94.4個百分點,年均下降2.4個百分點。②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參見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3_1620407.html。那么,城鎮化與農村貧困減少二者之間是否有關?
城鎮化通過如下幾個渠道影響農村家庭的收入、消費和貧困(Mallick,2014):其一,匯款渠道。城鎮化往往伴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這意味著勞動者從農業部門和農村地區轉向工業部門和城鎮地區,遷移會使農村移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通過移民的匯款,農村家庭收入和消費水平預期也會上升。匯款還可以用來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或社會資本投資,進而帶動農村勞動生產率提高或促進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活動。匯款在減少農村家庭的資源約束及在為負向沖擊提供保險方面有積極作用。當然,如考慮到以下情況,由城市轉移到農村的匯款凈流入可能會減少,即移民家庭往往給初次留在城市的移民提供貨幣或實物等經濟支持,這種旨在支付移民固定成本的支持可以解釋為一項投資,其回報是隨后收到的反向城鄉匯款流量(Stark,1980)。移民對留守家庭的影響在實證中并沒有一致的結論,一些文獻認為匯款對家庭收入增長和緩解貧困有積極作用(Bouiyour等,2016),另一些文獻則認為移民對貧困沒有作用(Yang,2008)。其二,非農就業渠道。城市地域擴張有利于非農經濟活動的多樣化,進而對收入有正面影響(Jacoby和Minten,2009),這種效應對地理上靠近城市的鄉村尤為重要,由于城市提供了密集的市場來更有效地交換商品和服務,靠近城市的農戶可以依據其比較優勢從事特定的經濟活動,依靠市場來滿足消費和投資需求,更廣泛的專業化生產可能會提高生產率和收入。此外,靠近城市能夠刺激農業貿易的非農活動,比如運輸和營銷。城市刺激附近農村高回報非農就業的例子在亞洲地區比較常見。城市擴張還使得城市周邊勞動者通勤的概率上升,進而會帶動城郊諸如消費和零售的非農活動的增長來滿足通勤人口不斷增長的服務業需求。企業在城市中集聚并吸引城市和城市附近的農村勞動者就業,農民工工資得以增加。另外,基于城鄉間工資差異的遷移可能會使農村勞動力供給下降并引致農村勞動力工資上升。其三,農產品消費需求渠道。農產品需求渠道主要通過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起作用。收入效應指城市收入高于農村而引致的對農產品需求增加,即城市對農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需求隨著城市經濟和人口密度的增長而增長,運輸條件和基礎設施的改善使農產品從農村運往城市的運輸成本降低。由于運輸成本降低,亞洲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從城市向農村轉包的情形增加。替代效應與較高附加值產品在農業總需求中所占比例的增加有關,這是典型的更復雜的城市消費者的特征(Cali和Menon,2013)。其四,農村土地渠道。城市擴張增加了附近農地改居住用地的需求,農地價格將上升,土地所有者可以通過租賃、售賣土地等形式獲得更高收入(Plantinga等,2002)。事實上,前述農產品消費需求渠道中,預期未來農業收入的上升也會帶動土地租賃價格上升。土地渠道對農村貧困的最終影響還取決于增加的這部分農業收入在農村人群中的分布,如果土地非常集中,這個渠道可能只會使少數地主受益,且沒有土地的人群獲得有償就業的機會也會受到限制,這時該渠道減少貧困的效果就會打折扣。此外,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城市無疑會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農村人均可用土地相應地增加,由于土地數量固定不變、土地邊際收益遞減,可用性土地的增加應該會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并給農村工資帶來上漲壓力(Cali和Menon,2013)。其五,技術和市場的溢出效應渠道。農村居民生活水平因城市化溢出效應而上升。除了遷移外(Arouri等,2017),城鄉之間諸如信息傳遞、先進技能和知識傳播等其他互動形式也對農村人力資本的形成產生積極影響。而且,城市化在城市和附近農村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為教育、健康服務和環境設施改進提供了機會。教育資本決定了農村居民學習與使用技術的能力,健康資本則影響經濟活動和減貧。
然而,城鎮化并不必然引起農村家庭收入的增長,比如勞動力向城市遷移降低了農村勞動力供給,短期內遷移者無法匯款給留守農村的家人,他們必然會經歷收入下降之痛。從長期來看,農村到城市的遷移會阻止這些家庭參與高回報的勞動密集型活動。再如,在農村土地渠道中,如果最具有生產效率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可能會抵消移民帶來的生產率提高效應。此外,匯款可能產生道德風險問題。一些文獻研究表明移民會影響遷移家庭中其他成員的勞動決策,并會提高他們的保留工資(Grigorian和Melkonyan,2011)。匯款會對接受者的勞動供給產生負向激勵。綜上所述,城鎮化可能通過匯款、非農就業、農產品消費需求、農村土地、技術和市場的溢出效應等渠道影響農村家庭的農業或非農活動,其對貧困的影響在理論上沒有明確答案,結論的得出依賴于上述不同渠道相對力量的比較。
從本世紀初起,學者們開始研究城鎮化對發展中國家貧困的影響,尤其是對農村貧困的影響。比如,Ravallion等(2007)研究發現,城鎮化對減少貧困有積極影響,但城鎮化減貧效力因地區不同而不同。Martinez-Vazquez等(2009)利用非平衡跨國的面板數據分析得出了城鎮化與貧困之間存在U形關系的結論。Cali和Menon(2013)利用印度1983—1999年的地區面板數據估計了城鎮化對貧困減少的影響,該研究使用地區間遷移數據預測了城市人口、城市就業中制造業人口就業比重,并借助了工具變量方法,他們得到的結論是,大約75%的城鎮化減貧效果可以用農村商品需求的增加來解釋,農村到城市遷移的貢獻不足20%。Mallick(2014)研究表明在印度農業部門萎縮的過程中,貧困勞動者從農村流向城市有助于減少農村貧困。Arouri等(2017)使用越南4個年份的微觀調查數據分析發現,城鎮化在增加農村非農收入的同時使得農業收入下降,城鎮化減少了農村貧困。Higashikata和Hashiguchi(2017)基于印度尼西亞家庭微觀數據,使用有效市場規模增長作為城鎮化的代理指標的分析表明,城鎮化導致農村家庭尤其是貧困農村家庭人均支出增加,貧困家庭福利增長主要由非農收入增加所致。楊沫等(2019)認為城鎮化過程使農業轉移人口具有較高的代際職業流動性。崔萬田和何春(2018)運用2000—2014年中國25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實證發現:城鎮化與農村貧困呈現出U形關系,在城鎮化發展前期,城鎮化有利于農村貧困的減少,在城鎮化發展后期,城鎮化不利于農村貧困的減少;城鎮化農村減貧的收入效應要大于轉移效應。何春和崔萬田(2017)選取32個發展中經濟體1992—2015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檢驗,表明城鎮化建設能夠提高教育、健康、農業生產率,從而有助于貧困的減少。夏慶杰等(2017)主要從城市化和城市貧困、城市化與農村貧困、中國城市化和貧困方面進行了綜述。萬廣華等(2017)研究發現,中國的城市化能有效減少農村和農民工的貧困。
本文基于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的面板數據,使用工具變量面板數據固定效應的兩部模型分析了城鎮化對農村家庭人均收入、消費及貧困的影響。本文在分析城鎮化對農村家庭收入的影響時,研究了城鎮化對經營收入、工資收入、財產收入、轉移收入等不同收入來源的影響,此外還把農村按郊區與純農村、東中西地域、平原與非平原地貌特征進行了分組并對其進行實證檢驗。
二、數據來源及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微觀數據來自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行的“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CFPS的抽樣設計關注初訪調查樣本的代表性,采用了內隱分層的、多階段的、多層次與人口規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樣方式(PPS)。樣本覆蓋了除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青海省、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海南省之外的25個省份。CFPS的問卷分為三個層級:個體,個體生活的緊密環境即家庭,家庭的緊密環境即村居,因此形成了三種問卷:個人問卷、家庭問卷、村居問卷,其中根據年齡特征把個人問卷分為成人問卷和少兒問卷。本文選取了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三次調查的面板數據,家庭數量為6 107個,三年樣本數量共計18 321個。以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衡量的各省份城鎮化水平,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城鎮化與農村家庭的收入、消費和貧困率的表格,感興趣的讀者可在《經濟科學》官網論文頁面“附錄與擴展”欄目下載。
(二)方法
基于面板數據把農村家庭的人均收入、收入來源中的人均經營性收入、人均工資性收入、人均財產性收入、人均轉移性收入、家庭生活條件、人均消費等結果變量寫成城鎮化及家庭特征變量的函數形式:

其中,Yijt代表j省的i家庭在t時期(2010年、2012年、2014年)的結果變量。urbanjt代表城鎮化水平,本文的城鎮化水平采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測度,urbanjt表示在t時期j省的城鎮人口占其總人口的比重,式(1)中的城鎮化用滯后一期(2009年、2011年、2013年)的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這說明城鎮化變量在結果變量之前就確定了。Tt代表t年份的啞變量。Xijt代表家庭特征變量。ηij和εijt分別代表時間不變和時間可變的不可觀測變量。β代表城鎮化對結果變量的彈性。因為城鎮化并非是隨機過程,城鎮化進程不能被完全觀測,為此,本文使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來消除可能引致內生性的不可觀測的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此外,本文還使用了工具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城鎮化(滯后一期的城鎮人口比重)的工具變量利用滯后兩期的城鎮人口比重來代替,即滯后的內生變量被當作當前內生變量的工具變量。
使用式(1)能較為恰當地分析城鎮化對消費和全部收入的影響,但全部收入的組成部分中的一部分變量比如工資收入、財產性收入等變量有較多的零值,因變量有較多零值時一般使用Tobit模型,可是由于最大似然估計方法中的偶然參數問題導致沒有固定效應的Tobit模型可用。另外,如果誤差項的正態性和同方差假定不滿足的話,Tobit模型估計并不是一致性的估計,而上述假定又太強無法在現實中得到滿足。因此,本文借鑒Arouri等(2017)的方法,使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的兩部模型:

式(2)中Dijt為二元啞變量,當Yijt>0時Dijt為1,當Yijt=0時Dijt為0。式(2)和式(3)使用固定效應回歸估計。雖然二元啞變量常用Probit或Logit模型來估計,但因為我們使用固定效應來估計式(2),而沒有可用的固定效應Probit模型,而固定效應的Logit模型會刪去觀測值為固定值的較多樣本導致樣本量不足,因此,本文使用線性概率模型來估計式(2)。
使用消費來衡量貧困比使用收入更合理,因為消費能直接與生活福利相關聯。基于式(1)的消費數據計算家庭i陷入貧困的概率如下:

式(4)可簡化為下式:

其中,P代表貧困概率,當家庭為貧困時P為1,否則為0。z代表貧困線。Φ代表標準正態分布函數。Y代表家庭人均消費(為簡單計,下標i、j、t略去)。σ是式(1)中ε的標準差。在固定效應模型中,η被假定為固定,ε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σ的正態分布,本文假定σ在各個觀測值之間可變。家庭人均消費基本上全為正數,估計式(1)時采用了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而非兩部法模型。城鎮化對貧困概率的效應為:

其中,φ代表標準正態分布的密度函數。城鎮化對貧困平均部分效應(Average Partial Effect,APE)估計為:

式(7)中,Hi是家庭i的人口數,N是全部樣本的人口數量,是基于對數人均消費固定效應估計得出。
三、實證分析
本部分首先對家庭收入與城鎮化進行回歸,并控制了如家庭結構、人力資本等其他可能影響收入的變量,本文的具體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口數量、家中小于15歲的人口比重、家中大于60歲的人口比重、戶主年齡、戶主教育程度①本文的分析單元是家庭,為控制家庭人口社會學變量,我們定義了虛擬的“戶主”,即把2010 CHFS調查中家庭中的主事者、2012年最熟悉家庭財務的人員、2014年財務回答人視為戶主。。地區這類時間不變的變量在固定效應中沒有納入。解釋變量不能受到城鎮化的影響,為此文章沒有納入更多的解釋變量。各變量的含義與描述性統計參見表1。
肖家山礦區含金礦脈主要賦存于冷家溪群黃滸洞組第二段粉砂質板巖、變質雜砂巖中,并受近乎順層產出層間滑動剪切帶和區域性斷裂旁側次級脆-韌性剪切帶控制,控礦構造以前者為主。

表1 變量含義及描述性統計
表1顯示,2010—2014年,收入、消費、資產及戶均打工寄回收入基本上均呈現增長態勢;農村家庭人口規模維持在4人左右;由于是虛擬戶主其年齡在面板數據中并非穩步上升;家庭撫養人口(包括兒童和老人)占比表現出上升態勢,其中老年撫養比上升態勢顯著,這說明農村的老齡化問題正在凸顯;農村戶主教育程度為小學畢業的占比基本在50%以上。
(一)城鎮化對全部農村樣本的影響
基于工具變量固定效應的經營收入、工資收入、財產收入、轉移收入回歸結果表明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基于工具變量固定效應的經營收入、工資收入、財產收入、轉移收入回歸結果的表格,感興趣的讀者可在《經濟科學》官網論文頁面“附錄與擴展”欄目下載。,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農村家庭有經營收入的概率下降0.56%。由于數據限制,本文無法區分農業經營收入和非農經營收入,為此經營收入的下降可能由多方面原因導致。一方面,它可能是由于農產品價格波動較大而農林生產和養殖業的種子化肥農藥費、雇工費、機器租賃費、灌溉費、種畜魚苗費、飼料費等中間投入高企,農林生產和養殖業的比較效益低下,城鎮化的拉力使得從事農林生產的勞動力離開農業經營市場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城鎮化使得土地流通速度加快導致一些農民主動或被動地無地可耕所致。此外,亦有可能是從事非農經營需要較高的資金投入且風險較高所致,而如果從事打工掙取工資收入的話,盡管工種的工作量可能比較繁重,但能準時、及時得到薪酬,下文城鎮化顯著地促進了工資收入的增長也從另一個側面佐證了這個答案。雖然城鎮化使得農村家庭有經營收入的概率顯著下降,但城鎮化并沒有顯著地促進農村家庭的經營收入下降。雖然城鎮化使農村家庭有工資收入的概率下降(僅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但城鎮化對農村家庭工資收入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農村家庭工資收入上升0.75%。城鎮化使得農村家庭的財產收入顯著增加,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農村家庭財產收入上升0.71%。城鎮化還顯著地增加了農村家庭獲得轉移收入的概率和轉移收入的數量,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農村家庭獲得轉移收入的數額增加0.66%。此外,城鎮化顯著促進了打工者寄回農村的收入。
城鎮化對各項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影響又會是什么情況呢?表2是基于兩部模型的工具變量固定效應考察的城鎮化對人均收入及各項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的影響的回歸結果。

表2 城鎮化對人均收入及各項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的影響
從表2可以看出,城鎮化對各項收入占總收入構成比重的影響不盡相同。城鎮化增加了工資收入比重、財產收入比重,城鎮化對經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經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下降0.13%。那么,在這些合力的作用下,城鎮化對農村家庭的全部收入有何影響呢?表2第一列的結果表明,城鎮化顯著地增加了農村家庭的人均收入,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農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0.67%。
接下來本文嘗試分析城鎮化對農村家庭生活條件的影響,并研究城鎮化對貧困下降的貢獻,本文的貧困以消費來衡量。已有研究表明使用貨幣貧困來表征人群福利并不全面,貧困應從多維角度進行測度,本文用飲用水、做飯燃料來反映非貨幣的農村家庭福利,城鎮化對飲用水、做飯燃料、家庭資產、消費的固定效應線性概率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生活條件、資產及人均消費的固定效應回歸
回歸結果表明,城鎮化顯著地改善了農村家庭的飲用水福利,但城鎮化對做飯燃料的使用沒有顯著影響。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變量后(篇幅所限,略去回歸結果),城鎮化對農村家庭的飲用水、燃料使用的結果沒有任何改變,這說明家庭收入不是城鎮化改善生活設施的主要渠道,這意味著城鎮化可能提升了農村家庭的飲用水質量安全意識,抑或是城鎮化帶來了基礎設施的升級。城鎮化顯著地增加了農村家庭的人均資產,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農村家庭人均資產增加1.4%。城鎮化也顯著地增加了農村家庭的人均消費,城鎮化水平每提高 1%,農村家庭人均消費增加0.87%。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變量后,城鎮化引致的消費增長效應仍在 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但農村家庭人均消費的回歸系數減小,這說明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使得收入的一部分轉化為了消費增加。
城鎮化對農村貧困的影響結果參見表4,表4列示了2$PPP、2.5$PPP兩條貧困線的影響結果。

表4 城鎮化對農村貧困的影響
城鎮化顯著地增加了農村家庭人均消費意味著城鎮化相應地使得消費貧困下降,與Cali和Menon(2013)、Arouri等(2017)分別對印度和越南的研究結論相同,本文研究表明城鎮化顯著地減少了農村貧困,但城鎮化減貧的程度較低。從表4的系數可以看出,無論貧困線劃在何處,2010—2014年,城鎮化減少農村貧困的程度在逐期下降。比如貧困線為2.5$PPP時,2010年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農村的消費貧困下降0.32%,而在2014年,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農村消費貧困僅下降0.01%。
(二)城鎮化對農村分組樣本的影響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城鎮化對農村分組樣本影響的表格,感興趣的讀者可在《經濟科學》官網論文頁面“附錄與擴展”欄目下載。
本小節進行異質性分析,將農村地區區分為純農村和郊區農村兩類②根據CFPS的調查標準“農村”通常指以村莊形態出現、主要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聚居區。“郊區”通常指建制市的人口稠密區邊緣、行政上屬于建制市的人口聚居區。,城鎮化對不同類型農村的經營收入、工資收入、財產收入和轉移收入的工具變量固定效應回歸結果顯示:城鎮化對純農村和郊區農村的經營收入影響結果相同,經營收入系數均為不顯著的負號。城鎮化對純農村和郊區農村的工資收入都起到了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郊區農村工資收入的回歸系數更大一些,這可能是由郊區農民從事打工的時間和地理位置相較純農村地區有比較優勢所致。城鎮化對財產收入的影響在純農村和郊區農村呈現出了不同,城鎮化顯著地促進了純農村地區的財產收入,但對郊區農村的財產收入沒有顯著影響。城鎮化對純農村和郊區農村的轉移收入影響結果相同,轉移收入系數均為非常顯著的正號,郊區農村轉移收入的系數遠大于純農村轉移收入的系數,這也說明郊區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享受的轉移收入增長的福利遠遠高于純農村地區的福利。城鎮化只對純農村地區的打工寄回收入有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而對郊區農村地區的打工寄回收入沒有影響。
城鎮化對不同類型農村的各項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的影響如何?回歸結果表明,城鎮化使純農村地區的經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下降非常顯著,城鎮化促進了純農村地區的工資收入占總收入比重、財產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的顯著增長,城鎮化對純農村地區不同收入占總收入比重有增有減的合力使得家庭人均收入呈現較強的上升態勢,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純農村地區的家庭人均收入增長0.65%,其與總樣本回歸中系數大小大致相同。城鎮化對郊區農村各收入比重的影響與對純農村的影響不盡相同,比如,城鎮化對郊區農村經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工資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家庭人均收入均無顯著影響。城鎮化對財產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產生了一些負向影響,但只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城鎮化對轉移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的影響呈現出了非常強的正向顯著作用,這可能是由于近年來城鎮普遍的擴容建新城的行動帶來了其郊區農村的大規模的拆遷重建,進而衍生出一批拿到大量拆遷款非常富足的“拆二代”所導致。此外,由于房屋拆遷,原有的住房不再能夠獲得出租形式的財產收入所以出現了財產收入比重的下降。這種現象與現在仍呈現擴張態勢的撤縣設區政策有關,撤縣設區擴大了中心城市城區的范圍,協調了中心城市與周邊市縣關系,被撤縣(市)實現了從農村經濟形態到城市經濟形態的跳躍,撤縣設區遵循了城鎮化方向由“中心向外圍”拓展的原則,有效地推動了城鎮化進程(林拓和申立,2016),進而對農村貧困減少起到積極的疊加作用。
城鎮化對不同類型農村生活條件、資產及人均消費的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表明,城鎮化顯著地改善了純農村地區的飲用水條件,使得純農村地區的人均資產和人均消費均顯著上升。城鎮化對純農村家庭燃料的使用沒有影響。控制了家庭人均收入變量后,城鎮化對純農村的飲用水條件、燃料使用影響的結果沒有改變,這進一步說明家庭收入不是城鎮化改善生活設施的主要渠道。比較有趣的是城鎮化對郊區農村飲用水條件、燃料使用、資產和消費均無顯著影響。
因為城鎮化對郊區農村的人均消費沒有顯著影響,本文只計算了城鎮化對純農村地區貧困的影響效應。結果表明,雖然在同樣的貧困線下城鎮化減貧效應比總樣本中的減貧效應大,但絕對數值仍然較低。與總樣本結果表現相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鎮化減貧效應減弱。
城鎮化對東中西部地區的農村減貧有何作用呢?結果表明,城鎮化對東中西部農村的各項收入的對數值及各項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的影響表現出較強的異質性。比如城鎮化對西部地區的對數經營收入、經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影響均存在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城鎮化對中部地區的對數經營收入、經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影響均存在非常顯著的負向影響。城鎮化對東部地區的對數經營收入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對經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存在非常顯著的負向影響。雖然城鎮化對東中西部農村的對數工資收入均存在非常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城鎮化只對東部地區的工資收入比重有正向影響,其對中部地區的工資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影響不顯著,對西部地區的工資收入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城鎮化對東部地區的打工寄回收入有較強的負向作用,對西部地區呈現非常強的正向作用,對中部地區則沒有影響。城鎮化對東中西部農村的財產收入、轉移收入及人均總收入也表現出了較大的地區差異性。城鎮化只對西部地區農村的人均消費起到了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在貧困線低于2.5$PPP時,其對西部地區農村減貧效應也不是太大(小于1%),并呈現出逐期下降的態勢。
城鎮化對地貌不同的農村家庭收入、消費、生活條件和貧困是否有差異呢?根據CFPS對農村地貌的不同分類,我們把農村地區分為平原地區農村和非平原地區農村兩類。①CFPS調查關于農村地貌的特征共有七個選項:丘陵山區、高山、高原、平原、草原、漁村、其他。城鎮化對平原和非平原地區農村的人均收入、各項收入占總收入比重、人均消費、生活條件及減貧效應的結果顯示,城鎮化對這些指標的影響表現出平原和非平原的異質性。比如,城鎮化雖然均顯著地促進了平原和非平原的人均收入,但在平原地區這主要得益于城鎮化使財產收入和轉移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增加,而在非平原地區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化使工資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增加。城鎮化對平原地區農村的打工寄回收入沒有影響,而對非平原地區則有非常強的正向作用。再比如,城鎮化只對非平原地區的家庭人均消費起到了顯著的提升作用,而對平原地區的家庭人均消費沒有作用。城鎮化對非平原地區的減貧作用比較微弱,2010年在貧困線分別為2.5$PPP和4$PPP時,城鎮化最大的減貧貢獻分別僅為0.41%、1.64%。與其他農村分組樣本的結論相同,城鎮化的減貧貢獻也呈現逐期下降的態勢。
總而言之,城鎮化使東中部農村、平原農村、郊區農村的轉移收入顯著增加,但對這些地區的消費卻沒有顯著影響。城鎮化主要減少了西部農村、非平原農村和純農村地區的貧困。這些結論可能從另一個側面佐證了城鎮化減貧邊際貢獻下降的原因,因為東部、平原地區、城郊的城鎮化水平已經較高,城鎮本身的諸如貧民區、環境、犯罪等社會問題開始顯現,城鎮貧困問題的出現可能影響了城鎮化對農村減貧作用的發揮。
(三)機制檢驗②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機制檢驗的回歸結果,感興趣的讀者可在《經濟科學》官網論文頁面“附錄與擴展”欄目下載。
前文的結論表明城鎮化顯著地減少了農村貧困,那么,城鎮化減少農村貧困的可能機制是什么呢?根據數據的可得性,本文將從農村土地渠道、匯款渠道、非農就業渠道及技術和市場的溢出效應渠道等方面對城鎮化減少農村貧困的可能機制進行探討。農村土地渠道我們擬從農村社區征地這個指標來入手,鑒于CFPS公開數據中只有2014年涉及了農村社區征地問題,下文將利用2014年的數據進行檢驗。匯款使用家庭是否有打工寄回收入來代表。非農就業使用家庭是否有工資收入代表。技術和市場的溢出效應則使用到縣城的距離來代替。前文曾歸納的農產品消費需求渠道因無法找到相應代理指標,這里略去該機制檢驗。使用線性模型的機制檢驗表明:無論是否控制家庭人口學變量,經歷過征地的社區的家庭人均消費顯著上升,即以家庭人均消費表示的福利顯著提升,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征地補償直接增加了農民的福利,另一方面征地可能使得非農就業增加,進而使被征地農民的福利得到改善。無論是否控制家庭人口學變量,非農就業的福利效應都在顯著增加。距離縣城越遠,家庭人均消費數量越低,這說明城鄉之間的物理分割會導致技術和市場的溢出效應降低,進而會影響到農民的福利改善。該結論與異質性分析中的城鎮化對郊區農村工資收入的影響更大一些的結論相呼應,即郊區農村相較純農村地區存在地理上的優勢。比較有趣的是,有無匯款對家庭的福利改善沒有顯著作用,這可能是由于接受匯款者并沒有把寄回收入直接用于消費,抑或是寄回收入的數量有限所致。總之,城鎮化減少農村貧困的機制是農村土地渠道、非農就業渠道及技術和市場的溢出效應渠道,匯款機制調節作用有限。
四、結 論
貧困作為一個廣發性、普遍性的問題,長期以來受到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實現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扶貧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譽。隨著扶貧開發事業向縱深推進,貧困程度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較大緩解,但剩下的扶貧開發難點區的貧困形勢更加復雜、扶貧難度更大,在減貧速度放緩的背景下,文章基于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面板數據,使用工具變量面板數據固定效應的兩部模型分析了城鎮化對農村家庭人均收入、消費及貧困的影響。結果顯示,城鎮化促進了農村家庭工資收入和財產收入的增長,城鎮化雖然對轉移收入的增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但對轉移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影響不顯著,城鎮化對經營收入影響微弱,對經營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的影響甚至存在顯著的負向作用。在上述合力作用下,城鎮化使農村家庭人均收入、人均消費顯著上升,城鎮化水平每提高1%,家庭人均收入增長約0.7%,家庭人均消費增長約1.1%;城鎮化還對以生活飲用水水平代表的生活條件提高起到了積極作用,該積極作用并不受收入的影響,表明城鎮化增加了農村家庭對飲用水質量或稱生活條件的意識與需求,抑或是城鎮化帶來了基礎設施質量的提升;城鎮化顯著地減少了農村貧困,但其減貧的作用較小,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鎮化減貧貢獻逐漸減弱;當把農村樣本分成純農村和郊區農村、東中西部地區、平原和非平原地區時,城鎮化對每一分組樣本下的人均收入、消費及貧困的效應均呈現出了異質性特點,城鎮化使東中部農村、平原農村、郊區農村的轉移收入顯著增加,但對這些地區的消費卻沒有顯著影響。城鎮化主要減少了西部農村、非平原農村和純農村地區的貧困;城鎮化減少農村貧困的機制是農村土地渠道、非農就業渠道及技術和市場的溢出效應渠道,匯款機制調節作用有限。
文章結論對扶貧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義:減貧與刺激城鎮發展相結合并注重城鄉統籌的政策可能有助于減少農村貧困和總體貧困;減貧政策制定中還應注意城鎮化在不同類型、地域、地貌農村存在減貧的異質性問題;貧困是復雜的多維問題,它涉及消費、儲蓄、資產配置、工資和收入政策等跨期問題,反貧困政策需把這些因素納入其中;應加快推進土地確權,在確保土地承包權長期穩定前提下,推動土地流轉,同時,圍繞農業的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如農產品加工、物流交通、信息服務等,增加非農就業崗位并借助信息和技術的溢出效應促進農民收入的提升;讓遷移到城鎮的農民工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樣的公共服務以實現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的目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本文的分析工作還有許多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城鎮化進程涉及全國人口,如果受城鎮化影響的群體被視為處理組,我們應找到不受影響的控制組進行比較,但受資料限制我們無法找到這樣的控制組。此外,本研究簡單地假定省級城鎮化只影響到省內居民。在工具變量回歸中,城鎮化變量(滯后一期城鎮化人口比重)的工具變量用滯后兩期的城鎮化人口比重來代替,盡管滯后內生變量常被用來作為當前內生變量的工具變量,但這樣做可能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未來研究的擴展可能包含以下內容:盡管我們也簡單地計算了城鎮化對城鎮家庭人均收入、消費和貧困的影響,但城鎮化減少城鎮貧困的機制明顯無法用前文綜述中的那些渠道來解釋,因此這其中應該存在另一個不同的問題。其實,隨著城鎮人口的增長,城鎮本身的貧困將可能成為主要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來評估城鎮人口增長是否意味著在城鎮和農村減貧之間進行權衡。不平等是貧困的另一個側面,在資料可得的情況下分析城鎮化與不平等的關系超越了本文主題,但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課題。